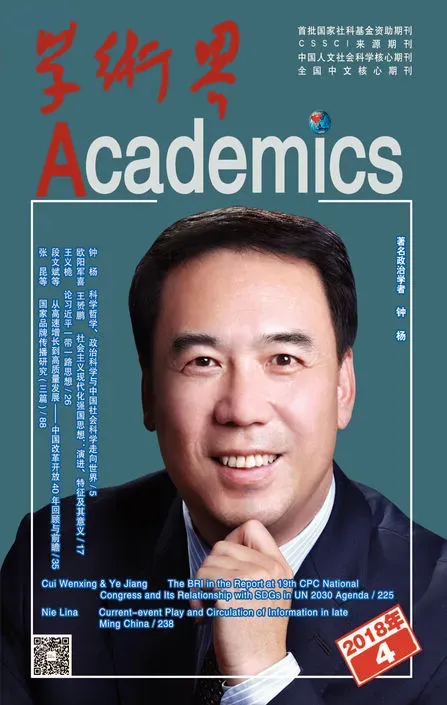汉语哲学普世心思的诗化叙事
——并借这一诗化哲学叙事,向中国哲学家致敬
○ 许章润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一
哲学是对于存在本身的永恒焦虑,出入神人之际,辗转生死两头,萦念普世心思。另一方面,所有的哲学与哲思,总是源于一己心事,舍不得当下肉身,满怀乡愁,讲一口方言。毕竟,哲学也好,哲思也罢,都是哲学家的思维花朵,那个当下存在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存在本身的反思,一种关于存在的永恒焦虑。比诸当下即是,其形上反思是如此高渺,却又无不源自此在的恨海情天。其逻辑建构是那般玄妙,虽不像柴米油盐,可抖露出的仍旧不过是永生永世、绵绵不休的汲汲惶惶。置此恨海情天,灵肉毕现,存在获得了存在性,这世界不再缥缈。源此汲汲惶惶,人性进行了自我佐证,生命原为性命,人口这才一转而为真实之人生。如果说亿万生民必得经由政治才能获秉存在的公共意义,而为真实之性命,则存在本身之存在性与人口之获享人生,而展露人性,终为性命,正需要恨海情天与汲汲惶惶以为触媒,天助自助,守经达权,而发酵,而滋长,而昂扬。在此,生死既做不了主,自家的灵肉也常常仿佛不是自己的,还真的就不是自己的,而美妙仙境不过是俗世的乌托邦,于是,人生在世,凄惶不免,一时暂居,永恒飘泊,而终究归还大地,化作虚无。
一时语塞,有所沉吟,多所回应,终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
从而,哲思超然,挣脱肉身,恰是基于肉身,旨在回应当下。其于一切形下器具提供心智支撑之际,将心性揽怀,给人生以抚慰,赋予蜉蝣生命以永恒性命,将蝼蚁人生提升为堂皇生命。如此这般,终究叫人活得下去,抑或,活不下去。有此支撑,附着于人世的种种,所谓文明的主体性、思想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的文化自觉,更不用说什么家国天下,一切的一切,才免于浮云;无此抚慰,肉身沉重,肉身即兽,人世等于匪帮,人没法活。职是之故,这个叫做哲学的家什,或质朴粗犷,智愚两隐,或空灵冲淡,骨相清奇,或冷峻刚健,凛然复萧然。但是,象殊理同,百川归一,它们都是人身痛痒,满腔子尘世烟火。
这不,哲学工作者众,是搞哲学的;哲学家少,是玩哲学的;哲人稀罕,径自沉湎于思,管他什么哲学不哲学。而思也浩茫,神驰八极,无论踟蹰街巷蓬头垢面引车卖浆,还是辗转山林放达不羁长啸短歌,抑或四仰八叉晒太阳。赤条条,地远天孤,疑是疑非。最无端,畏因畏果,是是非非。果报循环,不拘形迹。它们和他们,如同大雁掠过天宇,了无痕迹。
纵便装神弄鬼,念经赌咒,也还是个人形。鬼神哟,人类的至亲,我们的难兄难弟。
是啊,年年岁岁,春去秋来,自远古而至今朝,我们恒受照拂,不管是否意识到,其实一直沐浴在哲学的光中。启明,哲思的一丝丝一缕缕的神性抚慰与理性晓谕,让我们多少暂时摆脱沉重肉身,幸免此在欲望的奴役。虽说肉身及其欲望,恰恰定义了我们,可却是一切悲辛的渊薮。我们沉湎其中,乐不思蜀,却又痛不欲生,最终恨不能将它们砸个粉碎,还不是因为有口难言,词不达意,而终至此在不在。倘若如此,我不存在,灵魂出窍,便是对于物自身的反动,其余种种,云乎哉?但若非如此,可曾逃脱、可能逃脱?更深的困恼在于,这就是生命,一众性命之盎然妙趣生生不息,也就是它的冥晦黯然,而终究死无葬身之地。
幸亏有哲学,带我们返乡,大家仿佛得救。故尔,不仅全体生灵应当感恩哲思,一切知识与思想形式都要向哲学致敬,向配得上哲学家称谓的一流心智鞠躬。如果说高僧大德必为一流心性,至少,哲学家得谓一流心智。否则,别玩这行当。
最要命的是,无论今古东西,人渴望善,而哲学家们创造了人渴望善这一观念,也就是秉持一腔坚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善好的进程这一光明心态。对此保持信心与善念,同为渴望善这一善念之善果。善念,说到底,就是对此艰难进程保持信念。“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幸亏赖此一念不绝如缕,独力支撑,人才活到今天。
哲人,你这天人沟通的祭司,也是代我们受苦的艺匠,众生匍匐,献、献、献、献上我们的膝盖。
二
既然哲学讲一口方言,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则上述永恒焦虑及其支撑与抚慰,必然生发、跋涉于特定语言的密林之中。就我们这群此在而言,其必生聚作息于汉语,依恃汉语的氤氲涵养,有赖汉语的传递沟通。我们是汉语的造物,一如汉语之属于我们,并不止于属于我们。语言之属人,在此特定情境,专指属于我们,同样,并不止属于我们。由此而有汉语文明,立此才有华文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汉语就是世界,也就是世界观。
从而,汉语意味着启示,而在文明决定论的终极意义上,是以汉语表述自己的亿万生民的生存之道,也就是拯救之道。进而,文明之为一种存在,真实的存在,一定要借助语言来陈述和表达,并由此规范它的生活世界,则语言意味着法则,习得语言的艰辛历练就是在接受一套法则而训育成人的过程。人总是特定的人,在此,只能是特定语言训育成长的人,则由此团聚而成的文明板块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法则集团。其以特定法则表现自己,而分享内在更为深广之普世规度,恰为这个大千人世的绚烂所在。就此而言,汉语的语法,就是我们人间的律法。
循此以往,我们被纳入这一文明,进入这个世界,成为这一种人。人性,原是语言性也,某种特定的语言性也。也就因此,文明即语言,语言即存在,存在依凭言说来表达自己,证明自己。反过来说,噤声的世界不是人世,如同太过喧哗的人间必流于浅薄,反而消解其人间性。
如此这般,则汉语历经数千年的沿承接续,究竟如何塑造了我们这群华夏子民的心智和心性?世世代代,万年化育,此方水土选定的这一套表意体系,对于关乎存在的永恒焦虑会否发育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和气度?由此往下,其运思逻辑,其命名方式,其沟通流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对于这个现象界的体制化作业,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出一套洒扫应对的典仪礼规?凡此种种,不仅关乎这个叫做“汉语哲学”的思想门类的正当性,更关乎以汉语作为表意体系的亿万生灵的本体论意义。就是说,关乎我们的世俗存在与超越形式,进而,关乎我们的尊卑与生死。
故而,此间参差,看似文明论的高低生熟,实为道德论的尊卑文野。
因而,比诸哲学史就是哲学问题,而概念史就是概念这一命意,如前所述,语言就是存在,一如存在之存在于语言。中国存在于汉语,所谓的“中国哲学”诉诸汉语,用汉语来致思,在汉语中运思,并生发作育于汉语哲思,而孕育养护汉语哲思。故而,其形其神,光华烂漫,其思其虑,澎湃浩瀚。它们流光溢彩,万流归宗,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当然就是“汉语哲学”。
放行扁舟,踏歌江南,抚松长啸,朝来微雨晚来风。抑或,愁动鸿雁,纵马漠北,彩云轻举,满面冰霜一盅酒。——朋友,你和我,你们和我们,端赖此间一线牵连,幸能表达瀚海孤独而免于孤独,却又更深地陷入孤独,而终究不再孤单。
待月中庭,一天如水,文采风流,梨花满枝春带雨。不料,霎时风雷,如冥如晦,摧枯拉朽,少年心事转头空。——朋友,你和我,你们和我们,面对世事翻覆,人事无常,而幸能撑持到底,就在于常有佳言相劝,从容啸咏,编织起了另一个缥缈世界,最不济,洒家遁逃那方水土去也。
噫嘻,语文作育,一个微言大义的汉语修辞,概乎其意,而钩沉其义,造就了这方水土,为世间万物命名,也就是为我们定位,从而抚育我们安身立命,还不赶紧膜拜,还不伏惟感恩。
是啊,对于存在本身的永恒焦虑,必具体聚焦于生命之所徜徉的天人之际和生死两头。当此之际,面对有死性,彷徨焦灼,烟尘碌碌,而水流云在,梦远恨托,则其思其虑,必然诉诸一种语义体系,或嚎啕,或低泣,或沛然咏叹,或寂然默祷。是的,这一腔心事与心思,总得付诸言说,特定语意的言说。那万般希望和绝望,必须向天地倾述,谁让天地造人。朝雾肃穆,总想倾述。晚霞绚烂,引人歌啸。暗夜沉静,我们以默然无声滔滔不绝。对我们来说,这一特定的表意体系不是别的,它叫“汉语”或者“中文”,所谓“国语”者也,实则人声,一种自然的啸咏。因而,汉语之为世界的表象,这方水土之存在的镜像,或许,也是洞见,必然普世而普惠,其所指与能指,关乎文质、体用和知行,彰显的是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尽头这一生命征象。就此而言,语言就是世界,语法即世界规则,语言观就是世界观。操持何种语言作为运思工具,借由何种语言表达瀚海孤独,决定了你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从而,壶中日月,去难留,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嘿,月来弄影,城头玉漏,我醉欲眠,“山河天地点尘空”,一般情味。
在此,借助语法结构,将对象世界转圜为思想的观念世界,蔚为语言的神奇,其德与能,其意与义,同样为包括汉语在内的大型文明的纷繁语言所共享。苍穹之下,万丈苍茫,朝圣者的灵魂,不再无家可归。
至于说拼音文字优于方块文字的,不得要领,多半是顶着专家头衔的文盲。
三
可是,说到底,六合方内,可言说可思维。六合方外,那个神秘之域,不可言说不可思维。此间区际,不仅道出了语言本身的有限性及其寄托于有限理性这一真相,而且,还说明面对浩瀚世界,有限理性不得造次,必需时刻保有敬畏。从而,终究而言,世界是无法命名与不能命名的,也是不可言说与不能言说的,虽然这样说本身就已经是在言说,也就是在命名。说到底,纵观古今,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置此浩瀚,均无能为力。因此,语言就是命名,其之能与不能,其之有法与无法,说明了我们的渺小与思想的边界,在让我们无地彷徨、无从自拔之际,反而养育出以对于思想进行思想的人间智慧花朵。反抗命定,才有这性灵,虽说反抗本身也是一种命定。反思这一最高智慧花朵,总是这方水土的产物,从出生之日便呀呀学语,自众声喧哗至万籁无声。一言以蔽之,纵便是方外神秘之域,同样是一种命名,而命名就得动用语言,而且,是特定的语言。
况且,默也是说,声若洪雷。
在此,需于主客关系和主体间性,重新审视和认识汉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语本身属于一种有待完善的语言?还是因为我们身为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的中国学术从业者的汉语水平有待提升?汉语水平之高低,意味着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体认之深浅,决定了你和你背后的文明对于这个世界的命名能力之高低。从而,关乎文野,关乎尊卑。知识就是权力,就是力量,而知识首先是并最终是命名的权力与力量。同样在此,今日华夏,那种冒出一两个西文单词后,辄谓“这话中文怎么说来着?”(此处有奸笑!)虽说精致讨巧,装神弄鬼,心底的中国认知依旧滞留于三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的祖邦,却再也无法掩饰无知,不可能搪塞听众,哪怕是三线小城的大学生了。
生活世界错综纷繁,无边无际,需要表述,并无一例外地借助语言表述。表述表明了表述者的认知能力及其倾向性,时刻考验着借助语言对它进行理解与把握的人类——总是特定时空的人类——的心智与心性。而恰恰在此,作为有限理性存在,人类在它面前渺小不堪,恒为弱势。这不,说不可说时即已在说,故而说即为默,因而无答案,等于无问题。反之亦然。所以说,“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这种空灵超脱,一种地道的“汉语哲思”,却分享着对于存在的永恒焦虑、无远弗届之普世性,朋友,你说“这话中文怎么说来着?”
什么方言,咳,讲多了,讲得大家都跟着讲,从只好跟着讲,到觉得这样讲才讲得通,也才好听,那它就是普通话,进而,就是世界语!从而,汉语哲学,其思其虑,倾述的原是普世心思。
如同哲人所咏,一旦概念的世界发生了革命,现实的世界将难以为继,甚至,即刻土崩瓦解。此时此刻,朋友,就看你讲故事的能耐了。
说到底,方言才是母语,真正的人类语言,世界语不过是经由背弃与践踏方言而模仿的人类语言,一种群兽之鸣也。
四
斯宾诺莎曾经喟言,“你不知道一个身体所具有的本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则淳淳藐藐,其实指向肉身沉重而虚脱无实,挑明精神的坚忍不拔却又弱不禁风。内中一脉思绪就是,它不仅指谓身体对于灵魂的独立性,而且,相对于肉体,意在强调身体是属人的,也就是属己的,从而,秉具主题性与主体性。相较之下,肉体托形于身体,却其实无所归依,天造地设,源于自然,归于自然,既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放荡不羁。
这不,享乐至暂至微,肉体受理,但非喜乐。究其实,只有身体才懂得并且享受喜乐,故而,前者属天归地,本诸自然,后者属人悦己,受命魂灵。肉体总会腐朽,身体却长存,与人类这个物种相始终,灵魂在此安居,而得不朽。肉体没了,灵魂同在。身体没了,灵魂顿失家园,流离失所,同在却非共在,所谓孤魂野鬼者也。满世界孤魂野鬼,则此在恰为鬼魅人间,吾身招架不住,奈何。所幸身体继替而恒在,灵魂一脉婉转,终有家园。从而,人世终究是人世,人间总有人间性。
于是,肉体永恒躁动,生灭如流星。身体安适怡然,荣枯有定数。前者主动,后者主静。它们时常打架,更多时候则同在而共在,合力同心,想方设法烘托灵魂,也时不时操控灵魂。
但是,翻转过来,事犹未了,情犹未了。战争以对于和平的记忆滋养自身,也许,进而提升自身,一切和平都不过是在武力管制下并且依恃武力而实现的战争缺席状态。反之亦然。以此取譬,则更深的纠结在于,身体寄寓于肉体,一如灵魂栖息在身体,它们都依赖灵魂而存在,并因灵魂寄存于此,暂时寄存于此,方始获得意义。也正因此,“身体具有你所不知道的本领”这一陈述,却原来,是个道德判断,通达启示,而终究心怀怵惕、满含畏惧,又充满敬意、不无膜拜,却最终是无可如何的一声叹息。
一寸芳心,丈二肉身,千古文章,万里归舟,人也。
在此,借用“自由”和“解放”这一对概念,在启蒙与生命政治双重语境下衍生,则解放意味着解放自由并只能是解放自由,而自由倒不一定是解放的血酬,更非解放之树涵养怒放的花朵。毋宁,它常常外在于解放,可能会被解放所劫持。假若峰回路转,则自由巧妙借力解放,有望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公共生命。或者,经由超越个体生命与生命的个体性,自由将会赋予生命以公共意义,建构起公共意义上的生命意义。正是在此,自由通向民主宪政,解放却可能导向极权暴政。毕竟,自由的意思是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张,身心舒张却又紧张,在一切公共事务上公开展现自家的判断力,意味着身体与灵魂同时获释,固守道德哲学的现代意义。而解放多半源于“胃的造反”,指向无差等的平等,在将肉体放出牢笼之际,意味着也将身体一并放逐,灵魂脱缰嚣张无忌,终至肉体和身体一损俱损。因而,在肢解或者重新分配既有的公共性与共同性之际,此时此刻,“解放”一词等于将神学政治重新引向前台。也就因此,解放的主题和主体是肉体,自由的主题和主体则是身体,而且,只有身体具有批判能力。没有身体的自由,就没有灵魂的自由。事实上,不是别的,正是身体,还是身体,借用反抗与拒绝来建构自己的道德意识,基此道德意识,它以卑微的声音讲述了另一种生活,一个关于“不一样”的无限可能性。
所谓的生命政治,朋友,依然濡有深重的权力政治的烙印,最终寄身在那个它曾反叛的宿敌身上。
在此,一旦生命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而权力政治不过意味着垄断了宣布战争与和平的独断性,从而,对于身心的双重压迫,那么,权力意味着并总是意味着牢笼,铺天盖地。生命的世界惨遭窒息,人世便无异于集中营,所谓的人间秩序不过是狱政狱规。此时此刻,哲学仍在,哲思不息,昭示生命在反抗,至少是逃离,同时,将权力控制的边界锁定。崇高、受难与殉道,简单质朴,雄健热烈,而它们无一不是反抗。难怪,权力政治总是讨厌哲学反思。
任何反思总是特定语言的自我陈述,或喃喃自语,或短歌长啸。就此而言,从内部开辟出语言的可能性与可欲性,对于一种载述哲思的语言的多样性张力的不由自主的渴望,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与可欲性,而首先是抗拒一切垄断言说的可能边际与可能形式的专断性。是啊,语言伸张的是时代的强度与向度,未来在此展现出自己空间的无限性,正如在境性空间在此表达的是时代的刻度。从而,语言不仅是——如卡西尔所言——思想的飞轮,更是时代的身姿。进而,语言发自心田,特定在境性个体的心田,赋予思想以独特性,陈述的是反抗本身,从而,获秉普遍性,勾勒出的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正是在此,承载存在的时间构成了存在的中心,可望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是一切哲思的氤氲之所。否则,哲思丧失其时间性,等于流沙。正如一位当世西方左翼学者所言,不是别的,是恐惧以及崇高,将灵魂带回到了对于秩序的渴望。而流沙之上无法奠立可欲的秩序,时间遂自浮现。既然存在的起源同时意味着存在的秩序及其评判标准,而存在实际上存在于语言,那么,语言的形式不仅在于表征存在本身,而且,它实际上建构起一种关于存在本身是否存在的秩序。它生成于时间,可能,也终将消失于时间,时间借由它获得自己的刻度,从而,总是同时意味着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因而,在此,“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不是指向自身的逃离,也不再是内在超越式的理学进路,毋宁,是对于存在的起点的回归与再出发。——回到那个迫使我们发声的原点。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或者,至少,“追求别样的生活!”构成了一切乌托邦的起点,而引发的触媒,可能是义愤,包括“胃的造反”与道德反抗,引向抵抗与道义憧憬和政治方案;也可能是激情,而将欲望转化为一种爱的潜能,最好是一种公民友爱。不论义愤抑或激情,乌托邦所立基并映射的可能是向后回溯式的天国梦寻,对于人类原初理想状态的热烈礼赞,对于天国的永恒乡愁。从柏拉图到卢梭,从孔子到黄宗羲,咏哦的均为这一田园牧歌。也可能是向前看的伊甸园式牧歌主义,是对于世界尽头的伟大超越。从但丁的世界帝国到社会主义,奏响的是这阙战歌。置此语境,比较而言,所谓“三代之治”其实是经由回想田园而吹奏通达未来的战歌,而落脚点就在当下,自此刻批判入手去印证“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样,一切都在语言之中,一切全系乎语言。对,存在于并有赖于天长地久风雨化育的特定的语言。
于是,以母语为起点,从母语出发,而首先是回到母语,那个贴心贴肺的存在的家园。悃愊无华,一寸丹心,惟静惟默,去太去甚,恰为吾乡,适所安居,而身心舒展也。
2016年5月7日,在北大“黉门对话·汉语哲学论坛”上的发言,
七月下旬,天晴复天阴,据现场记录稿增订,十一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