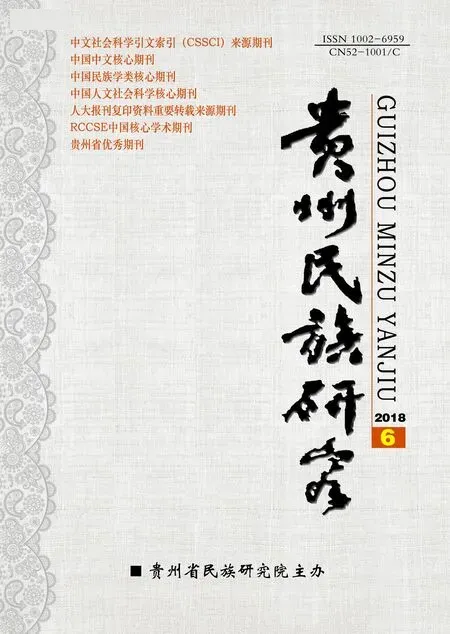民族地区村落的过疏化及其后果
——以贵州为例
李 航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一、民族地区村落过疏化的特征表现
(一)人口长期异地流动
中国大陆地区,乡村人口的流动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在地化流动,即乡村人口仅在本地区或本省范围内流动,并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很远。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系统的社会调研之后曾提出过农业人口转移的“离土不离乡”模式,即以扶持和繁荣乡镇工业发展的方式来实现农业人口的就近转移。[1]在一些发达地区,农业发展接近饱和,势必造成农村人口的大量过剩,急需转移出去,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的办法,大量农民可以实现在地化流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乡村人口的流动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在本地的乡镇企业做工,而是希望能够到离开自己家乡稍远一点的城市或者省城寻找一份工作并且留下来,这种现象在发达地区特别明显,例如江苏、浙江、广东、北京、上海等,也就是说,发达地区农民的流动倾向于留在发达地区之内,但流动的地域已从乡镇变为了城市。而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理位置偏远的民族地区的农民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出现了大规模向发达地区流动的景象,“‘孔雀东南飞’的势头多年持续不减”。[2]我们在贵州的黔北、黔南、黔东南等地对10个少数民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社会事实,越是偏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民族地区的农民越是偏好流向发达地区,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农民流动的第二种模式,异地化流动,这也是较长一段时期内民族地区村落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调查我们还了解到,这些由民族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由于制度的限制、城市社会的排斥、极高的生活成本,想要永久留在发达地区是极为困难的,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在发达地区与家乡之间进行候鸟式的流动。贵州民族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因为流向地距离自己的家乡很远,经常地往返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他们一般只能一年回乡一次,或者几年回乡一次。因此,这种异地化的流动模式也常伴有长时流动的特点。
(二)经济的“原始化”回归
社会主义经济积累理论认为,“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再分配以后形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3]即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可用于消费的资金会增加,可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升级的资金也同样会增加。但是,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村落里面却出现了经济回归“原始化”的明显倾向。贵州民族地区,无论是黔北的仡佬族村落,还是黔东南的苗族村落,抑或是黔南的布依族村落,凡是人口大规模外迁的,无一例外都呈现了这一倾向,并没有因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村落经济发展缓慢,个别地区出现了一定的倒退,除了人口外流因素,也还存在一些其他原因:其一,村落集体经济的式微使得村落集体经济的动员能力极大弱化,农户个体很难再从集体中获得帮助,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天气条件的制约,也使得农户个体的农业经营风险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所下降。其二,民族地区村落的经济目前依然以农业为主,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所采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也较为原始,生产效率不高。在贵州省10个被调查的民族村落中,农业产值在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68.8%到91.3%不等,现代化农具的使用率最高为12%,最低的只有3%。其三,村落青壮年的大量外流,使得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甚至是留守儿童、留守残疾人成为了村落的主要劳动力,生产力下降,经济回归“原始化”也就成了必然。
(三)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弱化
谢导认为“自组织是依靠基层自发组织的社会架构”。[4]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自元朝以来便普遍实行土司制和土舍制,前者的土司身份一旦得到“中央”认可便可世袭,其权力很少受到中央的干涉和影响,并可永久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治理。后者的土舍身份并不一定要得到中央认可,古代社会,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较为松散,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当地的头领即土舍来实施社会治理即可。土司制也好,土舍制也好,实际上是赋予了民族地区极大的自治权力,虽然土司制和土舍制在清朝雍正以后逐渐被取缔,但其历史的遗存却影响深远,甚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土司制和土舍制的痕迹。在那段时期,虽然中国的社会整体处于动荡之中,但民族地区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与民族地区较为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是分不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和实施有效管控,国家权力迅速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在此后的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快速地从瓦解走向消亡,直到1988年6月1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农村自组织力量才得以重新恢复。然而,在政治实践中,村委会往往被认为是替政府办事的准政府组织,其自组织能力是十分有限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村落迅速走向过疏化,集体经济瓦解,人口大量外流,民族认同与村落认同大大降低,村委会作为法律认可的自组织力量,其功能的发挥受到了进一步削弱,而新的自组织力量又难以在短时内形成和发展。
(四)民族文化特色的消解
在民族地区村落过疏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适应性较差,并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要么极端保守,要么完全消解。但随着民族地区过疏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民族文化的变迁正从极端保守的一极向完全消解的一极转化。在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完全固守是做不到的,民族文化不仅需要传承,同时,也需要发展,“不能将落后的、庸俗的东西视为特色。正确处理,‘扬弃’是关键”。[5]我们在贵州调查的10个民族村落中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有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但是,在这些少数民族村民中除了极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外,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比例非常低,日常交流基本上使用汉语。民族服饰也只有在重要的民族活动或民族节日中才会穿着,而且所谓的民族重要活动和节日,举办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其中还融入了大量的汉族元素,用这些少数民族村民的话说“我们都被汉化了”。民族文化特色在村落过疏化的过程中变得不再突出,有被完全消解的风险,在贵州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民族文化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双重压力。
二、民族地区村落过疏化的后果
(一)国家与市场全面退出
国家与市场的退出和民族地区村落的过疏化互为因果。但国家与市场的全面退出是民族地区村落变迁经历了若干过程才逐渐形成的结果,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家退出市场进入。改革开放标志着以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为特征的国家对村落社会的全面控制逐渐转变为国家力量的慢慢退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又与市场紧密相连,农民生产的余粮可以直接拿到市场上销售,令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阶段,国家返场与市场同在。政策放开了,控制减少了,虽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村落的“繁荣”,但国家力量的长期退出也为包括民族地区村落在内的广大中国乡村的萧条埋下了隐患,因此,国家力量重新返场必然成为自觉选择。1986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农村扶贫开发。同时,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政策鼓励企业也到农村去投资、创业,国家与市场出现了同时“在场”的局面。第三阶段,国家与市场全面退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国家与市场对过疏化村落的投入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产出效益却越来越低,这是促使国家与市场全面退出的重要因素。国家与市场的全面退出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村落的过疏化。当然,为了应对目前村落发展的窘境,国家在政策层面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但政策效果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很难一蹴而就。
(二)社会解构加速
村落过疏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直接后果,它导致了村落社会解构的加速。梅奥就将“社会解构归因于工业革命”,[6]作为一个连续体的工业化(城市化)—村落过疏化—社会解构,我们必须统一来看待。这一连续体所造成的不利社会结果也是综合性的,具体到民族地区的村落社会则表现为村落内部自生公共性的危机、村落人际联结纽带的脆弱、村民的民族认同与村落认同的弱化、村落经济文化生态的衰退以及村落组织崩坏的问题等。贵州民族地区的过疏化村落所呈现出的景象正是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彼此之间都是各忙各事,再也难觅过去那种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娱乐的场面,村落整体显得异常冷清;对于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活动也不再给予热情;对待村落的公共事务更是缺少关注,对于村委会“干部”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发展显然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原始化、碎片化成为一种常态,而这恰恰也是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人们自身的真实感受,无论是身在村外、还是留守在村内的人们都有的共同感受。这样的共同感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痛苦和折磨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构与现代转型,每一步前进都饱含着挫折和磨难”,[7]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共同感受”本身,而在于采用何种社会调整方式或者何种社会发展模式才能减轻人们的这种“不好”的感受才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三)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对立加剧
现代化实质是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全球推广和扩张的过程,中国在这场全球化的大变革中虽然略显被动(中国不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而是被迫卷入),但在对待现代化的态度和行动上却是积极的。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外国化”,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迫切需要发展的内在要求,积极吸收“国际经验”的带有积极适应并寻求改变和创新的过程,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然而,毕竟“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8]它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势必要向民族地区进行强力渗透,并导致民族“独立性”的保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得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对立日益加剧。民族地区村落的过疏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后果”,事实上已经引起了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很多民族性的特质正在快速消失。面对这种情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在保护民族性内核的同时,也要促进少数民族的历史转型。有人认为,在对待民族地区村落的发展问题上应该“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原生地存活状态原则”,[9]进而实现民族地区村落的“永续”发展。
三、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复兴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社会的和谐
总体上看,贵州的民族居住形态是混居的。因此,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复兴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在促进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的同时,又能保持各自的文化个性。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复兴有利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和谐。贵州民族地区村落的少数民族离开村落,走向城市,但其文明属性却是乡村的、民族的,唯有实现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全面复兴,才能重新建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和谐。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复兴有利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间的和谐。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反复提及“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涵盖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协调建设。抓好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全面复兴的工作就是要在广大的民族村落地区落实和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
(二)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
多民族的国家,多样性的文化,这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各具特色,又彼此互补。郭家骥把民族文化多样性系统概括为十个方面,[10]与之比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的任务显得十分艰巨。首先,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56个民族都有分布,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就有17个之多。此外,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村落的过疏化所导致的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发生的云谲波诡般的变迁使得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持更是困难重重。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少数民族的文化源流多来自村落,唯有实现民族地区过疏化村落的全面复兴,才是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的根本之策,民族文化的同一化、汉族化、边缘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