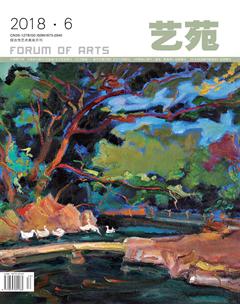侗族古歌中的生死观研究
王红 陈沛琦
【摘要】 侗族是聚居于湘赣桂鄂地区的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侗族常用歌和诗记录祖先历史、万物起源、风俗习惯等。侗族古歌是侗族人在悠久历史中创作的集诗、乐、舞于一体的作品,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祖先传说等。古歌是了解侗族人精神世界的密码。目前对侗族古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原始思维、生态意识等方面,有关生死观的研究还未见到。本文通过对侗族古歌的研究,试图理解侗族人的生命观念与死亡意识,进而理解侗族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在侗族古歌中,侗族人表达了理性而乐观的生命观、畏而不惧的死亡观以及丰富而充满矛盾的灵魂观。
【关键词】 侗族古歌;生命观;死亡观;灵魂观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理性乐观的生命观
在人类的诞生上,不同神话有不同的解释,早期人类起源神话有自然生人、诸神造人、动物变人、洪水再生等母题。侗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兼具了几种母题,糅合了多种因素。侗族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主要有三个:一是姜良姜妹造人,二是龟婆孵蛋,三是萨天巴将痣交给猴子再由猴子孵化出人类。姜良姜妹造人属典型的洪水再生神话,符合洪水过后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模式。龟婆孵蛋属卵生神话,情节不甚细致,人类的诞生过程只是一笔带过。而萨天巴与猴子造人的神话则具有与前两者不同的鲜明特色。萨天巴是侗族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祇,是万物之源、众神之神,不论是神祇还是人类英雄都由她诞生。萨天巴首先创造了火与冰,这成为昼夜更替的开始,也为万物生长创造了合适的环境,而后她用汗毛与虱蛋分别创造了植物与动物,万物开始繁荣滋长。至此,萨天巴创造万物的过程都较为顺利,下一步是创造人类。造人起因是万物自相残杀、“动物不能领会神的旨意和愿望”,因此造人的目的是治理万物。人类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一种具有更高智慧与力量的物种,不仅可以自治,还可以管理其它动物。并且人拥有其它物种没有的灵魂和思想。因为人类是更“高级”的物种,因此萨天巴在造人时也遇到了造万物时没有遇到的困难,过程十分艰难。萨天巴为难之时四处巡视遇到了四个萨狁(即猴婆),她化作苍鹰佯装受伤以考验萨狁,结果受到了萨狁悉心的照料。她仔细观察萨狁,认为无论是形象、动作还是品质,萨狁都是抚育人类的合适对象,于是萨天巴扯下四颗肉痣交给萨狁。“四个善良的萨狁啊,不吃不喝同孵蛋,就像鸡婆孵蛋一个样。”(1)最终孵化出了人类始祖松恩和松桑。在萨天巴与萨狁共同创造人类的这个神话中,人类的诞生过程漫长而艰难。人类由神创和进化共同产生。其中体现出理性与神性的结合。猴婆孵蛋是人类进化的原始雏形,蕴含了侗族先民对自然及人类的观察与认知。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人类与猿猴在形象与姿态上相似,但侗族先民对进化还并无科学全面的认识。因此侗族先民在解释人类诞生时,将猴与人视为具有同一祖源的生物,人类由猴产生,萨狁对松恩松桑的精心照料则体现了人类诞生的漫长艰难。萨天巴与萨狁是人类共同的始祖,分别代表了侗族人对人类起源的神性与理性理解。萨天巴赐予人类智慧与力量,萨天巴的痣可以视为侗族人对人类诞生难以解释部分的浓缩体现。具体繁育人类的过程则由萨狁承担。在人类起源神话中,侗族古歌的萨天巴与猴婆造人少见地在神性中融合了科学理性思想,神创与进化结合的繁育方式突破了单一的神造人模式,是侗族人在对自然万物诗意描绘之外的理性萌芽。
如果说人类起源神话中还笼罩着一层神性氛围,侗族初民在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上还充斥着浪漫想象,那么在对个体人生的理解上,侗族人则秉持着理性而达观的态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命定还是永生是一个宏观而关键的命题。人的生命是否有终止?侗族先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首先体现在对人寿命的认识上。在讲述万物起源的侗族史诗中,张古与马王是开天辟地的神,他们不仅是天地的创造者,还是万物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定老人守命到九十春。”(2)人类寿命不是无限的,而是被定到90岁,这大致符合生活中的实际状况。神话是初民基于对世界的理解创造出的解释,起源神话是人类综合生活经验与想象对万物进行的诗化溯源。“命定九十”是侗族先民借张古马王之口、以神话的形式表达出的对寿命的态度。原始人类在面对死亡、寿命等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时产生的无力感容易产生永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麻痹也是慰藉,让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得以安放与排解。所以即使在面对人类死亡的事实与永生观念的矛盾时,原始人会创造出更多的解释系统来化解矛盾,由此形成有关永生的一套观念体系。但侗族先民没有因为恐惧死亡而将人类神化为不灭的物种,反而清醒地看到了命有定数、人有衰亡,并将其写入神话,让“命定”成为神的旨意来指挥侗族人的生活,是以一种模拟圣旨的方式表达生命观。侗族人民虽然看似是天意的领受者,但其实他们是天意的拟定者。人寿有限是既定的事实,如何看待生命却是可以选择的。认定寿命有限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而依然可以为自身的生命奋斗。侗族古歌的命定观不是面对命运束手无策的宿命观,而是认清生命有限但依然不放弃努力的理性与达观。所以在张古马王造人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人类的奋斗史。
这也可以解释侗族古歌中的人类神化现象。在侗族远祖歌中,萨天巴与姜夫(张古)马王是创造万物的神祇,在他们之后,松恩松桑、宜仙宜美、姜良姜妹、王素、万亮、甫刚雅常、公曼等都是以人类身份出场的先祖,虽然他们的事迹多少带有神话色彩,归宿也高度浪漫化,似乎脱离了人类的范围,但他们的故事呈现出与之前神祇迥异的面貌。总体上,侗族古歌可以分为两个谱系,一个是以萨天巴为核心的神系,包括萨天巴、姜夫(张古)马王、冠共萨央等神祇,他们因为具有神的力量而几乎无所不能,他们的故事是创造万物、指点江山的开辟型故事,第二个谱系则是从松恩松桑开始的神化人谱系,他们是人类的祖先,他们的故事是一部濃缩的人类发展史,因为带有浪漫夸张的色彩而具有“神性”。在人类被创造出来后,人类就开始了不停息的努力与抗争。人类诞生后模拟其它动物的行为,逐渐掌握了生存技能;始祖与雷婆(有版本作“雷哥”)的故事具有复仇、报恩、战斗等复杂的情节,映射了人类与自然力量利用与抗争兼具的关系;洪水滔天后战素蟒、射神鹰、战魔王等故事更是人类在艰苦环境中谋求生存的一次次努力。第二个谱系中的人类先祖生命都有终结,无法像第一个谱系中的神一样“养尊处优”地安坐天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人类生存而抗争,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寿命有限,谋求生存的奋斗才更加迫切。人类的发展史漫长复杂,浓缩到短短几卷中就带有了神话的意味,加之侗族对始祖的祖先崇拜,第二个谱系中的人类也便神化了,侗族人是带着强烈感情来谱写远祖史诗的,人类始祖的行为与归宿因此带上了“神”的色彩。在命有定数、寿有穷尽的前提下依然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努力体现了侗族理性而乐观的生命观念。
二、畏而不惧的死亡观
对死亡的态度首先体现在是否承认并面对死亡这个事实。与对生命的态度相似,侗族先民在面对死亡时没有回避,没有惧怕,而是首先承认死亡的合理性并积极面对。从松恩松桑开始,一直到冠共萨央,这一脉人类始祖都会死亡。在侗族古歌中,衰老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死亡如同落叶归根,衰老到死亡的过程被描绘得自然而诗意,不见悲恸与凄凉。“光阴逝去不再复返,新生旧亡更替有常,你们人老年衰归期快到,何不捧宝回乡坐享俸养?”(3)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回归。“宜仙宜美人老了,如同枯叶萎黄。天上降下了圣旨,催促他们去天堂。……回到创世女神萨天巴身旁。”(4)宜仙宜美死前叮嘱儿女姜良姜妹:“笋子脱壳了啊,自会盘蔸繁衍成林而兴旺;儿女长大了啊,不用父母时时陪伴在身旁。听罢我们的话呦,不要难过悲伤。……我们老了不能久留世上。”(5)侗族人借祖先之口表达出视死如归的死亡观。再如第一次大迁徙中带领人类战胜灾害的王素族长,他在将死之时对族人说要到月亮上探望月姑,与月姑行歌坐夜,随后便逝去。死亡被诗化为一场浪漫的赴约。在承认人皆有一死后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死后的归宿。在生与死的关系上,侗族先民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在时间上将生死视为前后相继、落叶归根的自然现象,人类的生死被纳入到整个生态系统中,成为自然万物循环的一部分,这消解了死亡的悲怆,让先民更加达观地正视死亡,从中也可见生态思想对死亡观的积极影响。另一种理解方式则是在空间上将生死视为位置的移动。死亡被视作“上天庭”“回月堂”。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不是湮灭,而是在另一个空间继续生存。以空间变换理解死亡是图示化思维的体现,减轻了死亡的严肃性,同样给侗族先民以慰藉。
虽然并不惧怕死亡,但侗族先民对死亡怀有敬畏的态度。升天仪式的隆重是敬畏死亡的鲜明体现。史诗重点表现的是祖先拯救人类的丰功伟绩,但是作为人类,祖先终有一死,侗族古歌在处理祖先死亡的部分采用了委婉而史诗化的笔法,隐去了弥留之际的痛苦挣扎,重点描写死前对后人的叮嘱以及升天的仪式。祖先死亡时子孙的一系列举动形成了一套近乎祈祷与祭祀的仪式。侗族祖先的死亡具有训诫子孙的道德意义和预知未来的指示作用。如族长王素,他的死亡十分平静,在和众人交代了其死后的归途——月堂后静静躺下,闭目睡去七天七夜,“众人抬他到山顶,放在高高的岩石上,六十种姓做社三年,敬送族长进月堂。”(6)经过数年的祭仪,侗族族长得以成功升天,到月亮上继续“生活”。在漫长的祭仪中族长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他的意义从生前的具体事迹中抽离出来而转变为一种象征,或者说,此时的族长已经符号化为族人的精神图腾,族人在祭祀时是借族长的身份表达对死亡的崇敬,而后训诫子孙,让后人在祖先开创的业绩上继续奋斗。死亡祭仪的另一重意义是借祖先之口说出人类或世界命运的预言,祖先的遗嘱带有了神谕的性质,激励后世族人在知道前途艰难的情况下更加勤勉。如宜仙宜美死前说出的十三段叮嘱,它预言了洪水灾难和子女间的争斗,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类预知前路艰险而坐以待毙,而是让人类对未来的灾难有更充足的准备。这与侗族知命而不安于命的生命观是一致的。就这样,一代先祖的死亡成为下一代先祖生命的开始,谋求人类生存的任务在祭仪中传递。对死的崇敬进而成为对生的勉励,这也是侗族人蓬勃不息奋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人类祖先的死亡多带有预言与训诫的作用,子孙在面对祖先死亡时更加沉重,那么神祇死亡的意义则更侧重纪念。相同的是,他们的死亡都是族人的团结再出发的起点,祭仪都是凝聚人心的一次典礼。比如侗族农神冠共与谷神萨央,他们是在人类诞生初期帮助人类战胜灾害的夫妻神。冠共立款规、设月也、教会大家驯牛,萨央带领族人播种五谷、教会族人纺织制衣。两位神的事迹对人类社会具有开创性的作用,“款”成为侗族独特的民间规约,“月也”成为侗族一种集体互访的社交形式。冠共萨央的故事分别成为侗族节日洗牛节和尝新节的来源。神祇死亡的意义被凝聚在节日里流传下来,人类在摆脱了初创时期的困难、安居乐业后,依然采用节日这一具有高度仪式感的方式来纪念祖先的事迹,死亡的意义在节日中延续,节日中繁复而神秘的仪式便是敬畏死亡的体现。
三、灵魂:天地之外,生死之间
靈魂,或称鬼魂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人死后演化而成,一种是被创造出来的。在侗族神话中,鬼的性质兼而有之。在创世神话中,鬼在开天辟地的混沌时代就被祖先创造出来,和人同时存在。人与鬼分别居住在村寨与坟墓中,彼此独立,并不是演化的关系。侗族人从一开始就赋予了鬼魂的存在以合理性。因此,鬼魂成为神与人之外的又一个主体,由此构成了侗族是神、人、鬼的三分主体模式。这与三分模式的宇宙观密不可分。神、人、鬼分别对应神界、人间与冥界,三界各自独立但可相通。在侗族的创世神话中,天与地最初混沌不可分,萨天巴的助手姜夫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竖起四根擎天柱,扯起天蓬将天地分离,在大地的四周及下方是冰块与热气组成的“汪洋”。值得注意的是,侗族神话中的天地观念与中原神话中传统的“天圆地方”不同,它认为天地皆是圆形的(天神将天地由方修圆),形似盖子与盘子,天神居于天庭,人类像蚂蚁一样居于大地这个圆盘中,地角之外是五湖四海。促使大地剧烈动荡的力量是“热气”,但神话对这团热气的性质与来源没有更多的解释。这首先是源于侗族初民对自然的观察,但更多还蕴含了对未知力量的描绘与想象。在天地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它与天地彼此独立,却会对人类与大地造成影响。热气与冰块是侗族先民这种想象的具象化表达。这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画“非衣”中对三界的描绘十分相似,盘状大地之下是一个运动的暗世界。“大地环水的观念十分重要,由于水平系统中环绕大地的四海之水与垂直系统中地底的黄泉之水相通相连,这就使垂直模式同水平模式联系起来。由昏所代表的黑暗、死亡价值同由昔、冥所代表的光明、生命价值构成二元对立。”(7)阴阳观念同样体现在对鬼魂的认识中,侗族人将鬼魂分为阴魂与阳魂两种。阴魂是将死者拖入冥界的力量,阳魂则是人刚死时将人留在人间的力量。祖先纪子的死亡就是经历了阳魂与阴魂的拉扯。“纪子的阳魂硬拉着纪子,要他留在人间除魔王;纪子的阴魂也牵着纪子,要他到阴曹地府去游逛。阴魂牵着纪子往地府……阳魂拉着纪子走山间。”(8)弥留被理解为阳魂与阴魂的斗争。如果阳魂胜利,人便可以复活或转世,反之则死亡。这体现了侗族人强烈的生命意识。
灵魂虽然独立于天地之外,但却游走在生死之间。死后的归宿有几种,一是进入冥界,二是转世或复活,三是物化。复活与转世是以新的形式返回人间,物化是灵魂升上神界继续对人间施加影响。物化是非常普遍的模式,多出现在创世神及远古祖先身上,表现为死后肢体分解为山川草木等,物化的对象多为自然万物,而在侗族神话中又集中地表现为星宿,如宜仙宜美、万亮、雅常、公曼死后都化为指明方向、带来光亮的星;除直接化为星宿外,登上月堂也是神祇普遍的归宿,如王素、纪子等死后皆升上月亮继续保佑子孙。这与侗族初期艰辛的迁徙有关,因生存环境的恶劣,侗族祖先不得不多次迁徙,经过漫长的“祖公上河”终到达黔湘桂地区定居。不同于安土重迁的中原地区,迁移是侗族远古时期的常态,侗族的初创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迁徙史。方向及光明是迁徙民族汲汲渴求的两大要素,因此将祖先的归宿定为星宿是期望求得对自身命运的保护与庇佑,星宿型物化暗含了对族人命运的危机感,是人类生存意识在神话中的投射。
三界的划分与灵魂不灭的观念有关。“确定原始人对死人的观念是不容易的。……他既不在头脑中清楚地表新出他的思想,也不能清楚地向别人表达。……他们举行的仪式比起他们高声的信仰誓言来更能把稳地表明他们的真正信条。”(9)侗族人的灵魂观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仪式与习俗中。祭祀祖先公曼的仪式便是一例。当公曼与瓦星经过生死决战依然未决出胜负后,公曼的遗体被放入瓮坛中,等待转世后重新上战场。族人特意在瓮坛盖上留下了小孔,以供公曼的灵魂从中进出。瓮坛放在大寨的鼓楼坪中央,族人围着瓮坛唱歌跳舞,但有人不小心提前开了盖子,公曼化作一股精气与一道白光升天,化为参宿的一颗星。初民在面对生死时容易采取具象化的表达与理解方式。因为相信灵魂的存在,便在盛放遗体或骨灰的容器上留小孔,灵魂是“一股气”“一道光”这一类有形的实体。具体可感的操作和实物给了先民与祖先互动的机会,延缓了祖先逝去带来的悲哀。通过一整套仪式,祖先的逝世有了合理的解释,进行完仪式的子孙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祖先的死亡,同时还可以(在想象中)继续与祖先保持感应和联系。这也是祖先崇拜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原始神话中的祖先故事是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仪式与习俗便是观念的活态体现。侗族的灵魂观念没有固化在文本中,而是从原始神话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可见于丧葬习俗中。侗族的丧葬仪式隆重而細碎,从弥留之际到葬仪结束,其间要经历接气、通报、洗浴更衣、送钱、停灵、做法、入殓、停柩、出殡、复山、丧宴等流程,其中体现出侗族人对灵魂的矛盾态度。首先是对灵魂既亲近又畏惧,一方面希望延续同亲人的情感纽带,一方面又害怕死者将后人带人阴间。死者入棺时,儿子们要把自己穿过的有热气的衣服放在死者身边,目的是让死者到冥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后辈的温暖亲近。可是灵柩入土时家人却要回避,因为怕死者留恋家人或将其灵魂带入阴间。在送葬时,子女要边走边喊死者的名字,催其快走,这样死者才愿意离开家。送葬前后这两个行为的矛盾正体现了生者对死者亦亲亦惧的态度。与其说是对死者的害怕,不如说是对阴间这个未知世界的害怕。对鬼魂恐惧的细节不胜枚举,无论是灵柩抬出门后的各种辟邪手段(在门楣贴红纸、杀鸡放血、以火熏房等),还是送葬途中的诸多禁忌(棺材切忌沾地,否则亡灵将停滞不前等)都是鲜明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仪式过程中亲属的态度变化。虽然丧葬的全程都是虔敬而小心翼翼的,但随着仪式的进行,子孙对死者的避讳渐渐超过亲近,对灵魂的矛盾在葬仪过程中达到顶峰、在葬礼结束时便淡化了。这是由阳入阴、由人间进入冥界仪式结束的结果。子孙的复杂情感混合在仪式中,葬礼是让其接受死者死亡事实的途径,从亲近到疏离是完成了心理告别。丧葬的另一对矛盾是利他与利己的矛盾,亲属既切身为死者考虑,为其做多种准备,却又希望死者可以带来福佑,呈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如死者断气后,子孙需要打掉其门牙以顺利转生;更衣后要将适量碎银放入死者口中,意为让死者得到安宁,但入棺时银子要取出,否则子孙会不善言辞。“打门牙”与“塞碎银”可以解读为帮助死者顺利升天,但同样可以视为对尸体进行了“破坏”。如此的例子不胜枚举。从矛盾中可以看出丧葬仪式的作用,首先是维护人伦与宗族纽带,亲属(特别是子女)在葬礼全程中扮演者领路人和组织者的角色,下葬前要进行多次对死者的诉说,如果死者是女性,子女还要请求舅家原谅自己做的不周全之处。葬礼不仅为了死者安息,更是一次族人亲属的集会。繁复的仪式需要合理的分工,不同亲疏的家属各司其职,葬礼结束后还要办丧宴。有些地方死者不能立即下葬,需要等同族人都去世后一同入葬。家族观念在此时得到充分彰显。除道德意义外,仪式还具有抚慰与祈祷的心理意义,无论是对死者的照顾、倾诉,还是丧葬进行中的一系列禁忌,都是生者对自己与死者关系的一次反省。整个丧葬过程看似是以死者为中心,但生者才是主角。通过仪式,生者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接受亲人的死亡。同样生者在倾诉中还反省自己照顾不周之处以求原谅,倾诉的意义更多在于祈祷,死者在死亡后因此而神化了。在这个层面上,祭仪的作用已经近乎于宗教。
注释:
(1)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7.
(2)杨权,郑国乔.侗族史诗——起源之歌[Z].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1.
(3)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21.
(4)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3.
(5)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4.
(6)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47.
(7)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41.
(8)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53.
(9)J·G·弗雷泽.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M].李新萍,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108.
参考文献:
[1]J·G·弗雷泽.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M].李新萍,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2]J·G·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冯祖贻,等.侗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4]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石干成.古老的理性之光——侗族史诗《创世款》的文化人类学意义[J].民族论坛,2003(3).
[6]吴浩,梁杏云.侗族款词[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
[7]徐赣丽.侗族的转世传说、灵魂观与积阴德习俗[J].文化遗产,2013(5).
[8]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Z].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9]杨国仁,吴定国,等.侗族祖先哪里来(侗族古歌)[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10]杨权,郑国乔.侗族史诗——起源之歌[Z].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1]杨权.侗族民间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12]杨筑慧.侗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3]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14]朱慧珍.侗族民间文艺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