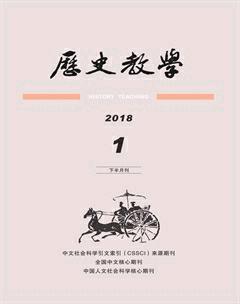日军空袭下的“反日常”旅行遭遇与“家国想象”

[摘 要]本文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空袭对游客的生命、旅行、游览造成的威胁与影响,以及特殊的旅行遭遇——“跑警报”下的生命体验。游客在经历个体之痛和家国之痛后,其个人际遇成为民族命运的缩影,并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想象与认同。而在转化过程中,风景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景叙事方式是采用风景意象来唤起民族共同价值认同、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痛斥侵略者的暴行、用风景的隐喻和比附来重塑民族性格。因而,游客的旅行和“家国想象”促进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空袭,旅行遭遇,风景叙事,“家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35-08
在全面抗战时期,面对山河破碎的状况,风景,因其蕴含着旅行者的价值观和身份意识,提供了一个切入文化问题的途径:文化价值、文化延续、文化的价值范畴和无价值范畴,以及文化身份形成神话的建构。风景还可以引起诸多思考:在个体被文化包容的同时,个体行动如何帮助形成文化;个人如何将自我视为某种特定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由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帝国扩张、战争或战争后果这类社会或民族创伤引起的动荡时期。①“万方多难此登临”,旅行者在面对国家——风景建构中,建构着自身的国民身份,也建构着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
西安旅游与交通状况
旅游在历史上一直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体消费活动,而到了近代,旅游已同社会化了的大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旅游消费具有类似商品消费的趋势,世界上从而开始形成一个新的行业——旅游业。旅游业是以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行、游、食、住、购、娱等各种需要,以提供旅游服务为主的综合性产业,它由有关国民经济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部门等构成,其中包括支撑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行业,并涉及许多相关行业、部门、机构及公共团体。②民国时,人们一般将“建立在大众旅游基础上的旅行事业的建设分为布置、宣传、接遇三部分”。③
1935年陇海线潼西段正式运营,年旅客发送量为189.5万人;次年,西宝段投入运营,旅客发送量激增为278.6万人。④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号召,前往西北考察的人员也与日俱增,其著述多达85种。⑤据笔者的考查,其中涵盖陕西的游记多达50种以上,而散见于报刊的游记多达200篇以上。由此可见,陇海铁路在刺激陕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陕西旅游业的发展。⑥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陇海铁路东段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占据(西段于1937年3月1日通至宝鸡),公路成为陕西的主要交通运输手段。西兰(西安—兰州)公路,川陕(宝鸡—成都)公路是西北的两条主要交通干线。因此,西北和西南的陆路旅行设施均得到发展。抗战时期,在没有全国性旅游机构的情况下,陕西乃至西北的旅游事业几乎全赖中国旅行社筹划组织和支撑。中旅驻秦办事处及它下辖的西安、兰州、哈密三个分支社,以及招待所和带有招待所性质的单位,最多时共有18个之多,它們共同组成了中旅在西北和西南的旅游服务网络。
内迁人员的旅行、物资运输、前往战地的考察与慰问,使得西安作为西北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旅行人数和旅馆数目也大为增加,至1947年,西安的旅馆数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共150家,房间数位居第六,共2858间。可见抗战时整个西安旅馆业发展的规模与状况,以及人员往来的情况是非常繁盛的。①
正是在人员频繁往来的情况下,旅行者留下大量的纪录与游记。据笔者统计,有近二十种。②其中,部分旅行者遭遇并见证了日军飞机对城市和平民的轰炸,并在旅行记录中予以记载和传播,而其记录中所承载的“家国”意象与生命体验成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今天看来,这些记载弥足珍贵。
因此,围绕轰炸下的“行”、特殊的旅行遭遇——“跑警报”“住”“景观”,从日常生活的角度,③讨论轰炸对旅行生活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这种“反日常”④的旅行对旅行者心态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家国想象”,从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特殊情况下的旅行体验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旅行是旅行者作为主体自发的、前往一定旅游目的地及景区、有计划的休闲与旅行活动,并伴随旅游产品的购买等行为,产生审美与休闲精神的活动。而逃亡是主体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的被动行为,一般不会前往景区进行游览观光,更很少有伴随的旅游产品的购买等行为。本文所采用的史料均为抗战时期游览及考察的记述,都是旅行主体(游客)的主动行为,并非从敌占区到后方被迫迁徙所作的逃亡记录。
二、轰炸威胁下的特殊旅行遭遇
——“跑警报”、参观、住防空洞
“西北、西南与华北,华中的交通联系,皆以西京作为总汇,商品资源运出或输入,亦莫不以西京为其运转枢纽,是以商贸接踵,贸易繁盛,成为今日西北第一个大都市。西安的交通地理位置导致其作为重要的轰炸目标。”①据档案资料统计,日军共计轰炸西安约145次,出动飞机560余架次,投弹1000余枚,伤亡1万余人,毁房4.3万余间。②在轰炸中游客不仅旅行计划被打断,所看到的景观被损坏,而且要应对轰炸进行防空,俗称“跑警报”,因此,“跑警报”成为抗战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旅行体验。
(一)“跑警报”中的遭遇与体验
1937年10月10日,西安遭日机空袭后,开始构筑防空避难室、防空壕以及防空地下室。1938年11月,西安构筑地下室20处,窑洞300多处,可容纳城内少数居民防空避难之用。除省政府少数厅、处建有防空洞、壕外,为居民避难用的防空洞、壕很少。由于日机空袭不断增多,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日益严重。
由于初期防护措施不足,居民因为城内自建防空洞过于简陋,容易被日机炸毁,所以许多居民选择到城外的田野或防空壕躲避。1939年4月9日,林焕平从重庆来到西安,记录了西安市居民无处藏身的窘况。“有二三处避难室(即防空洞)被惨无人道的敌机故意炸毁了,里面的市民,全被牺牲了。故现在市民多不敢入避难室,天一亮,不管有没有警报,都携男带女,到郊外的田野上躲飞机去了。”③1939年是抗战以来西安遭受日机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惨重的一年。敌机出动446架,44次轰炸西安。投弹1382枚,人员伤亡2346名,炸毁房屋3181间。④“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七日——炮击潼关的周年纪念日,那天一共发了四次警报,前三次警报都没有飞机来。最后一次是下午四点半,那时到城外躲警报的人都已经回来了,因为前三次都没有飞机来,所以第四次警报时,出去躲的人少,而飞机却来了二十一架,在城中各处投弹,死伤了一千多人,这是西安空袭损失最大的一次。不幸那时我正在城里,而且我的周围落了七个重磅炸弹。”⑤endprint
“跑警报”时有发生拥挤和踩踏事件。“有许多跑警报的人想往汽车上爬,汽车上的人用皮带向爬上去的人乱打,有的甚至被打得鲜血直流。这样,群众的激怒更增加起来。司机座位的玻璃被捣破了,司机被群众饱以老拳,汽车被停止在城门口的人群中。紧急警报尖锐的叫起来了,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后面的人挤得更紧。我刚刚挤到城门口,因为在我前面的几个人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又加紧挤上来,于是我也被挤倒了,许多人从我身上踏过,我感到疼痛,但神志很清楚,觉得这一回儿是糟了,会被人们踏成肉饼,不得不鼓起全身的勇气,从他们的脚下奋力爬起来,幸而得到了一位警察的帮助,我居然爬了起来,而且逃到了城外,躲在一个空旷的菜园子里休息。”⑥后来,为了方便群众疏散,当局在城墙开挖便门,以避免拥挤和踩踏事件的发生。
在城外的躲避空袭的群众也深受其苦。“成群结队的市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服褴褛破碎的也有,衣冠华贵摩登的也有,或坐着,或躺在绿油油的麦野上,有的翻来覆去在泥土上打鼾声,简直像泥人了。他们早上六七点钟出来,下午五点以后才回去,中午是饿着肚子,不吃东西了。”⑦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自1939年10月5日起,由各联保出民工,在城郊四周挖掘防空壕,深1.7米,10月15日竣工,能藏约15万人。
为了进一步保障西安市民生命安全,1940年12月22日,西安防空部队决定构筑城墙底下防空工程,环城墙一周,共构筑625个洞口,洞高1.5米至1.8米,洞宽1米至3米,总长51003米,其中第42号洞,长8.5米,宽3.1米,高1.5米,可容纳100多人,这项工程历时一年有余。据民国31年(1942年)11月21日《西京日报》刊登的“西安避难设备种类及容量统计资料”,全市防空洞、壕能藏27万多人。⑧这些沿城墙挖掘的防空措施,以及这种防空措施的优点也被游客记录下来:
西安市民于发警报时,除自动疏散乡间外,多至城墙根防空洞躲避,东西南北四城各就其近处入洞,西安土质富有粘性,虽不如渝市石层之坚固,但抵抗力亦强,且城墙为一线形,尤不易击中,故西安轰炸时,死伤甚少。①
旅馆为了保障旅客安全,也采取挖防空壕的措施应对轰炸,西京招待所就挖有防空壕。因此,旅客除了出城躲避或钻防空洞外,也可以躲避在旅店自设的防空壕。“回头我看到一个茶房,他告诉我楼房旁边有自己的防空壕,我进去了,只有寥寥六七人呆站在里面。”②
(二)对景观的防空保护与受损害的景观
为应对轰炸,碑林管理部门或转移文物,或采取保护措施,用泥对一些重要的碑刻进行“砖泥封固”,防止轰炸对碑刻表面造成伤害。因此,造成了“没字碑”的现象。“民国26年,由国府拨款五万元施工整理,派员监护,现有庙宇式巨室四进,将隋唐遗留诸碑,分室陈列,惜因避免轰炸,已将此类名碑,各用砖泥封固,其露出者,非赝品,即历经嵌刻,真迹全失之品,殊无足观。碑林附近,多售碑帖商店,但真品亦稀,且因碑经封固,索价特昂。”③从中可见,由于“砖泥封固”无法拓印,造成碑林特有旅游商品拓片的紧俏,价格上涨。
轰炸不仅给街市带来影响,也使景观建筑受损。大雁塔因驻军无法参观,城内的清真寺也遭受到轰炸。“十一月三日,晴。上午偕伟侠至西大街化觉巷游清真寺,为玄宗时建,碧瓦雕砖,气象瑰伟,即门首之照壁,亦镂刻极精。入门有长甬道,道旁白石栏杆,整齐精洁,惜有一处曾中一弹,现巨坑犹存,石栏则散卧坑旁,状如伤兵。”④日军轰炸对西安市内景观的破坏也反映在游客的记录中。“十二月六日,星期六,晴。早七时半,又发警报,敌机四架,侵入西安郊外,在乡间投弹后逸去。下午无警报,余以独居无聊,乃步至莲湖公园游览。公园在城西北隅大莲花池街,原为明季秦藩王妃放生池,引通济渠水注之,中植莲花甚茂,嗣以年久失修,渠塞水涸。清康熙七年,巡抚贾汉复濬渠池,植以莲花,遂名莲花池,池旁有莲花庵,元庆寺,莲花寺,为清雍正元年重修,民元辟园之东北部为体育场,为群众集会之所,旋废,民十重加修葺,渐复旧观。冯玉祥督陕时,毁寺改为公园,二十年又加整顿,引水植木,积土为邱,更名为莲湖公园,茅亭水榭,颇饶花木之胜,每夕阳西下时,游人甚众,但抗战后,情景稍衰,园内建筑,尝遭敌机扫射,墙壁上弹痕累累焉。西安城内,尚有一建国公园,凿池筑榭,略具规模,另有一革命公园,占地甚广,然除阵亡将士墓及纪念碑外,荒芜不堪。”⑤
(三)防空与防空洞中的生活
日军轰炸对旅行生活也造成极大的影响,商铺白天不敢开门营业。“路上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店门上一律贴着,‘下午五时开市或‘下午五时照常营业等字条。沿马路随处看到塌倒了的、焚毁了的店铺,有些已经挖掘了的,有些还没有挖掘,一片瓦砾颓垣,堆在那里。那种萧条悲惨的景象,森森然使自己寒心。”⑥
因此,在防空期间,对旅客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如,旅客要求服务员替自己购买食物遭到拒绝:“‘那么,你给我到外头买些点心回来吧。我这么样对他说。他也决然地回答我道:‘那也没有呀,先生!人都往城外躲飞机去了,商店都不开门哪!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来时所见一切店户,都是关闭著门了。我穿好衣服,走下楼去,往门外走去。我未到西安之前,已微闻西安马路上有许多防空壕,有些可通出城外的。我的下意识,是上马路找防空壕去。刚跨出门,被警察厉声喝住:‘不准走!往里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西安一拉出第一次警报,马路上就绝对禁止通行。”⑦
1938年3月1日,端木蕻良、萧红和聂绀弩随丁玲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演出,在排练过程中,3月13日和14日,日寇飞机侵袭了西安,并在14日的西安西郊投弹。当时西北战地服务团居住在城北梁府街一带,西安梁府街一带民众“跑警报”的方向是北城墙,北城墙上挖有洞,可以防空袭。有地下防空洞的,就下地下防空洞。塞克回忆:“空袭警报来了就下防空洞,解除警报就出来还排戏,演员拿着剧本下防空洞里背台词。”⑧
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是受到威胁。1938年11月23日,日机20架次轰炸西安城关,时恰值穆斯林开斋节日。“轰然一声,屋瓦纷飞,梁栋倾圮,血肉模糊,呻吟哀楚,而我若干忠实穆民遂作敌机炸弹下之牺牲者矣。经调查,伤亡百余人,尤以化觉寺寄居之义民为最,千里流亡,遽遭厄运,惨死他乡,明月秋风,谁人凭吊,矣可哀已。”①endprint
从以上材料来看,日军的空袭不仅给西安市民造成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也对西安的旅游业造成巨大影响。
三、空袭下的旅行心态与“家国”体验
“地方感所体现的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连结。”②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日军的入侵唤起了民众对家园风景的普遍关注,一旦风景自身稳定的“地方感”被威胁或被打破,民众就会产生持续的心理焦虑和明显的排外情绪。而想重新获得一种稳定的“地方感”,必然要在“风景”叙事上加以改变,从而重新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在强化或建构新国族的过程中,激发热情的爱乡爱国‘地方感正是建构国族认同的最有效途径之一。”③“我们经历了众多‘创伤性历史事件,弥补我们内心深处的‘匮乏(保国保种)已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一个共同认可之物,来治疗创伤,来投射欲望,弥补匮乏。”④而这种“共同认可之物”,就是国家。
日军的轰炸,首先让旅行者感受到是对中国国土的侵略。胡安·诺格指出:无论哪种国族主义都是一种疆域意识形态,要求明确的疆界以相互区别,从而使民族疆域观念成为国族认同的根基。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民族国家“更是一块封闭的和划定的领土”。“国家主权基本上是以领土来定义的。”⑤因此,日军空袭使旅行者直观感受到的是国家主权的被侵害,而这种侵害直接引起的是愤怒、痛苦,对于作为个体的现代国民来说,国家利益受损,则必然引起反抗的冲动与抗争意识。
一般而言,旅行者的心理体验轨迹为:个体之痛、家国之痛、国家想象与认同。国族自我意识的产生及凝聚力的形成,建立在对“他者”想象的基础上,日寇的轰炸直接造成了“自我”的痛苦,轰炸“是他残杀了我们的同胞,但这个血的教训只有加深了我们的仇恨”,⑥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为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同质性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与注脚。因此,由于在旅行中遭受空袭,进一步加深了游客对国家风景体认和认同,激发了人民抗战建国的热情和民族抗争精神。
(一)死亡的恐惧与对日军暴行的仇恨
日军的空袭轰炸对群众形成了死亡的威胁,而躲在防空洞中,这种随时被炸弹击中的危险更加深了死亡的恐惧,而在空袭之后,看到“血的教训只有加深了我们的仇恨”,加强了“我们的抗战决心”。
敌机成队的闯入市空,沉重而响亮的马达声震动了每一个人的耳鼓,都紧握着拳头,闭起眼睛,忍耐着炸弹的来临,炸弹声一声紧一阵,人底呼吸也随着急促起来,高射炮和机枪的射击附和着炸弹的声响,把每个人的生命都仿佛系在万丈崖头的细线上,一经微风拂过,马上便会粉身的危险,每一个炸弹爆发了以后,“啊!不在眼前”,又似乎觉得自己底生命可以保留下来,但接着第二颗炸弹的爆炸声又打断了人们的幻想。……轰炸任凭他怎样的残酷,轰炸虽然是他残杀了我们的同胞,但这个血的教训只有加深了我们的仇恨,我们去感谢他坚强我们的抗战决心,同胞啊!但愿打到东京去,以雪这不共戴天的仇恨。⑦
旁边的树枝断的断了,折的折了,电线断了没有一根整的了,被炸的家属和受伤的同胞都在大街惨哭,有的已经倒在血泊中,有的还没有断呼吸的呻吟着……一跨进寺门就见男女老友都在惊慌、痛恨地号哭中,有的是被鲜红的热血和夹杂的灰尘沾满了他的周身,惨呀!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蒂你……我这样自发地发出了痛恨的怨言,……被一颗重量的爆炸弹震塌了一个长方形的窑洞,里面所有的人无一幸免,后来启窑洞的时候已抬出了60多个男女尸体。⑧
种种惨状加深了民众与游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的仇恨。
(二)“凝视”自己——国破山河在的个人身世沉浮与感叹
个体际遇是个体在历史发展与环境变化中,因时空交错作用产生的一种生命认识,这种认识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变化中加深了对自我的国民身份的认同。在旅行中,游客凝视自己,也折射出“自己”所处的环境,个体的际遇也就有了“寻找民族自强与发展”的历史意境。1940年,喻血轮①赴陕、豫公干,恰逢其五十岁生日,因而倍加感慨:
今老矣!百事无成,际此风雪满天,复羁迟异地,中原未复,有家难归,缅念及此,不觉百感交集。
奉檄仓皇忽入川,巴山来去北泉边,
云橫铁马星辰动,月照尘沙骨血鲜。
离乱早乖黄鹄志,忧伤赖有细君怜。
荒村一住经三载,回首家园意惘然。
扑面寒风凛冽天,雪花飞舞马蹄前。
才从栈道穿秦岭,又逐征车到洛川。
半世漫游真厌倦,满腔心愿化云烟。
黄巾扫荡知何日?得赋归欤乐似仙。②
旅行的时空变化,加剧了个人的不安定感。在喻血轮对自身感慨的同时,其个人的际遇就自动放大为民族的命运的挫折。
(三)民族危亡下的风景叙事
段义孚认为,风景以及环境“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来源或者要适应的自然力量,也是安全和乐的源泉、寄予深厚情感和爱的所在,甚至也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重要渊源”。③原有空间被入侵者打破,是构建新的叙事空间的逻辑基础。一般而言,国族主义运动所采取的“自然国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的叙事策略,在这种模式下“国族将其历史、神话、记忆与‘国族特质投射于一块地理空间或特殊地景之上,从而将国族共同体与其特定疆域联系在一起,使后者转化为国族的‘家国。这种使国族疆域‘熟悉化(familiarized)的方式,所强调的面向,乃是国族历史与文化对土地空间的形塑与印刻(imprint)”。④
简要归纳来说,这种风景叙事发挥文化认同的手法主要有三种。⑤
其一是用风景意象唤起民族共同价值认同。
“尽千辛万苦,创造下这中华民族的锦绣山河,而今敌骑蹂躏华北,践踏中原,驰驱华南,连这黄帝坟陵所在的圣地,也已受到敌人炸弹的洗礼(按本年1月,曾有敌机轰炸过斯处,至发警报,则常有之)。进攻的威胁;现在的国人,追溯古史,静瞻现状,当是何等惶悚啊! 游陵后稍憩,继续进发,傍晚抵洛川。城与中部相若,被敌机轰炸之惨迹,历历在目。这里本来是后方的僻地;而敌机轰炸,也如其他大都市一样,敌人滥炸平民的丧心病狂,于此可见一斑。这情景使我想了去年5月末6月初敌机狂炸广州的悲惨!这是凶残的敌人给我们受的罪啊!我心头给愤恨刺激得隐隐作痛。”⑥这里,作者用“锦绣河山”“黄帝陵圣地”来唤起读者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日军空袭的愤怒。endprint
其二是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痛斥侵略者的暴行,喚起国民的同仇敌忾。
郁达夫在《感伤的行旅》中写道:“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⑦作者通过景物昨是今非的鲜明对比以及对被破坏的风景进行穿越千年的追思,以此来鼓舞国民团结一致共建理想中的国家。
作为旅行的交通工具,火车因随着国土丧失而沦落到敌手,作者用中国铁路的沦陷来展示国土的沦陷,又用“再坐着祖国的火车”形容自己回到祖国的怀抱之中,普通的铁路有了国家领土与版图的象征意义。游客林焕平在《再坐着祖国的火车》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再坐着祖国的火车/我的心有如/车头机器的轰动!/从香港,我没有坐/广九,粤汉/平汉车,过潼关/却经重庆,成都/过汉中,到宝鸡/东入西安!/车站旁,暗淡的灯光照着/如山的枕木/如丘的铁轨/无数车箱有如/巨兽躺在路轨上/它们标明着/平汉,平绥,粤汉,津浦/北宁,同蒲,沪杭甬/这一些我国的命脉/现正蠕动着恶毒的/兽骑,像爬虫!/车在轰隆,人在钻拥/深夜的寒风激荡起/乘客的愤恨/——乘客中有不少的/抗日英雄!——/脸部紧张的表情/宣示了他们的心誓/把失去的铁路干线/重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①
作者坐着“祖国的火车”心情激动的像“车头机器的轰动”,经“经重庆、成都、过汉中、到宝鸡,东入西安”,这一串的地名是中国内地的版图,暗示游客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国土丧失的“平汉,平绥,粤汉,津浦,北宁,同蒲,沪杭甬,这一些我国的命脉,现正蠕动着恶毒的兽骑,像爬虫”,日军的火车被贬称为“兽骑,爬虫”。“车在轰隆,人在钻拥,深夜的寒风激荡起乘客的愤恨——乘客中有不少的抗日英雄!——脸部紧张的表情宣示了他们的心誓”,机车的轰隆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铁路的收复也意味着国土的收复。因此,这种差异化、对比的叙事唤起的是同仇敌忾的气势,激励着更多的群众投入到抗战的事业中去。
其三是用风景的隐喻和比附重塑民族性格。
长城内外、白山黑水,这些风景不仅是国家的地理疆界,同时也见证着民族的历史、现在和将来,优美的风景成为民族美德和优秀价值观的体现。这类作品如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风景谈》等等。易君左认为“我们现代需要的国民精神、是热烈的情绪、兴奋的心理、和刚毅的意志”。“从龙灯、狮子、蚌壳精等涌现出的社会意识、无疑是民族的象征、无疑是国民精神的凝聚”,“以不怕死精神破国难”。②
作为为抗战前线的潼关,“象征了中华民族雄伟的气魄”。蒋经国在其游记《西北西南》中记载,因日寇占据潼关对岸的风陵渡,“不断的总从对岸用大炮来轰击,从上空用飞机来狂炸,其情形之凶,像是非把整个潼关生吞活剥地吃了不可”。“他们每于狂炸猛袭之后,总要硬着头皮来偷渡,结果除向黄河怒流白送上几只橡皮船之外,试看那‘高耸云霄、‘雄视山河的潼关,唐建五层高楼,不是始终在那里安然无恙‘远迈千古地使他们可望而不可即么?”所以,蒋经国赞叹道:“我看过中国许多的城市,从没有看到像潼关一样的雄壮,前面是黄河,后面是高山,它真是象征了中华民族雄伟的气魄。”③
在战争背景下,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风景”被赋予了民族之根本的特殊含义,承载着旅行者对寻找民族出路的各种想象。
(四)旅游与建国
在“河山破碎”的民族危亡之际,旅游更加激发了游客对国家的热爱。民国时期以提携交通、提倡旅行为宗旨的《旅行杂志》刊登过这样一段文字:考所以我们的见解,是要把国内名胜奥区,尽量阐扬其幽秘,考证其古迹,详计其道里,研求其民情,务使读者对于每一个地方,有深切之认识,油然而激发爱国之观念。故就表面看来,河山破碎何处游观,然而旅行杂志所贡献于读者的,是希望每个人于披读之余,注意到地理和人文所表现的事实,激发爱国之心情。④作者总结了“河山破碎”之际旅行的意义,由认识国家到热爱国家,这些都是在旅行中完成的。此外,一名叫黄伯樵的作者在《导游与爱国》力倡“使旅行者愈众,矜假而认识国家,爱护国家者愈众,而后国之‘基础赖以立,国之事业赖以振”。⑤发表于《旅行杂志》中的另一篇名为《游览建国》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了旅行之于国家的意义:
夫以吾国幅员之大,山川之富,世无与比,然舍东南数省外,大都地弃而不辟,货弃而不采,此国人只知闭门读书之大误也。总理遗教,首重建设,然不遍历各方,不知土地之肥脊,形势之险易,事业之宜与不宜;必也亲临游览,而后知有所轻重,有所取舍,有所先后,此实建国之一大助也。⑥
旅人在旅行过程中,通过他者的折射、对照与反思自我,眼中望去的世界反射了自身的希望与力量匮乏。旅行离开家园,身体的移动意味着跨越文化疆域,“人到了异地,会因为外在的景观而形成时空上文化差异的感受,对于异地、异国情调与当地的风土认清,产生吸收或自我改造的过程”。①旅行者面对残破的国家山河,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自我期许,进而将这种情感转化为“抗战建国”的热情和动力,完成了从旅行到建国的自我转化。而“正是这种富于流动性的空间(感)为个体或民族提供了与异质文化面对面的可能,进而塑造了现代人新的身份意识”。②
日军空袭对陇海铁路及西安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对游客的生命、旅行、游览都造成了威胁与影响,西安市当局也采取了多种防空措施,来保障民众的安全。但这种空袭并未使中国民众屈服,反而在饱览山河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家与民族文化的感情与体认,促进了全民族的抗战事业。
国家疆域内进行的旅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时代命题,而抗战时期的旅游者在陕西这片土地上进一步创造着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记忆。正如中旅总社社长潘恩霖在1943年出版的《西北行》中所总结的:“盖在今日而言旅行,如仅以遨游揽胜为事,已非社会所许可,必如顾亭林所言:有体国精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在抗战游记中,几乎所有旅客都打上了“体国经野之心”的烙印。③
【作者简介】杨博,长安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方向为区域社会史与区域文学。
【责任编辑:杨莲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