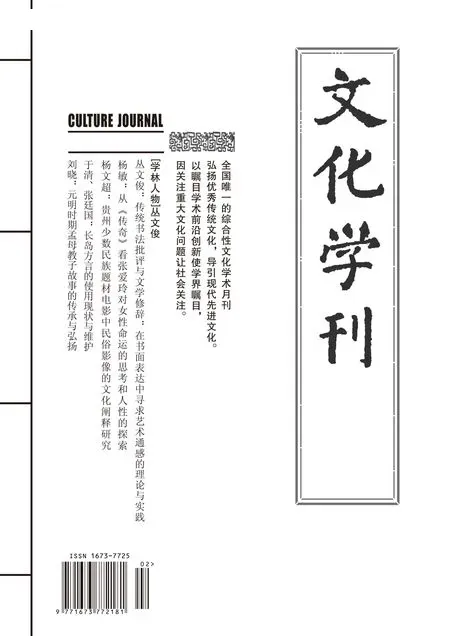原始宗教信仰在《阙特勤碑》中的痕迹
任仲夷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阙特勤碑,于1889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额尔浑河支流河谷和硕柴达木地方发现。该碑现在仍在原地。碑为大理石刻成,上刻汉文和古代突厥文两种文字语言。碑文为纪念第二突厥汗国重要人物阙特勤而立。碑高335厘米,东西宽132厘米,南北宽46厘米;古代突厥文共66行,刻在大、小两块石碑上,大碑(东面)写40行,小碑南北两面各写13行,应为碑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其余部分刻在碑的边上。背面(西面)为汉文部分,为唐玄宗开元20年(732)亲笔书写。古代突厥文部分由药利特勤书写。”[1]
一、对“天”的崇拜
“阙特勤碑南面:
我,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这时坐上了汗位。(南面第1行)
由于上天保佑,由于我自己有福分,我登基了。(南面第9行)
阙特勤碑东面:
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东面第1行)
上面是突厥的上天,下面是突厥的圣土。(东面第10行)
为了不使突厥民族毁灭,为了再建独立国家,他们簇拥着我的父汗颉跌利施可汗以及我母颉利毗伽可敦,高踞天顶,向上抬起。(东面第11行)
由于上天给予我父可汗力量,其军队像狼一般。(东面第12行)
由于上天保佑。(东面第15行)
为了使突厥人的名声不没落,上天使我父成为可汗,使我母成为可敦,赐予他们国家。(东面第25行)
上天保佑。(东面第29行)
阙特勤碑北面:
由于天地混乱成了敌人(北面第4行)
上天决定寿命。(北面第10行)
阙特勤碑东面:
在天上,活着/////(东面第1行)
阙特勤碑西南面:
我的官特勤向上天 ///碑石我写了。”[2]
在《阙特勤碑》中,“天”这个词语出现了15次,在较知名的突厥碑文中,如《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中,“天”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也是很高的,可见“天”一词对于人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文将“天”所表达的意义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人类。《阙特勤碑》东面第一行写到“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3],南面第一行“我,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这时坐上了汗位”[4]。与《阙特勤碑》同时同地发现的《毗伽可汗碑》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像天一样的,天作的突厥毗伽可汗”[5],天地之间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的生命也由天决定,并且上天赋予人以崇高的权力。第二,天能够赋予人无穷的力量。如,《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都有这样的语句:上天赋予了人类力量,我父亲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勇猛,敌人的军队像羊一样软弱,《毗伽可汗碑》中“乌古斯,敌人,由于上天的帮助,我们在那里把他们击溃了”[6]。第三,上天保佑。《阙特勤碑》中东面第15行,东面第29行,即“上天保佑”“由于上天保佑”。其实,关于上天保佑的这种说法,不仅存在于《阙特勤碑》中,在古代突厥的其他碑文中也有相关的叙述,如《铁尔痕碑》中“由于上面蓝天的保佑,下面褐色大地养育,我的国家和法制建立了,在我们的前面是日出之方的人们,在我们的背后是月升之方的人们,以及所有四方的人民都为我出力”[7]和“由于上天保佑和由于我的努力,突厥人民胜利了”[8]。也就是说,对天的这些表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以及当时其他的一些碑文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当时突厥人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及唐朝发生了很多战争,由于人们都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总是祈祷“天”的庇护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天”在突厥人的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天”能主宰人间的一切。在汉文的典籍中,记载古代突厥人崇拜天的史料较少,其对天的崇拜主要体现在祭祀活动中。如《周书·突厥传》载:“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9]古代突厥人祭拜天神,祈求风调雨顺,也是对天崇拜的一种表现。萨满教是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之一,其崇拜天。而突厥族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显然会受萨满教的影响,所以在《阙特勤碑》中出现崇拜天的这种信仰,就不足为奇了。
二、崇尚东方
古代突厥人崇尚“天”,自然也有崇拜日月的倾向。在辽阔的草原上,太阳从东方升起,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明。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驰骋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崇拜太阳,进而会崇尚太阳升起的方位—东方,“《阙特勤碑》碑文共66行,刻在大小两块石碑上,大碑(东面)写40行,小碑南北两面各写13行,应为碑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其余部分分别刻在碑的边上”[10],正面是向东的(即1-40行东面正文的部分)。一般来说,碑是立于祭祀宗庙的门口,碑的方向朝东,那么庙门的方向也是向东的。古代突厥人对东方很重视,在汉文的典籍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依据,如《周书·突厥传》中,“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11],这说明东方对于古代突厥人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其他少数民族文献中,如《乌古斯史诗》记载,乌古斯可汗举行盛大仪式时坐在东面。由此可见,突厥人也以东为尊。
三、颜色
“阙特勤骑拔野古的白马(东面第35行),

阙特勤骑白马进攻,杀死了六个人。(北面第5行)
第三次,我们在勃勒齐与乌古斯交战了,阙特勤骑白马进攻。(北6行)
骑白马ögsüz,刺杀了九人并守住了汉庭。(北面第9行)”[12]
我们知道,萨满教是游牧民族早期信仰的宗教之一,它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突厥人。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古代突厥人信仰萨满教,突厥人崇敬天,同时也崇敬天上的太阳,而太阳是白色的。由崇敬太阳,进而演变为崇拜白色,《阙特勤碑》中,主要记录了阙特勤个人的战功,阙特勤作为古代突厥人的领袖人物,多次选择以白色的马进攻敌人。在古代突厥人的意识形态中,白色象征着吉祥、光明和顺利。所以人们在战争中选择代表着吉祥颜色的马去作战,预示着吉祥、顺利。突厥之后,蒙古族入主了蒙古高原,成吉思汗的马也是白色的。此外,祭祀中,选择祭祀的牺牲是纯色的,最好是白色的,大概也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汉文典籍中记载有白龙马的故事,这主要还是因为“白马”在佛教中是最纯洁高贵的马,佛教在东传过程中,在我国建立的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白马寺。所以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白色都是人们崇尚和喜好的颜色。
四、数字
在《阙特勤碑》的碑文中,十三、十七和七百这样的数词出现的次数最多。如,
“我父可汗同十七人离开。(东面第12行)
听到外出的消息后,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人下来了,聚集起来是七十人。
由于上天赋予了力量,我父汗的战士们如狼一般,他们的敌人似绵羊。经过向着前方与后方的征战,他将人们召集起来,总共是七百人。(东面第13行)
他出征了四十七次,参加了二十次战斗(东面第15行)
他一共出征了二十五次,参加了十三次战斗(东面第18行)”[13]
中国古代,帝王封禅泰山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随着时间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封禅逐渐演变为祭祀,对巍峨高山的这种崇敬之情逐渐扩大到了民间,黎民百姓没有不知晓神山泰山的。此外,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三山”“五岳”“九山”“十山”等说法。《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14]由于人们对山川的崇拜,便有了“三山”“五岳”的说法,赋予了山川、河流等神秘色彩。同理,古代突厥人信仰萨满教,在萨满教的观念中,“三”和“七”这两个数字同样具有神秘色彩,并被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在突厥语民族当中,三被看作是具有强大巫术力量的数字。因此,民间谚语里说:好汉事不过三。在三兄弟故事里总是老大为恶,老三为善,老二或与老大为恶,或与老三从善,最后善要战胜恶,老三要战胜老大……认为三具有强大的巫术力,成为人们普遍的潜在社会心理意识。于是,凡诺言、誓言重复三遍不得反悔,并且才更有效力,而祝福、咒语重复三遍才更灵验。”[15]《阙特勤碑》中,多次出现了三、十三等词语。不仅如此,在古代突厥的其他碑文中,也能见到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古代突厥人将“三”看作是具有神秘力量的数字,而且他们不注重三之前的基数,对基数神秘化是从三的神秘化开始的。
古代突厥人对“七”这个数字也情有独钟,实质上是他们对天的崇拜。由于早期的人们无法对自然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在原始思维的作用之下,“七”成为了一个神秘的数字。同时,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古代突厥族,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将七与北斗星联系起来。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人们常常以北斗星作为参照物来确定方向。《阙特勤碑》中,与“七”相关的数字也出现了很多次,用这些数字记录战斗的次数,说明了阙特勤的英勇善战。总之,《阙特勤碑》文体现了突厥先民的原始信仰和原始文化。
综上所述,以上为原始宗信仰在《阙特勤碑》中的体现。原始宗教是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无论是早期的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蒙古族,原始宗教影响了他们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原始宗教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1][2][3][4][5][6][7][8][10][12][13]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15.115-137.121.116.149.161.208.162.115.123-125.148.
[9][11]岑仲勉.突厥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8.775.776.
[14]赵成.甲骨文与商代文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61.
[15]色音.中国萨满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