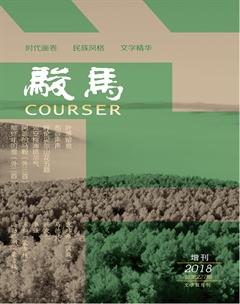那一年
吴俊
一
三十多年前,铁道南山坡遍地野花野草,恣意生长着白桦树、杨树和松树。再向南延伸着的是原生地,平时少有人来,夏季有人采野菜,秋天潮湿季节有人采蘑菇、土豆蘑、草蘑、白花脸、油蘑……到了冬天,这里便被铺天盖地的大雪紧紧覆盖,白茫茫的寂静。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王大生离开山东农村,只身一人跨越了半个中国,投奔他的叔叔,那时的牙克石还叫喜桂图旗,一批批人从天南海北投身林区,这片荒凉的土地成了一座宝矿,伐树加工成木材,冒着白烟的小火车,日夜兼程把木材从大山里运向天南海北。
大生在农村时才十六岁,大生的父亲跟他说,要不你去东北的叔叔那吧,那边日子好过些,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你去那边家里还能松松气,你从小有志气,到东北去闯荡闯荡,没准能过上好日子。父亲塞给了他五元钱,把地址写在一张破信封上,装了一袋子窝头,捆好行李,就把大生送上了车。
望着大生离去的背影,父亲的心沉沉的,这个爱穿白衬衣、叛逆的儿子,到了大山里能待得住吗?可留在这也早晚惹祸……
“叔,来这我能做什么?”
“半大小子,你爹养不起,倒扔我这,我可告诉你,我这一家子还吃不饱哪!”大生的叔叔,眯着眼吧嗒吧嗒吸着旱烟袋,蹲在土炉子边,升腾的烟雾笼罩着他,刚三十多岁的男人,倒像个小老头。
“你说让咱干啥就干啥。”大生硬硬地说。
“把行李放门斗里吧,出去把门口的柈子先劈两堆。”
大生推开屋门,把绳子捆的行李往角落一扔,向掌心吐了两口吐沫,搓了搓手就抡起斧子劈起木头来。没一会儿,头皮渍的汗就把头发洇得湿漉漉了,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冷空气中冒着热气。他大口喘着气,脸上都是白霜,抡起落下的斧子像上锈的开关,一顿一顿的。三天三夜的车程,把他载进大山里,出来时乡亲们都口耳相传的遍地金银的林区,转眼成了又一次遗落。
天色暗了下来,下起了鹅毛大雪。
王大生迈着疲软的步伐打开破毡布裹的门,门斗乌黑一片,凹凸不平的地面差点绊了他个跟头,屋里乌烟瘴气,叔叔王长力和几个面目不清的人围着炕头在打牌,吵吵嚷嚷,有人不时端起破茬的碗喝着酒。没有人看到他,他就站在墙边,屋里昏暗带着油腻的灯不会照到他,微小的他不会比一抹影子更清晰。他的肚子真是饿急了,摸索到水缸边,舀了一大舀子凉水,咕咚咕咚灌到肚子里,水带着冰碴,凉水让他清醒了许多,他轻步凑到叔叔身后。
“快打,母猪下崽哪!”
“哈哈,哈哈,随上一张。”
“长力,这狗崽子是谁家的,以前咋没见过?”
“老家讨饭来的,”接着哈哈笑了起来,“抠了,抠了……”“给钱给钱……”
王大生僵立在那里,脸憋得通红,刚清醒的头,顿时又被一股大旱烟的浓味熏晕了。他嗫声嗫语从嘴角挤出个“叔”字。根本没人听得见,一帮人依然嚷叫边打牌边说着乱七八遭的话,好像都很是兴奋,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拍着大腿懊悔……
不知过了多久,他真的饿得受不了了,肚子里像是千百条虫子在蠕动,掏得越来越空。
“叔,我饿了!”他终于鼓起勇气,大声说了出来。
长力像是突然发现身后冒出的声音,扭过头,往地上吐了口浓痰,“饿了,自己弄点去!”
王大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翻遍了碗架橱,好不容易找到了半个硬硬的窝头,吃完了,便蜷缩着身体,捂着疼痛的身体昏睡过去……
二
春天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季节,终于可以脱去棉衣服,整日到外面撒欢了。
南山積聚一冬的冰雪层层松软,厚厚的雪层挤压在一起松动着,沿着由南向北的坡度缓缓坍塌……阳光浓烈的晌午,雪面反射的光,闪得人眼睛生疼,仿佛拔根而起的生疼,风还很硬,冒出雪层的枯黄荒草在摇晃,裸露的石头不那么被冰包裹了。
屋子和小路隔着的木桥下开始有了水流。水流越来越大,天气也渐渐变暖。
滚滚涌来的流水,夹杂着冰屑和去冬的腐植,越来越大,淹没了坡道的土石,上升着,冲刷着,沿南山一股股欢腾冲涌过来。开始人们还欢欣地看这湍急的雪水,大生更是兴奋,大北方还有这好看的水流,比那村里的黄河支流有力量得多,耐看得多,没过几日,坎上坎下的人们开始慌了神,房屋都是依山而建,都是木土结构的板夹泥,能烧火度冬,可经不住这雪水的冲击呀……
长力叔也着急起来了,他妈的,咱们房靠着山,顶不住这山上的雪水这么撒野呀。大生子、带铃子、锈锁子……孩娃子们咱们都得上呀!趁着春暖,锹、镐、土篮子、推车子都出动,把房子围起来,把河沟子顺下去!
大生这下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像过狂欢节,把小伙子的蛮力都用出来,顺着河沟子能疏的就疏,烂泥巴下去掏,满街的人都热火朝天地干着,堆土的,捞堆木的,下石头的,从房里扬积水的……
大生成了主力,再没人呵斥他。他索性撒着性子,脱下衣服,光着膀子,东跑西撞,上窜下跳,谁也赶不上十六岁小伙子有精力。
在这一片混乱中,大生推着一独轮车石头往叔家去的街边,突然有个人扬着手大喊,快来呀,帮我一把,这发疯的臭水要冲进屋了,快来帮俺一下……大生闻声一转头,傻婆娘,还喊哪,那下势坡的地儿,大水要冲屋了,赶紧跑出来吧!
大生扔下独轮车冲了过去,“快呀,还不赶紧出来,水进了屋了!”说着拉着那人的手就往外走。
“你干嘛拉我,人跑了,屋里的东西咋整?”
“捡重要的拿,快点吧,山上水正往下涌哪!”
那人冲进屋,抢出个大盒子抱着,塞到大生手里,又往里冲,大生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硬生生往外拽,“水都没膝盖了,拿个啥子!”
大生把那女子拉到上坡,发现那不是个婆娘,瘦脸,瘦身,大大的眼睛跟他相仿,突然脸一阵热,撒开了手……后来,大生才知道她叫各多多,在离铁路车站不远的卫生所上班。
当山顶倾泻的雪水被遏制住的时候,大生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身满脸的泥巴,手脚也划了很多口子,但他感到酣畅淋漓,消耗掉的力气仿佛看得到摸得着。
黑色浑浊的流水在高垒的沟里急促地涌动,作为支流汇聚到扎敦河,这些枝枝蔓蔓的流水聚拢在一起,被大的河水冲洗干净,由东向西,滋润了大兴安岭的树木草地。
“大生,你真是把干活的好手呢!”王长力端着酒盅,吧嗒着嘴说。
“俺在村里也是能下地的哩。”
自从大生寄居到叔叔家,全家做饭、烧炉子、喂马、喂猪……这些零杂活都给了他,长力没完没了训斥他,干活没个样子,吃饭的时候总盯着碗。
“不是叔不给你找活,你才十多岁,山上的活都是吃力气的,采伐、倒小杆、装车,那操蛋的木头两个人都抱不过来,都成精了。”
王长力又滋溜喝了一口,美滋滋地吧唧下嘴,“知道咱吃这口饭多不容易了吗?”
“你老老实实把牲口养好,你叔下大力气才把这粮食挣回来……”
“今儿个挖河沟,疏导水,我看你还够机灵,肯下力气,明儿个捡煤跟着我去吧,也长长见识!”
大生答应了一声,但还不明白具体要做些啥。但长力叔今天的笑脸还是受用的,好像突然他也成了叔叔家的一员了……
三
大生没事的时候就坐在火车道边,看着车头冒着浓浓的白烟,硕大的车头轮子漆着鲜艳的大红汹涌转动,他感觉有种力量和激情,长长的黑铁皮车厢,一节连着一节,最多的数到六十九节,望着它们渐渐远去,直到消失,他心里慢慢地变空了。
车站旁有座小黄楼,年久失修,墙面斑驳着或白或灰的印记,门口玻璃遮着一块洗得很旧的白布,上面有个淡红的十字,这就是车站卫生所。
长力叔看着大生有力气,还机灵,就让他跟他晚上去捡煤,午夜时看站的打更人员困得厉害,那班运煤火车要在车站停留八分钟,附近的百姓就翻过围墙,去捡煤。火车掉落的煤块是有数的,很多机灵的就趁那几分钟爬上火车往下扔煤,底下的人往土篮子里装,越黑的晚上捡煤的人越多,车是黑的,煤是黑的,人影也是黑的,这时候战斗就开始了,这边捡煤,那边车站安防人员埋伏在暗处,哨声一响,捡煤的人作鸟兽散,接着喊叫声、哭声、骂声交响乐般在黑暗中响起。
捡煤是件危险又屡禁不绝的事,老百姓成功弄出一土篮子煤是了不得的,晚上压炉子有两块煤就够了,平时都是起夜压潮湿一点的柈子,烟大又不耐烧,这就意味着夜里总要挨冷受冻,有了煤就不一样了,可以过个暖融融的夜晚。所以,宁肯冒着被拘留被打,甚至摔坏、被打伤的危险也去捡煤。每年都有人坠车摔死,即使这样,捡煤还是人们重要的一项生计。
大生就这样光荣地成了捡煤队伍的成员,也是最小的爬车主力。在他看来爬车很简单,重要的就是手紧脚准速度快,农村时爬树爬得多了,爬火车似乎更拿手,因为树越往高爬树干越细晃动越剧烈,需要顶势平衡身体。开始捡煤时心里紧张,爬上去往下推大块的煤,在那八分钟就要完成上、推、下三个动作,还要躲开车厢下的安防人员的堵截,选择安全的点下地,之后就是逃跑。捡过几次煤就掌握了要领,大生开始不满足于这么简单的事,他开始尝试跨越车厢,从一节跳到另一节。脚下的煤块凹凸不平,他把小时走秃顶山峰的经验平移过来,跑跳时他听见风的声音,是那么悦耳,头顶上几颗星星对着他眨眼睛,最多时他在那个时间段跨越了十节火车厢。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等火车驶来没停就往上爬,启动后再往下跳,他要一种控制,一种超越,把看火车的惆怅感变为行走在火车上的实在感。
这一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晚,天气到了六月才暖和起来,阳光整日整日地照过来。
车站卫生所门口拴了一条长长的铁丝,上面挂着白床单、白被罩、白枕巾,各多多在门口坐着晒太阳,她是卫生所唯一的大夫,在那个年代卫生所就是土霉素片、四环素、青霉素针这样一些简单的药品,却承担着老百姓几乎所有疾病的治疗,包扎,打疫苗,注射,针灸,都要各多多一个人处理。
四
到了夏天,长力叔就结束了上山倒小杆的活计,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拉活儿,家里养的枣红骒马冬天上山干活累,每天都要拌麦麸子喂,即使这样也要瘦上两圈,春末夏初的时节,草地开始由黄转绿,就要到草甸子放马,天然的青草是最好的肥料,长力叔白天出马车拉沙子、黄土、石头等建筑用料,晚上回来就把骒马用长缰绳放到草甸子里。大生已经成为长力叔的得力助手,踏实认干,出车的时候大生就跟着装车、卸车。林区的生活带给大生不一样的感受,在农村家家都是种地种果园,务农的活比较固定,上东北来的在这里过活,主要是找活。
建筑工地活不多的时候,大生就去南山深些的地方打草,用大大的芟刀左手把住刀把前部,右手抓三角的把手,在没膝的草地沿圆弧形芟倒青草,等草晒干了,用草叉子把青草拢在一起,堆成草垛,用马车拉回长力叔家后院,堆成高高的草垛,儲存起来用作大骒马的过冬草。打草的季节,山里蚊子成灾,天再热也要穿厚厚的衣服裤子,头上要戴着蚊帽,大骒马只能用长尾巴甩打身上的蚊子和蠓虫,甩打不到的蚊子,肚子吸血撑得圆鼓鼓,几乎透明得要胀破。每次打草回来都是天黑了,大生躺在马车的草堆顶,浓浓的青草味儿包裹着他的身体,天空中布满锃亮的星星,随着马车的颠簸,整个星空也在晃动,长力叔坐在车辕子上悠着鞭子,“驾——驾”“喔——喔”,一路颠簸回到了家。
常年上山的,到了五六月份都要有很多人被草爬子咬到,这种虫子个头如米粒毒性却非常大,发现及时的用刀子剜出来,重的就会发热头痛,甚至会呼吸衰竭而死亡。大生在夏天打草时也被草爬子咬到了,长生叔急忙用刀子剜出那小虫子,疼得大生呲牙咧嘴,赶得马车飞快,往车站卫生所找各大夫瞧。
进了卫生所,就有一股浓重的来苏水味扑来,墙体下半部刷着绿油漆,上半部是白色,蓝色的木门擦得很干净,进到里间,看到几张病床,都是洁净的白色被褥床单,处置室里是一些瓶瓶罐罐,医用钳子镊子。大生还是头一次来卫生所,对一切都感到好奇,这里一点不像村医屋里那么脏乱。
“各大夫,各大夫,快帮大生子看看,他被草爬子咬了!”
这时各多多从诊室走出来,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
各多多认出了大生:“春天闹水灾那会儿,多亏了你哪!”
“应该的,不值一提的,各大夫。”
各多多仔细检查了草爬子咬的伤口,用体温计测了体温,“你们处理得还够及时,可是这土办法太野蛮,容易感染,现在我们可以碳化,再注射曾被草爬子咬过的患者的血清。”
“听长力叔说,林区这种小虫子特别厉害。”
“你的这种情况没事的,打几天消炎针吧。”各大夫很严肃地说。
“那还好,要把小命栽到这小虫子嘴下,那我可窝囊死了!”大生舒了一口气。
“跟我过来打针吧。”
大生跟在各多多身后,发现她长得真好看,声音也好听。
五
大生了解到各多多是八岁那年跟随母亲来林区的,母亲是教师,家里有本《赤脚医生手册》。多多带着好奇没事翻读,上海那边的亲戚看她喜欢医学,来林区给带了很多教科书和医学读物,那时林区还没有一所正式的卫生学校,她就自学,处理感冒发烧拉肚子这些病渐渐拿手起来,到了十六七岁,就成了铁道南百姓口中的小名医,得了病就到她那,多多说起来头头是道,用上药效果很好,到了十八岁时车站卫生所招人,那个年代还不讲究文凭,各多多报上名后,经过筛选居然成了正式的医生。
大生坐在椅子上输液,不忙的时候,多多就坐在窗下看书,上午的阳光从窗外扑进来,落在多多的身上、脸上,她是那么安静,像一支素净的水仙花。皮肤的纹理清晰如新、脸庞的曲线仿若定格的油画,大生看着,思绪飞到南山最深处的草原,看到多多穿着美丽的连衣裙,戴着挂着蝴蝶结的草帽,旋转、奔跑,脚下的青草擦过她光洁的脚踝,裙角与青草摩擦出细微的声响,阳光那么明亮,蓝得腻人的天空飘着淡淡的白云……
“发什么呆呢,让你看着输液瓶的液体,这都到底了!”多多拍了下大生的肩膀。
“我在想你看什么书这么认真,俺在农村听老人讲《三侠五义》,讲《三国》,我们娃子们围一圈,听也听不够哪。”大生说。
“我是在看医学书,你说那些我也懂些的。”多多边给换液体边问道,“你很喜欢读书吗?我这里有很多故事书的,你可以拿去看。”
“在农村上了三年学就下来种地了,只认识些简单的字,书在我们那很稀罕呢。”大生略做停顿,“我可能干活了,筛沙子、扛木头、打草样样在行的,还有捡煤,对捡煤,就是在你们卫生所东面停车场,有回被安保人员抓住,还被打了一顿。”
“你这么好的年龄,应该好好学点技术,要不总干那些力气活,一辈子都没出息。”多多说。
“我叔说要锻炼干各种活,什么活都能拿起来,就不会挨饿。”
各多多看着大生,明净阳光,身上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野味,虽然自己大他没几岁,可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自己被困居在小小的卫生所,脑袋里都是医学知识、治病救人,世上更多的事都在书本里知道。而跟大生交谈让她看到另外一种健康向上的奔波少年,虽然自己也是身在异乡,但生活是安定的,大生就像无根的浮萍,跟随着生活的洪流向前,他也许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但他热爱着自己的生活。
“是呀,只要肯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多多给大生拔了针,“记得明天还要来输消炎针,伤口那给你消毒包扎了,干活别把纱布弄掉感染了。”
“知道了,谢谢各大夫了。”
大生走出门口,还是那么恋恋不舍,她的声音好像还在耳畔,那么地亲切,一直传到心底。常听长力叔说见过大城市来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不一样,也许多多就是那种不一样吧。
六
这一天,大生跟叔去南山坡打石,就是用雷管炸开山坡,在碎石里挑选建筑工地所需的石头,这活有危险性,据长力叔说很挣钱的,一车符合要求的石头,收了能顶好几天干活的工钱。出发前,长力叔跟他讲要选从上到下往里凹的石头坡,雷管要伸进有大缝的石头里,雷管线要顺风布,点燃后要尽快逃离引爆点……这些让大生很是兴奋,爆炸声一定震耳欲聋,还没到地方,他就感觉耳朵里痒痒的,仿佛听到了震动的鸣响声了。
他们到了南山坡,把马车停在一千多米远的地方,拴好马,徒步选择爆破地方,那天风很大,两人都很激动,像揣个兔子似的,心蹦蹦跳,这是一件没干过的事,长力叔也是听别人讲过打石,有大生做助手,更壮了胆。按事先安排的要点布好雷管,开始爆破。大生看到长力叔手在抖动,就自告奋勇地要他来点线,长力叔让他一定小心,爆破点旁有三棵松树,整齐地排列着,风吹动着松针,呼呼地鸣响,“一、二、三,快跑!”大生点燃引线的一瞬间两人就拼命向远处逃跑,大生腿脚快,引线燃烧完的二十秒内,他已经跑出一百多米了,长力叔在他后面,他俩像被猛兽追赶的逃生者。荒芜的石头山坡在炸开,两个黑点缓缓离开一朵盛放的大烟花,巨大的爆炸声给定格的瞬间按下停止键。突然,長力叔被一块飞溅来的碎石击中腰部,发生的这一切大生根本不知道,当他停下大口大口喘息时,转身看到长力叔趴在地上背手按着腰“嗨呦嗨呦”叫,大生急忙向长力叔奔去,长力叔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大生背起长力叔,继续向前奔跑,到了马车处,卸下马车,骑马往回飞奔……
到了车站卫生所,各多多简单问了几句伤情,“可能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卫生所治不了,快去中心医院吧。”
长力叔后背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湿透了,到了医院几近昏迷,医院的骨科医生急忙给补血扩容抗休克,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腰椎做了手术,接下来是无尽的休养。
七
由于打石事件,长力叔不能再干重活,大生接替了他大部分的活计。
秋天到的时候,树叶枯黄,大片大片在呼啸的风里掉落,秋雨一场一场,浇凉了七九年铁道南这片灰暗的土地。
大生觉得很孤独,没有了长力叔整日对他粗口的训斥,没有长力叔带他去干很多没干过的活,他觉得干活是件很累的事,没有以前那么有趣。他还是会经常到各多多那里找她聊天,铁南火车站像风雨飘摇中的一个红色墙角,他可以躲一躲,蜷缩在那里安度一个夜晚……
秋天到了,叔家土房的裂缝没人修补,家里几个孩子还小,婶子连抱带背到南山去起土豆。秋天的风很大,她围着围巾,孩子们脸蛋被吹得像土豆,一层土一层皮的,可南山坡是孩子们的乐园。大人们在用三齿子、土篮子、耙子遛土豆的时候,他们钻进树林子里,踩着厚厚的松枝,漏洞的鞋子在软绵绵的松毯子上奔跑,松塔掉落都是大家抢夺的宝物,秋风吹动树林的声音就是孩子们梦的彩纱,有着波浪,有着屋顶的安身,待黄昏的晚霞剧烈地铺涌过来,透过树林缝隙照人的眼,那林中的小路也越发幽静深邃……这个时候大人们起的土豆也有三四袋子了,人们满身疲惫,大口喝着塑料壶里又温又浓的水,抖索著裤管里的泥土,看天空有三两飞鸟停落在树梢,忽的一声又飞远……
总有些往事如扎敦河的水在流淌,一百年前,四十年前,今天和明天,淌着,漫延着,不息,各多多也一样随着时代流逝着她的年轻时光,如满野的杜鹃花,不谢的车轮菊,河边的芦苇丛被吹成一片苍茫……
多多心里有大生。一如很多年以后还惦念着他,敦实的身体,黝黑的脸庞,像小兽一样为着生计在奔突。大生坐在卫生所的长凳上,斜叼着烟卷,穿着宽松的确良裤子,说晚上要掐架了,“多多,一道街那些王八蛋打了我们南山的小波,今晚八点我们就灭他们狗日的!”
多多嘴角一撇:“大生,别惹他们,那群孩子都是铁路的子弟,听姐的话,安份点吧!”
那年秋天的血斗就在他们说过不久,铁南的盲流军和铁路子弟兵在九月初五的晚上,在铁西道口火拼起来,大生领着三四十少年,抄着管锹、斧子、铁管、棍子……直捣一道街老铁的窝。那晚天黑风急,大生的胳膊和后背都起了鸡皮疙瘩,冻得腿有些抖,他奔跑着,喊着,跨过铁路口的闸口,带着人往一道街奔,他脸像燃烧着火,顶着风,不顾风割他的皮肤,有一种英勇、一种豪气,鼓动着他,拼死搏战的冲动盖住了一切,当老铁的帮派冲来时,棍棒声、砖头声、嚎哭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大生越战越勇,头被砖头呼上了,蹲下缓一缓,抹一抹血,拎起铁棒子就是抡……
当大生再次清醒时,已经躺在车站卫生所洁白的床上,他睁开眼,阳光刺过来,紧接着闭上,多多拉着他的手,“你觉得这样很好吗?”
“大生,一个男人出人头地是骨气,拼命也对……”
“我希望你好,别这样狼狈地做个战后英雄……”
大生脸和头脚缠着纱布,嘴动了动,没说出什么,紧攥住多多的手……
八
很快冬天就到了,刮起了白毛雪,铺天盖地,埋没了这个世界。
清晨,大生用力推开没了半截门的堆雪,刺眼的光折射过来,他趟了几步,没膝雪层塌了一层,边沿掉落,杖子处雪层层若白塔,他要奔跑,冲开这操蛋的世界,如茧包裹的生活。跑了几步,就狗屎般趴在雪壳子里,满脸锥子般地刺疼,十七岁,多想就这么大口地吃掉身边的雪,让这喜桂图旗的大雪把自己埋葬啊……
多多摊开一本书,透过窗子暖洋洋的光打到她的手臂上,外面封锁世界的大雪如一副画,她内心丰盈又空洞……九
喜桂图旗,这是个很怪但又好听的名字。
很多年以后,大生扎根在这里,同这片林区大地一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会记忆犹新地想起最初的那些往事。
二〇一三年棚户区改造,大生顺利拆迁了房屋和土地,得到的补偿款给儿子王源在呼伦贝尔买了房和车,儿子王源是一名优秀的画家;多多早在一九八四年就离开了牙克石。多多的女儿各一一出落得如出水芙蓉,王源和一一曾同届在俄语班读书。
各一一在二〇一七年春节来到牙克石寻找一个叫王大生的人,大生躺在肿瘤科病床做着化疗,相隔了三十年,其实只有那些年的往事才是真实的,至于以后宁愿成为永远的未知,如大生和多多,一一和源。
已经不再存在的喜桂图旗,在这一年春天的铁道南环城公园,有无数的青草转暖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