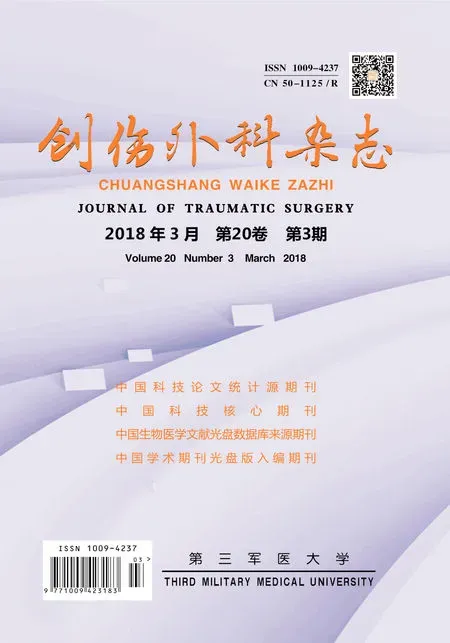道路交通伤的概况与救治现状
尹 文,李俊杰
自1896 年,伦敦发生第一例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病例以来,全球至今已有超过3 00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伤(road traffic injury,RTI)[1],造成无数家庭和人生悲剧,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重要不安全因素。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20万人因道路交通伤死亡,2 000万~3 000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2],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随着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建设以及汽车保有量的飞速增长,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始终在较高水平,由此导致道路交通伤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病死率较高。统计表明,2015年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87 800起,造成58 000人死亡,199 90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5亿[3],道路交通伤已经取代自杀成为我国伤害死亡的第一位原因[4]。
1 道路交通伤的主要特点
1.1高速公路交通伤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高速公路的开放里程迅猛增加,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高速公路作为中、长途出行的主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为380公里;而至2015年,这个数字已变为12.54万公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最长的国家[5]。但同时,本应与快速增长的高速公路里程相对应的道路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下的预防、急救措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较为滞后,存在严重的漏洞和缺陷,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不断出现,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7]。国内外的分析均表明,尽管高速公路上所发生的事故总数低于普通道路事故总数,但从事故死亡率、里程死亡率和里程受伤率来看,高速公路交通伤显著高于普通道路交通伤[8-10]。杨东等[3]分析2004—2015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发现高速公路里程死亡率为普通道路的4.51倍,事故死亡率为普通道路的2.21倍;每起事故直接财产损失约为普通道路的10倍,交通伤死亡率为普通道路的1.64倍。高速公路较普通道路发生死亡的相对危险度为1.97。唐斌等[11]统计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导致的器官或组织损伤发生率依次为头部创伤(38.27%)、四肢创伤(23.17%)、胸部创伤(15.26%)、软组织损伤(8.35%)、多发伤(4.15%)。宋斌等[12]报道某地级市2007—2011年共发生高速公路交通事故94起,伤员167人,死亡39人,死亡率高达23.35%;主要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并发脑疝,在救治途中或到医院时由于病情严重失去紧急手术机会;其次为胸腹联合伤。这些致死原因均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高速度、高能量特点有关[13]。总体上,高速公路交通伤具有以下特点:(1)突发性强,群伤、群死发生率高;(2)发生地点往往远离城市,及时救治的难度大;(3)重伤和危重伤的比例高,伤情严重且复杂;(4)重型颅脑损伤发生率高,造成死亡率较高。
1.2普通道路交通伤 与高速公路交通伤相比,普通道路交通伤的特点是:(1)多为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引发交通事故所致;(2)电动车、摩托车等骑乘人员所占比例较高;(3) 轻、中度伤所占比例高,但颅脑损伤仍是导致伤员死亡的主要病因。造成普通交通事故的原因很多,但酒后驾车是造成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14-16],尤其是恶性事故,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普通道路交通伤主要是撞击伤、车轮碾压伤和挤压伤。发达国家多以车与车的相撞多见,常常导致驾乘人员的颅脑和胸部创伤[17- 18]。但中、低收入国家因摩托车的使用较为普遍,常造成人与高速行驶的机动车相撞或因本身车速太快而与道路上的固定物体相碰撞,故四肢与颅脑创伤更为常见,其最典型的致死方式为头部碰撞到坚硬地面,造成严重的颅骨骨折和颅脑损伤[19]。特别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通工具,电动摩托车在我国城市里的保有量迅猛增加,而由于电动摩托车的不安全驾驶造成很多普通道路交通伤[20- 21]。2014年,全国范围内交通事故造成死亡67 759人,其中因驾驶电动摩托车死亡3 872例[22]。陈卫云和郭君[23]报道某市三甲医院收治的4 836例交通伤中,电动车造成交通事故751例,占15.53%;损伤部位的前两位是下肢和颅脑,分别占30.22%和26.63%,但颅脑损伤的死亡病例占总死亡病例数的91.3%。李莉等[24]对493例电动车碰撞交通事故的分析表明,驾驶员严重和致命颅脑损伤达50%;颅脑损伤是造成电动摩托车驾驶员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使用头盔是电动车驾驶员最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合格的头盔可吸收部分碰撞能量,从而减少颅脑损伤。有研究表明,佩戴安全头盔可使普通道路交通伤导致的死亡和严重颅脑损伤分别减少40%和70%[25- 26]。
2 道路交通伤的救治
影响道路交通伤救治效果的主要因素是院前反应时间、现场急救、中途转运、急诊急救的时间长短[27]。因此,在最短时间内对伤员进行正确、及时、有效的救治,是提高道路交通伤抢救成功率的主要策略[28]。
2.1建立联动合作型院前急救模式,提高现场救治成功率 传统的院前急救服务模式强调在现场紧急处理后尽快把伤员安全转运到医院再进行有效治疗,即“将伤员带到医院”。随着现代急救技术和观念的发展,目前更强调医院抢救小组尽快到达现场,在现场对伤员进行救治,然后再转运到医院继续治疗的模式,就是“将医院带给现场的伤员”。这种急救服务模式的转变,无疑更符合交通伤尤其是高速公路交通伤的救治要求,但这需要卫生机构与非卫生机构如交警、路政等部门共同合作,建立高效的急救调度网络,将医疗急救资源前置,建立联动合作型院前急救模式[29]。在接到交通事故的呼救后,医护人员与交警、路政管理人员组成救援小队赶到事故现场,根据伤员的损伤部位、损伤类型、伤情严重程度及事故现场条件等进行准确伤情评估并展开现场救治,快速完成伤情分类及初步急救后迅速转入后送过程中。这种联动合作型院前急救模式与传统急救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1)将急救点前推至急救最前沿,确保院前急救的时效性,使交通伤的总死亡率明显降低,救治时间大幅缩短;(2)以交通信息为主要来源,使急救信息能够及时抵达急救中心;(3)医疗急救、交警、路政业务的相互交叉,有利于快速消除交通道路事故的负面影响。
2.2快速到达事故现场 交通事故发生后,急救人员快速到达事故现场展开急救,是减少死亡和伤残率、提高救治效果的关键第一步。但我国的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环境,且双向的车道基本被中央隔离带隔离,故发生交通事故后,极易造成交通中断并堵塞应急车道,导致急救人员难以及时到达现场,伤员难以获得有效救治。城市里的普通道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也经常处于拥堵状态,造成地面救援难以及时到达。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航空医疗救援已成为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面救援相比,空中急救转运伤员速度快且机动灵活,不受地面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大大地缩短了院前急救患者的转运时间,使危重症患者能及时接受到有效治疗,增加患者的生存概率[30]。2008年汶川地震后,构建以直升机为支撑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已成为国家、军队和各界学者的主流意见和共识,我国的立体救援救护体系正在成型[31]。在此背景下,笔者所在的医院自2014年10月开通了“空中紧急医疗救援通道”,成立了国内首支成建制专业飞行医疗队,利用医疗救援直升机完成数十例的紧急救援任务,其中包括国内首次直升机现场救援、首次高速公路休息站救援等,抢救成功率高达100%,满足了当地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效率医疗急救服务的要求。不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情况看,“使用直升机参与应急救援,形成立体救援体系”的理念,已逐步成为快速反应、快速处置突发事故灾难及紧急情况、有效实施医疗救助的一个重要选择和发展趋势,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例如,德国的空中急救在组织和管理上被认为是当代世界最有成效者,其交通伤院前急救工作已覆盖全国;在事故发生后的10~30min,医疗救援人员即可赶到现场[32]。这种迅速的院前急救模式可为交通伤伤员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
2.3快速判断伤情,正确进行检伤分类 交通事故发生时,由于伤员受到撞击、冲击、碾压、挤压等高速的机械打击,常造成多脏器的损伤或复合伤,伤情复杂。同时,较大规模的交通事故往往在同一时间点造成大量伤员,此时正确判断伤情、对伤员进行分类,把有限的急救资源用于最需要急救的伤员,对提高救治整体效果极为关键。一般来说,治疗时常把伤员的伤情分为四大类:第一级伤员用红色表示,是最需要抢救、最有抢救价值的伤员;第二级为延后治疗伤员,用黄色表示,这类伤员需要得到恰当的治疗,但是应该排到第二位;第三级伤员用绿色表示,是轻伤,只需要轻微治疗无需紧急救治;最后一级伤员用黑色表示,表明其情况极其严重,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简明损伤定级标准(abbreviated injury scale,AIS)也是交通事故现场判断伤情严重程度的常用方法。AIS 是以解剖损伤为依据的损伤严重度定级法,其优势在于按照解剖位置和局部损伤情况,对每一处创伤都进行准确评分,其严重程度分为1~6分;1分为轻微损伤,而6 分为严重或致命性损伤。损伤严重度评分法(injury severity score,ISS)是以AIS为基础的多发伤损伤严重度定级法。ISS值为3个最严重损伤部位AIS值的平方和,当ISS评分>15分时,即为严重损伤。Pfeifer 等[33]分析了227例因道路交通伤致死的伤员,其中40.5%的伤员ISS得分达到75分,且头部和胸部创伤患者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部位受伤的患者。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医院提出“Triage-RTS”评分方法,将伤情按严重程度分为0~12分,而得分越高,伤员的预后越好[34]。此评分方法更适用于院前对患者伤情的评估,目前在国外得到广泛应用。而法国里昂大学的Sartorius等[35]综合致伤机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年龄和动脉血压四方面因素,创建了创伤患者的MGAP评分方法。23~29分为轻度创伤,18~22 分为中度创伤,<18分为重度创伤。经多中心大样本量的临床试验验证(样本量1 003例),轻度、中度和重度创伤人群的住院死亡率分为2.8%、15% 和48%,提示该方法在损伤程度和预后判断中有较高应用价值。
2.4积极开展现场急救,做好后送工作 挽救伤员生命是现场急救的首位工作,其次是尽可能保存损伤的组织与器官,为随后的院内救治及进一步的功能恢复治疗提供条件和基础。现场急救的工作主要包括心肺复苏和保持气道通畅,提高有效的呼吸和循环功能,另外还包括控制外出血、保护受伤的脊柱和固定骨折等。
窒息是交通事故中导致伤员现场死亡的常见原因,故现场急救的第一步工作是恢复并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首先,及时移走压在伤员身上的物品,去除口腔、面部、胸腔及腹腔的外在压力,恢复伤员自由呼吸。其次,对神志清醒的伤员,嘱其保持半卧位;意识丧失的伤员,应使其稳定侧卧位,可有效避免因呕吐物或血液造成的呼吸道堵塞。随后,全面检查并彻底清理口鼻中的血液、异物等,取出活动假牙,必要时可插入口咽管,保持气流进出顺畅。对明显呼吸功能障碍的患者,应立即给予呼吸支持,如人工呼吸、供氧等,有条件的可实施气管插管并机械通气。
交通伤造成肢体或内脏损伤往往伴随较为严重的活动性出血,造成失血性休克,这也是伤员现场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针对失血要立即采取紧急的止血措施,这是现场急救的关键措施之一。首先明确出血部位并禁止伤员活动,避免加速失血。其次,对于头面部出血,可采取加压包扎止血;对于肢体出血,可采用加压包扎或止血带,但需清晰标记开始使用止血带的时间。对于内脏出血的伤员,应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转运至医院,力争为院内抢救赢得“黄金时间”。严重创伤患者若在入院前得不到及时、有效挽救生命的措施和迅速转运,则往往死于事故现场或转运途中。
快速判断伤情、正确分类后,及时选择重伤员并决定运送顺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患者安全转送至医院以进行有效救治。转运过程中应严密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和生命体征,及时建立静脉输液和供氧通道,尽最大努力维持伤员生命体征的稳定。及时发现并处理创面出血,注意加压包扎或使用止血带的肢体的末梢血液循环。怀疑颈椎损伤的伤员使用颈托,并保持头部与躯干长轴一致,避免头颈部活动。注意保持各种治疗管道的通畅,避免输液管、氧气管受压、堵塞等。
2.5及时进行院内救治,构建规范化创伤救治模式 尽管院前救治在道路交通伤急救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就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城市的发展现状来看,院前救治受交通状况、现场环境、技术装备等因素限制,因而交通伤诊治的重点还在于提高院内救治水平。但严重交通伤救治涉及多学科的协作与配合,这与现代医学的专科化趋势有明显矛盾。因此,建立高效的急救团队,集中收治交通伤,才能避免分诊式救治模式下的各种弊端,如救治时效性差、缺乏整体观念、互相推诿等。通过组建以急诊科、骨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普通外科、ICU、麻醉科等医师为主要成员的创伤急救团队,在院内实施一体化创伤救治模式,规范院内救治路径,减少创伤患者因过多会诊导致院内救治中不必要的延误,以提高创伤救治效率。
与院前救治相同,时间仍然是院内救治最关键的指标。在保证准确诊断的前提下,伤员从到达急诊室到进入手术室的时间越短,其术后生存情况越好。如胸部创伤引起严重血气胸或心脏压塞危及生命时,应在数分钟内做出判断并立即进行引流,而不是先行X线或CT检查。躯干大动脉的损伤,应在数分钟到数十分钟内做出判断,以及时进行手术治疗,挽救生命。腹部空腔脏器损伤时,应在数小时内确诊病情,而后急诊手术,避免腹腔内严重的弥漫性感染。同时,在对创伤患者的医疗及护理过程中注重早期心理干预,以减少创伤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患者伤后进行X线和CT检查的比例较低[36]。分析其原因,除了疾病谱的差异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国部分急诊医务人员在接诊道路交通伤患者时多按照经验思维来评估病情,尤其是对表现为轻度损伤的患者仅通过简单的检体诊断即做出伤情判断和处理措施,没能严格按照诊治标准和规范对患者伤情进行客观的动态评估,而这种情况往往导致误诊和漏诊。因此,合理、规范应用影像学检查是院内救治的重要工作内容。
3 结束语
我国交通建设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可以预期未来较长时间内交通事故发生率还将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地开展交通伤伤员的急救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交通伤的死亡率和伤残率,成为全社会和医学领域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加强该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制定科学的防范措施,建立科学的创伤急救模式,提供快速、有效的规范化救治,有效提高交通伤救治成功率,才能达到“挽救生命,减少伤残”的目的。
[1] Rissanen R,Berg HY,Hasselberg M.Quality of life following road traffic injury: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Accid Anal Prev,2017,108:308-320.
[2] Staton C,Vissoci J,Gong E,et al.Road 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 initiativ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summary of effectivenes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J].PLoS One,2016,11(1):e0144971.
[3] 杨东,张岫竹,张彦琦,等.2004-2015年中国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交通伤对比研究[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7,39(6):589-596.
[4] 汤中飞,李兵,阮海林,等.规范化救治模式在严重交通伤救治中的应用[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2016,4(4):186-189.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5年度)[EB/OL].http: //www.Stats.gov.cn/tjsj/ndsj/.
[6] Stewart BT,Yankson IK,Afukaar F,et al.Road traffic and other unintentional injuries among traveler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J].Med Clin North(Am),2016,100(2):331-343.
[7] Araujo M,Illanes E,Chapman E,et al.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motorcycle injuries: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Int J Inj Contr Saf Promot,2017,24(3):406-422.
[8] Charters KE,Gabbe BJ,Mitra B.Population incidence of pedestrian traffic injury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J].Injury,2017,48(7):1331-1338.
[9] Zeng Q,Wen H,Huang H,et al.A multivariate random-parameters Tobit model for analyzing highway crash rates by injury severity[J].Accid Anal Prev,2017,99(Pt A):184-191.
[10] Wada T,Nakahara S,Bounta B,et al.Road traffic injury among child motorcyclists in Vientiane Capital,Lao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using a hospital-based injury surveillance database[J].Int J Inj Contr Saf Promot,2017,24(2):152-157.
[11] 唐斌,王玲,廖晓斌,等.高速公路急救住院伤员损伤构成比调查分析[J].西南国防医药,2014,24(4):463-464.
[12] 宋斌,王怀云,王剑火.某地区高速公路交通伤流行病学分析[J].东南国防医药,2012,14(4):308-310.
[13] Hao W,Kamga C,Daniel J.The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on motor vehicle driver injury severity at highway-rail grade cross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J].J Safety Resm,2015,55:105-113.
[14] Yu W,Chen H,Lv Y,et al.Comparis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outcomes of single and multiple road traffic injuries: a regional study in Shanghai,China (2011-2014)[J].PLoS One,2017,12(5):e0176907.
[15] Craig A,Elbers NA,Jagnoor J,et al.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raffic injuries sustained in a road crash by bicyclists: a prospective study[J].Traffic Inj Prev,2017,18(3):273-280.
[16] Borges G,Monteiro M,Cherpitel CJ,et al.Alcohol and road traffic inju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case-crossover study[J].Alcohol Clin Exp Res,2017,41(10):1731-1737.
[17] Silver D,Macinko J,Bae JY,et al.Variation in U.S.traffic safety policy environments and motor vehicle fatalities 1980-2010[J].Public Health,2013,127(12):1117-1125.
[18] Heron-Delaney M,Warren J,Kenardy JA.Predictors of non-return to work 2 years post-injury in road traffic crash survivors: results from the UQ SuPPORT study[J].Injury,2017,48(6):1120-1128.
[19] Li Y,Zhou J,Chen F,et al.Epidemiology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older inpatients in Chinese military hospitals,2001-2007[J].J Clin Neurosci,2017,44:107-113.
[20] Ding Y,Zhou J,Yang J,et al.Demographic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oad traffic injury deaths in Jiangsu Province,China[J].J Public Health(Oxf),2017,39(3):e79-87.
[21] Rockett IRH,Jiang S,Yang Q,et al.Prevalence and regional correlates of road traffic injury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a 21-city population-based study[J].Traffic Inj Prev,2017,18(6):623-630.
[22] 胡沣,方健.电动车道路伤害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进展[J].安徽医药,2014,35(2):243-246.
[23] 陈卫云,郭君.电动自行车相关交通伤的特点分析[J].浙江创伤外科,2013,18(2):157-159.
[24] 李莉,杨济匡,Dietmar O.长沙地区电动自行车碰撞事故研究[C]/ /第九届国际汽车交通安全论坛.长沙:湖南大学,2011:219-225.
[25] Gupta S,Klaric K,Sam N,et al.Impact of helmet use 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from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Cambodia[J].Traffic Inj Prev,2018,19(1):66-70.
[26] Singleton MD.Differential protective effects of motorcycle helmets against head injury[J].Traffic Inj Prev,2017,18(4):387-392.
[27] Ernstberger A,Joeris A,Daigl M,et al.Decrease of morbidity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a high income country - an analysis of 24,405 accidents in a 21 year period[J].Injury,2015,46(S4):S135-143.
[28] Page Y,Cuny S,Hermitte T,et al.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frequency and the severity of injuries sustained by car occupants and subsequent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injury prevention[J].Ann Adv Automot Med,2012,56:165-174.
[29] Aduayi OS,Aduayi VA,Komolafe EO.Patterns of pre-hospital events and management of motorcycle-related injuries in a tropical setting[J].Int J Inj Contr Saf Promot,2017,24(3):382-387.
[30] 袁家乐,周开园,任杰,等.外军直升机医疗救援队伍建设对我军的启示[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16,23(4):399-400.
[31] 谢雷星,欧阳亚迪,周登峰,等.直升机紧急救援服务(HEMS)在保健工作中的应用与思考[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17,19(1):74-75.
[32] Andruszkow H,Hildebrand F,Lefering R,et al.Ten years of helicopte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in Germany: do we still need the helicopter rescue in multiple traumatised patients[J].Injury,2014,45(S3):S53-58.
[33] Pfeifer R,Schick S,Holzmann C,et al.Analysis of injury and mortality patterns in deceased patients with road traffic injuries: an autopsy study[J].World J Surg,2017,41(12):3111-3119.
[34] Raux M,Thicoipe M,Wiel E,et al.Comparison of respiratory rate and peripheral oxygen saturation to assess severity in trauma patients[J].Intensive Care Med,2006,32(3):405-412.
[35] Sartorius D,Le Manach Y,David JS,et al.Mechanism,glasgow coma scale,age,and arterial pressure (MGAP): a new simple prehospital triage score to predict mortality in trauma patients[J].Crit Care Med,2010,38(3):831-837.
[36] 涂建锋,张可,周晟昂,等.中美急诊道路交通伤患者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5,18(26):3223-3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