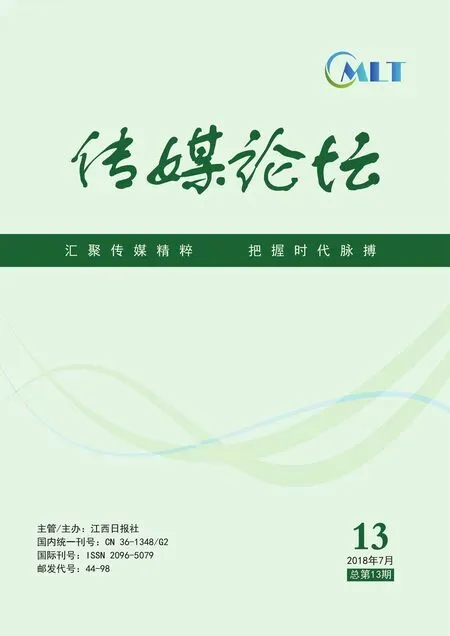论新生代小城镇电影的空间叙事差异
(浙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开始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生代导演的主要以本土小城镇为叙事空间的电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和《秘语十七小时》,贾樟柯导演的《小武》《站台》《任逍遥》和《三峡好人》,王小帅导演的《二弟》《青红》和《我11》,李扬导演的《盲井》,张扬导演的《向日葵》以及陆川导演的《寻枪》等作品。这些小城镇电影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的《小城之春》、张艺谋的《活着》和《山楂树之恋》,以及顾长卫所导演的《孔雀》和《立春》等小城镇电影,虽然两者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小城镇作为影片背景和叙事空间,但在空间叙事上还是有着诸多不同。而且,不仅第五代导演和新生代导演的小城镇电影存在着空间叙事转向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90年代以来出现的小城镇电影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还会发现即使在这些新生代导演的小城镇电影中,其在空间叙事结构、空间叙事视角及空间叙事形态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本文接下来主要以李扬的《盲井》(2003)、贾樟柯的《三峡好人》(2006)和张猛的《钢的琴》(2010)为例,探讨新生代电影导演如何通过不同空间叙事策略描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小城镇生活,并呈现他们的电影叙事美学观念。
一、空间叙事结构的差异
在导演李扬的《盲井》里,第五代导演的传统历时性空间叙事模式很好地被继承下来。电影完全没有使用插叙、倒叙、闪回、闪前等时空转换技巧,也没有设置或明或暗的多条叙事线索,空间叙事基本就是按照一条“杀人、索赔”的直线来进行。没有多余的废话和多余的段落,一环扣着一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电影整个都是在一个极为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中讲述故事,尊重现实的发展线路,不做过多的主观剪切和人为安排,以图再现事件在现实状态下自身的连续性。不过,与第五代导演的封闭式空间叙事结构不同,李扬的《盲井》的结尾却是开放性的:元凤鸣并没有像小说的结尾那样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放弃赔偿金并独自回乡,而是从矿主那接过了抚恤金。单纯的少年会不会从此以后成为第二个宋金明或唐朝阳,从“受害者”一方转向“作恶者”?影片到此戛然而止,没有交代。
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里,传统的历时性戏剧叙事模式被舍弃,整体性、连贯性、因果性的叙事结构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情节不连贯的空间叙事模式。《三峡好人》分别讲述了矿工韩三明和护士沈红到三峡库区奉节县“找人”的两段故事。为了更大范围呈现三峡拆迁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导演贾樟柯在空间叙事方式上没有采用历时性戏剧叙事模式来强化戏剧性冲突和推进情节发展,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与纷繁的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多重杂糅的叙事结构,这种不为因果,按照人物故事的空间顺序安排情节发展的多重叙事模式,能够很好地保持两条线索各自的叙述张力和阐释空间,以此呈现日常生活的偶然性、无序性和复杂性。
而张猛导演的《钢的琴》与《三峡好人》不一样,尽管影片和《三峡好人》都有一个较为沉重和庞大的背景,但是在叙事上其实采用的是一个常见的有明显连贯性的线性叙事结构模式,即以陈桂林为核心角色,融入进其他配角,来共同实现制造一架钢琴的任务。《钢的琴》的空间环境有两大块,一块是已经变成废墟的工厂,另一块就是生活区,但由于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生活设施很齐全,包括职工宿舍、猪圈、发廊、棋牌室、路边摊、俱乐部等。所以电影的空间叙事都是在钢铁厂里完成的。这一点与《盲井》一样,电影也在一个极为封闭的线性空间叙事结构中讲述故事的。
不过,与《盲井》不同的是,影片在空间叙事上有时游离开来,会节外生枝插入一些虚幻空间,如陈桂林邀约一群穷哥们开着屠宰车去偷琴,在偷琴不成却被发现,其他人都翻墙逃跑好不狼狈的这个段落。漫天雪花中,陈桂林正襟危坐地在琴前弹琴,这时周围的光线全部暗下,只有一束聚光灯打在他身上。这个虚幻场景的插入,将陈桂林的失意与梦想表现得淋漓极致。再比如钢的“琴”制作完成后,在破败的厂房里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超现实场景:一座仪式感很强的舞台,工人们在这舞台上自娱自乐,小乐队演奏斗牛士之歌,淑娴领衔西班牙舞蹈等等。造琴行动到这里竟变成了一个盛大的庆典,非常虚幻不真实。类似的还有电影开头,陈桂林和他的伙伴在葬礼上演奏《三套车》。这时候电影的前景是死者的祭坛,而后景却是象征工业化时代的两根大烟囱。在哀悼工人阶级丧失主人翁地位后,电影接下来很快就用一种调侃、诙谐的调子冲淡了之前的感伤和怀旧。在遭到家属抗议《三套车》曲子太沉重之后,陈桂林他们立马换了《步步高》激昂乐观的曲子。没有沉湎于声色俱厉的悲情和控诉,影片时不时流露出的幽默、温情的以及非现实空间的狂欢叙事,为电影《钢的琴》增加了浪漫和乐观的基调,而不是像《盲井》那样一味地沉浸在悲情和控诉中。
二、空间叙事视角的差异
不同的电影的空间叙事的处理上还存在一个视角选择的问题,即影片对故事进行讲述和审视的角度,这主要体现在镜头的设置和叙事空间的选择与重组上。在新生代导演的小城镇电影里,《盲井》《三峡好人》和《钢的琴》在空间叙事视角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
李扬的《盲井》,采用的是全知无限制视角特征来叙述故事。影片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提前知道了骗子唐朝阳和宋金明的发家致富的套路,那就是先套近乎,将打工无门的农民工骗作亲人,然后将他们带到煤矿做工,接着一起在井下工作时故意制造“安全事故”,把这些骗来的农民工弄死,最后找矿主要求私了来骗钱。由于影片开始已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杀人、赔偿”的唐朝阳和宋金明的作案套路,所以,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就成为套路的重演而已,虽然中间添加的令人意外的转折使观众产生了一些预期受挫感,但观众还是可以预见即将“重演”的结局的。
另外,影片《盲井》在处理人物时,一种是采用大全景甚至远全景的拍摄,把人物置身于车站广场或荒凉的矿区荒山里,让人物在社会生活中和自然环境下都处于非常渺小局促的状态。比如,矿工们相继从平房出来向山坡上的管理房走去的一个场景,电影在这里不惜使用半分以上的长镜头来拍摄这个场景,并使用全景拍摄加平摇的运动方式,来集中呈现矿工冗长的、乏味的直线式生活以及简陋、肮脏、单调的煤矿环境。另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近景,通过镜头直逼人物的脸部,放大角色每一丝卑劣的迹象或内心的挣扎。这种通过摄影机对叙事视角的参与在电影《盲井》中是比较明显和突出的,镜头语言所指涉的各种言外之意非常直接地呈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观众对人物的评判。
而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里,影片却是以当事人的限制视角来叙述故事的。故事情节发展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观众大都是未知和隐蔽的。从电影的情节进展中,我们只能知道韩三明在奉节旧城寻找他十几年未见的妻子,护士沈虹在奉节新城寻找两年没回家的丈夫,而他们过去的故事及未来我们却是无从获知的。电影有意地采用了一种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对于韩三明和沈虹的内心情感纠缠,影片既不安排画外音来补充,也不在镜头的处理上有深入他们内心的尝试。演员的表情通常是呆呆的,镜头一般也都是不动声色的。对此贾樟柯曾经这样解释:“在我们的民族性里面,这么多年,集权性的影响远远没有消除。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消除的一个表现就是,人们那么崇拜法西斯性的作品,或者说渗透出来那样一种气质,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也是面对我们作品那么多质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看新导演的作品,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转变就是,在这些电影里面,叙述者本身是一个疑惑者,他不是一个无所不知、上帝式的人物,他不是强制性的观影,不是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识和感受强加给观众的一种叙述的态度。”
其实,在《三峡好人》里,影片试图想保持的中立并非像导演所宣称得那么彻底。电影偶尔呈现的一些荒诞场景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导演一些或明或暗的叙述态度和立场。如在高度现实的场景中设置一个荒诞的飞碟造型形象,再如京剧花脸狂热的打游戏的场景,如同穿越的一个景象。特别是电影最后,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条钢缆,似乎一个踩钢丝的人要挑战长江天堑一样。这些荒诞的空间叙事都被导演负载了一定时代意义,成为了故事的人物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的象征。
在张猛的《钢的琴》中,为了避免叙事视角的主观化,摄影机在低角度拍摄人物时采用了中规中矩的正面或侧面拍摄人物或场景的方式,这样就保证了影像不会扭曲变形,从而使镜头保持了如同坐在戏剧舞台前面的观众的客观视点。如电影开场的第一场戏,陈桂林和他的妻子站在摄影机前,面向摄影机开始戏剧舞台式的对白:“离婚,就是互相成全。你成全我,我成全你。”这时的摄影机采取就是中规中矩正面对准人物的方向拍摄。影片没有让人物所在的位置和摄影机所在的位置以及废弃的工厂空间之间形成任何角度,它让废弃的工厂空间就那样存在于人物背后,像舞台布景一样存在那里。
影片中这种反电影逻辑的拍摄手法的运用,在呈现叙事视角中立的同时,也给影片营造出了一种假定性、非真实性的效果,并因此让影片的叙述态度和立场变得主观起来。在《钢的琴》前面部分中,也就是在陈桂林开始召集哥们制造“钢的琴”之前,陈桂林尝试与朋友借钱买钢琴、偷钢琴的情节段落里,由于这期间他们生活是窘迫的,精神是涣散的,所以镜头的运动通常是水平移动机位,人物右侧入画、左侧出画,摄影机似乎不愿去干预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人物也无力掌控镜头。如影片多次拍摄人物在巨大的废旧工业建筑中穿行的镜头时,都采用了大全景水平移动拍摄,刻意把巨大的废旧工厂建筑展示出来,让人物在画面中显得渺小。不过,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随着陈桂林他们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逐渐被唤醒,当他们再度享受集体劳动的快乐时,镜头的运动虽还是水平移动机位居多,但是摄影机的位置却变得越来越低,摄影机的角度也开始越来越仰,人物对镜头的把握似乎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这些空间叙事视角前后的变化给电影本身增添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意蕴和魅力。
三、空间叙事风格的差异
在李扬的《盲井》里,电影大多是通过真实空间再现生命原有的生存状态,以纪实风格来造就一种朴实自然的空间叙事形态。夹杂大量俚语和粗话的河南方言使角色的性格鲜明而突出,演员也尽力洗去表演的痕迹,唐朝阳和宋金明以及元凤鸣站在矿工们的队伍里好像三滴水融入大海,无迹可寻。与表演风格保持着高度一致的还有摄影上的空间纪实风格。全片几乎全用手持摄影,画面很少会安静地停留在一个均衡的构图上,而是有意识地通过镜头有节制地晃动和抖震来充分呈现电影的“纪录性”。另外,电影中大量的跟拍、尾随长镜头,展现全景画面,都能使观众产生如现场观看的参与感和拟真感。由于许多场景是在私人煤矿里实地拍摄的,光线不足,照明因此也受到极大限制,为了既不使用违反生活真实的人工照明,又能在极低亮度的环境中获得较清晰的画面效果,影片采用了高感光度的胶片拍摄,以及精确的曝光控制,黑暗的井下世界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生活的真实。
在电影《三峡好人》的开头,贾樟柯电影一贯追求的纪实风格非常明显。随着一声轮渡的长鸣,电影以缓慢的镜头横移呈现出渡轮上的一切:船客们或交谈,或递烟,或饮茶,或独自凝思等。这一组如长组画卷般镜头的结束后,影片又把我们的视线渐渐转向故事的主角韩三民。与身旁的人声鼎沸完全不同,他凝望远处,不发一言,静默如静物般,就像这部影片的英文名Still Life。为什么要如此处理,贾樟柯曾这样解释:“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也许在贾樟柯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我们忽略的现实,呈现出更多的真实。
不过,与《盲井》完全纪实风格造就朴实自然的空间形态相比,电影《三峡好人》似乎更注重通过空间选择和重组以及细节的运用,来展现其诗化风格。随着故事的进展,银幕上先后出现“烟” “酒” “茶”和“糖”四字,它们不仅将电影划巧妙地分成了四个段落,而且影片还借这些“烟” “酒” “茶”和“糖”承载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由疏远到亲近,由亲近再到疏远的复杂社会变迁。就像著名学者戴锦华所分析的那样:“烟酒茶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奢侈品和润滑剂,但有趣的是,在电影中,烟酒茶糖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带给了电影第三个层次的空间——社会空间,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在激烈变动中失去了传统,我们面临着匮乏和贫瘠。”
除了烟、酒、茶、糖外,在空间选择与重组上还有奉节县城——这座将要被拆迁的城市。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奉节县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形态。一种是坍塌拆毁的房屋和街道、腐坏破败的工厂、肮脏狭窄的旅社、逼仄拥挤的渡船,而另一种却是宽阔洋气的奉节新城、灯火璀璨的新桥和巍然耸立的三峡大坝等。不仅是奉节县城,而且“三峡”本身都是非常意味无穷的意象——一个既是毁坏也是新生的悖论空间。通过空间选择和重组所营造出来的这些丰富意象,影片《三峡好人》留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影片本身的纪实性真实,更有意味无穷的思索。
与《三峡好人》的诗化风格不同,电影《钢的琴》在空间叙事上则竭力营造出一种假定性戏剧化风格。这种假定性戏剧化风格首先体现为影片在叙事空间的舞台化设置上。比如电影开始,一个固定的中景镜头。陈桂林和他的妻子,男居左女居右,分列画面的两侧,面向观众对话。景深处,一处人字形屋檐的房屋,丈夫身后的屋檐是破损的,妻子身后的屋檐是完好的。这种通过对丈夫与妻子屋檐的对比空间取景,巧妙地呈现出了丈夫和妻子在社会、经济,乃至心理地位等诸多冲突现状。再比如卡拉OK里唱歌的那场戏,这里的卡拉OK厅是没有观众的,不过,镜头给人的感觉却是在舞台上,演员们是在对着摄影机进行表演。影中这种贯穿始终的舞台化空间叙事风格,让影片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独特艺术效果。对于下岗工人陈桂林他们,生存是艰难的,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是封闭的,但导演似乎就是要给这群被时代抛弃,被社会遗忘的底层老百姓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电影《钢的琴》在空间叙事上的假定性戏剧化风格特点还体现在叙事空间的封闭性。这不仅体现为影片的空间环境都是在钢铁厂里完成的,包括职工宿舍、猪圈、发廊、棋牌室、路边摊、俱乐部等,还体现为影片中一些阻碍视觉前进和人物活动的空间设置上,如围墙、窗、门等。影片开篇紧闭的房门,拉着帘子的门缝,偷琴教室的门,工厂封闭的大门,女主角淑娴家的房门等。门是我们走出自我小圈子、走入外面世界的一个象征,但由于钢铁厂这个大空间环境的封闭性,陈桂林造琴的一切奔走与努力就显得无太大意义,而电影所有这些努力,也因此具有了特别的纪念性意义,“如此充满假定性风格化的电影风格成就了这部电影,这不仅仅是表象的、物质的、现实的、数据的、细节真实的电影,它尝试构造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努力。”
四、结语
新生代导演的小城镇电影,与当代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同步,呈现了当前的小城镇生活及其社会发展问题,体现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盲井》《三峡好人》和《钢的琴》三部小城镇电影在空间叙事结构、空间叙事视角及空间叙事形态上呈现出的诸多差异,究其原因,不仅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同地域小城镇空间风貌差异有关,与其独特的空间载体所负载的深层社会文化有关,更与导演不同的电影美学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