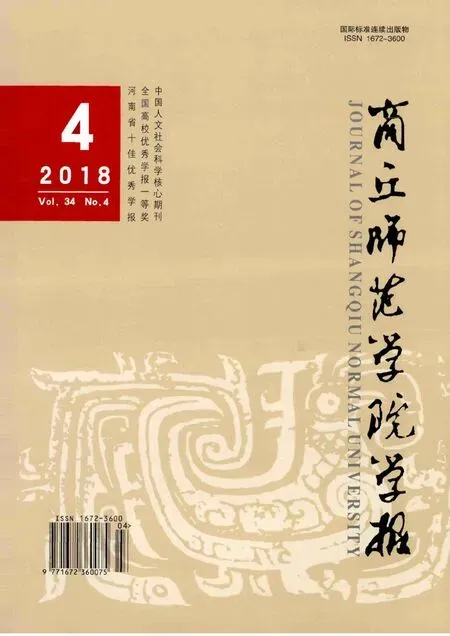清代“以情体庄”视域下的庄学研究
——以清初胡文蔚《南华真经合注吹影》为例
彭 时 权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自宋王安石提出透过《庄子》文本了解内在的深刻用意,“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1]1118,后世文人开始注意庄文滑稽荒诞之言背后,实则饱含着欲矫弊救世的深情。另一方面,文人受时文“代圣立言”思维的长期影响,注重体察文字细微,揣摩经书中圣人情感语气,要求精神情感与圣贤契合,这种思维模式也影响到对《庄子》文本的理解。明人董其昌《论文》曾说:“有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乃谓注于不涸之源。”[2]2428他从创作的角度讲究体察作者内在情感语气,从而代写作者心事。清人李光地也说:“做时文要讲口气,口气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经便是如此。若口气错,道理都错矣。”[3]272管世铭也说:“前人以传注解经,终是离而二之。惟制义代言,直与圣贤为一,不得不逼入深细。”[3]272这都可看出文人对揣摩圣人情感语气的重视。这种思维模式深刻影响着明清两代文人,因此在注解《庄子》过程中往往也能体察庄文背后的深意,感受其内在的情感张力,而由于自身心灵与庄文精神的某些契合,在其注解中往往能看到作者自身的精神情感状态。李波在谈论明代庄学特点时就说:“明代学者在评点《庄子》时往往喜欢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悟和个人情感,以意逆志,从而能深刻地还原出《庄子》文章中蕴含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人生情绪、生活体验和内心世界,为世人深入了解庄子作出了有益的尝试。”[4]55释德清评《逍遥游》说:“言虽戏剧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则不可以正解,别是一种风味,所谓诗有别趣也。”[5]一册104认为庄文“言虽戏剧而心良苦矣”,要求读者透过表层的戏谑文字把握庄文内在的“别趣”。陆西星对《山木》篇“市南宜僚劝鲁侯南去建德之国”一段中描写的离别场景感叹道:“尝谓庄子善体物情,等闲发出送行二句,宛然离情别思,‘渭城朝雨’之词不过是也。”[6]285他带着浓厚的情感体味庄文,认为其间描写的离情别思,就是王维那首描写离情的名诗《送元二使安西》也不过如此。可见明人解庄关注到庄子“心良苦矣”“善体物情”,带有浓郁的情感体验色彩。而这一特点在由明入清的胡文蔚身上具有鲜明的体现,并且比之明代文人对庄子的人生感悟,情感体验,胡氏更以自身的身世漂泊、生存困境以及朝代更迭的时代感受去体悟《庄子》,显然对《庄子》中蕴含的深情厚谊更多了一份生命的体悟与知心的领会。
一、“一身如寄”,领悟庄子“高节讽世”
从其周遭经历来说,胡文蔚饱受漂泊、生存困境之苦,他在《南华真经合注吹影·自序》(以下该书简称《吹影》)中说:“岁癸巳,流寓东粤之海滨,时值大饥,斗米千钱,枯坐一室中,再食不饱,百忧相续,计无所以陶情拨闷者,因取南华诵之,顿觉心爽神开,视一切死生荣辱,宛如游尘聚散。”[7]155-156可见,在胡氏流落广东海滨,遭逢饥饿,一日两餐而不得饱,心中忧闷无法排解之时,正是《庄子》一书给予了他极大的精神慰藉,使得他看淡死生荣辱。其同窗尹治进在其《吹影序》中也提到胡氏经历与所著《吹影》关系:
庄子生于周末不用于世而著是书,故首托《逍遥游》以寓意。胡公则逍遥而游于吾粤者十余年,一身如寄,栖托不一,或流连往事而发为诗歌,或匏系一官而施之政事,迹其三十年前与查伊璜同举于乡,名噪海内,安知不若垂天之云而瞬息几万里者哉,乃不免六月之息。至于流寓海滨,斗粟千钱,然后闭门厘定斯书,是犹庄子自托于《逍遥游》之意也。[7]159-160
认为庄子不用于世而著书,托意《逍遥游》。而胡文蔚在广东漂泊十余年,游走栖居,一无定所,或作诗流连往事,或为官以施政事。当年与查伊璜举试于乡,名声享誉海内,而今却流落寄居海滨,遭逢饥馑,故著《吹影》一书,犹如庄子著书以自托于《逍遥游》。可见胡氏的身世漂泊与困境经历让他对于《庄子》有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使得他在解庄中灌注着自己的生命感受。如《外物》篇“庄周家贫,往贷粟于监河侯”一段,胡氏感慨道:
予流寓广州陈村,自戊及癸,获注此书,时值大饥,流离之子,薄粥野蔬,日才二餐,愧无粟贷友,亦无从乞升斗。若监河侯之诺贷,未见其人也,况三百金云,虽多而未与,不若少而有济。吾以庄子之忿然作色,犹行古之道也。今则何敢。陆方壶以为穷涂仗友生,仁者宜亟恤之,乃出此迂缓不急之语。庄子偶记于此,以见世俗之益偷也。悲哉,天乎!当日如是,兹更甚焉,慎毋使人与人相食之言,验于后世,则斯人之福矣。[7]1048
胡氏将自己身历饥困,日仅二餐又无亲友可乞贷粟粮的往事叙述于此,对庄周遭遇贫饥的困境体切犹深,钦慕庄子尚能忿然作色,犹行古道,感慨自己哪敢有此气度。也正是因为对饥饿困境有着切身体会,胡文蔚才说陆西星的“穷涂仗友生,仁者宜亟恤之”,乃是“迂缓不急之语”。更由自身困境而悲叹世事,“慎毋使人与人相食之言,验于后世”。正是胡文蔚有着切身的困境体会,对庄文的理解也就不仅仅局于义理的阐释,而往往融入了他自身的生命体验。
另一方面,由明入清的文人们对世道变迁有着椎心泣血的痛切体会,饱受朝代更迭时期的生死抉择之苦,王夫之“以死为道,然后审乎所以处死之道”[8]887的感叹在明末清初拷问着无数节义之士,屈大均的“一日之生,即一日之死”[9]40,归庄所谓的“恨其不能死”[9]41,黄宗羲所谓“其死操之己者,是志在于死者也,方可曰死之;其死操之人者,原无欲死之心,亦曰遇难而已”[9]46,无疑都展示出明末文人对于“以死为道”的深刻反省与拷问。而形成如此强烈的生死节义观,除了士人对儒家“杀身成仁”观念的认同,更有着君王“死社稷”以身为则的道德垂范。诚如赵园所说,“崇祯之死即使不是此后一系列的死的直接诱因,也是其鼓舞,是道义启导、激发,是示范、垂训,是人主施之于臣子的最后命令”[9]24。而这一影响在由明入清的时代背景下一直延续着,是清初文人们不能不回应的问题。胡文蔚作为一个由明入清的遗民,感受着时代风云的更迭变迁,对其“生死节义”问题不能不有所感触。尹治进《吹影序》中说胡氏“流连往事而发为诗歌”,也可见其对前朝的感念追怀。而其在《吹影》中也隐隐透出这份遗民之情,如《让王》篇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山一段,胡氏注曰:“庄子引此,见二士之饿,非矫激伤身,义不得已,故立高节以讽世也。”[7]1116在胡文蔚看来,此则寓言并非有悖于庄子养生之道,而纯是对世德沦丧的深切悲情,伯夷、叔齐皆“非娇激伤身”,实是朝代更迭“义不得已”的抉择。在他看来,庄子无疑是以高节讽世,是对那些忘义之徒谄媚权贵的深切诫训。而胡文蔚有此看法,实则也正是由其历经明清易代,饱含着对时代更迭的无奈和民族节义的强烈认同。但另一面又对节义之士一味殉死有所质疑,如“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一段,胡氏注道:“三子之自溺,未免矫激太过,以身殉名。庄子警醒世人之意深哉!……立言有反有正,无择以上,欲人之取法也;无择以下,欲人之鉴戒也。”[7]1114认为北人无择、卞随、瞀光三者以身殉名,自溺而死,矫激太过,而这其实是庄子篇章立言的正反设计,“无择以上,欲人之取法也,无择以下,欲人之鉴戒也”。无疑对明末那些节义之士一味轻生重死的反思,认为庄子用“无择、卞随、瞀光”三人殉名而死作为反面申说,用以警戒世人。由此可见,胡氏以自身的生存困境和时代更迭的切身体验对《庄子》内在的思想情感进行了深刻体悟,这种生命体验无疑是之前明代治庄家所不具备的。
二、体会庄子“婆心”,授道“下根人”
胡氏以情体庄,每每关注到《庄子》对世人悲悯关怀的“婆心”。如对《齐物论》中“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胡氏对此注道:“此段为‘彼是者’指引一虚心对勘之法,以消除其偏执,庄子何等婆心。”[7]271这里,胡氏认为,庄子用“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来现身说法,为那些自以为是的偏执之人指引对勘之法,是何等苦口婆心。又如《天地》篇“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至“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一段,胡氏注道:
盖深有所激而愤悱之词,既知其惑而强人以必行,则我反为不智。是又自增其惑也,莫若舍而不推。推,求也。然不推,则天下之祸,何时而解。谁其与我同忧哉!比,同也。明知天下无人,又不敢绝望于斯人,此老婆心处。[7]603
庄子恐天下皆“惑”故而强向世人倡明大道以从,如此自己反而“不智”增惑,然而抱着“至言不出,俗言胜也”的救世之心,“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终是不能“释之而不推”,只得感叹“谁其比忧”。胡氏关注到庄子这种矛盾的救世心理,体会到庄子的良苦之心,故而说:“明知天下无人,又不敢绝望于斯人,此老婆心处。”胡氏无疑是看见了庄子对人世抱有极大的悲悯情怀,对芸芸的“下根人”深陷迷途不能体悟大道有着热切的拯救之心,往往苦口婆心地为“下根人”启迪一些入道法门。如《庚桑楚》中南荣趎受“知、仁、义”三者所患,求见老聃,老聃道:“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胡氏注曰:“老子曰‘丧’,曰‘亡’,曰‘反而无由’,曰‘可怜’,即显斥之又深悯之。实善诱之也。”[7]918关注到老聃“丧”“亡”“反而无由”“可怜”等语词背后,既是对南荣趎的斥责,同时也饱含了深深的悲悯之情。其后南荣趎十日自愁,复见老聃,老聃曰:“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揵;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荣趎觉得自己根器浅薄,便仅求“卫生之经”,老聃则告以“九能”。胡氏又注解道:“只此数语,点破他胸中病根,当下爽然自失,以为饮药加病,深愧根器浅薄,仅求卫生之经,不知卫生正是大道。老子却不说明,就随他转头处,引他上路。”[7]921又说:“九能中,至人之道,不外于此。单把儿子再说一段,分明教他卫生之经,当如赤子之无知无识。由‘侗然翛然’以至于‘能勿忘失’,而后能抱大道。确有次第,但不肯说破耳。”[7]922认为老聃所说的“卫生之经”正是“至人之道”,不过是以这种随其婉转的方式引南荣趎入道而已,并认为从“侗然翛然”至于“能勿忘失”正是入道次第,不过不肯直接说破而已。又在南荣趎问老聃“至人之德”一段注解道:“‘至人’一问,未为不是,缘趎躁进而畏难。老子恐其不能当下承受,又曰‘非也,冰解冻释者。’已隐然示以一解尽解之旨,却从至人身上说,至所说同食乐,忘利害,不为怪,不为谋,不为事,总是如儿子之无心。结以‘翛然侗然’,又说是‘卫生之经’。岂不是教以儿子为入圣之基。隐然使趎自家理会,趎复日是至乎,犹是畏难之见。老子更提前头‘儿子乎’,阐发一番,则由浅入深之次第和盘托出,而趎始有会于心矣。”[7]923认为老聃知道南荣趎“躁进而畏难”,担心他“不能当下承受”,故而又否认自己所说的正是“至人之道”,转而申说“卫生之经”,提起“能儿子乎”。如此随其婉转答以大道,以启迪南荣趎,使其有会于心。并在《总论》中说道:“此真人传授大关窍,内外篇所未有者。”[7]900通过胡文蔚的详解,庄子通过老聃对南荣趎循循善诱的一番入道启示,可见其对“下根人”深切的关怀,真是苦口婆心。又如《知北游》篇知谓无为谓“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一段,胡氏注道:“‘何思何虑’三问,体贴下根人心口,最亲切。”[7]855可见胡氏认为,庄子绝非远离人间,冥入虚空的修道者,而是关怀世间,有着极大救世热忱的“婆心”人。
三、“漆园非激,意在还醇”
《庄子》一书,每每“非仁义”“薄尧舜”“贱儒墨”,常以一种激愤的姿态评论世事,抨击儒墨。王安石虽洞悉庄子用心,认为“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也”,然而也说:“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1]1119即认为庄子矫枉过正,过于激愤。清人刘城也评道:“周之观理也,精其忧世也。亟观理精,故穷极乎道义之原。忧世亟,故愤极乎污流之俗。”[1]1176认为庄子观理极精,而忧世愤极。王先谦亦评道:“其志已伤,其词过激。”[1]1201可见,历代不少文人都认为庄子愤世过激。如《胠箧》篇就为不少治庄家排斥质疑。陈深对其评道:“此篇言圣人立法以利盗贼,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类多愤世之言。”[5]三册90王夫之评此篇道:“盖惩战国之纷纭,而为激愤之言,亦学庄者已甚之成心也。”[5]三册92认为此篇为激愤之言,是学庄者成心已甚而作。胡文蔚则从庄子“婆心”处体会其文,并为其辩解。他在“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至“法之所以无用也”一段评道:“人以为此漆园有激之言,不知太上无为之世,原未尝有珠玉、斗衡、圣法、仁义、聪明、工拙,意在还醇,非激也。”[7]517认为那些人看到庄子说“掊斗折衡”“攘弃仁义”的话就认为是激愤之言,只是不知道太上无为之世本来就没有这些“珠玉、斗衡、圣法、仁义、聪明、工拙”等利益名誉可争夺分别,庄子本意不过在呼唤大众返回那最初的淳朴之心罢了,并非过激之言。又在其后“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有三代以下者是已”一句注曰:“低回而甚叹其乱天下。试看三代,以至于春秋战国,何等变乱,安得不伤今而吊古!”[7]521从“甚矣”两字看出庄子不得“还醇”的悲叹,认为庄子面对如此乱世,“安得不伤今吊古”。显然,胡氏以情体庄,在看似简单文字的背后,将庄子内在深情揭示出来,那些看似激愤的言语,实则是庄子以清醒的目光审视世事古今,关怀芸芸大众不得“还醇”的悲叹。陈鼓应就曾说:“庄子的清醒与殊异,并非基于愤世之孤傲与洁身之坚持,而是以广袤无垠的宇宙意识与天地精神,对世间多怀一份醒觉的洞悉与深情的理解。”[10]5如《庚桑楚》篇曰:“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胡氏对此句注解道:“盗贼弑逆之事,势所必然,率兽食人,易子而食,岂所忍言。不但千世之后,春秋之时,已有之矣。小眼孔翻以庄子之言过激,吾以为只见得破,说得出耳。”[7]909认为庄子所说的“盗贼弑逆之事”乃是世事本然如此,更有“率兽食人,易子而食”的人间惨祸存在,只是庄子不忍再说罢了。不但是千世之后,就是在春秋之时,也已经存在“人与人相食”的现象,而那些眼光狭小之辈反而以为庄子言语过激,其实不过是庄子能将人间惨象说得出罢了。可见,所谓的庄子言语过激,其实正是庄子内心深处对人类命运、社会乱象关怀的彻骨悲凉感。清代黄中就曾说:“庄子愤世嫉俗,慷慨激烈,而叹息悲伤,其言似为放荡恣肆,而原其情,则出于悲天悯人也。”[11]89胡氏从“婆心”处看到了庄子内在的深情,强调庄子并非过激,不过是悲天悯人,“意在还醇”罢了。
胡氏对庄子内心的悲悯之情有着深刻的体悟,这种以情体庄的心境在之后的治庄家身上也屡屡出现。如宣颖解《齐物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一段:“与下凡三节迭迭为世人寄痛,以深见其可悲,直从明眼慈心流出一副血泪来也。”[12]12又在“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独我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句评注道:“怪叹众生汶汶,反借自己为普天一哭。”[12]12可见宣颖以情体庄,感悟到庄子内在的“血泪”和“为普天一哭”的悲悯之情。胡文英更是推进一步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昧其指者,笑如苍蝇。”[13]6将屈原与庄子对比,认为“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更加见证了庄子对天下乱象的哀怨情深。之后的刘凤苞亦深有体会,如他在《德充符》评道:“别开生面,别有一副悲悯心肠。”[14]113对《天道》篇评道:“庄子为天下后世深致悲痛,一腔心血,一副眼泪,信手挥来,正和秋夜寒砧,音传空外。”[14]304由此可见,胡氏关注庄子“非激”而“意在还醇”的情感体悟,对之后的治庄家们以情体庄,感悟庄子的悲悯深情,有着重要影响。
四、揣摩字句语气,分析心理情态
明清两代文人受时文“代圣立言”思维影响,制义作文时往往揣摩圣人语气。而这对治庄家们深入体会庄文蕴含的思想情感,无疑有着积极的文学审美意义。诚如李波所说,他们“更多地把文学审美融入其中,用身心来涵泳《庄子》,揣摩语气、文气”[4]334。胡文蔚在领悟庄子悲悯情怀的同时,更是善于揣摩文中语气,从而将《庄子》中那些以往未为人所注意的细腻情感揭露出来。如《则阳》篇“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之何!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一段,胡氏注道:
师天者,若有心要去师法他,便不见得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未免芸芸逐逐,劳形揺精,其以此为事也。若之何能见性。夫师天之圣人,并不知有天,又安知有所谓人,所谓始,所谓物,虽绸缪揺作,与世偕行,而保己守真,自无废替,即周尽一体。所行之备而复命归根,不与物并溺。若之,何其不合于道乎。两‘若之何’,一抑之,一赞之也。[7]1006
这里胡氏将两“若之何”背后的义理进行对比,前者“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是“不得自然”“不安自然”,故而“芸芸逐逐,劳形揺精”,最终“与物皆殉”;后者“圣人未始有天”是“不知有天”,能够“与世偕行,而保己守真”,“不与物并溺”。两者鲜明对比,从而看出“若之何”一句背后透露着庄子对“不得师天”“与物皆殉”的生存行为的批评和对能够“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合于大道精神的赞美之情。又如《山木》“市南宜僚劝鲁侯南去建德之国”一段中,分别提及三次“吾愿”:第一次市南宜僚借“丰狐文豹”有皮而遭“罔罗机辟之患”告诫鲁君:“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第二次市南宜僚谈及建德之国的民众愚朴寡欲,不知礼义,生死自然,告诫鲁君:“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第三次则对鲁君前往建德之国畏惧“幽险”“无邻”“无粮”而告诫道:“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野。”胡氏对此注评道:“三‘吾愿’,具见恳挚。”[7]807认为三次“吾愿”可见市南宜僚对鲁君劝勉的真诚恳切之情。而对市南宜僚劝鲁君去除畏难情绪所说的“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胡氏评道:“此警策畏难之人,发其猛心也。”[7]807认为这是市南宜僚在给有畏难情绪的鲁君给予警策激励,让鲁君能够鼓起勇气面对前行。可见,胡氏的评语虽少,但着实把握住寓言中人物的语气,揣摩人物心境,揭示出其心理状态。又如《则阳》篇则阳求王果引荐于楚王,王果则推卸道:“必待公阅休。”然后申说“夷节之为人”和“楚王之为人”,推出圣人“不言而饮人以和”,最终归于“必待公阅休”。胡氏对王果话语进行揣摩,评道:“王果心鄙之,因盛称捉鳖休樊之公阅休,一曰‘我不若’,再曰‘夷节已不能’,隐然见恬退保己者,我三人皆当尊事之。一抑一扬,令其自悟。曰‘我又不若夷节’,似谦实傲,意谓我不若夷节之干进也。”[7]998认为王果心里其实鄙视则阳如此贪求禄位,盛赞“恬退保己”的公阅休,并将其与夷节对比,一抑一扬,让则阳自行领悟。又对“我又不若夷节”一句语气进行揣摩,认为王果似谦实傲。胡氏继而评道:“嗟嗟!休,高士也,岂有谒王侯而荐士,王果不过远引高人,以示典型,婉辞之,阴抑之也。”[7]1000认为王果不过是用公阅休这一世外高人来给则阳示以不逐外物的精神典型,让其明白自身竞逐功利,为有道者所不齿,婉言拒绝而暗中批评他。通过胡文蔚对王果话语语气的揣摩,其内心情态也得以展现于前。此外,胡氏还对《庄子》寓言中人物心理活动进行了很好的揭示。如《达生》篇桓公在泽地见鬼,返回之后,竟得诶诒之病。皇子告敖向桓公列举诸鬼,然后描述“委蛇”之鬼,并说“见者殆乎霸”。桓公闻言不治而愈。胡氏对此则寓言注解道:“皇子蚤(早)知桓公所见者为委蛇,恐其不信。先历举诸鬼,末说泽中之鬼,迨桓公问而述之,耸动桓公,使之快心兴起者。只‘见之者殆乎霸’一句正中国君之所好,疑虑之疾,不攻而自去矣。”[7]783认为皇子告敖其实早知桓公所见是“委蛇”,只是担心直言相告桓公不信,故而通过历举诸鬼的方式与桓公虚与委蛇,最终提出“委蛇”,以此耸动桓公,以“见之者殆乎霸”投中其所好,故而桓公疾病不攻自去。显然,胡氏不像以前注家注重义理阐释或鬼怪神巫,而将关注中心放在寓言本身的故事性上,对皇子这一人物进行细腻的心理分析,认为皇子与桓公对话是早有准备,列举诸鬼都是在故意引导,而“见之者殆乎霸”正中桓公心中所想,最终消除了桓公的病症。通过胡氏的注解,可见皇子告敖确实是一位善于体察君心的人。又如《说剑》篇中庄子向赵文王讲述“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最终使赵文王不再热衷剑斗。胡氏注道:“妙在胜称天子之匡服,合其自失,继举诸侯之安和,令其自雄,下鄙庶人之格斗,令其自惭自悔。”[7]1164全篇寓言中其实并未描写赵文王的心理状态,所写也仅限于对庄子言说“三剑”之后的行为举动:“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而胡氏则对庄子每次描述“剑势”之时,揣摩体察此时赵文王的心理情态,称庄子谈及“天子之剑”时,赵王“自失”;谈及“诸侯之剑”时,赵王“自雄”;谈及“庶人之剑”时,赵王“自惭自悔”。如此将赵王的心理路程一一揭露,使得寓言故事的内在情态呈现于读者,意态盎然。
胡氏对庄文的字句语气揣摩和对寓言人物的心理情态分析,挖掘出庄文中那些看似无甚大义而实则饱含深情的内涵,从而在文章义理中透出一种意态盎然的情趣。而对庄子情感的细腻体会无疑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推动着清代庄子文章学的深入探索,之后的刘凤苞则对文中语气精细体悟,向读者揭示出庄文浓厚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学色彩。如《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栎社树”一段,刘评曰:“‘且予求无所可用’二句,再透人一层,不求其可用,而求其无所可用,翻尽常解,极超脱,又极悲凉。‘久矣’、‘几死’四字,极力摹神,可见世道之危,不如是几不能自全,而夭于中道也。‘乃今得之’一转,分外出力,若自誉,若自嘲,若自为慰藉,写得淋漓恣肆。一片机锋,全在梦中托出。”[14]106刘凤苞透过“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看出栎社树身处世间,委屈保全的内在悲凉,认为“若自誉,若自嘲,若自为慰藉”,从而挖掘出寓言内在深厚的情感寄托,令人感慨万端,情思若哀。由此可见,刘凤苞沿着胡氏对文辞语气的揣摩和对心理情态的分析,深入探索出庄文内在的深刻而丰富的情蕴,足可见胡氏对后来治庄家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清初胡文蔚以自身的身世经历、生存困境以及朝代更迭的时代感受,对庄子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认为庄子具有关怀世人的“婆心”,内心深处实是悲天悯人,其言辞并非“过激”,乃是“意在还醇”。并且揣摩庄文语气,对人物的心理情态进行分析,将庄文中饱含深情的内涵挖掘出来,使文章义理透出一种盎然的情趣,无疑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由此也影响了之后宣颖、胡文英、刘凤苞等治庄家以情体庄的精细化感受能力,提高了对庄子文章美学意境的领悟层次。
[1]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M].成都:巴蜀书社,2007.
[2]王水照.历代文话:第3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李波.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5]方勇.庄子纂要[M].北京:学院出版社,2012.
[6]陆西星,撰.蒋门马,点校.南华真经副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胡文蔚.南华真经合注吹影[M].北京:国家图书馆清代影印藏本.
[8]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9]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方勇:庄子学史: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黄中.黄雪瀑集[M].清康熙二十九年咏古堂刻增修本.
[12]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3]胡文英,撰.李花蕾,点校.庄子独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4]刘凤苞,撰.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3.
——以衡南县杨柳村胡氏宗祠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