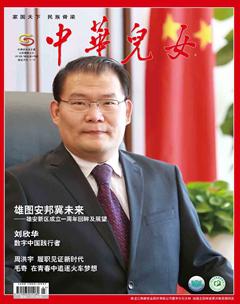一篇报告文学引发的情与缘
康胜利
不久前,突然接到中华儿女报刊社余玮的电话,说杂志创刊30年了,要我写写与《中华儿女》有关的往事。余玮的话不听则罢,一听我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多年来的旧友、往事一个个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逐帧再现于眼前。一脑子的事一肚子的话缠绕交织,一是不知该从何说起。
最早“认识”《中华儿女》,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单位的图书馆里。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百分之百的独家文章”印在封面之上,恢弘大气的风格,让我这个刚刚从电大新闻专业毕业的半老青年仰慕不已。共青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又显得如此“高大上”,我真觉得她是那么高不可攀。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走进心目中的这座殿堂。
1994年12月8日,祖国大西北油城克拉玛依友谊馆一场大火,把300多名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生生吞噬了。惨绝人寰,天地恸哭。事故发生后,我以基层文化工作调研的事由到了那里。在克拉玛依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痛不堪言,双眼流出的似乎不是泪,而是血。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悼念我们的石油孩子,讴歌在生死抉择面前英勇无畏的人民教师,报道党和政府以及中国石油主要领导对此次灾难的慰问善后工作,回京后我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克拉玛依:跨世纪之痛》。
记得当时社会各大媒体对此次重大事故噤若寒蝉,只报道了几行同文的短消息,国人亟需知悉内情却概莫能知。我拿着一沓子稿纸,问哪家都唯恐烫土豆落到自家手上。许多人还有领导劝我,说披露事故详情是“负面影响”。急来抱佛脚,也许是缘分,我抱着北京市电信局的电话簿拨通了《中华儿女》雜志领导的座机电话。对方的声音既亲切又好听,简单问了下就说你送稿来吧。真没想到,如此高层次、高格调的国家级大刊,大门就这么走近了。当时我激动得手足无措,揣起稿子蹬上自行车就从六铺炕往前门东大街狂奔。那时杂志社还在团中央机关后面的一座小楼里,到门口了,心里仍忐忑不安。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杨筱怀社长。不久,稿子发在醒目位置,题目为《面对大火的克拉玛依人》。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杨筱怀对我说还中宣部也看到了。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华儿女》无私无畏的忧患意识、有责任有担当的家国情怀。4年后中华文学基金会“铁人文学奖”征集评奖作品,我想拿篇保险的,文联同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肖复华力主报上这篇。评选会评委分成两派,结果与此奖失之交臂。尽管这样,但我依然无悔。我相信,当年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中华儿女》的奋力呐喊,让我们的社会切实汲取了这惨痛的教训,从而有助于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

《中华儿女》尊重作者。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不管是社长、总编辑乃至各级各部门的同志,无不把作者首先作为朋友。那些年,即使是王维玲、杨筱怀这样的司局级领导,进了他们的办公室都是起身相迎,沏茶倒水。一声亲切的话语,让人冬暖夏凉,亲情油然。应该说是上行下效树正影直,其他同志就更不必单说了。按说,编辑掌握着作品的斧正甚至“生杀大权”,这里不是。编辑们既严谨又谦虚,与作者共同商量探讨,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有时还说,咱这里稿费不高,您别嫌少。其实,就我本人的心里话,能在《中华儿女》这个大窗口上显山露水,是作者荣幸与光荣,没有稿费我也乐意干。在《中华儿女》上,我发了《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渤海二号事件之后的康世恩》等诸多文章。在我们这些作者眼里,看重看好的只有《中华儿女》之正、《中华儿女》之情。
《中华儿女》爱护作者。一个杂志要想办得出人头地,除了杂志同志本身,就要依靠作者了。多年来,《中华儿女》不仅仅是依靠作者,更多的是关心、引导、培养作者。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经常打电话询问最近有无作品、什么内容,或提供采访线索,或提供帮助。这在其他刊物,可能是罕见的。那些年,我曾几次参加《中华儿女》笔会和多项活动。上黄山、下廊坊、赴重庆,每一次笔会,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明确了任务,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情谊。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许多为《中华儿女》撰稿的作家、专家朋友,如肖思科、褚银、梁秉坤、黄宏、邵维正、王凡……,结识了老一辈革命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张玉凤、黄佐良、李文普等,还有开国元勋的后人及亲属,如周秉德、周秉建、伍绍祖、陶斯亮、陈伟华、刘刚等等,谅我不能一一具名了。同样难忘的还有2002年在大观园酒店参加的座谈会,我见到了自小仰慕的大作家管桦老师,小学时代就学他的课文《小英雄雨来》,唱他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次《中华儿女》的座谈会,连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都来了,可见《中华儿女》的威望与影响力。
2008年11月9日,《中华儿女》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晚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让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一文被授予“《中华儿女》20年代表作品奖”。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把奖状奖杯颁到我手中那一刻,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激。
多年来,我得到过《中华儿女》杂志多位领导和老师的帮助,受益匪浅。在我心底里,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王维玲、杨筱怀、何青龙、李静、陈宝洪、刘之昆、曾平、包文辉、张晓莉、弋阳,还有后来的石国雄、李而亮、陈安钰、余玮等等。我感谢《中华儿女》的领导和编辑部所有老师。是你们,此地无声胜有声,多年坚守,默默地甘为她人做嫁衣。可以说,作者前台发的亮,有你们后台闪的光。
在这里,想说说我最尊重的师长王维玲老先生。他当年不仅是《中华儿女》杂志主编,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这位享有很高威望的老作家、编辑家,面容和善,虚怀若谷,看上去只是个有文化的普通老汉。是王老,引领我加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并连届担任学会理事。从王老身上,我汲取到许多历史的、社会的、文学的素养。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在他的镜片后面,总是透着一双慈祥父爱般的目光。每次笔会出去采风,我总爱跟着他。王老走一路讲一路,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底蕴的那样的丰厚,有很多东西,即使在名牌大学里也是学不到的。他讲柳青和《创业史》、梁斌和《红旗谱》、姚雪垠和《李自成》,以及刘白羽、管桦、路遥、周克芹等作家的作品,还讲与这些人的真情交往、深厚友谊。印象尤深的是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此处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办公地点。站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王老激动地讲述起1958年跟随老领导、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到成都出差,经作家沙汀推荐题材线索,由重庆罗广斌、杨益言创作小说《红岩》的往事,以及从选题到1961年出版,那个期间在北京、重庆与作者的交往过程。说到这部红色经典,我上初中前就读过。没想到帮助修改创作提纲和出版的伯乐之一,就在我的眼前。我想,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王老几十年默默提携扶植多少作者,恐怕难以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