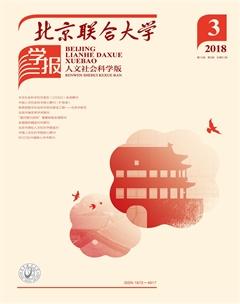合宪性审查机制建设的40年
莫纪宏
[摘 要] 回顾我国1982年现行宪法生效以后过去36年中宪法实施监督机构和合宪性审查机制建立的过程、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实践中有代表和影响性的案例,可以看到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建立在法理上和实践中经历了“机构优先”“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和“合宪性审查”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在学理和实践中都形成了主流性的观点和做法。笔者认为,只有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职责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重要实践才真正具有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要求,是在总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过去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正是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建立和健全的必然要求,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会在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合宪性审查工作;机构优先;司法审查;违宪审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宪立法
[中图分类号] D91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8)03-0016-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1]。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了“合宪性审查”概念,对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合宪性审查”作为加强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措施,从1982年现行宪法制定时就已经得到了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其中经过了“机构先导”“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到“合宪性审查”几个发展阶段,最终走向了成熟。“合宪性审查”机制确立和发展的历程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基本同步,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体现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价值要求。
一、“机构先导”开启了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序幕
改革开放以来,以合宪审查或违宪审查为契机来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最早始于建立什么样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的学术争论和制度建设。早在1982年现行宪法制定的过程中,作为负责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就曾经被宪法修改委员会考虑过①,后来基于各种因素没有写到宪法文本中,但现行宪法把宪法实施和监督的职责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现行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为了推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地履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1983年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六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议案,建议在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1989年,湖北李崇淮等31位代表、四川王叔文等32位代表向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关于建议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的议案(第316号、392号)[2]。
关于建立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构,法学界最早对该问题明确加以学术讨论的是发表在198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由陈云生撰写的《论宪法实施的组织保障》,其后胡锦光教授也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机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探讨。从1985年开始,胡锦光教授连续在几篇学术论文中探讨了在我国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的可行性,这些论文包括发表在1985年第1期《中国法学》上的《论宪法监督制度》,与董成美教授合作发表在198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的《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组织探讨》,以及发表在1987年第3期《法律学习与研究》上的《我国违宪审查的方式与处理初探》等等。由于王叔文等全国人大代表的多次提议以及法学界的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建立专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进入了高层议题。1993年修宪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以下简称《补充建议》)中指出:“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上述《补充建议》向社会公众表达了全国人大无需经过修宪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设立专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不过,在实践中,在不修改宪法的前提下来推动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实施监督的专门机构非常困难。直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才再一次提到了宪法实施监督的专门机构问题,即在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由此来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随后,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宪法实施监督的要求,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44条第2款规定:宪法第70条第1款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至此,作为制度体制机制上行使监督宪法实施职责的专门机构终于落到实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也成为十三届全国人大设立的第一个组织机构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會议表决通过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产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个机构。,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保障宪法实施方面寄予了厚望。
二、“司法审查”掀起了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的热潮
改革开放以来,合宪问题、违宪问题以及通过司法审查途径、宪法司法化等方式来保证合宪性一直受到我国宪法学界的关注。CNKI数据库显示,早在1979年第6期《法学译丛》上就刊登了潘汉典先生翻译的《法国对法律合宪性的监督》一文;把法律的合宪性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学术论文最早见于黎建飞、孔小红撰写的1985年第1期《社会科学》上的《法律的合宪性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文;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介绍合宪审查或违宪审查的最早是龚祥瑞、罗豪才、吴撷英发表在1981年第1期《法学研究》上的《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结合中国实际来探讨违宪审查模式的学术论文最早可见于费善诚撰写的发表在1999年第2期《政法论坛》上的《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随后,王磊[3]、王振民[4]等宪法学者对通过司法审查方式来实现宪法实施监督都推出了个人的学术专著,丰富了宪法学界对司法审查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能否通过司法审查途径来实现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学术观点最具影响的当属胡锦光发表在1993年第1期《法学家》上的《宪法司法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探讨》以及蔡定剑发表在2005年第5期《法学研究》上的《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尽管学界对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合宪或违宪审查展开了深度理论性探讨,从司法审查角度来适用宪法真正得到法律实务界的重视,则始于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玲案”作出的批复(又称“8·13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于2001年6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8月13日起施行。该批复是针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批复答道:“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8·13批复”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亮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第一次以司法批复的方式确认了公民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这一精神使得“司法审查”成为合宪性审查机制建设方向的理论探讨热点;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8·13批复”中创设了违宪审查的重要观点,即一个公民“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另一个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述司法意见肯定了普通公民可以构成侵犯宪法上基本权利的行为主体。
“8·13批复”在学界和司法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学界,“司法审查”成为加强宪法实施监督的“制度突破口”的主张受到热捧,“宪法司法化”[5]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在实务界,一大批司法判决都积极主动地引用宪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形成了一股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宪法”判案的司法倾向。不过,“8·13批复”的生命力并不强,首先,学界经过若干年的探讨,基本上否定了“8·13批复”中的合宪性审查理念,普通公民可以侵犯另一个公民的宪法上基本权利的观点没有得到有效支持,国家机关负有保护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的观点得到了基本认同;其次,在实务界,由于“8·13批复”导致了“司法审查”理念与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职责存在着制度和价值上的内在冲突,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8日发布如下公告:该院审判委员会第1457次会议于2008年12月8日通过了《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包括以“已停止适用”为理由,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该决定自2008年12月24日起施行,此次,在司法审判适用宪法来作为判案依据的声音渐趋式微[6]。
宪法学界针对“齐玉玲案”司法批复的“已停止适用”也作出了相应的学术回应。《法学》(主编童之伟)专门在2009年第3、4期组织了专家笔谈。代表性论文是:《宪法适用应依据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童之伟)、《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童之伟)、《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韩大元)、《齐案“批复”的废止与“宪法司法化”和法院援引宪法问题》(陈弘毅)、《废止齐案“批复”是宪法适用的理性回归——兼论“宪法司法化”的理论之非与实践之误》(董和平)、《呼唤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宪审查制度》(虞平)、《齐案“批复”的废止与中国宪法适用的未来》(林峰)、《理性看待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玲案“批复”的废止》(朱福惠)、《从废止齐案“批复”看司法改革的方向》(董茂云)、《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兼论我国宪法适用的特点和前景》(刘松山)、《“停止适用”齐玉玲案“批复”之正面解析》(郑贤君)、《齐案“批复”并非解释宪法最高法院不应废止》(胡锦光)、《我国法院是否可以解释宪法》(张千帆)等等,随后,关于“齐玉玲案”司法批复的学术争鸣也基本停止,从司法审查的途径来寻找突破合宪性审查瓶颈的学术企图逐渐被主流学者所放弃。
三、“违宪审查”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
在“司法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方向不断受到学界质疑的情形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现行《宪法》《立法法》的规定行使对法规条例的违宪审查权来搭建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的实践平台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最直接的制度推动力是2000年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2000年《立法法》第90条非常明确地肯定了违宪审查的对象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宪审查的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宪审查的提请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类是上述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从实践层面来看,推动“违宪审查”影响最大的当属“三博士上书”[7]。2003年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腾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的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参见百度文库:《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https://wenku.baidu.com/view/bac48cfd910ef12d2af9e74f.html。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三博士在建议书中写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建议书》建议审查事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7条第1款规定的“超越权限的”和第2款规定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7条第1款规定的“超越权限的”和第2款规定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建议书》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6条规定,被收容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遵守收容遣送站的规章制度,这是授权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可以对被收容遣送对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实际上赋予了行政部门具有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该办法的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收容遣送站要及时组织遣送。被收容人员留站待遣时间:省内的一般不超过十五天;外省的一般不超过一个月。”这说明,有关行政部门可以把那些没有违法的人关押在收容所里,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长达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我们认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国务院没有权力制定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行政法规。我国宪法以及立法法颁布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7条第1款规定的“超越权限的”和第2款规定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应该予以改变或撤销。基于上述说明,《建议书》提出:“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毋庸置疑,“三博士上书”在推进违宪审查领域影响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制度收益就是: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当然,“三博士上书”取得的社会影响是积极的,但从构建合宪性审查理论的角度来看,却存在严重的法理瑕疵。“三博士上书”是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条件为限的,但是,在《建议书》中,“三博士”并没有论证他们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对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属于“行政法规”。事实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而“行政法规”的概念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现行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采取行政措施,发布命令和决定。很显然,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早于现行宪法产生,而现行宪法生效之后,国务院作为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也从未发文认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所以,从严格的违宪审查理论来看,“三博士上书”提出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的法理和法律依据都不足,这也充分反映了即便是在社会上形成热点的合宪性审查事件,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在理论上立得住,在制度上推得开。
对于基于2000年《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这项违宪审查机制落实的推动,实践中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还有胡星斗教授先后多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某些法规和制度的合宪性的事例,例如,2004年11月,胡星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8],以及2010年4月提出的《对歧视性、多轨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9],但总体上看,“公民上书”推动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和制度化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也很不够。
四、“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推动了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制度化
尽管设立什么样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等曾经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亮点”“热点”,但由于在法理上和制度上都没有形成比较科学的学说,故在实践中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力。真正对于合宪性审查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还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在加强宪法实施监督方面的实践。
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通过将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公安机关”扩大解释后包含了“国家安全机关”该决定所列出的宪法条文包括:第37条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4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从而开启了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序幕。该《决定》规定:“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则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上述决定从法律功能来看,是最典型的“合宪性审查”文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的充分肯定。2011年8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第1款和第19条的解释”明确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9)项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对外事务的职权,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属于国家对外事务中的外交事务范畴,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统一实施。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第1款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规定,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上述解释中蕴含了“合宪性”的基本要求和判断,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行使合宪性审查权。
鉴于现行宪法把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发展轨迹,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在合宪性审查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并且应当是合宪性审查工作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值得一提的是,从执政党关于加强宪法实施的要求来看,对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期待和要求也主要是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而言的。例如,2014年10月23日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原有的监督宪法实施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在保证法规条例合宪性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0]。报告显示,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法工委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据悉,1527件審查建议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有1206件,其中建议对行政法规进行审查的有24件,建议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的有66件,建议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有1116件。根据2016年中国建筑业行业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对地方性法规中关于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于2017年2月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地方性法规中直接规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或者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条款进行清理,适时予以纠正。目前已有7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改。根据2017年4位学者联名提出的审查建议,对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超生即辞退”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于2017年9月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有关地方性法规中类似的控制措施和处罚处分处理规定作出修改。目前已有1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改。根据2017年上海大学等20多所高校108位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联名提出的审查建议,对地方性法规中规定的著名商标制度进行审查研究,于2017年11月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有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规予以清理废止,并致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建议其对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同步进行清理。
由此可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有一定的制度基础,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履行宪法所赋予的监督宪法实施职责方面,在根据《立法法》规定对法规条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作机制。党的十九大从维护宪法权威的高度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既是对既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方面工作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同时也对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方面的作用表示了更多的期待。
党的十九大之后,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在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专家提出的“监察法缺少宪法依据”[11]的观点,2018年两会期间,首先于2018年3月11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第52条在现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之后单设“监察委员会”作为第七节,并且增加第123条到第127条,详细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性质、法律地位、组成、领导体制和活动原则。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過《宪法修正案》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之后,才于2018年3月20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并在《监察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充分体现了监察法的立法“合宪”的特征。另外一个体现“依宪立法”的例子是此次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而在此之前,仅由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明确了设区的市人大及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也就是说,在宪法修正案没有明确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之前,设区的市享有立法权只符合《立法法》的规定,具有“合法性”,而不具有“合宪性”。而根据《立法法》第3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很显然,立法法自身规定的设区的市享有立法权的规定与《立法法》第3条规定的“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不一致,为了解决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合宪性”问题,2018年修宪时把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写进了宪法文本,从而保证了立法法关于设区的市享有的地方立法权“合宪”,之所以这样规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下“合宪性审查”范围的感染和影响。
此外,根据199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的建议,全国人大可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不过在过去的25年中,在宪法不做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确实很难推动合宪性审查机构的成立。故此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12],虽然只在法律委员会之前加了“宪法和”,但这样的变动意义非凡。一方面,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之后,对于此次宪法修改应当修改的内容仍然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新的修宪建议,这充分表明了执政党“依宪治国”和尊重宪法修改客观规律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利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专责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自身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从而真正地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到实处,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得合宪性审查成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并成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的制度依托。
总之,在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40年中,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从无到有,以1982年现行宪法将宪法实施监督的职责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契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全面推进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建设,最终这些努力在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现行宪法第5个修正案中以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得到了制度化的体现。上述过程是不断渐进的过程,其中学术界的深入探讨以及法律实践的不断推陈出新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可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要求,只要在实践中采取确实有效的机制来落实合宪性审查的各项措施,我国的宪法实施监督工作必然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对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价值的落实起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2] 曹志:《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7/content_2278.htm。
[3] 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 马岭:《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理由”探析》,《法学》2009年第4期。
[7] 杨涛:《宪政视角下的“公民上书”》,《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6年第2期。
[8] 阿富:《向现行户籍制度提出违宪审查》,《时代信报》2004年11月25日,http://post.blogchina.com/p/68035。
[9] 袁诚:《胡星斗上书人大呼吁对社保多轨制进行违宪审查》,《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4月16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416/14/314572_23340693.shtml。
[10] 陈菲、熊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多起备案审查典型案例》,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whhy/12jcwh/2017-12/25/content_2035097.htm。
[11] 陈瑞华:《〈监察法〉草案存在的七個问题》,http://wemedia.ifeng.com/36271260/wemedia.shtml。
[12] 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in detail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oversight bodies and the constitutionality review mechanism in the past 36 years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in 1982, the mainstream view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examples of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practices, and propos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mechanism in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a number of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such as “legislation priority,” “judicial review,” “unconstitutional review”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both in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Howeve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only have the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 and really possess the i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nty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promoting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and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 It is a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in supervi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past. The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ssed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anged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aw Committee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mechanism in China.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ill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assist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in supervi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review work; organization priority; judicial review; unconstitutional review; governing the n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al Law; ruling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al Law;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