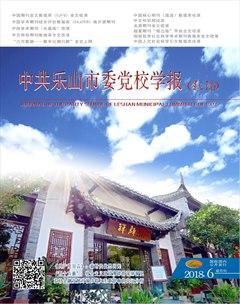《破产法》第四十三条司法实践研究
杨云超
摘 要:我国破产法43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而实践中存在破产财产还有升值空间,统一适用终结程序可能会阻碍破产财产的增加,出现形式公平掩盖实质不公平的情况。通过司法实践案例研究,对比英国、德国此类案件司法实践,得出结论:债务人财产还有升值余地时,应坚持实质公平扩大债务人财产,保障各方利益。
关键词:破产法第43条;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债务人财产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6.015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6-70-05
2006年《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关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在新《破产法》第43条中有先后顺序,即优先清偿破产费用,这意味着: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普通债权。新《破产法》第43条第4款规定针对的是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适用,严格适用该规定将会导致破产程序终结,其结果是对债务人进行注销登记。一旦债务人被注销,在清偿率本来就低的破产案件中,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就完全丧失。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财产仅能支付破产费用,但不能清偿共益债务,如果继续执行破产程序并不能实质扩大债务人财产;二是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能支付破产费用,但继续执行破产程序还能恢复、扩大债务人财产。第一种情况是标准的第43条的情况,应当继续进行破产程序;第二种情况是如果严格按照新《破产法》第43条规定,应当终结破产程序,但是从做大“债务人财产”这块“蛋糕”出发,要保障后续顺位主体利益,此种情况下是否值当终止破产程序值得探讨。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范围之厘定
破产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为顺利进行破产程序而必须随时支付的费用。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对第三人所负担的债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在债务人财产中应当随时清偿,这意味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优先于破产债权得到清偿,即清偿顺序为: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普通债权。破产案件是发生在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前提下,在有限的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供债权人清偿的财产相对减少。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范围的界定涉及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三方利益。新《破产法》对198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称旧《破产法》)关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范围做出了修改。
(一)新、旧《破产法》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规定
旧《破产法》第34条规定:“下列破产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1.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所需要的费用,包括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2.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3.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在破产程序中支付的其他费用。”由此可以看出,旧破产法将管理人为执行破产事务产生的费用统一规定为破产费用,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并没有进行区分,其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美国、日本、德国等破产立法例,即合并制。不区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为司法实践带来很大困惑,为此,在2006年通过的《企业破产法》专门对此问题作出了立法回应,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进行区分,以此来解决司法实践的难题。
新《破产法》专门在第五章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以及二者的清偿顺序。新《破产法》第41条明确界定了破产费用的范围。第42条规定共益债务的范围。第43条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新《破产法》一改旧《破产法》的合并制为分别制,将破产管理人执行破产事务产生的费用区分为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其在立法体例上采取我国台湾地区破产“立法例”,即分别制。虽然立法者力求在新《破产法》中通过立法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破产案件越来越复杂,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二)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之比较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具有以下相似之处:第一,二者都是破产管理人在执行破产过程中,为了管理破产事务所产生的费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破产管理人、债权人等主体利益。第二,按照新破产法第43条规定,二者在破产财产中随时清偿,即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不受普通债权的约束。债务人財产足以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总和是理想状态;而在实践中,通常会有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小于破产费用或者小于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二者总和的情况,此时严格区分二者的不同之处便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新《破产法》在用词方面,将破产费用范围界定在“费用”,共益债务的范围界定在“债务”。费用是为破产管理人推进破产的顺利进行而必须支出的成本性费用,债务是破产管理人在执行破产管理事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之债。第二,新《破产法》第41条以列举的方式定义破产费用,从列举的范围看,诉讼费用、管理变价费用、聘用工作人员费用相较于共益债务都是一种消极维持。新《破产法》第42条同样以列举的方式定义共益债务,从列举范围看,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侵权之债都属于为了积极扩大债务人财产的支出,属于积极维持。第三,新《破产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二者适用的清偿原则因此有所不同。有学者把新《破产法》第43条清偿顺序总结出三条原则,即随时清偿原则、优先清偿原则、按比例清偿原则。
二、《破产法》第43条司法实践之窘境
新《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以下简称《管理人报酬规定》)第12条第二款: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和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上述两条规定为界定破产案件陷入窘境之法律依据。
(一)窘境之案例检讨
通过案例检讨,可以清晰地洞察破产财产小于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总和的窘境。某冷气机电工程公司申请破产案中,该机电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冷气公司”)成立于1985年8月1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以空调制冷管道安装为主要业务。由于经营管理和公司战略问题发生严重亏损,到2004年12月31日,冷气公司对外负债822527.42元,资产总额为252763.09元,其中包括对外债权218906.93元。因此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但是冷气公司对外享有218906.93元债权,管理人通过各种渠道均未核查相关债务人联系方式和地址,无法对其进行催收,所以冷气公司实际破产财产仅33856.16元。管理人在管理中所产生的费用为89164.5元,此时债务人财产小于破产费用,因此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在冷气公司破产案件中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是正确的,虽然从表面看,债务人总资产252763.09元足以支付破产费用89164.5元,但是组成其资产总额的218906.93元对外债权属于不能收回。如果此时不终结破产程序,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支出只会增加,不能补齐的窟窿只会越来越大。
但是,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出发,实践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某实业公司破产案中,该实业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对外负债60427126.61元,账面资产8772.62元,资不抵债,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管理人发现,该实业公司破产财产合计人民币138772.62元,为管理破产事务产生139765.87元,债务人财产与破产费用之间差额为993.25元。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在该破产案件中,法院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时终结破产程序。但是,通过对比冷气公司破产终结的情形,本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债务人财产与破产费用之间的差额仅为993.25元。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债务人还存在不动产的情形下,或者还有可能将债务人财产这一块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终结破产程序是否真正有利于维护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真正做到了实质公平?
深圳M公司是一家旅游企业,以经营航母军事主题公园为主。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作为其债权人,2004年10月29日向深圳中院申请M公司破产。2005年2月25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M公司破产还债。2010年3月4日,深圳中院裁定终结M公司破产案的破产程序。在2005年3月1日—2006年7月20日,为了实现M公司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做大债务人财产这块蛋糕,M公司继续正常经营,并且在此期间收入8849915.06元。对比M公司与实业公司破产案件,M公司在还有可能做大“蛋糕”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终结破产程序。因为债务人财產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随之发生的法律后果是对债务人进行注销登记,即该主体彻底退出市场,并且对其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不再承担责任,这是公司法赋予法人的独特优势,也是成熟市场应有的退出机制。
结合实业公司和M公司破产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但是债务人的破产财产还有较大升值空间,继续进行破产程序可以做大债务人财产这块蛋糕,我们是否可以考虑M公司破产案中的思路,暂时不终结破产程序,尤其是对于目前升值空间较大的不动产财产。
(二)窘境之学者观点
对于以上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司法适用窘境,现行法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规定。在学界,有学者已经对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清偿问题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新《破产法》第43条是漏写了共益债务,可能是立法者在没有细细分析《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破产费用”概念与《企业破产法》中的“破产费用”概念有重大区别的情形下,简单套用了原有的条款规定所致。笔者对此观点持不同态度。破产法的理念之一是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债权人与债权人、债权人与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利益。如前述案例分析的M公司破产案,如果统一的规定为适用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规定,管理人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将会损害共益债务相对人、债权人的利益而丧失实质公平。
众多学者已经对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的清偿顺序问题提出了可行的法律建议。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破产案件复杂性的增加,本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也应当受到重视,为破产司法实践提供更多的可行性建议。对此情形,可以参考英国、德国在“无产可破”案件中的操作模式,为新《破产法》第43条司法实践提供新路径。
三、英、德模式对我国破产法第43条司法实践的借鉴意义
破产发生的原因在于破产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之债。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时,说明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已经陷入不能清偿的境地,甚至不但不能清偿债务,而且连破产费用都不能清偿。在学界,有学者称之为“无产可破”案件。按照我国新《破产法》第43条规定,破产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而在英国和德国却并不是直接终结破产程序。
(一)德国“无产可破”操作模式
德国破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开始破产程序的,由破产法院任命一名破产管理人。法官在选任破产管理人方面拥有较大的决定权,法官可以根据案件难度、赚钱与否等综合因素评析之后,任命适合的破产管理人。法官在考虑此类案件“适合”破产管理人时,可以采用“风水轮流转”的方式指定。即指定在之前破产案件中已经赚钱的管理人担任“无产可破”案件的管理人,待其他尚未赚钱的管理人管理几个赚钱案件后再担任“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采用此种平衡的方式指定管理人,不但使管理人能在公平之中创造自身价值,也可以使管理人肩负起社会责任。有学者总结此种模式为“交叉补贴”的操作模式。
我国现行《破产法》第22条第一款也规定:破产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虽然我国的破产管理人也是由法院指定。德国模式对法官的独立性和职业操守要求较高,而我国目前司法现状还未达到如此,不可能完全照搬德国模式,否则法官权力过大将使这一领域成为司法腐败的高发区。
虽然笔者不赞同完全照搬德国模式,但是德国模式也有值得借鉴的意义。德国模式的特色在于将最大的自由决定权给法官,由法官自由决定,同时要求管理人承担起社会责任。而我国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在破产法院内部形成一种规定:将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单中的管理人每次受理案件的实际管理报酬做出详细统计,一定时间内已经在破产管理中取得较高管理报酬的管理人是法院指定“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的优先考虑对象。将德国模式下的法官自由决定权规则化。当出现债务人财产刚好或者尚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尤其是案例检讨中M公司类型破产案件情形,管理人仍应当尽最大能力追查是否还有可以增加债务人财产的财产,在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评估时,考虑在一定时间内债务人财产是否还有较大的升值空间。若经追查或者法院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确已没有可以追回的财产、债务人财产已经没有升值空间来增加债务人财产,适用破产管理人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此种继续管理模式会增加破产费用的支出,但是我们选取的管理人是在之前破产案件中已经取得高额报酬的管理人,此时可以降低破產费用的比率,从破产费用中承担继续管理的费用。若经追查发现,债务人财产还有升值空间,债务人还存在可追回债权,继续管理模式就真正实现了实质公平。
(二)英国“无产可破”案件操作模式
英国破产司法实践中遇到“无产可破”案件的具体做法是政府介入,即破产署会指定官方管理人来负责接手并处理“无产可破”的案件。原则上凡是私人管理人赚不到钱的案件就由官方管理人办理。政府从所有破产人的不动产变价款中提取17%的费用作为破产和清算不动产基金,用于管理“无产可破”案件。英国此种操作模式可谓是“取之于债务人,用之于债权人”,根本上符合破产法立法初衷。笔者持赞同意见。
将英国“无产可破”操作模式引入我国债务人财产不足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实践,同样可以从债务人财产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管理基金”。管理基金主要作用是为了保障管理人尽职追查债务人财产,当出现债务人财产不能清偿破产费用或者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时,不当然终结破产程序,由管理人继续履行管理职责。若经追查证明确已没有可以追回的财产或者债务人财产没有升值空间时,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出现债务人财产不能清偿破产费用之后的追查费用从管理基金中支出。若经追查扩大了债务人财产,则将此基金中的费用返还到债务人财产,用以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以及债权人债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出现债务人财产小于破产费用或者小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总和时,不能直接适用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规定。在坚持新《破产法》第43条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对此问题明确化、具体化。具体操作模式可以借鉴英国、德国的模式,一是让管理人肩负起社会责任;二是法院介入在破产之前提取一笔基金,采取“取之于债务人,用之于债权人”的模式,尽可能有效增加债务人可供用于清偿的财产,以此来保护社会利益和债务人、债权人利益。
参考文献:
[1]李永军,王欣新,邹海林,徐阳光.企业破产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2]]霍敏.破产审判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3]邢丹.破产案件窘境之处理[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4]徐辉,冀宗儒.破产法案例评析[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5]韩传华.企业破产法解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6]李飞.当代外国破产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康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