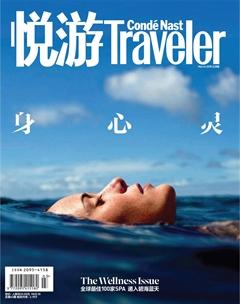爱的治愈

是超越阶层、超越种族、超越地域的爱治愈了柏林,治愈了我。
在去跳芭蕾舞的路上,从亚历山大广场地铁站走出来换有轨电车,一幅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个公益广告,关于平等,关于世界和平。我在车上看着这幅广告一闪即过,突然胸口变得滚烫,一种陌生的感觉击中了我:我爱柏林。
这是多么陌生的感觉,我对柏林从来没有过爱,只有抱怨和不满,我想过无数次要离开它,留下来的理由仅仅是我也没有能力搬到其他地方。我在咬紧牙关忍受,忍受没有阳光的冬季,忍受种种陌生,忍受陌生人面无表情的脸庞,忍受脏乱差的地铁,忍受大部分消费场所还需要用现金的陈规。我身边的朋友们大多数对柏林都赞不绝口,就连在杂志和公众号上的柏林也大多是赞誉。也许只有我,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柏林,我是一个格格不入者,或像一条鱼走入了沙漠。我和当年暂居在此的纳博科夫一样,拒绝融入,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从生活方式来说,柏林又算是最“朋克”的一个。它地下、反叛、反商业,这里到处是涂鸦,到处是乐队演出海报,拥有无数的跳舞音乐俱乐部,夜生活丰富,写着“BIO”字样的有机超市随处可见,柏林人热衷于素食和简单又实用的穿着,以黑色为主。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会一下子爱上这里。可惜当我搬到柏林时,很快就怀孕了,生了孩子以后,没什么时间享受这里的优点,反而看到的都是缺点。这让我对柏林产生了一种幻灭感。东西德合并快三十年了,当年留下的阴影和断裂感依然存在。我这么一个敏感的人,看到黑暗的过去,让我感觉不适和痛苦。它不像巴黎,从未毁于“二战”,曾经的柏林在“二战”后已被彻底摧毁,新的精神尚未重建起来,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依然在流血。
柏林曾经出产大明星、大艺术家和作家。他们的生活都被“二战”彻底搅乱了,他们的选择也导致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和身后不同的名声。马琳黛德丽,1901年生于柏林,“二战”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邀请她回德国,她拒绝了,后来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她亲赴战线参加慰问演出,积极参与和资助战争时的避难和流亡者。“二战”后,她回到柏林演出,市民对她热烈欢迎,右翼媒体却攻击她,将她视为“叛国者”。直到2001年,柏林政府终于为当年对她的敌意正式道歉。
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莱妮里芬斯塔尔,只比马琳黛德丽小一岁,她拥有导演的才华,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和资助,拍了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战后,她因受纳粹牵连被关进监狱,流亡多年。后来她出过一本厚厚的自传,剖白自己的人生和当年的选择,但艺术和政
这是柏林第一场雪。昏黄的路灯下,一片片雪花_從天而降,路上行人的表情都变得柔和起来,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我拖着有点发酸的腿,穿过马路去坐有轨电车。在亚历山大地铁站,我看到一句话,“ICH LIEBE DICH”,是德语的“我爱你”。
治之间的立场问题一直缠绕着后世的人们。苏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里谴责她的审美其实正是法西斯的审美。
他们在柏林是否留下了痕迹?柏林又吸收和保存了多少他们思想的精华和黑暗?我不知道,两种力一直在角逐,过去与未来、黑暗和光明。光明总要多于黑暗,废墟总要进行重建。
从舞蹈教室走出来,雪花漫天飞舞。啊!这是柏林第一场雪。昏黄的路灯下,一片片雪花从天而降,路上行人的表情都变得柔和起来,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我拖着有点发酸的腿,穿过马路去坐有轨电车。在亚历山大地铁站,我看到一句话,“ICH LIEBE DICH”,是德语的“我爱你”。
我又想起我曾在地铁里看过一幅关于抵制血汗工厂的廉价快销服装的广告,在路边看到过帮助贫困儿童的广告。在看电影前播放的广告片里看过的关于上夜班的公共汽车司机的生活的广告,那是一个关于提高最低工资的广告。从对穷人和公平贸易的角度讲,柏林应该是欧洲首都里最“左派”的一个了。
仿佛就是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开始习惯了柏林的生活,至少我发现了它最卓越的一面:超越阶层、超越种族、超越地域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