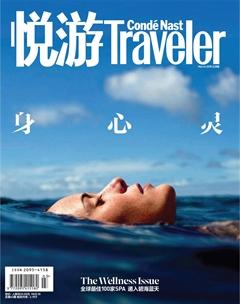诗意栖居
夏莲



如果要将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分个究竟,差别也许是一时间一这个维度。在崭新而相似的中国城市里,人们头也不回地向前奔忙,似乎只看得到「今天」和「明天」,唯在乡村还幸存着「昨天」。我在这次旅行中,到浙江乡下去尝试了几天当代乡居生活。所谓当代,是因为乡村中有城市回望者所填入的舒适和野趣。趁「昨天」还在,下乡去吧。
“我想留下的是记忆”
进入马岭脚村的第一天,我因手机崩溃而完全失联,被迫暂别信息时代。随后几天,我发现这种断电生活正是马岭脚村山居生活的—种镜像。我重温了旧时等一个人只能不见不散的时光,而这座已改名为不舍·野马岭中国村的新式山村所要呈现的,正是村子的新主人吴国平想要找回和重写的记忆。
这座叫“马岭脚”的小山村未来或许会被写进教科书。在过去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它都籍籍无名地蜗居在浙江省浦江、建德、桐庐三地交界的崇山之中,几乎遗世独立,唯有一条马岭古道曲曲折折通向山外。80米的山势落差让依山而建的马岭脚村有种一览无遗的明朗,又有一种小村庄难得的气魄。前景是层层叠叠的黑瓦夯土民居,民居后的山坡上摇曳着一丛丛四季潇洒翠绿的毛竹。视线再向上移,三面绝壁耸入云烟、若隐若现,平白无故地给村子点染了仙气。这一幕看得我十分惊讶,那时车刚驶出马岭隧道,我很难想象在照片上所见的隐世山村这么快就出现在省道的路边。
道路三次改变了村子的命运。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在那之前,村民深居山里,不通水电。省道建成后,村民到邻县建德梓洲村的时间从两小时缩短到五十分钟。第二次变迁是在2008年,近六百米长的马岭隧道贯通,原本蜿蜒曲折的山路变成了直线。也因为这样,这个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古村等来了第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被开车经过的外婆家创始人吴国平发现。
人到中年,人称“Uncle吴”的吴国平到了回望的年纪。当时,这位从餐饮业起家的时髦绅士花五年时间跑遍了全国的原生态村落,想要寻找—个制造记忆的落脚点。“我在莫干山见到司徒雷登,很受触动。我问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做法国山居?他说他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过,他想找回祖辈的记忆。我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记忆是什么呢?”
吴国平初见马岭脚村,三四十栋夯土民居几乎人去楼空,村民已搬至山下的新村,但村口那棵一千二百年的榧树和三面颓而不倾的夯土墙像是钉在了他的原乡记忆里,“这棵树看着几十代人来了去了,还有最打动我的这三堵墙,日晒雨淋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再过段时间,墙可能就没了。我要把它们留下来”。在他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的杭州,城市和农村还没有太大分别,“住的是泥巴墙,水要到弄堂口去挑,还要倒马桶,唯一的工业标志是电灯”。童年带着土腥味儿,记忆好像也得掺着土腥味儿才对,这座夯土村落正像是他回望过去的分身。2014年,吴国平租下村子,找来几个好友一起筑梦,有丁磊、Gad建筑设计的老友,还有内建筑的这设计师沈雷。他对伙伴们说:“我们都会老的,我们找一个老了能待着的地方,里面还有时髦的年轻人出入,好不好?”这—次,与他过往的经验全然不同——无关生意,他想留下—小段“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史”。
我在迷雾中走进石墙与篱笆构筑的村落入口,石缝中的苔藓吸吮着雨雾中的能量,隔开的是公路——现代文明的表征之一。再沿湿漉漉的石板路曲折而上,夯土房、砖房、木板房参差错落。斑驳的墙体上恣意生长着野草,门当上附着青苔,溪水从山上淌下来——刚下过雨,活泼欢畅极了。这里有城市中最缺少的东西——纯粹的自然与时间的痕迹。
“这里的屋子完全是当地的生活长出来的。”吴国平的建筑师好友当时看完马岭脚村后对他说。所谓“长出来”是没有运用机械的、人搬得动的。所以吴国平改造村子的方式也退回到原始,在还未完工的野马岭里,工人们戴着安全帽挑着簸箕从我身边经过。因为不愿意破坏原有的石板路和植被,改造过程便以最原始的人工方式运输、施工,每块石头、每块砖、水泥、家具都是挑上去的。改造过程极其缓漫。
三年后,让Uncle吴一眼就喜欢上的夯土墙已经以另一种表达呈现:土墙被加固,与清水混凝土、黑色框架、玻璃搭建成一间通透的玻璃凉亭。残墙上依然有时间的裂纹,有藤蔓攀爬,又被植入了现代用途,比如嵌入了插座開关。在Uncle吴的设想里,这处凉亭会是一间充满烟火气的茶肉铺,“附近村子里做小吃的、卖菜的、养鸡的都可以到这里来摆摊,客人可以买整鸡回去、吃小吃或者把最新鲜的西红柿带回去”。村落还是要被还原以聚会、聊天、吃饭、居住的元素,才有生活的温度。对于山上开垦出的梯田,Uncle吴想由客人认领——自己种菜,累了在树下歇脚,渴了捧山泉来喝,用洁净的食材自己动手做饭。“我虽然做餐饮,但在这里开酒楼不就又回到城市了吗?自己洗洗萝卜、青菜和烧饭不是蛮好的事?”
“这是一场确定关系的旅行”
时间可以在野马岭倒流,也可以被注入现代的需求和审美趣味,一切都是“可逆的”。野马岭的合伙人之一、建筑师沈雷欣赏欧洲对旧建筑保护的层级,比如一座古堡,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人改造留下的“时间的流线”。在野马岭,沈雷的改造是一种“可逆的”的加法。“保留温度,加建一些新的东西,让它整体看起来是符合当下的。”至于新的东西好不好,他也非常洒脱:“觉得不好,二三十年后拆掉没问题。”重要的是,拿出村子的旧照做对比,发现原先的每一间屋子、每一座石桥,甚至一根木头柱子、一堵残墙都还在。我和Uncle吴在大堂的火炉旁捧一杯热茶聊天,这里原本就有漂亮的苔藓和石头,所以大堂索性被做成了一间半开放式的玻璃花房。地面动都不动,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让它自然滋长。
75间由石板路、石桥串联起来的鳞次栉比的客房已被填入现代生活方式。冬日山间湿气重,但在房间里地暖热得人冒汗。那些所能感知的奢华——大地般触感的棉麻床单、舒适得不想翻身的床垫、精致的工业感卫浴,甚至是马毛包裹的淋浴间门把手……实则融进了村落原有的质朴底色中,因为我头顶依旧是用旧木搭的房梁,背靠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藤编椅子,从四处搜集来的古董落地灯照亮着幽静的山中之夜。这些填充进去的旧物,与石墙上养出的青苔、房门上时间留下的斑驳、裂纹甚至虫洞一起,营造出一种“包浆感”,让像我这样的城市中的来客能透气。
傍晚时分,我走向村子高处回望野马岭,这里能见山、见水、见村、见云雾。天已经泛蓝,雾开始从四面八方沿着山脊流泻入山谷,将村子蒙上一层纱幕。客房灯光亮起后,依然是幽幽暗暗的黄色光晕。这一刻看去,这里仿佛还是六百年来那个静谧的小山村。
在离野马岭一小时车程的桐庐,还有一个人在构筑当代乡土记忆一来自南京的建筑师张雷。巧合的是,他第一次动手尝试的也是夯土民居。翠竹掩映的戴家山村是浙江唯一的原生少数民族畲族的聚集地。张雷构建了云夕戴家山——一个乡村图书馆和一间带有泳池的民宿。他以山民最熟悉的扫把草编织露台围栏,用柴垛砌墙,又在夯土民居内部嵌入现代建筑的框架。从建造过程开始,到融入乡村生活的文化经营,张雷的“新”与“旧”都在构造一个城市中的下乡者与原乡者共同生活的场景。
云夕深澳里是张雷在桐庐的第二个乡村实践,也是“80后”女生小熊的当代乡居尝试。桐庐县深澳村距离杭州市区不到一小时车程,下高速转向山脚开去,导航将我带入常见的江浙农村里。这里背靠丘陵,有溪流从村后流过。我们有些迷失在二层小楼和粉墙黛瓦混杂的挟窄巷弄里,直到从一个巷口瞥见了那片比周围更雪白一些的墙体。一千九百年的时光从这个人口稠密的村子走过,它却刚刚迎来第一个真正的外来者——云夕深澳里。
云夕深澳里由客厅、社区图书馆和客房三栋独立建筑串联而成。跨过门前淌着水声的沟渠,进入客厅右转掀开布帘,一股书香混杂着上了年头的木头味儿扑过来,调和出一种立刻让人沉静下来的气场。云夕图书馆的前身是一幢清代老宅景松堂。一面面书架铺陈在老宅的天与地里,坐在任何角落,你都能看见从天井掉落的淅淅沥沥的雨线,仿佛一卷被洗掉的录音带上出现的杂线,让人沉入一种晃神的空白里。我在那里见到了小熊,大多数时候,她会像个客人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
小熊是桐庐县莪山乡的畲族人,公务员辞职后,因为向往自由的生活,与一直在农村寻找做乡建项目机会的建筑师张雷一拍即合,创建了“云夕”。云夕的英文名是“Ruralation”,意为“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云夕与我这样寻求乡居生活的城市人产生关系之前,它首先要面对的是与原生建筑、当地村民的关系。
有着一千九百年历史的深澳村是申屠姓氏的血缘村落,还难得地保留着四十余幢明清堂楼和一百多栋民国建筑。张雷和小熊反而是从中挑了“同比之下雕花不算特别精美”的景松堂,因为出于对美好旧物的敬畏,“所以不敢去要特别好的房子。好的东西,只可远观,不好意思动手”。景松堂在改造前原有六户人家居住,在改造中,张雷坚持“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学习”。“乡村不是一个实现建筑师个人理想的试验场。”张雷在《莪山实践》中说。与实现建筑师的个人理想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向乡村本来的生活智慧学习,“去延续地域的时间性,延续日常生活的温暖文脉”。例如,原本居住在景松堂的老人们担心20年租约期满之后,分不清各家界限,自己的后代无法返乡认祖,所以张雷在地板上画上红线,以作为分界线;拆门槛是当地人的一大忌讳,所以景松堂的门槛被悉数保留在改造过的地板下面;客厅原本是废弃的牛栏和猪栏,张雷用拆除的石头重砌了一个酷酷的方盒子,与当地民居唯一的区别是他保留了卵石墙裸露的肌理,然后刷白。“但是住在对面的老人觉得正方形棱角太锐利,会对着她。我们就放弃了设计上的一点点追求,加上了乡民都能接受的斜屋顶。”小熊说。对于云夕来说,一切都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然后才是以当代眼光去再创造和分享。
下午四点,雨还没停。村里的小学生放了学,叽叽喳喳、三三两两地跑来图书馆做作业。他们一边做作业,一边抓起云夕的阿姨们刚炸好的“油几”(一种当地小吃)往嘴里放。“在我小时候生活的农村里,村头的一家小店就是大家茶余饭后交流的社区。”这间社区图书馆寄托着小熊把阅读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融合到乡村里的尝试,她也希望能在日益“空心化”的乡村重新营造出社交中心。考虑到村民的需求,图书馆中至少一半的书籍都是儿童读物、养生书和故事书。
深澳村或许是二十年前的周庄、乌镇,这个百废待兴的村落有太多改头换面的可能,但需要更為小心翼翼地开发。在石板路巷子里随意散步,所见均是砖墙斑驳、芭蕉掩映。恭思堂、怀素堂、凤林堂……在这些荒废的明清老宅里,祖辈留下来的精美木雕与当代农村填充进去的粗糙的铁皮隔间并存,住在里面的多是一些独居老人。怀素堂门楣上的彩色气球和古老厅堂中悬挂的“囍”字,表明这里刚办完一场婚宴。尽管老宅早已失去居住功能,但这里仍是举办家族大事的场所。与这些正在腐朽、亟待拯救的建筑相比,俗称“澳”的引泉暗渠是深澳村穿越时间的存在。在整座古村建村之初就先构建起用水体系,饮用水、生活用水、污水分别由不同的水渠引流。全村目前还保留有17口坎儿井、12个水塘。走在老街上,水渠因为下雨而发出有生命力的声响。
这些千年延绵不断的生机如同在乡村衰落的背景下一息尚存的人情关系和地域文化。在清晨走街串巷的流动豆腐摊、猪肉摊旁,小贩发出悠长的属于记忆中的叫卖声,石板路上三三两两的狗游荡着,温顺地避开行人,又追随着。在村子入口的申屠氏宗祠,练毛笔字的守祠人和退休后义务为游客讲解村史的老人让人隐约感受到曾经宗祠和家族的影响力—老先生向我一一列举祖上的重要人物和村里的美德典范。宗祠堂口的《告宗亲书》里表彰着古稀老人申屠先生捐赠一万斤大米的价款以祭祖并供养村中百岁老人的事迹。这些被反复传颂的善举自然而然形成了中国古代民间的道德规范。
反观自己下乡的愿望,或许已超越了回归清净生活本身,更像是重新体会以血脉、聚落为纽带的文化传承,而这些都早在城市生活中被瓦解。无论晴雨,从云夕深澳里的“白盒子”散发出的橘黄色的光都是这座古村温暖的存在。在那里面,我跟着民宿的阿姨一起擀面、翻油几,村里的孩子在身旁看书、写字,当地大厨烧的菜永远少不了时鲜——春笋、鲈鱼、地皮菜。在对面,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会在天气晴好时,搬把椅子在门口晒太阳,用吴语跟你聊上几句。始终贯穿着的声响是门前的渠水,流了千年,以后还会继续流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