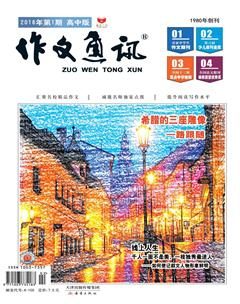希腊的三座雕像
陈静


希腊,四月的清晨,晨光熹微,微风轻拂。远远看见米勒岛入口处的两尊雕像,我不觉停住了前行的脚步。
左手边是当年米勒岛上那位专制的君王——西绪弗斯。他傲视万物,面露戾色,双眼闪烁着锐利的令人恐惧的光芒,恍若一只伺机捕食的恶狼。他的脚底,踩踏着被铁链捆住的奴隶的脊背。那些奴隶的身形被艺术化地缩小,嘴巴却夸张地大张着,仿佛在控诉着那满身狼性的君主人性的缺失。
在神话里,西绪弗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亵渎神灵,随意践踏百姓,常年对克里特岛征战,虚耗着国力,逼得人民揭竿而起,却只换来他更残酷的镇压。后来,诸神为了惩罚西绪弗斯,便让他做着推巨石上山的无效无望的劳动。
轻揉额角,想舒缓一下被思绪刺痛的神经。一转眼,视线恰巧与右手边柏拉图雕像那略带忧郁的目光相接。他身着破旧的长衫,双手枯瘦。他的雕像背后,是一群对他指指戳戳的市民的雕像。看到这儿,我的心一点点被愤懑注满。
在世时,柏拉图潜心治学,从不争虚名浮利,面对质疑,也只是默默忍受。一生贫病的他在《理想国》中发出了无比沉重的哀叹!就是这样一个羔羊般温驯的哲人,生前很不得志,死后又被学生拉下神坛,掀翻在地。直到14世纪,他的思想才照亮西方哲学的天空。
难道“狼性”会使人偏离正轨,变得凶残暴戾,而“羊性”又会让人逆来顺受,生前的理想难以实现?
面对眼前两位性情、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物的雕像,我顿感彷徨无绪。踉跄着脚步,走到爱琴海边,任温润的海水打湿双脚。
蓦然抬头,又瞥见一道目光——威严而又慈爱,令人景仰却又不致畏怯。我挪动脚步,靠近了那道目光的发源地:是宙斯!他张开双臂,微微敛眉,一只手持着雷霆,一只手高擎着橄榄枝,在薄雾笼罩的清晨,带给人的是无限的清晰和宁静。
心,一点点被濡湿。我看见许多早起的人拥到他的身边,或祝福,或微笑,更多的人则是对着他喃喃诉说着久藏心中的夙愿。
宙斯面色恬静,不怒而威。他是刚烈的,面对凶残的父亲,铤而走险,救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地母盖亚和她的12个儿子攻上奥林匹斯山时,他沉着指挥,化险为夷。他又是温情的,他摘下百合,送到美丽的伊娥手中;纵使伊米阿洛斯当众欺骗他,他也只是轻叹一声,化解恩怨。
坐在宙斯的脚下,感受着他的庄严和慈悲,心底萌生出无限的虔敬与感动。望着为宙斯而倾倒的希腊人,我恍然大悟:这个在大是大非面前如狼般果敢坚决,回归生活却又充满悲悯情怀的神,才是他们心中的王。如狼般英勇,如羊般温和,狼性和羊性的完美融合才能绽放出真正的王者之美。
再见,西绪弗斯!再见,柏拉图!我站起身,向宙斯雕像深鞠一躬,朝海滩走去。有狼的利齒又如何,没有羊的温和,只能如纵横半世的拿破仑一般,病逝在圣赫勒拿岛;有羊的温驯又如何,没有狼的勇武,只能如囿于心灵一隅的周作人一般,窒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
让心底住上一匹狼和一只羊吧!让狼去成就宏图霸业,兼济天下,承受生命中一切不可承受之重;让羊去给心灵筑一间温馨的居室,爱人,隐忍,承受生命中一切不能承受之轻。
阳光酒向海面,化成片片碎金。恍惚中,我听到了一支远古的赞歌:“我主用雷霆,一击沧海平;我主持橄榄,悲悯化人心……”
佳作点评
这是一篇游记,更是一则心灵感悟。作者描写的三尊雕像,实际上正代表了三种迥然不同的处世方式、三种不同的精神境界和三种不同的人生:一种失之于刚,一种失之于柔,另一种则是刚柔相济、剑胆琴心。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要想获得众人的认可,进而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就必须既有坚毅和果敢,亦有柔情和仁厚——即“狼性”和“羊性”的完美融合。作者融理入事入景,借历史和神话人物抒自身情怀,颇有创意。
(王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