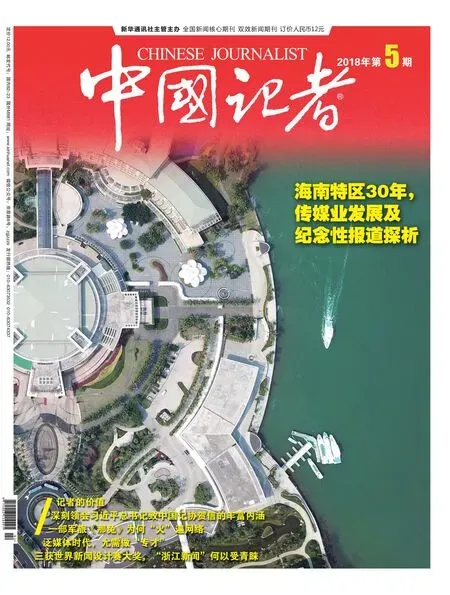泛媒体时代,尤需做“专才”
——一名“老新闻”走过的由“杂”而“专”之路
□ 文/侯 军
(作者是深圳新闻学会副会长、高级记者、深圳特区报原副总编辑)
我是1977年底进入天津日报社当记者的。一入门,就听老一代报人传授经验说,干新闻这一行,一定要让自己成为“杂家”。有一位老编辑还悄悄告诉我,当年,人民日报的老总编辑邓拓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欢迎杂家》,讲的就是做好记者的“独门秘诀”,一定要找来读一读。当时,邓拓的《燕山夜话》还是没解禁的“毒草”,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老同事说报社图书室就有,他还帮我找熟人“顺”出一本。我如获至宝地读了这篇《欢迎杂家》,为了记牢还认真抄了一份留底,才把原书还回去。从此,自己就在心里确立了一个目标,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杂家”——无论采访什么人,无论涉及哪一行的事儿,都要先让自己成为内行。因为邓拓说了,“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

侯 军深圳新闻学会副会长、高级记者、深圳特区报原副总编辑
此后几年,我节衣缩食,疯狂购书,作为对十年浩劫中严重书荒的心理补偿;而且如饥似渴地读书,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什么杂书闲书、有用的无用的,什么都读。其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杂”起来。而在最初的新闻实践中,我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知识的贫乏或广博对于新闻采写是何等的重要。具体说来,当一名记者具备了广博的知识储备,那么你采访任何行业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占据一个无形的“制高点”,相反,如果你的知识贫乏视野局促,你就会错失采访良机,留下终身遗憾——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记者队伍里的一员新丁,一天,突然接到一个指令,替一位休假的同事到一所大学去采访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当时我还是农村部记者,属于临时“客串”,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所知甚少,时间也不容许我做充分的准备。而且,到了之后才被告知我只有15分钟的单独采访时间,顿时心慌意乱,当我怯生生地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对方就微微皱起了眉头。接着,他让助手找来几份资料,很客气地对我说:“请记者先生先读一读这些材料吧,您刚才提的问题,我很难在15分钟里解答清楚,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它太……哦,因为它在这些资料里,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次失败的采访给我早期的记者生涯留下了一个羞愧难当的印记。而幸运的是,几年以后,同样是采访杨振宁,我却得到了一个“就地翻盘”的机会——那是在1985年秋天,当时我已是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了。一位负责高教报道的记者汇报选题时说,南开大学请回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创建南开数学所。届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要专程前来祝贺。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新闻线索。当时这位记者还是刚刚到岗的新人,对采访如此重量级的名人心存畏惧,希望我能跟她一起去。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自己当年的窘境,自然体会到一名新记者此时此刻那种紧张心理,当即答应与她一同采访,并一同研究采访计划。这时,我此前“恶补”的那些杂学就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世人皆知杨振宁是陈省身的学生,但往往不清楚陈省身还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的学生;而且,当年杨武之曾写诗赞誉陈省身,若干年后,陈省身又写诗赞誉了杨振宁……我为此次采访定制的采访计划,第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两代师生”的两首诗来破题……
那次采访非常成功:当时,主办方安排两位科学家会见记者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我因为有过一次“滑铁卢”的教训,怕被认出影响采访效果,就让同去的记者抢先提问。她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伶牙俐齿地抛了出去,只见陈杨二位相视一笑,顿时来了兴致,杨振宁拿过话筒,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从杨陈两代人的师承渊源讲到西南联大,又讲到在美国科研的突破与“陈氏定理”的关系,最后还讲到陈先生回到南开创建数学所的意义……转瞬之间,半个小时过去了,预定的见面会严重超时,现场的几十位记者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捞到,整个见面会变成了我们所在媒体的“独家专访”,而此次专访的绝妙之处在于:只提了一个问题,就得到了“超值”的回应。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杨先生不得不放下了话筒,显然意犹未尽,而坐在旁边的陈省身先生似乎还有话要说。主办方悄悄征询两位科学家的意见,结果是,两位记者“破例”被邀请与他们同车前往下一个参观点,一路上又延续着刚才的话题,谈了很多趣事。当天夜里,我们赶写出一篇既有现场感又有纵深感的新闻通讯《双星会南开》,登上《天津日报》头版头条。这篇稿件荣获了当年的中国好新闻奖,只不过获奖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因为在稿件见报前我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对我来说,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自己的实力抹去了前番失败的阴影。
这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我萌生了倡导“记者学者化”的念头,并且在天津日报政教部里着实“鼓吹”了一番。不过,说句老实话,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倡导“记者学者化”其实有些不合时宜,大家关注的热点是“下海经商”、是尽快变成“万元户”,一些编辑记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家庭“尽快实现现代化”……因此,任凭我“鼓吹”了半天,却应者寥寥。于是,我只能也“以身试法”,先逼着自己向着“学者化”的方向去努力。
转眼之间,40多年过去了,我不敢说已经实现了当年的初心,但至少没有虚度光阴。如今,我已到了临近退休的年龄,有时,夜深人静之际,独自环顾书架上历年出版的几十本著作,心里还是聊堪自慰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新闻业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靠“博闻强记”“博览群书”才能达到的知识储备,如今似乎不用那么“辛苦”就能唾手可得,无论需要什么知识和信息,只需在手机上点几下立即就会“奔来眼底”。如此一来,以往被推崇的“杂家”,似乎也不再那么“难能可贵”了。知识爆炸信息爆炸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信息科技带来的巨大变化,已使当今的媒体人拥有了无远弗届的眼界和瞬间即至的快捷。当此之际,“广博”已经不在话下,而“专精”则成了各大媒体的“稀缺资源”。1993年2月,在南巡“谈话”掀起的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我来到深圳特区,加盟深圳商报社。2001年从《深圳商报》被调到刚刚合并成立的深圳报业集团担任副总编辑兼系列报刊编委会总编辑,分管十几家子报子刊,内容涉及到新闻焦点、旅游文化、汽车时尚、青少年教育等方方面面。分管的领域涉及面宽,自然使我的“杂学”一度非常管用。但是,过了不久就发现,杂而不专“杂而不深”杂而不系统,往往只能触及浅层次的问题,一旦深入到各个报刊的专业领域,我就很难再有发言权了。至此,我对做新闻应为杂家的“传统观念”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刚好在2005年前后,我又转岗到《深圳特区报》主管文化体育等部门,策划和编辑副刊又成了我的主业。此时,我不再一味鼓吹“杂家”了,而是大力倡导每名编辑记者都应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其专业水准必须达到行业公认的“意见领袖”的水平。为了推进人才的专业化转型,我还与部门主任们商议了一些“度身定制”的岗位安排,核心是让最擅长的人去做他最喜欢的事儿,开绿灯,分小灶,期待着沉潜渐进日积月累会涌现出各个门类的专才。我还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记者去采访各类文化艺术的专业研讨活动时,应当追求的不仅仅是旁听的采访者,而且是正式的发言者,乃至成为受邀去发表真知灼见的专家,“你的胸牌应该是代表证,而不能满足于只是个采访证”。此议一出,我就听到有人抱怨,说这是“加压加码”,很难做到。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我虽已退居二线,但却欣喜地看到,当年所倡导的“专家”路线已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就以我分管的文艺副刊部为例,当年的一班副刊编辑,通过各自坚持不懈的努力,已在各自的媒体平台上八仙过海、各展所长,如今大部分卓然有成,有的成了“海洋文化专家”、有的成了“敦煌文化专家”、有的成为“流行音乐全才”、有的成为“电影理论权威”……即便是在当今纸媒遭遇极大困境时,他们的专业素质也为其赢得了相对广阔的职场空间,有的被调到子报当了总编辑,有的转行到大企业做了“音乐总监”,也有的直接去大学当了教授……
我很欣慰,甚至比自己出了多少著作还要高兴。我深知,人才成长的关键要靠自身的资质和长期的努力,但是,环境的营造和路向的指引无疑也非常重要。现在大家常说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觉得,这些同事以其各自的成功,助力我实现了在新闻从业之初就立下的一个“初心”。为此,我要感谢他们,并将他们的成功引为自豪!
至于我自己,不得不回到“杂家”这个话题上——早期成就记者生涯的确实是这条“杂家”之路。然而后来却一路“杂”了下去,未能及时转向“专精”,不免感到一丝遗憾:几十年下来,除了新闻这个本行之外,我涉猎的范围过宽、感兴趣的领域也太多了,写过小说、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出版过“舆论社会学”专著、研究过“茶文化”、痴迷过“艺术美学”、钻研过“西方艺术史”、编导过电视纪录片……就像狗熊掰棒子,一路掰一路扔,杂是够杂了,但每个领域都是浅尝辄止,深度严重不足。最早就杂与专的问题给我提醒的,是我的书法恩师宁书纶先生,他对我的字有句评点,叫做“临帖虽多,收束不够。”他给我的建议就是四个字“由博而约”。自我检讨起来,岂止是书法,在其他方面,我也是失之于兴趣太广,转向太快;到处挖井,出水不多。幸好,随着年龄渐长,认识也逐渐加深,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收缩战线,也就是按照宁先生所说的“由博而约”,渐渐把注意力集中于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理论方面,并且陆续有了一些收获——近年来,我在各类专业学术杂志上刊发了十几篇有一定学术分量的论文,如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画与世纪现代潮》,在《西泠艺丛》上发表了《宦海风波几度看——简论张宗祥的为官之道与文人风骨》,在《敦煌研究》上发表了《饶宗颐与敦煌书风》,在《中国篆刻》上发表了《诗意的方寸》……
此外,我还经常应邀到各大高校去做有关文化艺术的主题演讲,单是2017年下半年,就先后在南开大学讲过《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木板年画》,在清华大学讲过《内外之辩——纪念张仃先生百年诞辰》,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过《孤独的大师——从西方美术史看艺术家们的时代命运》等。此后,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为该校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西方艺术史(人物与作品欣赏)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受到了年轻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回顾40年的新闻生涯,真是苦辣酸甜,百感丛生。庆幸命运很早就把我推进时代的大潮,在波峰浪谷间沉浮跌宕,在众声喧哗中被锤炼成一名能够在各种新闻岗位上应付自如的“杂家”;同时也庆幸科技的进步又把我逼进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并且在一个新兴的城市里品味着求学问道的寂寞。如今老之将至,才逐渐接近“术业有专攻”的境界。我没有正式考入过大学,可以说基本是靠自学走上了新闻之路。如今,除了对编报纸写文章我可以自诩“专家”之外,对其他领域,尽管兴趣浓郁,却依旧不敢妄称自己是“专家”。我至今依旧跋涉在求学问道的路上。只不过,现在已开始体味到学问对个人生命的滋养,那种丰赡和澄明,确实是人生难得的一种境界。当然,对学问之事也确实比入道之初多了几分清醒。只可惜,这种清醒来得有些晚了——我常常想,为什么最早给我提醒的是一位书法家而不是报界中人呢?要是早一点有新闻界的同行给我提个醒,岂不是更好么?
正缘于此,我今天就借此机会,与年轻一代媒体人分享一点我的教训:新闻生涯需要认真的自我设计,由杂家入门,可以广博其视野,撑大其格局;打下坚实基础之后,则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切入点,深钻细研,精耕细作。在当今这个“泛媒体时代”,你要比别人做得好,就必须努力让自己成为某一领域的专才。这,也是我今天写下此文的初衷!
2018年4月2日于北京寄荃斋中
(作者是深圳新闻学会副会长、高级记者、深圳特区报原副总编辑)
编 辑 文璐 wenlu@xinhu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