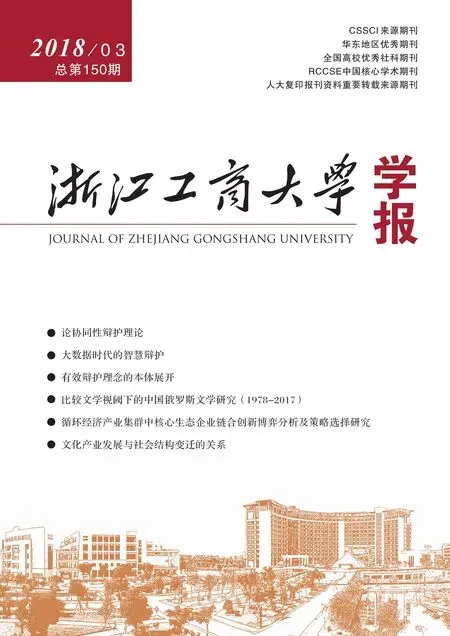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1978—2017)
杨明明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1902年梁启超以《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开启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之先河。此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思想领袖的推波助澜下,“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了怀抱救亡图强诉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而俄罗斯文学作为当时国人了解俄国的主要渠道,对其的译介与研究亦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文化风尚与精神旨趣。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也在“中外文化冲撞与交流的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基于中外文学对话与中国文学革新的内在需求”[1]1应运而生。自俄罗斯文学进入我国学者视野之日起,比较文学即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眼光、一种视野体现在对其的研究当中,《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3)、王国维的《脱尔斯泰的近世科学评》(1904)、李大钊的《日本之托尔斯泰热》(1917)和《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便是早期的代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在百年研究历程中常常承担了超出其本性的过于深重的政治和道德的负荷”[2]3,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在材料把握、理论创新和体现中国学术的特色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4。百余年来,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杂语性与对话性的特质,为我国学者解读俄罗斯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与有效范式,也贡献了诸多富于独创性的成果。但是,时至今日,相较于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比较文学于俄罗斯文学还是存在着研究思路与话语陈旧、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意识与民族立场弱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欠缺等一系列问题。有鉴于此,文章选择我国研究成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应用情况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今后的发展走向做一些大胆的预测与展望。
一、 中俄文学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开始面临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比较文学以其跨文化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为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带来了丰硕成果,而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则成为其卓有建树的领域。基于“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运动、文学观念和作家的创作、评论家的批评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也主要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研究”[1]197-198,而从已有成果的内容来看,似可划分为总体研究、个案研究和翻译文学史研究三大类。
第一,总体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在总体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戈宝权的《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倪蕊琴的《论中苏文学的发展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王智量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赵明的《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五四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陈国恩、庄桂成、雍青合著的《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李明滨、查晓燕合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等。上述成果“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立场,从中国文学主体创造的角度”梳理和考察了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影响和接受”[3],重点探讨了其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二,个案研究。在中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俄罗斯文学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的影响问题,如王富仁在《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孙郁的《鲁迅与俄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陈遐的《时代与心灵的契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前期创造社文学之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等;二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以及中国文化对其思想与创作的影响问题,如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88)、张铁夫的《普希金与中国》(岳麓出版社,2000)、吴泽霖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刘研的《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等。
第三,翻译文学史研究。俄罗斯文学翻译史的梳理与反思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新课题。目前我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除了一些探讨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翻译情况的论文之外,王迎胜的《苏联文学图书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杨义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的《近代卷》《五四卷》《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中的相关章节以及曾思艺的《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算是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中俄文学关系领域虽然取得了可喜成果,也涌现出了戈宝权、王智量、倪蕊琴、陈建华、吴泽霖、汪介之、陈国恩等一批成就斐然的学者,但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其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研究视野与范围亟需拓展。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化思潮和社会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再无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出其右者,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国学者也仅仅对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经典作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虽有所涉及,但至今仍未有专项研究。不仅如此,这种视野的狭窄还直接导致了相关研究成果人云亦云,缺乏原创性与创新点。
其次,原始材料挖掘不够,分析与阐释角度单一。从现有成果看,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中俄文学关系史、代表性俄罗斯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制于对相关资料搜集整理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研究思路不够开阔,方法与手段陈旧单一。为此,今后我们应该建构一个更加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从以下两个层面具体切入:一是对中俄文学之间“事实联系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梳理和叙述”,我国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尚存在着不少疑难问题,有待通过对新材料的挖掘与分析来解决;二是从“文学思潮层面”[4]进行梳理、分析与论述,俄国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都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创作理念和风格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理应成为今后国内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再次,翻译文学史有待全景式回顾。自1872年《中西闻见录》上首次刊发俄罗斯文学作品《俄人寓言》起,百余年来,已有五千余部俄罗斯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堪称是世界文学翻译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但至今为止,我国既没有一部完整详细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也没有一部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俄罗斯经典作家个案翻译史,实在落后于我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第一大国的现实。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进、中俄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历程进行梳理与总结无疑成为一项十分必要且紧迫的任务。
最后,研究队伍后继乏人。老一辈学者对中俄两国文学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中俄文学交流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当前我国的中青年学者较少涉足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不仅没有出版过相关专著,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也不多,力作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普遍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读与考量,而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俄罗斯文学也是一样,其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完全不懂俄语。这种学术素养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近年来该领域平庸雷同之作屡屡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在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亟需对中俄文学关系问题进行一次全面回顾、细致梳理与深刻反思。同时,作为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21世纪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从观念、思路到视野都亟需更新,为此,尽快完成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范式与接受模式向多元化、个性化、民族化研究范式的突破与转型,无疑将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二、 比较方法的应用
新时期我国的俄罗斯文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除了传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实证方法与20世纪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文本细读法、接受美学之外,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超文学研究等比较方法的引入,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范式的变革。
超文学研究致力于以某些具体的国际性和世界性的历史现象、社会事件、文化思潮、宗教信仰和哲学美学思想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学,其应用是新时期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而其中成果最为丰厚的就是从宗教维度对俄罗斯文学的考察与阐释。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基辅罗斯—19世纪俄国文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赵桂莲的《飘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金亚娜等合著的《充盈与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与《期盼索菲亚—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与文化探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刘锟的《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体现出我国学者在这一课题研究中的优势,即“他者的视野”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一些学者“对作为俄罗斯文化主体的东正教的理解上的表面化”[5],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关研究中存在着简单罗列材料、论述空泛肤浅等问题,有待在日后研究中继续深化。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除了将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应用于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还从东西方文学与文化与俄罗斯文学双向交流等角度进行了探索。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从总体上看,论文数量不多,并且限于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功底,学术价值也有待提高,至今也只有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学林出版社,1999)算是这方面比较有分量的一部专著。
平行研究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些,鉴于这一方法的始作俑者美国学派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单薄,加之我国学者又未能深刻领悟这一方法的精髓,所以导致了相关研究中的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等种种弊端。以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为例,将娜塔莎、安娜、玛丝洛娃等与杜十娘、潘金莲、林黛玉、娜拉、包法利夫人、简·爱、弗兰西斯卡等林林总总、古今中外的人物进行比较的论文,就达数百篇之多。虽然其中不乏立意新颖、言之有据的佳作,但绝大多数都是立论牵强、内容雷同乃至哗众取宠之作。事实上,这种简单生硬的“X与Y”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遭到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的严厉批评,近年来在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中亦较少出现,唯有俄罗斯文学是“例外”,至今为止,每年仍不断有“新”作问世,且作者多为青年学者。大胆假设是允许的,但小心求证更是必须的。在此,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可比性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平行比较并非轻率粗浅的对比或比照,而是一种开放灵活的、哲学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其实质在于打破时间、空间、质量和强度的限制,打通与贯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之间没有事实关联的文学现象,以期从更高层面上去探寻不同的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中存在的共同文学规律,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因此,相较于其他几种方法,其应用难度无疑也是最大的,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思辨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俄罗斯文化与中国等其它国家、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特别是对于俄国这样一个长期徘徊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其文化所呈现出的欧亚属性,为我们运用平行研究方法提供了可供比较的前提;而中俄两国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又都以富国强兵、启迪民智为目标进行了革新,从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启蒙运动到中国的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都在两国的文学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留待我们从人物形象、作品主题、情节风格、意象象征、文学思潮与流派到审美观照与精神旨趣等多个方面去深入挖掘与阐发。
三、 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逐渐成为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战略性命题。中国形象作为“流行于社会的一整套关于中国的表现或表述系统,其中同时包含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内容,具有话语的知识与权力两方面的功能”。中国形象作为俄罗斯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涵盖了三层意义:一是“对现实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与想象”,二是对中俄关系的“自我体认、焦虑与期望”,三是对俄罗斯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6]22-23。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形象的书写与建构充分体现了上述因素,但亦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关怀、独特的问题与价值”[6]143。
俄罗斯作家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书写,据陈建华先生考证,成书于12世纪、被誉为古代俄罗斯文学丰碑的《伊戈尔远征记》中出现的“Хинова”一词极有可能是指中国。此后,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孔教乌托邦”“停滞的帝国”到苏联时期的“黄皮肤兄弟”,再到今日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色彩的复杂演变历程,亟需我们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思考。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依然较为薄弱,只有汪介之、陈建华合著的《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一书的相关章节和查晓燕的《“异”之诠释: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李逸津的《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文本中中国概念内涵的演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亚丁的《回归“哲人之邦”套话——近30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象》(《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王树福的《俄罗斯文学的东方幻象:佩列文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刘潇娴的《试析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因素和印象》(《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36期)等论文探讨和分析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形象的书写和表达。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文学中关涉中国形象的文本虽然体量并不大,但其对于中国学者的特殊意义却是不言自明的。鉴于现有成果的单薄、缺乏系统性,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实证研究,继续大力发掘、收集和整理新的文本资料,努力填补俄罗斯文学中国形象建构历程研究中的空白点,从资料上完成对其的全景式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历程进行历时性梳理、全方位扫描与深层次反思;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共时性分析和阐释,不仅要继续关注与审视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对中国形象的书写,还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对斯拉夫主义、西方主义、根基主义、民粹主义、欧亚主义等重要社会思潮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与评价部分进行拣选与分析,以期从更深层面上探寻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的思想根源。
最后,在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的研究中,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文化成见乃至意识形态偏见问题。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俄罗斯文学亦不例外,在个别作品中甚至还有作家出于对中国的敌视使用“黄祸”一词。对此,我们必须抱有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态度,对俄罗斯文学中肆意歪曲、丑化、侮辱、蔑视中国的内容予以坚决的批判与回击。
四、 俄罗斯文学史写作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文学史并不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但是,任何一部国别文学史的写作都离不开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的观念[7],其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不可能在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相隔绝的情况下孤立发展起来,俄罗斯文学更不例外。
俄罗斯文学自形成之日起,就受到东西方多个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基辅罗斯时期起,俄罗斯就从拜占廷和保加利亚引入了大量宗教典籍和世俗著作,从而赋予了古代俄罗斯文学以浓厚的宗教色彩。此后,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文学思潮与流派又相继从西欧传入俄国,在与俄罗斯文学融合与互动的过程中,将俄罗斯文学推进至世界文学高峰。20世纪的俄侨文学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展现了俄罗斯文学绚烂多姿的面貌。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对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俄罗斯文学发展进程中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双向传播与接受问题却一直未能获得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
从我国现有的几部俄罗斯文学史著作来看,其作者虽然具有一定的世界文学意识,但限于篇幅与时代,还是存在一定欠缺。此外,俄罗斯学者在撰写本国文学史时,常常偏重于强调俄罗斯文学的民族性、独立性和独特性,而选择有意忽视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学的交流。鉴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深受俄苏影响这一事实,我国学者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史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上述倾向。在此我们以普希金为例,众所周知普希金的创作曾受到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等英国作家的影响,但是在我国学者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史中,在论及普希金的创作时,虽然也会提及莎士比亚的影响,却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其他经典作家的情况亦是大同小异。此外,在这些文学史中对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文学流派的论述也往往是以强调其异质性为主,而较少涉及其与西欧鼻祖的同源性。这种相对封闭狭隘的文学史观带来的后果就是未能真正揭示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以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为参照系,在世界文学史上恰如其分地对其进行定位。上述问题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令人颇为遗憾的。
作为一名客观公正的俄罗斯文学史书写者,在追溯与重构俄罗斯文学的千年发展历程时,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是一件不可或缺的武器。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例,其思想与创作不仅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还受到了共济会思想、启蒙主义以及道家、儒家、伊斯兰教等东方文化的影响;而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与经典作品又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欧美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抛开这些因素,是无法还原作家的创作全貌并准确评价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有鉴于此,我们只有把俄罗斯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才能充分揭示其文学运动、文学思潮、风格流派、作家作品与其他国别文学的关系,才能全方位地展现俄罗斯文学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在接受和消化外来影响中发展嬗变的轨迹与历程。
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性源于其自身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价值内涵”,融入世界文学谱系的俄罗斯文学“并没有丧失其鲜明的本土化民族特征”[8],而是始终以一种高昂的民族化姿态、深邃厚重的个性化气质对抗着全球化进程。其对中国文学、社会与文化影响之深刻也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所不能比拟的。基于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实语境、审美习惯与价值取向,比较文学必将以其跨文化的宏观视野与整体化的思维方式,为今后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拓宽研究范围、更新研究对象、转换研究范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同时,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下,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入侵与挑战,对此,比较文学作为我国学者避免盲从西方或俄罗斯的文学研究模式、坚持中国学者独立立场的强大武器,必将彻底打破现有研究的单极化倾向,开拓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天地,促进中国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为真正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1]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M]// 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2]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3]宋柄辉.30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综述[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27-131.

[4]宋柄辉.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主体立场及其方法[J].山东社会科学,2014(5):63-70.
[5]陈建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04-241.
[6]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7]陈红玉,方汉文.“世界文学翻译”:文化转向之后的“转向”[J].中国文学研究,2015(4):119-123.
[8]张建华.重新融入世界文学谱系的俄罗斯文学[J].外国文学,2014(2):3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