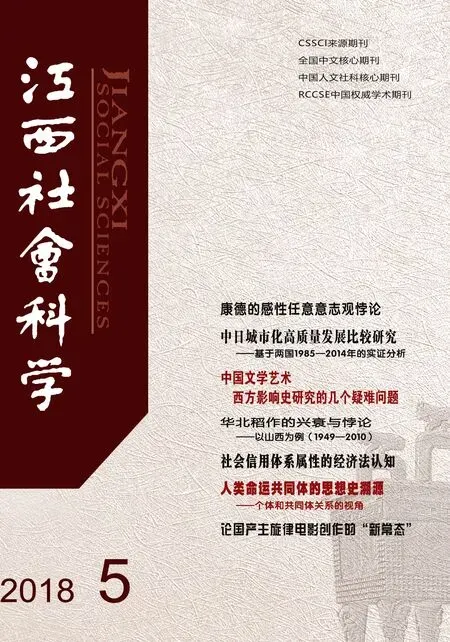近代铁矿业的发展困境
——以裕繁公司为中心
中国近代铁矿业诞生于西力冲击、内忧外患的环境中。甲午战后,列强各国依恃不平等条约,采取华洋合股、借款、成立外资矿业公司等方式,对中国矿业资源进行掠夺。中外因矿务问题不断激起矛盾纷争。随着中国社会变化和民族意识觉醒,清末爆发收回矿权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效。进入民国,政府与实业界都非常重视矿业发展,推动制定了不少矿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民初时期安徽就出现过一阵办矿热潮,皖南沿江一带多家铁矿公司纷纷申请注册,从矿区探明储量而言,仅次于辽宁与湖北,而领办最早、产量最大的就是裕繁铁矿公司。①自1913年裕繁公司成立,至1937年矿区被日本侵略者强占,二十余年间,因日方利益夹杂其中,围绕矿权争夺充满诸多的博弈与无奈,公司经营步履维艰。本文拟通过对这一时期裕繁公司创办及经营过程的简要梳理,剖析近代中国铁矿业的生存困境,进而深化对民国时期矿业利权问题的探讨。
一、裕繁公司的创办及开工波折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核心在于机械制造,机械制造则需要与采矿业、钢铁业协调发展。采矿冶炼既需要资本、市场,也需要人才、技术,这些相关要素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均不同程度的缺乏。当然,近代铁矿业的诞生是开展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由于潜在市场需求与高额利润预期,加之外来资本对矿业投资的诱导,本国资本也选择对近代铁矿业进行投资。但上述叠合因素的存在也注定了近代中国铁矿业曲折发展的一面。
创办铁矿公司首先需要巨额资本,近代,是否借用外资或借用外资会否造成矿权受损,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裕繁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霍守华,广东南海人,清末民初在安徽芜湖开设顺泰成米号,组织同丰机器碾米公司。1913年秋,霍与陈梅庭等人勘察桃冲铁矿,开始集议招股开办,成立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1](P703-704),霍被推为总经理。奉时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批准,同年12月领到探矿执照。由于先前申请的五百余亩矿区似难满足日后需求,1914年5月霍守华呈请增加矿区八百余亩,9月领到农商部颁给的安徽铁矿第一号开矿照[2](P21),准备在11月正式开工。然而,裕繁公司的开工并不顺利。
公司探矿后即开始考虑矿石销路问题,1914年10月霍守华与中日实业公司②代表森恪订立售卖矿砂合同,专售合约期限40年,其中:第六款,裕繁“应得之净利每一吨上海规元银一两,公司办事费及一切间接费每吨不得过洋一元,以上三项各费为将来定价之标准”;第八款,矿石含铁成分“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达不到要求则按标准扣价;第九款,日方先交洋20万元,裕繁“照周年六厘行息,按年交付”,“惟以该款为矿石价值之一部分,由载船矿石价值内分还”;第十款,按照预算,裕繁“筑造采运矿石铁路码头及开采矿石各机件等所需经费”,由日方供给,裕繁按年摊还,“仍以六厘息计算”。[3]可以看出合约条款相当苛刻,公司的探采施工、经费预算、运输交付、销售价格完全被中日实业公司所掌控,特别是矿石的定价标准也由日方设定。
1914年11月中日实业公司将合同呈明农商部批准,农商部感到问题极为棘手,许多在京皖籍要人“先后迭次函电禁阻”,认为:“奸商霍守华与日人森恪订立卖砂合同,先借款二十万订聘日人高校雄治为技师,旋又聘日人为助手,名为自办,实为外人所利用,名为买卖,实不啻为外人承办之替身。”[4]农商部迁延数月,未予批复,个中原因在于同年11月21日奉大总统批令,以铁矿关系重要,拟定“作为国家专营”。对于之前已取得矿权的外商股本企业,“或将其矿权设法收回,或将其矿砂由官收买”[5](P509)。1914年3月北京政府颁布的《矿业条例》第四条曾规定,“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并“愿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法律”。[5](P40)“铁矿国有策,是北京政府对当年3月颁布的《矿业条例》所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6],一改《矿业条例》中的允许外资入股,裕繁公司立时陷入困境。日方通过外交关系施加压力,经袁世凯允诺,农商部最终同意批复。
不过事情并未平息,1916年5月裕繁公司禀请敷设专用铁路以便外运存积矿砂。7月,中日实业公司运送铁路材料前往繁昌荻港,因该港并非通商口岸,便由日本公使申请中央政府特予通融办理。[4]敷设运矿专用铁路一事,经交通部核准,认为与现行专用铁路章程相符,便饬知皖省财政厅准予立案。但是舆论又生哗然。安徽省议会以霍守华丧权辱国,主张取消该矿权,声称裕繁为筑路拟借日本30万元,并聘请日人为工程师,应吊销裕繁公司矿照,并请交通部停止核准该公司请修专用铁道照。[4]
实际上,霍守华此前在提请增扩矿区时,已引起“皖省旅京要人之注意,于是李经羲、周学熙、王揖唐、杨士琦、孙多森、孙毓筠等,以铁矿国有名义坚请农商部扣发霍某增区矿照”[1](P704)。旅京皖人认为,霍守华迭借外款,没有资本,不管是已领矿区还是修筑铁路,全借外来力量,公司悉操之于日人。倪嗣冲经过考虑,亦对给予裕繁筑路矿权持反对态度。
中日实业公司致函交通部,称专用铁路建设“延搁进行”,公司所受损失为数甚巨,请将“专用铁路执照毋庸发由安徽省长转发,就近直接交与敝公司代领”。驻日公使章宗祥从东京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言称“该公司殊受损害”,“可否请转商倪省长体察情形,速行办理,以免酿成问题”。[4]而安徽省议会及公益维持会则先后咨请撤销矿权,要求扣留路照。1917年3月,森恪赴蚌谒见倪嗣冲,倪“当与约定在此案未解决之先由官厅派人代理裕繁公司,俾该矿山工程照旧进行”[4]。5月倪嗣冲致函交通部,仍请将筑路执照交由安徽省长领收,以便派员赴矿地接洽办理。[7](P76)交通总长曹汝霖认为,“此案殊无可据以拒绝之理由”,应速给予路照,并向国务会议提案。8月国务会议致函交通部办理,于是交通部填发执照,函送安徽省长转发。[7](P78)安徽绅商闻之,异常激昂,再以全省公益维持会名义具呈抗议。
面对日方压力与本地绅民抗争,9月倪嗣冲致电农商部长,提议将裕繁公司改为官督商办,并加派监督,“庶泯双方争执”[4]。倪嗣冲咨商农商部任用高炳麟督办矿务,常驻裕繁公司督理一切事务,举凡该公司招股营业、开采建筑、账据货款、外界交涉等事宜,应秉承监督查考核办,公司应纳铁捐,由监督征收分别报解。[8]12月高抵达繁昌县,依照探采铁矿办法、监督办法各条,开始督理裕繁矿务。对于裕繁公司改为官督商办及加派监督一事,森恪多次赴部恫吓,后经安徽派员到京说和,才算妥善处理。裕繁公司领到路照后,即开足马力修筑12华里的单线专用铁路,“公司雇用小工一千八百余名,均并力修筑专用铁路,在山工人仅二百八十余名,复以一半修砌山路”[8]。1918年10月26日专用铁路通车,正式开车运砂。
自1913年10月裕繁公司禀请领办铁矿,至1918年10月矿砂得以外运,其间经历了诸多波折。值得深思的是,安徽本地矿商联合地方绅民、京中皖籍要人,并得到安徽督军倪嗣冲的支持,攻击霍守华实为“奸商”,声势浩大,强烈要求取消其矿权,然迁延数年,几经波折,裕繁公司却仍得以开工运营。显然,除了裕繁的日资背景是双方纠葛的焦点,双方博弈应还有着其他更为深刻的原因。
二、围绕裕繁开工的博弈与妥协
近代日本发展钢铁业需要稳定的矿砂来源,而其矿产资源极为缺乏,为此日方处心积虑,积极谋求中国的铁矿资源。裕繁公司矿区储量大、矿质高,靠近长江,外运便利,因资本、市场、技术等要素不足而愿意依恃日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暗订买卖合同,日方以预借砂款方式支持裕繁。北京政府制定的最初矿章中允可引进外资、外人参股办矿,后来改为铁矿国有专营的办法,对于以往非国有的矿务合同,“或将其矿权设法收回,或将其矿砂由官收买”,这一法律文本的变动就构成了皖人抗诉的法理依据,实际上该办法并不切合实际。当然就裕繁公司而言,即使向日本人退还借款,让其放弃铁矿合同估计也是异常艰难。
从皖籍要人与绅商来说,不仅在于声援挽回利权,捍卫矿产,更为重要的是,霍守华与一些安徽绅商在矿业经营上存在同业竞争与潜在矛盾。一战爆发,铁价飞涨,经营铁矿者风起,许多公司纷纷注册领矿,就皖南沿江一带而言,先后有裕繁、宝兴、振冶、福利民、益华、昌华等多家公司请领矿区,截至1918年皖南主要铁矿公司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913年时就有裕繁、宝兴、福利民等公司申请领办矿区,而最先拿到矿照的是裕繁公司,1914年9月领到安徽铁矿第一号开矿执照。[9]上述诸公司的开办者非官即商,或亦官亦商。开办宝兴公司的章维藩、福利民公司的徐静仁、振冶公司的方履中并非等闲之辈,在实业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力。章维藩(1858—1921),字干臣,原籍浙江吴兴,1890年在芜湖筹建益新面粉公司,曾任芜湖商会会长。1913年在当涂创建宝兴铁矿公司,并得到周学熙支持。徐静仁(1872—1948),名国安,安徽当涂人,近代实业家。长期与张謇合作共事。1913年先后创立福民、利民两个铁矿公司,后来合并为福利民铁矿公司,自任总经理。方履中(1864—1932),字玉山,安徽桐城人,先后任两淮盐政使、安徽矿务总理,清末时期领导了收回安徽铜官山矿权运动,组织成立泾铜铁矿公司。就倪嗣冲家族而言,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益华铁矿公司,1918年倪道烺、倪道杰、宁资愚等人分别请办当涂县黄梅山、龙家山、虾蟆山等处铁矿,倪嗣冲幕僚胡夔文、王鼎昌则分别请领繁昌县铁矿区,不排除他们借助倪嗣冲官威的动机。当然倪嗣冲对此也予以认可与支持,1918年2月倪嗣冲致函田文烈,称“特为劝谕地方富绅并舍亲及子姪辈联同呈请,特准试探,选聘矿师,前往测勘,如计划可办”,“换照从事开采”,请农商部给予注册便利。[8]此外,周学熙嘱劝陈惟彦出面向部请领矿区办理矿业。诸人对于日资背景的裕繁公司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安徽本地矿商上有省政府支持,下有地方绅民呼应,积极注册争夺皖南矿权,强调自己身份是“本省正绅”,且“资本充足”,以自办挽回利权为号召,不唯办矿试图获取大利,亦在困厄裕繁,背后不单是中日经济纠纷,更是同业矿商间的暗斗。

表1 1913—1918年皖南主要铁矿公司情况表
不论是皖籍旅京要人李经羲、周学熙、孙毓筠等,还是安徽督军倪嗣冲以及地方绅商,均认为霍守华依恃外人,实乃“奸商”,无异于出卖国家权益,然而日方及霍守华并未退让。最后裕繁公司以名义上改为官督商办而妥协收场,中日多方博弈过程中各自考量如何,为何会以妥协收场?
首先,就日本方面来说,森恪以中日实业公司名义与霍守华签订买卖矿砂条约,通过预付定金的方式来控制裕繁公司的销售,合同条款极其苛刻。随后又通过派驻日本工程师、代为购买材料、筹办修筑专用铁路等多种方式将裕繁公司控为己有。在此过程中,不管是中央相关部门、安徽省政府,还是在京皖籍要人、安徽本地绅商,对此矿路案都曾试图阻拦甚至要求取消矿权。日方通过各方运作,起用多重关系,毫不退让,争夺矿路利权。中日实业公司的中方代表李士伟、孙毓筠等人代为出力,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总长曹汝霖等大员直接致电中央,要求转饬相关部门速予颁发证照,日本公使与外交部亦为后援,甚至中日实业公司致函交通部要求将路照直接发给该公司。因安徽绅商反对甚烈,省公署便扣发路照,森恪则赴蚌埠面见倪嗣冲。倪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依照特准探采铁矿暂行办法,将该公司改为官督商办并加派监督。森恪又赴农商部施加压力,甚至出言恐吓,意图取消监督权限。在与日方沟通协调过程中,中央相关部门不免软弱与偏袒,如章宗祥、曹汝霖的从中说合,这与北京政府的亲日倾向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就安徽省政府而言,倪嗣冲还是比较支持工矿业发展的,然当逐渐查明裕繁公司资本不足,霍守华虽自行办矿,却权操外人之手,安徽省议会、公益维持会及绅商各界起而反对,要求取消矿权,倪嗣冲亦能抵住中央压力,以理据争。但裕繁公司已得农商部批准采矿,交通部也颁发路照准予修筑专用铁路。揆诸事实,倪嗣冲最终同意裕繁公司继续进行各项工程,但通过加派监督,对该矿予以监视,试图将该矿纳入省管范围。当然安徽省政府与一些绅商人士对于该矿的价值取向不同。从省政府而言,需要通盘考虑,兼顾中央相关部门与日方关系的协调,并借助皖籍要人、省议会等力量,对该矿予以施压,农商部批准矿照时要求遵部令每吨捐洋四角,而在交通路照争执过程中则将该矿改为官督商办,并要求报解铁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倪嗣冲对该矿并非排斥心态,但该矿能否增加本省收益是值得考虑的。
再次,就霍守华本人而言,领办桃冲铁矿是其事业的一大转折。桃冲一带矿藏丰富,规模仅亚于湖北大冶铁矿。然而霍守华资本不足,于是通过与日本签订卖砂合同,以预付砂价作为开工费用,又通过借款来修筑专用铁路。裕繁虽然号称注册百万,实际上资本极为有限。1918年3月16日高炳麟呈文农商部,称“再查该公司原定股本系二万元,以前曾否发行股票,嗣后有无续刊股票,添招股本暨采矿施工计划,雇佣外国技师,现时有无变更情事,及与外国人有无其他交涉事项”,均需逐细调查。[8]公司开办之初股本只有2万元,当时办矿风气未能全开,加之先前霍守华两次探矿的失利,投入太多资本亦不可能。可见霍守华作为一介商人,并非如他自己所称“素性愚憨”,而是极为精明,想着借助外力办矿,既可分担风险,又可以小搏大。当然,其蒙受“丧权辱国之谤”[2](P22)就事所难免了。
皖籍要人、本地绅商等多方力量卷入抵制,亦未能阻止裕繁开工。裕繁由日本财团支撑,借用外资不成问题,矿砂销路也不成问题,本应是大获其利。时人就认为“裕繁一矿,析利为十,外人占八,国人占二,奸商霍某以月获万金,坐拥厚资,逍遥沪上,矿区既广,铁厂复开,百倍裕繁”[10]。1927年,皖人控告霍守华,认为“霍卖矿起家,发财至千万之巨”[11]。不过,对于霍守华来说,裕繁公司的经营成效实际上并不令人如意。
三、近代铁矿业的经营困境与利权外溢
近代中国铁矿公司经营处于困境之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了追求利润,开辟税源,以“挽回利权”作为诉求,一些铁矿公司注册成立,事实上它们的经营往往事与愿违。裕繁公司领办过程中被指依赖日资,霍守华实为“奸商”。裕繁开工后以矿砂输日抵偿债务,被日方牢牢牵制,经营非常困难。问题是,曾经以收回利权为名抵制裕繁开工的其他铁矿公司,它们的生存命运与裕繁并无大的差异,不管有无日资背景都将日本作为销售市场,挽回利权似乎成为空谈,利权外溢却是不争的事实。
受资本、技术、市场等因素制约,皖南各铁矿公司产量有限。截至1919年,领得矿照最早的裕繁公司总产量达20万吨,而稍后开矿生产的宝兴公司、振冶公司,分别仅为9.7万吨、1.4万吨。[12](P419-422)福利民公司迁延数年,1920年才动工开采,又因矿脉不清而中止,直到1930年始向日商交货。[13](P41)振冶公司因探矿技术不足,截至1929年整个开采量不过十三四万吨。[14](P89)宝兴公司截至1920年底,共产砂二十三四万吨。[15]益华公司1923年至1926年共采矿10余万吨。[13](P70)整个20世纪20年代,除裕繁公司产量较为充足外,其他铁矿公司时开时停,甚至难以维持运转。
裕繁公司在皖南铁矿公司中产量最多,但由于日本通过预购及高息借款订立合同,控制了裕繁的矿砂生产,该公司开工后即向日本出口矿砂。皖南其他铁矿公司大体上也均以日本为主要销售市场。1929—1933年安徽铁砂每年输日数量如表2所示。

表2 安徽铁砂每年输日数量总计 单位:吨
表2显示出1929年至1932年向日输出矿量最多的就是裕繁公司,几乎占安徽铁矿公司出口的一半以上。自1918年10月裕繁矿砂外运至1937年矿区被日本占领,裕繁共向日本输送矿石345.49万吨,日本的制铁公司、钢管公司、三井公司、三菱公司等钢铁厂,均用安徽的铁矿石。[16]裕繁矿砂虽大量出口,却始终未能有大的盈利。由于公司借债发展,在债务上越陷越深,据日本单方面声称1936年裕繁已欠日债多达1508.6万元,经济状况处于绝境。[13](P25)裕繁债息越滚越大,对于霍守华本人而言颇为头疼,本想凭借日资做强企业,不想反被控制,霍守华从矿砂交易中未能捞到预想的好处。
其实,不仅裕繁公司陷入债务深渊,皖南其他铁矿公司情况也大体类似。宝兴公司所产矿石除运往上海与武汉外,大部分运往日本,甚至没有日本订单就不敢开工生产。1918年3月福利民公司与日本小柴商会签订40年的售砂合同[2](P33),由于收了日商定金,却因事态变化公司合同违约,1938年福利民已欠日商债务日金达210余万元。[17](P46)振冶公司铁矿销路依然是日本,1928年4月方履中经英人介绍与日本石原公司签订售砂合同10万英吨。因公司开采运输不力,逾期未能履约,为赔偿日商损失,方无奈只得出卖钟山矿权。[14](P91)益华公司本想通过入股上海和兴钢铁厂解决销路问题,结果事与愿违,同样只得寻求向日方销售来换取生存。皖南铁矿公司在矿砂外销上,难能抱团作战与合力发展,特别是在与日商矿砂买卖合同签订上,各公司往往自行其是,使得同行业整体利益受损。
汉冶萍公司的命运也说明了这一点。汉冶萍公司以预售矿石、生铁方式向外大量借款,20世纪20年代汉阳、大冶炼钢炉停产后,汉冶萍仍继续向日本输出矿石来偿还欠款。“1927—1937年汉冶萍公司共生产铁矿石4507 912吨,其中输往日本的为4240 709吨,约占矿石总产量的94%。”[18](P856)近代中国铁矿石大量外销,“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向日本输出”,东北沦陷后“占全国储量百分之七十六的铁产已非我有”。[19]对日售砂铁矿公司之间也存在竞争,象鼻山销售先经石原东亚各公司之转运,“且又与南洋安徽太平各铁砂互相竞争,运销前途实多窒碍”,终象鼻山因为含磷少得以生存,“否则为同业所压迫,久已不能存在矣”。[20]
皖南各铁矿公司生存严重依赖出口,没有出口就不能生存,由于中日关系恶化,1928年12月农矿部已下令铁矿不许售与日商,但一些铁矿公司置若罔闻,福利民、宝兴公司依然暗中输日。1933年初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设法加以制止,派员到场,“令其具结保证永不供给敌人铁山”,并交罚金2万元。然而福利民“公司口是心非,墨迹未干,近复假籍中日停战为名又运砂于日商”,矿砂输日无异于“供敌制造枪炮原料之用”。[2](P129-131)日本通过预购及高息借款合同控制了中国矿砂生产,对日输出一直未停止。抗战全面爆发后,皖南一带沦陷,裕繁公司即被日军强占,后来日本又强行将各铁矿公司加入华中矿业股份公司,皖南铁矿业彻底为日本控制。
日本从中国攫取铁锰,除汉冶萍外,“假借中日合办名义,掠夺辽宁之庙儿沟、弓长岭、鞍山等铁矿,安徽繁昌、当涂,湖北象鼻山等处铁矿;湖南湘潭,江西乐平,广东钦州,广西武宣等处锰矿”,数目惊人。日本的“飞机、军舰、重炮、坦克、枪弹,这些残杀我国同胞的利器,含了我国供给多少万吨的铁和锰”。九·一八事变后,“铁锰对日输出,并未因领土丧失,同胞牺牲而受阻”。[21]本溪湖煤铁公司创办时中日双方投资各半,合同有效期为30年,其“所产铁质甚佳,日本购去多以为鼓铸枪炮原料”,此处出产的低磷铁,“用以制为枪炮里膛,富有弹力,且不爆炸”。[22]
榆阳北部风沙草滩区已初步形成了“林灌固沙-固沙培地-培地种粮-粮农促牧”的林灌农牧复合经营生态农业模式。
如何停止售砂于日,有人提议让这些“公司永久停工,以至于完全破产”,“提高铁砂出口税,宣布铁矿国有”。[23]1933年1月《矿业周报》发布本社宣言,要求“铁钢国营,一律封禁,不准开采”[21]。 事实上,近代中国既缺乏炼铁之经费,又无售砂之国内市场。中国矿权的挽回,不仅在于收回自办,更在于中国近代工业系统性的全面铺开与升级,在于中国如何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完成工业化。1920年前后,“中国销铁数额不过等于世界平均之四十分之一。而较之英美德诸大国则不过百分之一”[24](P280)。中国近代矿业之不振,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外,也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系以农业为基础,而非以工业为基础。工业之发展固待矿业作先驱,然在工业幼稚之社会中,如无计划经济之推动,其自然的进步必甚迟缓”[25](P64)。
客观来说,近代铁矿业投资成本大、周期长、风险多、回收慢,一旦运转不灵,结果难卜,企业发展往往受到资本不足、市场狭小、冶炼能力缺失等因素制约。另一方面,又因市场需求,近代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钢铁,1934—1936年三年间输入钢铁已达“二万五千万元”[19]。一些铁矿公司亦曾考虑自炼或合办钢铁厂。福利民公司试图自建小高炉炼铁,终因经费无着、政局不稳、技术跟不上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宝兴公司计划与开滦公司在秦皇岛共建开平钢铁冶炼厂,结果不了了之。裕繁公司“自行化炼铁砂,延聘中国技士二人在山建一小化铁炉,靡费数万金,改良两次,竟不适应”[9]。至于“本溪湖、和兴、龙烟、保晋、裕繁、湖北官矿局等不下十余处”终因铁价暴落,“矿厂赔累不堪乃相继停工”。[19]1918年安徽财政厅筹划设立省办炼铁所[26],但该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也一度规划在马鞍山建立中央钢铁厂,但从1928年提议到1935年计划被迫流产,筹建依然停留在讨论中。
国内冶炼能力低、产业结构滞后,造成铁矿业难以强健成长;资本缺乏、市场狭小则直接制约了铁矿业的生存,近代中国铁矿业陷入困境之中。挽回利权需要启动近代铁矿业的发展,而事实上铁矿业的发展却又是以利权丧失为代价,这一悖论折射出近代中国铁矿业依然没有找到产业经济起飞的动力。
四、结 语
甲午战后,列强获取在中国开矿设厂的特权,于是纷纷在华投资,直接对中国进行权益掠夺。利权的大量丧失加深了民族危机,唤醒了民众“实业救国”的意识,收回利权运动随之兴起,要求将被列强攫取的铁路、矿山利权收回。清政府为挽回路矿利权基本上采取偿款赎回或以借款自办的条件收回。就铁矿业而言,19世纪末中国进口生铁已达年10万吨,为挽回利权,国人开始在中国自建新式炼厂,制炼钢铁替代外洋进口,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汉阳铁厂即是如此。
民国肇建,不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振兴矿业都出台了系列政策,然由于铁矿业发展的内部要素与外在环境并无太多改善,在挽回利权方面,实际上并无更大进展。民国时期铁矿业的生产销售,事实上在为日本钢铁业提供原料,矿价、矿质评判掌握在日人手中,客观上每输出一吨矿石,就为日本工业现代化增添一分力量,而中国则丧失一份权益。当时中日之间的矿砂贸易,并未有效促进中国钢铁业的现代化。日本在华投资的本溪湖煤铁公司和鞍山制铁所,其产品主要为日本所用,从技术本土化来说,日本控制的技术系统也只是建立在中国境内的一块技术飞地,在二战之前,其几乎没有对中国本土钢铁技术进步发挥作用。[27](P178)
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企业生存内外环境极为恶劣,裕繁等铁矿公司的诞生,似乎一出生就注定难以挣脱发展的困境,而日本处心积虑地掠夺中国矿石资源,清政府与民国政府方面对于日本压迫的软弱无力,使得它们最终只能“惨淡经营”。中国近代铁矿业发展困境,映射着深重的民族危机。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马陵合《倪氏家族与皖南铁矿业》(参见施立业、李良玉主编《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民国时期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的债务纠纷》(《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韩剑尘《北洋时期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债务问题再研究》(《江汉论坛》2016年第11期)。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裕繁公司的债务问题而展开。
②中日实业公司由杨士琦、李士伟、孙多森与日本人仓知铁吉、中岛久万吉等组织,1914年6月呈部注册给照,原定资本500万元,成立时先收125万元,1917年12月添收125万元,共有资本250万元,公司营业为通融资金、应募债票及承办调查事项,故非专营业之机关,其办矿始于1914年9月。参见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1]陈真,姚洛,逄先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8.
[2]马鞍山市志资料:第1辑[Z].马鞍山:马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1984.
[3]裕繁铁公司[Z].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卷宗号:08-24-12-057-01.
[4]繁昌县桃冲地方铁矿[Z].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卷宗号:08-24-12-055-01.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6]李海涛.民国初年铁矿国有策述评[J].江西社会科学,2016,(3).
[7]交通史·路政编:第17册[Z].南京: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
[8]裕繁铁矿公司[Z].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卷宗号:08-24-12-058-01.
[9]安徽繁昌县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霍守华启事[N].申报,1917-05-21(1).
[10]皖省议通电[N].申报,1919-01-16(3).
[11]皖闻纪要[N].申报,1927-07-02(10).
[12]王鹤鸣,施立业.安徽近代经济轨迹[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13]马鞍山文史:第4辑[Z].马鞍山:马鞍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14]马鞍山文史:第3辑[Z].马鞍山:马鞍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
[15]芋.安徽当涂宝兴铁矿调查记[J].矿业周报,1929,(53).
[16]马陵合.民国时期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的债务纠纷[J].安徽史学,2010,(5).
[17]马鞍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近代实业家徐静仁[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8]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949):第2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19]军扩声中钢铁恐慌与中国(续)[N].申报,1937-08-09(11).
[20]象鼻山官铁矿历年售砂概况[J].中国建设(上海),1931,3,(5).
[21]本社为铁锰对日输出宣言[J].矿业周报,1933,(224).
[22]本溪湖煤铁公司状况[J].实业导报(上海),1930,(3).
[23]庶.日本反抗接管大冶铁矿[J].现代评论,1928,7,(166).
[24]丁格兰.中国铁矿志[Z].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
[25]曹立瀛.工业化与中国矿业建设[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26]安徽省办炼铁所咨请备案[Z].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卷宗号:08-24-12-049-01.
[27]方一兵.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M].济南:山东教育教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