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刘项原来不读书(下)
赵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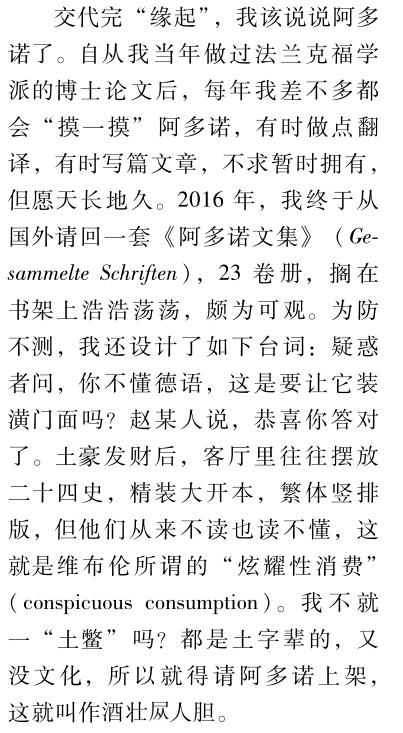
读路遥与海波:守住自家坟头哭
我一直思谋着重读一遍《平凡的世界》,借机琢磨其中的一些道理。似乎是2017年年初,我取出这部小说的第一卷,读了几页,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结果,这本书至今仍放在床头。
但我读过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2017年5月,程光炜教授召集一哨人马开“《路遥年谱》研讨会”,我在其中滥竽充数,但这本年谱读得还算仔细。我在随后的读后感中说,《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一文,我大概是第一时间读到的,但却死活想不起是在哪里读到的,是这本书让我恢复了记忆。此书在梳理路遥1992年5月的活动情况时指出:“《早晨从中午开始》开始在《女友》第5期连载,至第10期结束。”[1]读到这里时我眼睛一亮:哈哈,水落石出!当年我在一所地方院校教书,那里的图书馆或中文系资料室就订有《女友》,我肯定是在那上面读到路遥的创作随笔的。随之想起的是当时的疑惑:这篇很严肃的文章怎么发表在这种通俗类的读物上?路遥是要提升这本杂志的文化品位吗?
这就是读年谱的好处,它可以激活记忆。
书中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一条注释。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名知识青年到延川县插队落户。作者先引知青王晓建的回忆:“在延安读什么都没人干涉,从《中国通史简编》到《斯大林时代》,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可以达到‘雪夜闭门读禁书的至乐境界。”然后评述道:“路遥的成长除了自身的天赋外,自然离不开与知青的交往。这些北京来的知青多数是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有的比路遥大好几岁。路遥听说他们谁读书多,有见识,就去请教,彻夜长谈。后来证明,与北京知青的交往,对路遥的影响很大。”[1]67北京知青对路遥的影响当然很大,知识层面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恐怕还在情感层面。路遥被初恋对象林虹抛弃,差点自杀;后与林达结婚,又琴瑟不调。他与北京女知青的婚恋史,其实是很值得大做文章的。
书中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路遥写《人生》时与编辑的交往。因为读《路遥年谱》中所引的片断文字不过瘾,我又买回王维玲的《岁月传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重点阅读《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人生》就是被他催出来、唤出来的。他与作家打交道的故事很多,那些故事也很有史料价值。这本书我准备再读读他写柳青、梁斌、姚雪垠、刘白羽、周克芹等作家的部分,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上半年琢磨了一下路遥,下半年就有了延安之行。11月17日是路遥祭日,我应邀前往延安大学,参加“路遥逝世25周年纪念暨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会上听路遥生前师友讲述路遥故事,会下登文汇山,谒路遥墓,参观路遥故居,路遥的一切也开始丰满起来。遗憾的是,我当时只是匆匆准备了一个发言题目:《“民选经典”时代的文学英雄———对路遥其人其作的再认识》,本想随后成文,却一拖再拖,至今没有拿起笔来。
延安之行的收获之一是认识了路遥的生前好友海波先生。其实,我在2015年就“认识”他了。那一年,我读厚夫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带出了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我想把这本书收入囊中,却上天入地求之遍,两处茫茫皆不见。无奈之下只好向我的一位學生求助(她在该出版社北京分社供职)。她也真下功夫,库房里找不着,就托同事,找朋友,硬是跟责编要来本样书。见面时我与海波说起寻找此书的艰难,他才给我透露,当年这本书是买了个书号,只印了1000册。我大惊,居然有这等事情!不久我遇广东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向继东先生,他约我出书,我却想着成人之美。于是,尽管与向编辑只是一面之交,我却向他推荐开海波了。向编辑雷厉风行,不久决定把彼书易名为《说不尽的路遥》,再版面世。海波一高兴,就邀我写序;我一激动,就大包大揽,一点都不谦虚。我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做好事要留名,还要写到日记里。
我在序文中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把真实一分为三:“本我”之真、“自我”之真和“超我”之真。我说,许多人在“超我”之真上下功夫,做文章,所写之人往往就成了高大全,伟光正。海波却聚焦于“自我”,探测其“本我”,“于是面对路遥,他不但呈现其‘高大上,更要描摹其‘矮矬穷;不但写他走阳关道,更是画他过独木桥。而路遥的矛盾、苦恼,影响的焦虑,自我中的本我、小我中的大我,凌云壮志中的私心杂念、比学赶帮超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等,都被他回溯、捕捉、记录、咀嚼。这样一来,就觉得海波笔下的路遥不是完人,也不是美人,却更是真人———绝假纯真,真实得一塌糊涂。”我也是真人一枚啊,真人不说假话,这几行文字其实就是我2017年重读《我所认识的路遥》的真切感受。
那天参观路遥故居归来,海波到我房间聊天,说来说去,主题还是路遥。我就意识到,海波心中早已有颗“路遥疙瘩”在潜滋暗长(为了与海波的乡土风格搭调,我这里不得不弃“路遥情结”,用“路遥疙瘩”。为什么把“complex”说成“疙瘩”,答案请在尘元先生的《在语词的密林里》一书中找)。临别时,他赠我大作两册,一本是自传:《回望来路笑成痴》(黄河出版社2010年版),另一本是随笔集:《延川城里去赶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我正想了解一番海波,没想到瞌睡时送来个大枕头,不由得大喜过望。从延安回来,我偷工摸夫读海波,收获的全是惊喜。
说几句《回望来路笑成痴》。记得香港作家林振强说过:“平凡的人出自传,就如同平胸的舞娘跳脱衣舞。”海波平凡吗?平凡。尤其与路遥相比,海波或许就成了“平凡的世界”。然而,把这本自传读进去,我又读出了许多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可谓步步惊心,平凡的世界不平凡。海波当过社员,当过民工,当民办教师三进三出,在县剧团里干过编剧,远走青海任过文学编辑,回到西影厂当过干事,看过大门,甚至还跑到北京,扎扎实实当了几年北漂。在海波的大半生中,他讲述的是一个欲跳龙门而不得的故事,农转非的故事,不断进城的故事,由土包子变成写作能手的故事。与路遥相比,他显然更有故事,他的故事也更困顿,更曲折,更风沙扑面,更让人扼腕长叹。我读着,一边感叹一边笑,还暗自嘀咕:海波的“脱衣舞”跳美了。
为什么发笑?因为海波会写。搁给别人,如此苦大仇深,肯定是要字字血,声声泪,痛说革命家史的。海波不是这样,而是笑着说,疯着写。以喜写悲,悲喜交加;以乐叙苦,忆苦思甜。于是此书读过,我立刻微信他:大作《回望来路笑成痴》昨晚读完了,很喜欢。本来是一把辛酸泪,但你却欢歌笑语,叙述出一种喜剧效果。语言也好,土话俚语歇后语穿插其中,再加上一些四六句,音韵铿锵,戏谑幽默,有了一种节奏感,像赵树理一样。
我现在要补充的是,海波前期写秧歌,编剧本,更像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我们来欣赏海波的两段文字。
他说校长讲课的嗓门:“他教五年级算术,讲课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那声音能震得窗纸里外扇动,呼呼地响。他讲课时,学生都仰了身子靠在后排桌子上听,不然耳朵受不了。讲课效果极好,不但学生听懂了,对面山上干活的人也听懂了,捎带着就为村人扫了盲。大家自然高兴,只是苦了他自己。讲一堂课比刨一天地还累,出了教室还气喘吁吁,浑身是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2]
他说有一次穷得揭不开锅,忽然发现书架上有一扎陕西省党校的饭菜票,立刻率领妻子前往党校餐厅,先吃饱肚子,又买46个馒头,装了满满一网兜。他紧接着说:
我提着“祥云馒头”在前面开路,妻子推着自行车在后边紧跟,一路上吸引了无数眼球。众人的目光里有火,我只觉得浑身发热,走着走着,表演欲就上来了,一会装作患气管炎的罗锅,咳嗽得高一声、低一声,步步都像倒栽葱;一会又装成个“拐子”,扬起一只脚在空中划拉,左划一个逗点,右划一个问号,把个腿抡得像面条般柔软。气得妻子脖子和头一样粗,一把推倒自行车,气狠狠地走了,嫌和我一块走丢脸。我扶起车子望了她好久,最后亮开嗓子唱了首陕北民歌,以此来抒发心中的叹息。[2]201—20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前面我引休谟的话说:“只有写了自己丢脸之处的自传,才可能是真实的自传。”我颠来倒去读海波,似乎就没看到他写过多少“长脸”的事情,字里行间全是“丢脸”,话里话外全被“打脸”。如此自传,你说它真实不真实?
想起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那是“创作随笔”,自然也可以读成作者的自叙传。路遥写自己,庄重、得体,里面还透着一种崇高和神圣,那应该也是“把笔磨秃了写”的功劳。海波却反其道而行之:躲避崇高,消解神圣,嘻嘻哈哈,大大咧咧。这两种笔法孰优孰劣?只能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海波对于他和路遥的分歧,自然也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我所认识的路遥》中谈及写作观,觉得他俩的分歧尤其大:“他认为文学是历史的镜子,应该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构思,不但要反映现实,更要写出趋势;我认为文学就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守住自家坟头哭,就会得到相关人的共鸣。他认为作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政治上不敏锐、不正确、不坚定,写得再好也是‘鸡零狗碎‘小儿科;我则认为作家应该是自己所在阶层的‘代言人,‘争辩地、强辩地发出自己的声音。”[3]
守住自家坟头哭———这是我读海波的一个重要收获。此谓个人化叙事,微小叙事,其实它更接近文学的本来面目。然而,在路遥的宏大叙事面前,这种微小叙事却长期失语。或者是,路遥的气场太强大,大叙事遮蔽了小叙事。
于是,我很想为海波鸣不平:我们当然需要路遥,但也需要海波。正如我们需要奥威尔也需要纳博科夫一样。在陕西作家中,追求“社会正义”可能有其传统,路遥便是其代表。但除此之外,难道我们不该向追求“私人完美”的作家行一行注目礼吗?比如海波。
说出这番话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读过海波的小说。于是我决定把他的《高原落日》和《民办教师》列入书单,准备瞧瞧那里的成色。
读巴塔耶与赵天舒:你看那是多么蓝的天啊
赵天舒是我儿子,巴塔耶不用解释。
我在前面说过,2017年年初我买了本《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加]卜正民、[法]巩涛、[加]格力高利·布鲁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这本书就是从我儿子那里听说的。当时他在索邦大学念书,正与巴塔耶较劲。他说,《杀千刀》中有章内容说的是“巴塔耶的解读”,我就买回了这本书。
不仅是《杀千刀》,我还买回了巴塔耶《内在经验》的两个中译本(程小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尉光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后者译作《内在体验》)。为什么要读巴塔耶?当然与赵天舒同学有关。他在做与巴塔耶有关的硕士论文,我得了解一下他的研究对象如何高端大气上档次,捎带着补补课。许多年前,我就把汪民安编的《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巴塔耶文选》请回家了,记得当时也翻阅一番,但并没有入乎其内。如今,儿子与这位大人物叫板,也让他爹我鼓起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革命”斗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不读,更待何时?
但《内在经验》我到现在也没读完,读的那些也是稀里糊涂。好几次,我都把它带在出差的路上,打开读几页,困劲就上来了。有位朋友告诉我,治疗失眠的办法是读哲学书,一拿起康德、黑格尔,读不了几页你就呵欠連天了。巴塔耶是不是也有这种功效?
所以,这本书我没法谈,只能引用程小牧老师的解读文字装潢门面。她说:“借助‘内在经验这一奇特的概念,巴塔耶试图发现经验主体和认识客体在最炽热状态中的融合,在一种语言不能限定其界限的未知中,探索人的可能性的极限、非逻辑或非语言所达到的交流。”[4]这个解释让我恍然大悟:哲学的极限处是宗教,宗教的极限处是什么?还有,文学、语言乃至音乐的极限处呢?巴塔耶琢磨的应该是极限处的经验,如失控的大笑,凌迟酷刑的极苦,兰波意义上的诗意闪现。这种经验,语言无法固定(那里甚至没有成龙配套的语词),常常惊鸿一瞥。巴塔耶玩这个,佩服,佩服。
程老师还说:“这部书介于哲学与文学之间,思辨、叙事与诗歌杂糅,分析、想象与抒情并置。作者本人称其为‘记叙(récit),实为平时写下的思想笔记的集合。”[4]13我就想到了阿多诺所谓的“论笔”(Essay)。Essai(一般译作“随笔”)本是蒙田开创的法国文体,后被尼采、西美尔、卢卡奇、本雅明和阿多诺等人挪用,加工再造,于是又有了德国分支,我把它对译为“论笔”。巴塔耶钟情于此种文体,是不是对蒙田的发扬光大?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儿子,他便给我讲解récit(一般译作“叙述”)是怎么回事,“论笔”又该如何理解。他说:《内在经验》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与“论笔”截然不同:形式上,“论笔”单独成篇,每篇都是独立的文章,《内在经验》更像是一种碎片化、片段化的个人意识与体验的记录;内容上,“论笔”每篇都有独立的主题,论述的对象,理性的推理,《内在经验》则并不存在“论”的层面;而且,《内在经验》内容的核心是要把外在束缚完全剥离,回归一种本质上的意识活动。语言、理性都是巴塔耶所反对的东西,所以这本书是反理性的。儿子给我上课,激起了我说阿多诺的冲动。欲知阿氏“论笔”,且听下回分解。
话说《内在经验》我读出了睡意,《杀千刀》却读得我头皮发麻,如看惊悚大片。此书从王维勤的处决讲起,详解晚清刑律,回溯凌迟起源,罗列折磨死者的种种办法,解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酷刑。加之书中配有大量图片、照片,受刑者在哀号,刽子手很严肃,看客们摩肩接踵,正一睹为快,凡此种种,都会让人食不甘味,夜做噩梦。所以,尽管这本书史料丰富,分析细腻,很值得一读,我还是要劝告神经脆弱者谨慎打开。
但是,我却打开了,而且还从头读到了尾。从书中得知,反对凌迟的第一人其实是大诗人陆游。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凌迟“对身体的亵渎不但违背自然秩序而且还嘲弄了仁政,而好政府实行的正是仁政”。[5]但为什么凌迟处死却写入律法,变得名正言顺、光明正大了呢?作者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君主政体的精神是荣誉,共和政体是公民道德,专制政体是恐惧。”[5]181而在另一处地方,作者又特别指出:“执行一次死刑是政府用以展示其权威的时刻。而政府发威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框架内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5]24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次行刑不仅允许围观,而且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围观。在鲁迅先生笔下,看客均麻木不仁,但对于政府来说,这却是一次绝好的教育示范。它就是要用这种千刀万剐让人心惊胆战,这样就有了震慑效果。
关于巴塔耶那章,其实应该是辨伪之作。据说,巴塔耶对一幅中国凌迟图片沉思10年,然后琢磨出了他的“牺牲”本体论和“极苦”美学。但本书作者却认为:巴氏的《爱神之泪》书写风格可憎,语言表述贫乏,甚至不合法语文法,由此形成的核心观点(受刑时“痛苦与欣喜交融并不断加剧”)也相当可疑。经过一番考证,尤其通过对一句法语的分析之后,作者指出:“我们是否可以从中窥见一种意大利风格,它泄露了巴塔耶的助手,洛杜卡?这个错误提出一个严肃而广泛的问题:洛杜卡可能撰写了整本书?”[5]264
这一处让我大吃一惊,于是又问儿子:巴塔耶研究界是不是认同这种看法?儿子说:“这种批评其实只是本书作者巩涛(JérmeBourgo)一人的看法,别人并不这么认为,而且可以说,巴塔耶研究界甚至没有质疑过《爱神之泪》的真实性。我以为,巩涛和巴塔耶研究者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巩涛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考据的方式研究巴塔耶笔下的中国酷刑,发现了一些史实问题,并批判巴塔耶对中国酷刑的论述有失公允。但问题在于,巴塔耶本人并非历史学家,他也并非站在一个史学家的立场谈论中国酷刑的种种历史问题。在巴塔耶那里,中国酷刑完全是一个剥离了任何历史、政治含义的工具,一种图像工具,只是用来阐发他自己的那种观点。另外,巩涛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法语专著,名字就叫《中国酷刑》(Suppliceschinois)。《杀千刀》是2008年出版的,其中一些内容基本和《中国酷刑》一致。”
原来如此!接着我又琢磨了一番巴氏所谓的“狂喜式痛苦”(ecstaticsuffering)———该书译作“狂欢痛苦”[5]265,似不确。问儿子,他说:法语应该是douleurextatique,其实是一种迷狂的、心醉神迷的痛苦。记得莫言在《檀香刑》中写刽子手赵甲行刑,一口气写了五百刀(当然有详有略),有人直呼读得过瘾,有人批评写得血腥。莫言对此辩解道:“我写的时候也觉得过分,甚至有一种要受惩罚的感觉。今后还是应该节制一点。小说中关于凌迟的场面,出版社跟我商量这个地方能否删去一点,我删掉了一些,即使这样,很多读者还是难以接受。现在批评最多的就是关于凌迟的描写,有的文章甚至说我是虐待狂,我辩解的理由就是读者在批评小说时,应该把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区别开来。那是刽子手的感觉,不是作家的感觉,当然刽子手的感觉也是我写的,是我想象的。”[6]我现在想说的是,巴塔耶从凌迟图片中读出了痛喜交加,莫言是不是也在书写凌迟中享受着一种ecstatic般的写作快感?因为详写那十多刀,里面确实有炫技的成分。赵甲炫的是刀法,莫言炫的是笔法。
关于这一切,有时我是很想与儿子当面聊聊的,无奈他远在天边。我也想读读他的硕士论文,可惜我又是“法盲”。直到他把巴塔耶的《天空之蓝》转换成汉语,我才觉得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度交流。
2015年年底,有出版社找我儿子翻译《天空之蓝》,他问我意见。我说,既然你准备与巴塔耶过不去,做翻译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年之后,他与出版社签订合同,译事提上日程。但因硕士将要毕业,申博还没眉目,有大半年时间,他白天忙论文,晚上愁“嫁人”(找导师),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翻译并未顺利展开。直到一切理顺后,他才撸起袖子加油干,每天钻在图书馆。有一天他说,译完了。我说,发过来,瞧瞧看。
我把《天空之蓝》打印出来,带在了开会的路上。开完旧体诗会议一上车,我就读起这篇译稿,回京后又一鼓作气,读完之后写邮件,先是夸———译得不错,一些地方甚至读出了一种节奏感;然后写批注,提建议,给他下点毛毛雨。紧接着我又说:“我觉得巴塔耶的这个小说确实需要做些解读,因为看过之后,我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因嘛,一是我对巴氏所知甚少,黑灯瞎火看不出究竟。二是我读时更关注具体的句子,反而抑制了整体的感觉。我的初步印象是里面写出了一堆很迷乱的东西:性、革命、主人公怪异的感觉或体验等,它們纠缠在一起,让人觉得很特殊又很抓狂。也许我要读一读他的《内在经验》。”
后来我与儿子通话,明确给他布置任务:写篇解读文章,作为译者导言放前头。你爹我没文化,看不懂,能不能给我扫扫盲?儿子还真听话,奋战一个月后,说写成了。打开瞧,艾玛!一万七!
除了引言结语,他写了五部分内容:坎坷的出版历程、政治介入的局外人、形而上的焦虑、人类学的解答、文学的意义。他说:《天空之蓝》可能与尼采有关,因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曾用过时间状语“amhellenVormittage”,法译为“enpleinjour”,但巴塔耶两次引用尼采,写的却是“enpleinmidi”(在正午)。英译本的题目恰恰又是“BlueofNoon”,实为“正午之蓝”。我就想起余虹自杀后有人说过一句话,广为流传:“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我读儿子译稿前后,正好有人在纪念余虹,一转眼,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以巴塔耶的“色情”为例解读其“僭越”概念,说:“色情行为不同于生殖行为(procréation),不以创造后代为目的;相反,它的目的是享乐,是一种纯粹的能量消耗,是一种非生产性(improductif)的性行为。在这样的僭越之中,人可以暂时摆脱功利原则的束缚,重新以自我本质而存在,找回失却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读到此处,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耗费”在巴塔耶那里意在何处。他还说,巴塔耶这部小说,笔法刻意笨拙,风格力求生涩,“这种故意卖破绽、毁文笔的做法,在作家群中似不多见。也许巴塔耶如此起意,仍然源自于其献祭观:文学不仅在内容上充斥着色情、残酷、恐怖,在形式上也要对读者造成不适”。我就想起儿子翻译此作时跟我说过一个技术问题:巴塔耶“把笔磨秃了写”,我要不要译出这种稚拙感?这么译,一是不好译,二是别人译,为照顾国内读者,译得油光水滑怎么办?
他又说……不能再往下说了,否则剧透太多,影响观看。
总之,我是借助我儿子这篇文字,才算是读懂了一点《天空之蓝》。扫盲结束后,我长舒一口气,叫过老伴儿说:你家儿子上道了。老伴儿顿时面若桃花,露出了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我还不满足,又跟儿子说,得认真写个译后记,读书人看书,往往是从后记看起的。
儿子进入最后的校对阶段。一次通电话,他说另一个《天空之蓝》的译本好像出版了。我才想起他曾经说过,有位博士生也在翻译《天空之蓝》,且利用巴黎訪学之机,约他聊过巴塔耶。随后我在亚马逊下单,买回这个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译者名叫施雪莹,翻几页,感觉译得不错,挺顺畅。又翻阅译后记,发现有处地方说:“我衷心感谢那些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尤其是勒克莱齐奥先生与我就小说片段的讨论,以及赵天舒在参考书目上给我的建议。”[7]我把这些信息告诉儿子,说,人家在译后记中可是提了一句你啊,礼尚往来。儿子说,好,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我又说,要不我给你寄本,参考一下人家的译法?
儿子回答得斩钉截铁:不看!
你小子可以!说完这句,我也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读阿多诺:翻译才能读彻底
暑假期间,《文艺争鸣》喊我开会,我先是答应,后来反水。反水的原因是那里变动了日期,开会之日正是吾儿返校之时。于是我跟张涛说: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给儿子送行,因为他在巴黎念书,一年就回来这么一趟,不送送觉得说不过去。送完他我再赶过去参会,也参不成样子了,所以还是不折腾为好。区区私情,望你理解,亦请你把此情况转告王主编。张涛兄代表王主编回复我:要不您就送完儿子再来开会?会也不是只开一天,头天参不成可以参第二天的嘛。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就没了退路,决定以实际行动响应王主编号召。于是我请老司机张巨才出山,让他开车送人,把我们爷俩儿打包。那天我与儿子先在机场T1话别,随即奔赴T2航站楼,中午飞抵长春,正好赶上了下午的会。主持人说,首先请赵老师发言。我说,我先听几句,顺便喘口气。第一人发言完毕,主持人接着点将,却之不恭,我便抖起精神,说,我报来的题目是《“论笔”与文学批评》……
这次会议名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学术研讨会”。开会之前,我虽匆匆报了个题目,但实际上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开会期间,王主编叮嘱我要写成文章,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无法蒙混过关了。回京之后,我摆开架势,先读阿多诺的文章“TheEssayasForm”“On theCrisisofLiteraryCriticism”和《哲学的现实性》,后读《卢卡奇早期文选》,接着又读UlrichPlass的《阿多诺〈文学笔记〉中的语言和历史》(LanguageandHistoryinTheodor W.AdornosNotestoLiterature),读SusanBuckMorss《否定的辩证法之起源》(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中的相关论述,大干快上20天,写出了《作为“论笔”的文学批评———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说起》(《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20天左右,连读带写,按说速度不慢,但实际上,写与读都颇费周折。例如读,“TheEssayasForm”总共23页,我读了整整三天,读得还是云里雾里。写中还涉及译:既有的译文不满意,需重译;没译过来的要引用,更得译。例如,《论文学批评的危机》是篇短文,读过之后觉得重要,干脆全部译出。张涛那里催稿峻急,我也想提速,把“动车”提成“高铁”,但不幸却成了“绿皮火车”。稿子完成后我给张涛写邮件,讲述艰难险阻,谢他耐心等待。最后我说: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小型会议及大力邀请,否则按我当时那种偷懒状态,就既去不了现场,也写不出文章了。你们“逼住”了我,我才交出了这三斗粮,也才让我有了重温阿多诺的机会,这是要特别说明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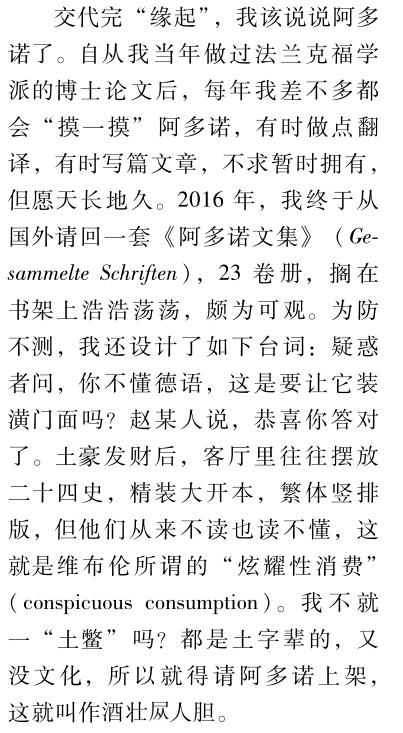
万没想到,一年之后,我启用了《文集》的第11卷———《文学笔记》(NotenzurLiteratur)。我是在读《哲学的现实性》时意识到德语版的好处的。阿多诺的这篇文章早有翻译(收入《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但我读得吃力(读阿多诺没有不吃力的)。随后又看英译文,琢磨其中的一些译法。中译者在“盲目的精灵(Dmonie)”处作注道:“在现代西文中,Dmonie通常都是些只具有消极意义的恶魔恶鬼。不过,阿多诺显然是在歌德意义上来理解Daemon的,着重强调了它的积极意义。”[8]我便顺藤摸瓜,找出朱光潜译本《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琢磨歌德说法与朱光潜注释。[9]但“盲目的”精灵该如何理解?这个表达英译为blinddemons,原文是怎么说的?我取下《文集》第1卷,在第334页找到了对应说法:blindenDmonie。又查字典,问跟我念书的博士生李莎,最终决定译为“看不见的精灵”。
这是我动用《文集》的开始。随后,为完整引用最后两段文字,我一边译英文,一边对德文。此文最后一句原译为:“精神真的不能制造或抓住真实实在的总体性,但是,它却能够渗透到细节之中,小规模地突破大群的单纯存在物。”[8]260我的译法是:“因为精神(Geist/mind)固然确实不能产生或抓住现实的整体性,但它穿透(einzudringen/penetrate)细节、小规模地炸毁(sprengen/explode)现存实在的大块东西还是可能的。”把einzudringen/penetrate译为“渗透”,把sprengen/explode译为“突破”,当然并不为错,但我却以为太文质彬彬了,还无法体现出阿多诺用词的“暴力性”。
还有“论说文”(Essay)和“论说文主义”(Essayismus/Essaynism)。Essay译作“论说文”我早有想法,现在又有了“论说文主义”。郭力曾请教《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的作者瓦尔特布什,问他德文词尾“mus”如何译。后者解释道:这个词尾并非“主义”之意,而是“方式、风格”等。我对这本书中的有些译法并不满意(如把“批判理论”译作“评判理论”),但这里的解释却正合我意。Essayismus译成“论说文主义”,字数多还挺费解,译为“论笔体”多简洁明了?当然,这么译,前提是得把“论说文”译成“论笔”。
在写给《文艺争鸣》的文章中,我已用4000字的篇幅,详细谈论为什么要把阿多诺所谓的Essay译为“论笔”,兹不赘述。但其中提到了我曾指导过的博士生常培杰同学,这里需要稍做补充。
常培杰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论说文”行文,谈论阿多诺的文学理论,我感觉不对,便让他进一步推敲,他却觉得“论说文最妥当”,这个问题就没法讨论了。受梁归智老师启发,我犹豫两三年后,决定借用他的发明成果,以“论笔”对译Essay,并让它在访谈韦伯先生时先行亮相,加注简要说明。2017年2月,常培杰通过微信发来一篇阿多诺译文,打开一瞧,是《作为形式的论说文》。我便说:“关于Essay,我还是认为‘论说文可能不是最好的译法(记得以前有一次提醒过你)。我后来琢磨,觉得可把它译成‘论笔。韦伯来北师大时,我通过李莎,跟他做了一个访谈,主要问他关于阿多诺的一些问题,其中也涉及Essay的译法。前些日子也刚把这个访谈整理出来,现发给你,供你参考。”
一小时后他回复我:“刚在路上读完。非常有意思的访谈!Essay翻译为‘论笔我觉得太突兀了。要理解这个词的译法还是要参考卢卡奇那篇论说文的本质与形式。德语中Essay确实有versuch的意思,这点阿多诺在文中明确谈到了,其主要区分对象是dissertation,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论文,学术论文。文中很多地方《否定辩证法的起源》一书都有谈到,但是他对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很有意思。至于‘独异性概念,跟我这两年关于艺术的思考竟有相通处,但就理论本身的创新性而言,法国哲学现有的讨论已经有很多。”
我说:“‘论笔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我的一位做古典文学的大学老师那里借用来的,我曾跟他请教过此问题,这里暂不谈论。‘论说文我之所以觉得并非最佳译法,主要是考虑它在汉语中的感觉和联想。就是说,一旦把Essay译作‘论说文,汉语中的联想可能就是别的样子而不太像阿多诺所说的那个东西了。我觉得当时翻译卢卡奇时,译者可能没太仔细琢磨汉语的感觉问题,所以译成了‘论说文,这样就给后来者带来了某种心理暗示。”
他说:“我一直觉得特定术语能贴合最好,但是中英文差异肯定存在,而且这也是文体本身的差异,汉语中本不存在的文体,就没办法用汉语本有的术语对译,只能通过文章语境来确定特定译词的意义,只要不是太偏离就好了。”
我说:“OK,此问题不再讨论了。”
常培杰的“执着”我是心里有底的,何况微信中三言两语,展不开也说不透。这样,我就计划不争论了,以后找到机会,再写文章解释。没想到这个机会来得如此之快。我在写给《文艺争鸣》的文中说过:论笔、论笔体“这种译法是否合适,当然还需要接受学界检验”。我现在想说的是,翻译之事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朱光潜先生觉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终结”(Ausgang)译得欠妥,随后他思考十数年,查阅英德多种版本,反复琢磨其中思想,最终才觉得应该译为“结果”。与翻译界泰斗相比,我才琢磨了几年Essay?所以,“论笔”这个译法是否妥当,究竟如何,我是欢迎同行拍砖的。我也将与培杰博士继续面对这一问题,共同思考下去。
我倒是很想读读常培杰译作,无奈琐事缠身,直到9月准备写文章读开“TheEssayasForm”,我才把他的译文过一遍。常译加快了我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进度,我要在此表示谢意。同时,我也要对包括常培杰在内的所有阿多诺译者表示敬意,因为阿多诺太难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法,《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阿什顿说过,《启蒙辩证法》的中译者曹卫东教授也说过,他指出:
由于阿多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一贯主张“小品文”(Essay)的写作方法,加上许多著作或是断片之作或是未竟之作,使他成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艰涩的一位,给读者、特别是非德语语境的读者带来了重重的阅读障碍。据说,德国有两个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可翻译的,一个是本雅明,再一个就是阿多诺。而阿多诺尤以为甚,他一生坚持用德语写作,即便是流亡美国期间,也断然拒绝用英文写作。在西方,阿多诺成了不可翻译的代名词。出于尝试,我和友人曾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辩证法》。虽然经过认真准备,还得到了许多德国专家的大力帮助,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小心加谨慎,然而,译本终究还是留下许多的遗憾,让我切身体会了阿多诺的不可译。从此,我决计轻易不再去翻译阿多诺。[10]
曹老师似乎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后来他好像就只与本雅明叫板,精心打造开《本雅明作品系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让阿多诺到一边凉快去了。
与此同时,我也想起方维规教授的一个说法,大意是:那些大思想家个个都聪明绝顶,思路清晰,他们绝不会说出一些不明不白的糊涂话。如果我们读译文读不懂,读得疙疙瘩瘩,一头雾水,绝对不是他没说清楚,肯定是你没译明白。译错了还怎么往下读?跳过去!方老师深谙翻译之道,我觉得他一不留神就说了句真理。难道不是这样吗?
于是,写完那篇文章,我开始犹豫:要不要重译《作为形式的论笔》?译的话好处有二:一、可以把这篇文章吃得透,拿得准,余光中不是说过“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吗?[11]阿多诺的思路与表达本來就曲径通幽,神出鬼没,如果只读不译,充其量,只能把握他百分之五十的意思。而翻译一遍,既是用汉语固定其表达,以免那如烟似雾的句子随风飘散,也是要加强理解。译过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个八九不离十?二、既然启用“论笔”对译Essay,只是写篇文章作用不大,只有亲自动手做翻译,才能把生米煮成熟饭。用膳者走过路过,尝过吃过,觉得味道尚可,便可记住这个译法。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打广告,搞推销。
但转念一想,意识到又要与阿多诺较劲,我就两股战战,坐立不安———对付阿多诺?那是脱一层皮,掉几斤肉的事情吗?你既不懂德语,英文又是“菜英文”,怎么把阿多诺拿下?
说来也巧,我这边文章刚刚出炉,“论笔”的发明者梁归智老师驾到。于是,我乘兴向他汇报这篇文章,感谢他让我移花接木,似乎还跟他说到了我译不译阿多诺的纠结。因《文学笔记》的德、英文版就放在茶几上,他又拿起来翻阅,对着标题琢磨。这时候他才告诉我,他英语最好,德语学过,逛涅瓦大街时,俄语也能派上用场。原来我只知道梁老师是红学专家,没想到他外语如此了得。厉害了我的……师(差点说成“哥”)!他说,术语翻译确实要考虑简洁,Essay又是两个音节,宜在汉语中找双音词对译。翻译有时就是要自造新词,这样才能陌生化,才有新鲜感。例如,原来并无“范式”一说,从意思上看,它与“模式”几无差别,但翻译时造“范式”而弃“模式”,新鲜感就来了。
老师就是老师,每次与梁老师聊天,都能让我获益很多。那天长谈过后,我发去《作为“论笔”的文学批评》请他指正,他发来《禅在红楼第几层》(即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作弁言”让我阅读。打开看,发现他在批评“论文体”“繁征琐引,三纸无驴”,也在阐释自己的“论笔观”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他说:“我杜撰的‘论笔,意思是提倡一种随笔文章其形而有论文之实的文体,或者说‘做论文要和‘写文章水乳交融。其特点是研究和写作都要突出‘灵感和‘悟性,‘逻辑是内在而非外在的,还要讲究行文措辞的‘笔法,而不呆板地标榜所谓‘学术规范。”说得太好了!我对这种境界不是也心向往之吗?于是我向梁老师汇报:我正宅在家里做翻译,深入学习“論笔体”,《作为形式的论笔》开工了。他发来一个大大的表情包:棒极了。
实际上,也正是在与梁老师长谈之后我才结束纠结的。或许是他哪句话击中了我?我决定一试,却只能从英文入手,便先在英文书中寻寻觅觅。忽然发现除ShierryWeber Nicholsen翻译过此作外,《阿多诺读本》(TheAdornoReader)中还有Bob HullotKentor译本。太好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给自己倒杯酒。两个译本全复印,比对起来更容易。又把德文版《文学笔记》置案头,跟李莎说,德语方面的问题我要请教你。跟儿子说,你手头不是有《文学笔记》的法译本吗?以后两个英译本不一致处,难理解处,你要给我看看法译者SibylleMuller如何遣词造句。我准备折腾自己,当然也不能让众弟子闲着。于是开译不久,我又给他们发邮件:这里是三个版本的阿多诺,你们也把这篇文章读起来。待我译完后,提交读书会讨论,给我挑毛病、找错误。
抗旨不读怎么办?拉大旗做虎皮啊:行家说了,若想了解阿多诺,最好是从《小伦理学》(我的译法,一般译作《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文学笔记》中的首篇文章《作为形式的论笔》读起。行家是谁呢?阿多诺的学生瓦尔特布什。
准备工作就绪,自我折腾开始。阿多诺本来就难,这篇似乎更难。头两句之后,第三句话我就摆不顺了。第一页中阿多诺说“论笔唤醒了intellectualfreedom”,这个“intellectualfreedom”如何译?以前引用我只是按英译翻成“智性自由”,这回看原文是“FreiheitdesGeistes”,又与李莎讨论,立刻觉得译为“精神自由”才最为准确。阿多诺提到了论笔的“Alexandrinismus/Alexandrianism”,千万不能“亚历山大主义”了,绝对是“亚历山大风格”。有句英文很简单:“Luckandplayare essentialtoit.”但luckandplay(GlückundSpiel)直译为“运气与游戏”感觉不对,能不能译成“碰运气和赌一把”?有处原文是“TatsachenmenschoderLuftmensch,dasist dieAlternative”,两个英译本译得一长一短。长者说:“Amanwithhisfeet onthegroundoramanwithhisheadin theclouds,thosearethealternatives.”短者云:“Technicianordreamer,those arethealternatives.”依前者,两类人是“脚踏实地者和异想天开者”,照后者,应该是“实干家和梦想家”,采用哪个版本更合适?文中阿多诺引用卢卡奇,其中有“thegreatSieur deMontaigne”之说,有人译为“伟大的索尔·德·蒙田”,但蒙田全名不是“MicheldeMontaigne”吗?问儿子,他给我解释:法语版是“le grandMonsieurdeMontaigne”,大意为“伟大的蒙田先生/阁下”,Monsieur等于Sieur。这个词不算是一个具体的头衔(如侯爵、伯爵等),而是一个表示尊敬的称谓(泛指),译成“索尔”肯定不对……
阿多诺几次引用卢卡奇,《灵魂与形式》中的《论笔的本质与形式》一文当然需要细读,但除此之外,他还谈及斯宾诺莎、笛卡儿、尼采、柏拉图等,他们的书要不要翻一翻?翻!一定要翻。于是我又去找《伦理学》《谈谈方法》《权力意志》《会饮篇》,甚至还找出了古留加的《康德传》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就这样,三个版本,翻来覆去,吭吭哧哧,牛步蜗行。我每天统计劳动所得,字数或是五六百,或是七八百。有一天译了一千三,居然觉得幸福满满。但仔细一想,又悲从中来。按眼下行情,千字七八十,我这个劳力出全工,一天还挣不够一百元。人都饿残了,这阿多诺还怎么往下译?因开机守着电脑琢磨,关机盯着手机修改,日思夜想,有时睡不着,有时醒得早。有一天八点上课,法兰克福学派正好讲至尾声,我一“开场”就“白”道:如果今天我脑子不转,口齿不清,先要请大家原谅,因为睡得太少。凌晨三点,半夜鸡没叫我就醒了。为什么醒得这么早?主要是在想一个人。想谁呢?———停顿三秒钟,卖关子———阿多诺!———哄堂大笑,余音袅袅。
与阿多诺搏斗一个月之后,我才拿出了这篇两万字的初译稿。记得译完之后的第二天,我半躺在床上,先读朱光潜译的《会饮篇》,后读他写的《谈翻译》,既琢磨其翻译笔法,也思考其所谈的翻译道理。朱先生译:“他迎来和穆,逐去暴戾,好施福惠,怕惹仇恨,既慷慨而又和蔼,所以引起哲人的欣羡,神明的惊赞。”[12]这是翻译,也是优美的汉语。朱先生说:“翻译上的错误不外两种:不是上文所说的字义的误解,就是语句的文法组织没有弄清楚。……所以翻译在文法组织上的错误是不可宽恕的,但是最常见的错误也起于文法上的忽略。”[13]这句话让我很受震动,我就琢磨,自己能否避免这样的错误?我就这样读着,想着。深秋的阳光照进来,晒暖了腿,晒热了脚,晒得印堂發亮,满面红光。“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林语堂的妙论开始浮现———“最佳的姿势不是躺直在床上,而是用软绵绵的大枕头垫高,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角度,而把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论躺在床上》)我不正是这样的姿势吗?半前晌,静卧在床,捧着读物,沐着阳光,心旷神怡,左思右想———我是不是很久没有这样的阅读状态了?
我想趁热打铁,把初译稿修订一遍,没想到后来天下大乱。我随身带着复印件,到庆阳,飞上海,下杭州,去延安,赴天津,走济南,却也只是改到一半,然后就全面中止,至今也未接上茬。
有一天翻书,忽然发现阿多诺的《新音乐的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一时间买回了,却还没来得及打开,便先读译者曹俊峰先生长序。其间审读一篇稿子,又觉得要想把这本书读透,不妨先读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诗学六讲》、查韦斯的《音乐中的思想》、达尔豪斯的《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休伊特的《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我先给盛世情书店老板发微信,让他们帮我找书,又见这几本书都关联着杨燕迪教授,或译,或校,或主编,便忍不住给他发微信,向他致敬。我说:音乐美学方面我想补补课,您能否给我推荐点书?他说:推荐这本———《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于润洋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我说:谢谢杨老师,这本书我多年前读过,确实好。我读的是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推出的最初版。
我是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听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杨老师的,记得当时与他聊阿多诺,说的就是《新音乐的哲学》。而他发言时引用英国美学家一句话,更是让我沉思良久。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说:“一切艺术都渴望达至音乐的境地(Allartaspirestotheconditionofmusic)。”
年头岁尾,我去盛世情书店取书。老板看见我,说:“走,咱出去抽根烟。”他带着我出书店门,左转走通道,进入一个小房间。房间转圈堆着书,码着箱,顶天立地,靠墙却放一张大木床,床边仅容一人侧身通过。随后我卧大床头,君卧大床尾,盛满烟头的烟灰缸搁中间,我们抽起了烟。老板讲起了他卖过的书,读过的书,那真是竹筒倒豆子,倒在脸盆里———作者、书名、出版社,呼呼啦啦,叮当作响。末了他还要总结陈词,求点赞:您说咱一卖书的,能做到这个份儿上,还算是有点情怀吧?我说,哪里是有点,是太有情怀了。说书名您就像报菜名,一口清,嘎嘣脆。书店老板做到您这层次的,少。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苏联,说起蓝英年,他说,蓝英年的《那么远那么近》我们两口子都读了,写得真是好!他见我一脸茫然,就说,赵老师啊,我觉得这本书您可真该读读。要不这么着吧,随后我给您找本,送您,留个纪念。他喜欢说“我觉得”,“觉”字还要发成三声,这是老北京的范儿还是拽他当年下放时学回来的“花盆儿”(延庆与河北交界地)口音?
老板与我同龄,我来北京念书的时候,这家书店正好开张。那是1999年。
这一次,老板送我上楼,我们站在空空荡荡的美甲店里抽烟,话别。拎着一包书出门,我心黯然。这么说,北师大东门外这个文化地标般的书店真要吹灯拔蜡了?它陪伴我将近20年,我又能为它做点什么呢?
回来先读《音乐诗学六讲》。岁末整书,忽然发现《那么远那么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压在一堆书中,很兴奋,立刻微信范老板,大呼小叫,这本书我已经找到了。
蓝英年先生的书如今我已读过大半。我发现,那里面的故事拐弯抹角之后,都能与阿多诺批判的对象挂钩牵连。
同时,我也读懂了范老板藏得更深的情怀。我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了。
注释
[1]王刚著.路遥年谱[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273.
[2]海波著.回望来路笑成痴[M].济南:黄河出版社,2010:81.
[3]海波著.我所认识的路遥[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163.
[4][法]乔治·巴塔耶著.内在经验[M].程小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2.
[5][加]卜正民、[法]巩涛、[加]布鲁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M].张光润、乐凌、伍洁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03.
[6]莫言著.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10.
[7][法]乔治·巴塔耶著.天空之蓝[M].施雪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77.
[8]张一兵著.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254.
[9]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35—237.
[10]曹卫东著.人书情未了[J].读书,2005(5).
[11]余光中著.余光中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450.
[12]柏拉图著.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50.
[13]朱光潜著.朱光潜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294—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