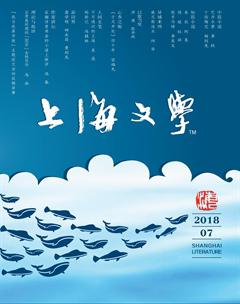《于无声处》四十年
过了年便陆续有记者来采访,说:《于无声处》四十年了。
小时候听说“抗战八年”,觉得不可思议的漫长;一眨眼,五个“抗战”过去了。
四十年来所有采访过我的记者无一例外地问我:你当时就不害怕么?我也无一例外地回答:不害怕。这次一个记者死不买账,盯着问:中央定的反革命事件哎,你怎么可能不害怕?!我认真地回答她:这个真没有。她固执地说:没平反哎。我笑了:没害怕哎。
害怕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它会压在你的心头,迫使你惴惴不安、坐卧不宁。我没有。有过担心,但那是挥之即去的。于是有人得出另一个结论:你胆子大,勇敢。又错了,总的来讲我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
三月初,当年上海热处理厂的几位工友到我家聚会,其中一位后来上过大学的师弟说:“你还记得么,当时你把蓝印纸复写的《于无声处》的稿子带到厂里给我们看,我带到大学里去给同学看,他们开始也没当回事;不久后,纷纷来找我,说我们家乡演了、我们家乡也演了,天南地北全都演了!那个时候我得意啊!”
我突然明白,那时候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了。
周围强烈的民意与火热的民心,给了我底气,给了我良知与勇气。你在做一件周围所有的人都赞成的事,你在做一件没有一个人反对的事,你感觉不到一点点对立、对抗的气息,为什么要害怕?
一
首先给我勇气的当然是1976年清明节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抗“四人帮”的人们。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生活在今天信息爆炸年代的年轻人,完全想不到那个年代信息闭塞之可怕!一方面是有意封锁,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知道,早在1969年美国人就登上月球了。这么大的事,十亿中国人十年不知,只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二是技术手段落后,家中有电话的极为罕见,打长途十分之艰难与昂贵。北京已经好几天上百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了,上海的人们还丝毫不知。
1976年4月6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路过上海,是一位河南的朋友托他找我取一样东西(来取的是一篇当时在地下流传的“反动”文章《献给四届人大》,这也是当时一个重大反革命案,1978年获得平反),约我到上海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见面。河南朋友说过此事,我就去了。来人年龄比我稍大,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忿忿不平地问:你们上海怎么那么平静?北京上百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一下子愣住了!他详细地告诉了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悲壮、雄伟的一幕。他说:我是个老“红卫兵”,后来发现被他们利用了,就退出来了;现在有人说你怎么又跳出来了?我说:江青、张春桥反周总理,我能不跳出来吗?!我听得目瞪口呆,我听得热血沸腾!对于“文革”我早有腹诽,但是不敢讲。现在这些话却被眼前这位陌生的朋友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上百万朋友,大声地喊出来了!我心里简直是狂喜!因为我终于知道了,不是我一个人心里反对“文革”,而是千百万中国人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了!那样一种喜悦、幸福、踏实,真是我成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享受!陌生的朋友临分手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写作,现在不是写的时候,但是你观察人最好的时候,将来总有能写的一天。
我的喜悦仅仅维持了一天多。第二天,4月7日晚上七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中央的决定:“四五运动”为反革命事件。我从一百度跌到零度。我也不知道那位始终没告诉我姓名的朋友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个夏天沉闷到了令我窒息。
但我看街上的行人,个个面无表情。明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怎么还是那么恭顺,那么沉默?!
我托一位画家为我画一幅月夜下的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是,终于没有画成。
1976年10月,我和哥哥陪母亲登黄山。黄山里面当时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既没有无线电,也看不见报纸,与世隔绝。一周后出山,长途汽车拐了一个弯,突然看见山上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的名字上都按“文革”惯例,打上了红叉叉。刚才还喧闹嘈杂的汽车里,一下子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心里却翻江倒海!可我又不敢太高兴,怕再来一次乐极生悲。
我连夜赶回上海,看到的是满街大标语、大字报。第二天我到当时大字报最集中的人民广场,看到庆祝的人群载歌载舞,一片欢腾。看着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错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那天起我就想写一个话剧:想写一件事,“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想寫一个人,1976年夏天从北京来到“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的一位天安门英雄;想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二
也有记者问我:你怎么会想到写一个话剧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约是中国作家涌现最集中的时段,而且基本上都是从业余作者中产生。这也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中国文艺界的大爆发!作家中绝大多数是写小说、诗歌、散文,写戏的很少。因为写戏有两个难点:一是受舞台限制多;更难的是,单单剧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作品,必须要在舞台上立起来,演出了,才算数。有几个业余作者有剧团?
而我那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学习写话剧,已经有三年了。
我的老师叫曲信先,是中国话剧泰斗熊佛西的弟子。他经常对我们讲起佛老每周两次在自家的花园里,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对他单独授课的情景。他把佛老传授给他的全部的写戏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我只要说一点,大家就能够明白曲老师的本事有多大了:他每周只给我们上两个晚上的专业课,其他时间就是经常跟我们一起集体谈创作、讨论剧本提纲,甚至是聊天。三四年中,他能够在我们这些毫无戏剧基础和背景的普通工人中间,培养出一批剧作家!这恐怕是我国戏剧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例。
我们能够迅速成长还得感谢另一位老师:导演苏乐慈。她是曲信先的同学,她在工人文化宫开办了一个业余表演训练班。于是我们创作训练班写出来的习作,可以拿到表演训练班排练。在台上立起来看自己的剧本可完全不一样,自以为很得意的剧本,台上一立起来,惨不忍睹!几次下来,我们就慢慢找到了舞台上的感觉。
但是,我学习时间短,创作经验缺乏;再加上毕竟是在“文革”期间参加的学习班,难免沾染“帮腔帮调”,说是反“四人帮”的题材,一下笔还是主题先行、“高大全”那一套,自己都看不下去。所以我除了积极搜集资料,例如“天安门诗歌”、“文革”中的各种人物、故事等,一直没有动笔,只是在苦苦思索,如何表达,寻求创作上的提升。
1978年5月1日,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天,被封禁了十多年的一大批中外名著,一下子在所有的新华书店里上架!每个书店门口都挤满了抢购的人群。由于书的种类太多,买的人也太多,不但采取限购的办法,每个书店卖的品种还不一样。于是大家都是从一家书店买到另外一家书店,买重了,互相在大街上交换。这种壮观的场面持续了好多天。可惜,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我也买到一批好书,而其中就有两本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书:《曹禺选集》和《易卜生戏剧四种》。曹禺老师的剧本我很早就读过,但那时没学写戏,感触不深。这次重读《雷雨》联想到“文革”中偷偷看过的惊心动魄的《原野》,还有第一次读到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深受震撼:原来戏应当这样写!戏里的人物应当这样写!这几个戏中的人物,每个人物都可以一层一层往下剥,而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而采用“三一律”的经典写法,把这样一群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想要不出事是不可能的,戏剧性自然而然就强烈了。而且这种短兵相接的、浓缩的写法,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茅塞顿开。
于是我坐下来,铺开一张白纸,画了一张六角形的图案,其中每一个顶端就是我剧中的一个人物。我一再琢磨每一个人物,还能挖掘出什么?按照曲老师教我的,再挖一层、再挖一层……同时我在六个人之间寻找关系联线,他和其他五个人有什么戏?她呢?他呢?
当整张图上线条密密麻麻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动笔了。
写得非常顺畅。有了这样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有些戏甚至不用细想,到了那里就自然而然写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我这个剧本完全是在脑后木拖板(一种厚木板制作的拖鞋,底厚一寸半以上)的“踢踏”声中完成的。我父亲解放前是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香港区公司经理。上海解放后,他接受上海市委工业书记刘晓、许涤新的指示,把解放前夕被国民党从上海胁迫开到香港的轮船,分期分批开回了大陆。大部分回到了上海,小部分回到了广州,只有极小一部分被国民党军舰拦截到了台湾。于是他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了,1950年,带领我们全家回到上海。当时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待遇……但是“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撤销了一切待遇,批斗、隔离、关押、监督劳动,前后整整十二年,到我写完剧本,他还在上海到苏北的客轮上扫厕所。带队抄家的公安民警问我母亲:1950年人家都往外跑,你们怎么回来了?原来有关部门多年来一直怀疑他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我们家的住房也被外人占了。最倒霉的是我睡觉吃饭写字的房间,是外来人盥洗如厕的必经之路,他们又是穿着木拖板住进来的,于是,他们一家四口来来回回的木拖板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这次也许我太兴奋太投入,木拖板声并未打断我的创作。三个星期,一气呵成,初稿完成了。那是一个深夜,扔下稿子我瘫坐在椅子上眼泪就流下来了,仿佛全身的激情与力量,一下子全消耗光了。
第二天,我把初稿送到了导演苏乐慈家里。
三
写小说,小说完成了,作品就完成了,最多是到哪里发表的问题;写剧本,剧本完成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有没有人看中投资?有没有导演愿意排?导演、演员对剧本的理解是不是与你相近?演出又有一大摊事……总之,后面还有千山万水。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跟你的戏是否成功性命攸关,但是,你却可能完全无权干预。这时候就看别人是不是愿意伸手推你一把了。
而我,命好。岂止是好,好到逆天。一路上,遇到的每一只手都在把这个戏往上推、往上推。最后,千千万万只手终于把这个戏推到了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高峰。
推这个戏的第一只手是导演苏乐慈。
她后来说:我一口气把剧本看完,内心非常激动!“四五运动”表达了中国人在心底深处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愤怒,宗福先写的这个剧本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人们心底压抑了那么久的一种呼唤在剧本当中迸发出来了。她说: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戏排出来!
当时有个规定,群众业余文艺只能排独幕剧;而这个戏是四幕大剧。苏乐慈把剧本送给文化宫文艺科副科长苏兴熇批准。那天我正在办公室,老苏叼着香烟走过来,把剧本往苏乐慈桌子上一扔:你们排吧。
演员找来了。张孝中读完剧本说:这个戏不演我们演什么?但是过了一些年,他坦承,曾经有一个晚上,他睡不着觉,久久地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儿子。
都是业余演员,都是厂里的工人,每天白天要上班,下班后才能赶到西藏中路的工人文化宫来排戏。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张孝中(剧中欧阳平的饰演者)所在的上钢一厂在吴淞,距离市宫22.4公里,冯广泉(剧中何为的饰演者)的吴泾化工厂,距离市宫19.1公里,施建华(剧中梅林的饰演者)的重型机器厂,在老闵行,距离市宫33.4公里……在四十年前的交通条件下,在炎热的夏季,他们来来回回奔波了整整两个月。
而且,他们无论排练还是后来的演出,都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只有超过晚上十点,有两毛七分加班费。导演和我都一样。由于导演和演员的要求,在他们排练期间,我始终参加,这样就使得我们一起融合在了戏中。
我还把剧本给了曲老师以及中学同学、厂里的師傅、文化宫创作班的师兄弟们等等所有我熟悉的朋友们看。大家都觉得不错。厂里大约有二十位师傅看过我的剧本,我特地问他们:这样的戏老百姓会要看么?他们说:会!后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这其中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个题材能不能写、有没有风险;相反,还有好几个人说:“四五运动”么老早好平反了。
9月22日,话剧《于无声处》第一次登上舞台。那是一次彩排。
那时的业余演出条件真是简陋,舞台非常小,也没有纵深,台上还有两个大圆柱子,演评弹挺合适,演戏真是难为导演和演员们了。服装道具大部分是大家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女主角穿的衣服就是苏乐慈的。还有人拿来黄豆和竹匾,把黄豆放进竹匾一摇,就是雨声了。
由于是彩排,不发票,凭通知进场——其实没通知也能进场。来看戏的除了市宫和各区县工人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大多数还是他们的家属,包括我们自己演职人员的家属。所以老人也有孩子也有,剧场里弄得跟菜场差不多。我心里烦躁不安:这毕竟是我处女作的处女演啊。但是开场没多少时间,剧场里就渐渐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一直保持到全剧结束。
戏结束了,大幕拉上了,但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他们是不是以为还有?片刻,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顿时热泪盈眶:观众认可这个戏了!台上的苏乐慈急了,催促着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快点!谢幕!谢幕!苏乐慈亲自拉开了大幕,演员们激动地跑出来面对同样激动的观众,鞠躬。以前,群众业余演出从来没有谢幕的习惯,从那一天起,我们有了。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剧组全体都把这次彩排当成了《于无声处》的首演:1978年9月22日。
我站在剧场门口,看着慢慢散去的观众从我身边走过,我听见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说:迪只戏倒蛮好看格,下趟再来看!
当晚,就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我们剧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集体照,一共十八个人。今天再看这张照片,觉得当时的我们怎么会那么年轻?
没有宣传、没有广告,这个戏却慢慢热起来了。过了两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居然有人排队了,这以前从来没见过。
文艺界第一个来看的是我同学的父亲、上海人艺的老导演何适。他早先听说我写了个剧本,曾經让我同学拿去看过,后来又送回来了。这次他拉着人艺老演员姚明荣一起来看,看完一言不发就走了。但是过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又回到了剧场后台。他对我说:当初看了剧本,我想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样的戏你们都敢排?今天看了戏,实在太棒了!我跟老姚一激动找了个小酒馆喝酒去了!宗福先啊,我们真是老了。
再过两天黄佐临老师来看戏了。第二天他到人艺说:人艺所有的人都要去看看这个戏。
随后,上海文艺界许多老前辈络绎不绝地都来看戏了,先后有袁雪芬、朱端钧、吴强、茹志鹃、吴仞之、邵滨孙、筱文艳……
而文化宫小窗口前已经不容易买到票了。
10月1日下午,总工会领导李家齐、张伟强等带领裔式娟、杨富珍等全市劳模观看了此剧,大家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
总工会是文化宫的直接领导,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我们的心就更定了。起码,演出条件可以得到改善了。四
写到这里,我们剧组的一位重要人物要出场了,她就是《文汇报》记者,“与我们一伙的”好朋友,周玉明。令人痛心的是,就在不久以前,她因病去世了。我在国外听说她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幸亏苏乐慈等立即赶到医院探望;我今年4月28日回到国内,29日即去看她,30日,她就走了。我至今仍不能接受,一个像她这样全身充满活力的人,会走得那么早,那么快。
我们的演出没有做广告,但是为了庆祝国庆,9月30日上海的报刊照例要做一个所有演出的通栏大广告,这里面就有一小块“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演出《于无声处》”的小广告。周玉明看到了,她想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就打电话到文化宫来打听。她也不知道是谁接的电话,那人告诉她:老好看的,大家都要看。她就来了。
看完戏她红肿着眼睛到后台找到苏乐慈,问她:谁是作者?苏乐慈朝站在门口的我一指,于是就出现了我永世不会忘记的一幕:她迈着充满弹性的步伐,就跟踩在弹簧上一样,一跳,一跳,跳到了我的面前。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生都是这样走路的,步伐中充满了激情、勇敢、快乐和自信。然后,她跟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一样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说:我要告诉天下所有的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好戏!
以后有好几天她都和我们整个剧组泡在一起,很快,我们成了“哥们”。她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文汇报》领导马达、史中兴的支持下,于10月12日在《文汇报》登出了。
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于无声处》,我们自然非常开心,但是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这篇报道后来会被胡乔木看到,会引起后面那么大的波澜!
紧接着周玉明又组织了一篇王家熙的《寒凝大地发春华》,在10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这也是媒体上第一篇《于无声处》的评论文章。文章和前面的通讯一样,都旗帜鲜明地点出了这个戏是歌颂“四五运动”的。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马达同志还在认真考虑在报纸上发表《于无声处》剧本全文的可能性。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有两位专业的老师看了戏对我们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意见本身挺好的,我们也很感谢。但是他们向苏乐慈和我提出把戏停下来,改剧本、下生活、重新排戏,再增加两名副导演,专管语言和动作。这个我们就不理解了。一个是演出任务那么紧,都是市级机关、单位、部队通过总工会安排的包场,要停也不是我们两人说了算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去找总工会说呢?增加两个副导演,这从来不是我们群众业余演出的风格啊?
10月25日晚上市委宣传部洪泽、江岚、吴健三位副部长看戏后,洪泽同志说:“我们三个人意见一致,这个戏不要改了,就这么演。三天以后到友谊电影院演出,有中央领导看戏。”但是10月26日这两位老师又向苏乐慈和我提出要我们停戏改剧本重排,我们要求他们向有关领导部门去提出,他们却坚持针对我们个人,并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据说某单位事后还出了一份简报,说我们剧组骄傲了,翘尾巴了。我当时只是一个青年工人、业余作者,真的感到压力很大。
10月27日,史中兴、周玉明找到了我,说《文汇报》28日准备发表剧本。我吓一跳,我说这个剧本、老师昨天还要我修改呢。史中兴说:你不能谁的意见都去听。我还是担心。最后他说:发表剧本是总工会同意的,然后他直接拨通了总工会宣教部部长傅惠霖的电话,叫傅部长直接和我说。傅部长对我说,《文汇报》发剧本是总工会领导研究同意的,其他人有什么意见你叫他们来找我们。
于是,10月28日起,《文汇报》连续三天连载了剧本。从此以后,那两位老师再也没有找过我们。后来好几位北京来的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看到了,有人说你们骄傲了,翘尾巴了,我们不相信。相信你们是经得起这个考验的。意见要听,但不要马上改。
当然,《文汇报》发表剧本的意义并不在此。后来我想,我们的戏在一个四百人的小剧场里演出,演一百场也不过四万人看,影响范围有限;《文汇报》一发表可就是撒向全国了!它当时订户有九十七万份!再加零售呢?说我有勇气,我觉得马达的勇气比我大。
以后我们去北京演出,周玉明随行。她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北京的首演,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朗诵怀念周总理的诗歌,一起参加和天安门英雄的聚会,一起到北京的各个工厂企业去巡演……她真的成了我们剧组的一员。
但是有一次她也“出卖”了我。由于对事情的背景不了解,所以《于无声处》后来跟坐过山车一样陡然升温让我害怕了。我对周玉明说:我害怕《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样板戏绝无好下场;我害怕我自己成为“暴发户”,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发户”绝无好下场。不久一位领导见到我说:你很清醒啊,你不想当“暴发户”。我吓一跳,除了周玉明,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啊。后来她承认,是她写了份内参。
2008年,《于无声处》三十周年,在我们大家一起编写的纪念文集中,她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她说:“三十年了,我们一个个从天真的小青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理想主义的守望者。我们坚守理想,坚守责任与良知。”
2018年,《于无声处》四十年了,她不在了,而我们,依然会坚守理想,坚守责任与良知。
五
从市宫那个简陋的小剧场,一下子走进友谊电影院,真正叫一步登天了!但是布景成了问题,这个舞台要大四倍也不止。上海戏剧学院党委连夜开会,决定支持我们一堂布景!舞台设计他们请出了著名舞美专家周本义老师。据说周老师一开始不理解:业余的戏为什么要叫我设计?看完剧本后,他连夜画出了设计图。
当我们走进剧场,看到那堂布景,简直是……没话说了!导演和演员赶紧重新调度重新走台,原来说话鼻子顶着鼻子,现在隔开一丈远。
几乎上海所有的媒体都来了,电视台、电台、各家报纸,剧场里热闹非凡。
晚上来看戏的是胡乔木同志,由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和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陪同。看完戏他们上台接见了剧组,表示感谢与祝贺。后来胡乔木同志说:我可以见见作者么?张伟强同志把我从边上拉到当中,胡乔木同志握着我的手开口就问:你生什么病?我一愣。后来猜想他是看了周玉明的通讯说我抱病写剧本。我说:哮喘病。他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个好剧本,希望你看好病,写出更多的好戏。我说:这个剧本还有很多毛病。他说:不,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也就是当天,《文汇报》开始连载剧本。前面还有一个编者按,是史中兴写的,我注意到,它里面强硬地指出,这个剧本“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76年天安门广场前发生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历史事件,用文艺形式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说出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
还是当天,《解放日报》头版大标题是《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文汇报》头版大标题是《〈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看到自己的戏口碑不错、门庭若市,受到观众喜爱和老师们的褒奖,我心里有一种简单而饱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一天,我心里却有一丝疑惑:怎么调门越来越高了?不就是一个戏么?
十一月初,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到上海来看戏,看完了上台就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顿时一片欢腾,我们想去天安门广场,我们想去慰问天安门英雄!
那些天我們接连为市体委、科委、民盟、市工交组、铁路局、剧协、各出版社、文联、市委组织部、上海戏剧学院、《解放日报》通讯员等专场演出。有时候一天演两场。
也是那些天,外地来了许多老师看戏:李准、田华、徐晓钟、夏淳……常香玉老师给我写来了信,希望我同意她把《于无声处》改编成豫剧,我连忙回信同意。
那些天里北京所有中央的大报都报道了《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而且都说了是歌颂“四五运动”的戏。
11月7日,应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通过央视,向全国实况转播《于无声处》的演出。这对于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都是第一次,所以央视在报纸的广告上写明“试转上海电视台节目”。不知为什么,在转播节目以前还要求先播出我和苏乐慈的单独画面,先向观众介绍编剧、导演。这在以前和以后的转播中好像都没有过。强烈的灯光打向我,我像傻子一样坐在那里。那年头也没有回放,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形象,只知道内心一片空白。
下来我就对周玉明说了关于样板戏和“暴发户”的话。
此刻,有一件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重大事情正在发生,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原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等,不料一开始陈云同志就在会上提出要解决六个“遗留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同志讲话的第二天,11月13日我们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4日中午到达北京,进入站台后我们大吃一惊:月台上居然站满了欢迎的人!其中有吴雪、金山、赵寻、阿甲、夏淳、于是之等许多我们仰慕已久的老前辈!北京文艺界几百人夹道欢迎我们这群普通的工人、年轻的业余戏剧爱好者,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交谈,让我们既感动又不安!吴雪同志在讲话中说,这个戏“给中国戏剧史写下了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刚到招待所休息下来,我便得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景仰已久的曹禺老师,邀请我今晚去他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