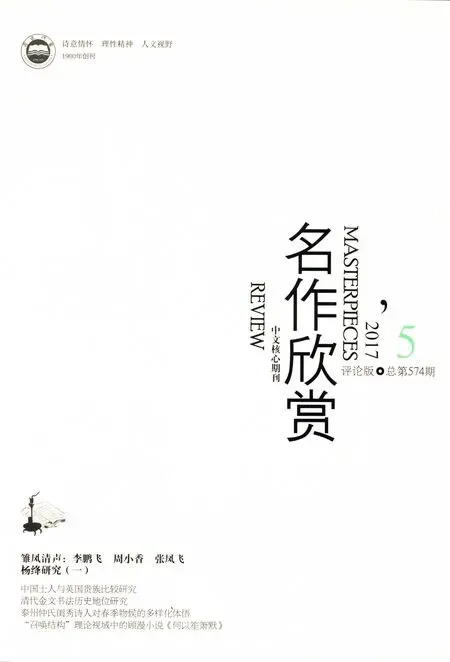看似平凡实奇崛
——论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的叙事技巧
⊙张立勇[玉林师范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在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中,主人公端方被妈妈带着磕了很多头之后到了王家庄,高中是妈妈逼着继父供读的,异父异母的姐姐红粉对他不错,但为了给妈妈挣个名分,在红粉出嫁的时候他却逼着她喊妈。继父对这个儿子并不看好,可他能够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弟弟,因此也承认了他在这个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在外面,端方用智慧和武力征服了佩全小团伙,虽然村里的地位得以确立,端方仍然是同学眼中的“下面人”,练就很好的身体仍然不能去当兵,而全村瞧不起的混世魔王最终得到了当兵的机会。端方终于认清了自己是谁,知道下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再也不允许亲弟弟端正给没有亏欠的人下跪。村支书吴蔓玲被迫答应混世魔王去当兵之后,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发疯,一口咬住了心上人端方的脖子。
如果按照成长小说的类型特征来考量,端方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主人公,因为他的主动性不够强烈,虽然长相好,身体棒,有才能,但遇到阻碍却容易退缩,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毕飞宇的高明之处在于,用这样一个不太合适的主人公串起了性格鲜明的配角形象,仪式感的运用,奇观化的展示,精描写的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时代的众生相,并在端方身上烛照了普通人的努力与追求。
一、仪式感
仪式感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程序动作长期重复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它在形成个体对集体的归属和服从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作家通过仪式感的刻画来唤起读者对特定时代、人物、情感的记忆,产生共鸣,实现吸引读者的目标。《平原》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把最重要的仪式感分布在小说开头、高潮和结尾处,涉及主人公端方的三次下跪。第一次下跪出现在第一章:母亲沈翠珍赶了一天的路,从王家庄来到了东潭村,领着端方四处磕头。先是给活人磕,磕完了再给死人磕。端方木头木脑的,从东潭村一直磕到西潭村,再从西潭村一直磕到兴化市的王家庄。端方一到王家庄就有爹了,姓王,王存粮。那一年端方十四岁,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母亲的带领下一路跪下来之后,就有了保障衣食的场所,有了爹,并且这个爹供他上了高中,成了全家最有文化的人。磕头不好,但磕头能解决问题的观念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也使得第二次磕头成为可能。
端方想去当兵,因为在部队上学会了做好喝汽水的能人王兴隆告诉他“混好了还能弄一把手枪玩玩”。但是当所有的努力都抵不过村支书一句话的时候,当理想就要泡汤而自己又极其渴望的时候,他想到了最后一招:给支书跪下:
端方怕了,想都没想,他的膝盖一软,对着吴蔓玲的床沿就跪了下来。这样的举动太过突然,太过意外了,连吴蔓玲的狗都吓了一大跳,身子一下子缩了回去,十分警惕地盯着端方。端方的心思不在那条狗上,他的脑袋在地面上不停地磕,一边磕一边说:“吴支书,求求你!吴支书,我求求你了,你放我一条生路,来世我给你做狗,我给你看门!我替你咬人!我求求你!”①
第一次跪是被动的,这次跪是主动的,成年的主人公端方主动放弃了人格尊严,这是理想对不合理制度的屈服,这屈服把故事发展推向高潮。下跪的基本模式是低头、弯腰、屈膝、头触地,对有独立精神的人类个体而言,低头本身就是示弱,弯腰是向对方缴械,屈膝带有臣服的性质,头触地则可以看作为对方献出一切,相当于放弃自身人格。然而却失败了!吴蔓玲看到这个内定候选人的表现,心凉了,失望了,把机会给了强奸自己的混世魔王,她觉得与其帮助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如先为自己考虑退路。这次失败让端方迅速成长起来,他放弃了当兵的念头,逃到养猪场用劳动去证明自己,下决心再也不跪。这时候第三次跪出现了。
母亲沈翠珍接连做噩梦,她意识到该回乡走亲戚,看看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她带着端方和端正回到东潭村见到老母亲:沈翠珍跪在地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端正拽过来,让他跪。端方却一把拖住了,恭恭敬敬地尊了一声“婆奶奶”。端方不能让自己的亲弟弟下跪,对谁都不能。人一旦跪下了,那你就跪不完了,这是没完没了的,会成为习惯。他的弟弟不欠东潭村什么,端方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在这个地方跪下去。
端方不让端正跪,因为端正是端方的亲弟弟,相当于端方的延续,他不让弟弟跪就是代表自己再也不会干跪人的事情了。
小说故事架构要考虑三条线:事件线,逻辑线,思想线。初级作者往往把事件线当作故事的主线,事件发生、发展、高潮、结局,事件结束了,小说就完了。中级作者则把逻辑线看得比较重要,事件的发展要符合日常逻辑,违背逻辑意味着小说的失败。毕飞宇写《平原》则超出了前两种情况,甚至摆脱了“设定目标——遇到阻力——努力进步——取得成果——发生意外——柳暗花明——实现目标”的故事成规,从主人公思想发展的角度去完成故事化。端方被动跪人的时候思想还不成熟,长大成人后为了目标主动跪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想利用原有的规则,是思想的发展。最后他阻止端正去跪没有亏欠的人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有了成熟的思想。如果从事件线去看,主人公去当兵的事并没有讲完;如果从逻辑线上去看,吴蔓玲咬住端方脖子的嘴应该松开;这两条线都没有完成,因此给人故事戛然而止、半途中断的感觉,但是从思想线上看,故事到此应该结束了。
下跪的仪式感构成了故事的思想线,其他的仪式感则可以唤起读者对特定时代、人物、情感的记忆,产生共鸣。比如生产队出发割麦的仪式:生产队的劳力们一起汇聚在队长家的后门口,大伙儿闷不吭声,一起往田里走。比如吴支书站立的仪式:这一来好了,两只手空下来,那就撑在腰的后头吧,两条腿做出“稍息”的姿势,舒服了,这是吴蔓玲一天当中最清闲的时刻,也是最满足的时刻。比如偷偷拜佛的仪式:孔素珍蹑手蹑脚,她来到了堂屋,把佛龛请出来了,净手、点灯,燃香,孔素珍盘在了蒲团上,她的女儿三丫也盘在了蒲团上,孔素珍说:“清净持戒者”,三丫说:“清净持戒者。”比如猪吃食的仪式:醒了再吃,吃了再醉,醉了还睡,睡了再醒,醒了还吃,吃了还醉,醉了还睡,睡了还醒,醒了又接着吃。比如端方吃赵洁送的金刚脐时的仪式:“打开来,一股香味扑面而来。端方尝了尝。好吃。馋了。咬了一大口,又咬了一大口。嘴里头顿时就塞满了。噎住了。眼泪也出来了,在眼眶里漂。端方想,不该读高中的,不该读。不该到镇上来的,不该来”,等等。仪式是岁月的刻痕,有了仪式才有历史,有了仪式才有人生。
二、奇观化
小说里的人要比生活中的好人好,还要比生活中的坏人坏。这好和坏都有一个限度,纯粹的好和纯粹的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前者让人怀疑,后者令人难受。这个限度控制在读者看了新鲜但不陌生,了解而不熟悉的水平,就可以实现奇观化,奇观化带来的精神愉悦是小说阅读不竭的动力。
《平原》中类似的奇观化很多。
蚂蚁搬家是农村人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但毕飞宇笔下的蚂蚁搬家却与众不同:“它们把树根当成了广场,在广场上,它们万头攒动——似乎得到了什么紧急通知,集中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正在举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游行。天这么热,它们忙什么呢,一副群情激奋的样子。它们很积极,很投入,很亢奋,究竟是为了什么?天热得近乎疯狂,但更疯狂的还是蚂蚁。”
生产队生活的人们对集合太熟悉了,农民对蚂蚁太熟悉了,但蚂蚁像社员一样的集合就新鲜了。说你了么?没有。没说你么,怎么左看右看都是你?
端方跟三丫在小学教室里办完事后回到家,是沈翠珍发现端方身上有红疙瘩的。最先是在脸上,一脸。脱下衣服一看,沈翠珍慌了,端方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一张皮简直就是一个马蜂窝,人了。沈翠珍的头皮一阵发麻,额头上暴起了鸡皮疙瘩,以为端方得了什么急病了。
谁都被蚊子咬过,谁都看过蚊子咬过的包,但是被蚊子咬成马蜂窝的样子就新鲜了,能被蚊子咬成马蜂窝而浑然不觉的那种激情场面,就不言而喻了。读者比沈翠珍明白得早,沈翠珍明白了,读者会心地笑了。
端方想当兵,不敢直接跟吴蔓玲支书说,在顾先生那里也没找到答案,嘴里淡出鸟来,想喝酒。混世魔王家里没有酒,只有酱油。端方把酱油拿过来,咕咚咕咚倒了半碗,尝了尝,有点意思了,点点头说:“有滋味在嘴里就好。”舌头上还是有点儿寡,就又放了一把盐。端方一不做二不休,又放了一把。这一来酱油的滋味已经再也不像酱油了,咸得厉害,接近于苦了。端方端着酱油,慢慢地喝。他喝得有滋有味了,还滋呀咂的。喝到后来,他终于像李玉和那样,端起了碗。混世魔王说:“你可悠着一点。”端方一口干了,脸上痛快的样子,放下碗,抹了抹嘴,说:“没事的。我醉不了。”
人在失意的时候就想吃东西,没有想吃的东西就用可找到的东西代替,酱油拌盐喝出了酒的味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失意?读者看着端方一口干了,自己嗓子发紧,仿佛倒进了自己的嘴里。想象作为一种能力,可以把意念变成现实,奇观化无疑是最佳的手段。
奇观作为对审美对象的新异化展现,主要有视觉奇观、听觉奇观、触觉奇观、味觉奇观和嗅觉奇观,如前面的蚂蚁搬家和端方身上的红疙瘩,就是视觉奇观。端方喝酱油,属于味觉奇观。文学是想象力艺术,归根结底这些奇观都会转化为读者的意象,造成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象奇观,也使得文学欣赏呈现多元共生的局面。
三、精描写
文学具有图解和记录时代的功能和意义,不同于历史记载真人真事,文学记录真情感真体验,这些体验反过来更深刻地反映了情感发生的环境和氛围。如果说仪式感是由内向外的,奇观化是由外向内的,那么精描写则是内外兼修的。毕飞宇在平原中,把文字使用得臻入化境,手里有刀,仿佛无刀,手里无刀,却刀光剑影。精描写是精彩描写,是精细描写,是人物在素描大师眼前的舞蹈,而素描大师把这种舞蹈二次创作升华为艺术品展现给读者,不怕你不懂,就是要你懂还不会产生求知的自卑。平原的精描写表现在对顾先生、老鱼叉、三丫等人物的集中展现上。
顾先生是个右派,自己掰着手指头教给王家庄人自己是右派;写一手好字,写标语让王家庄跟北京的距离空前的拉近;把做代课老师看成天降大任,一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背出连公社书记、县委书记都背不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在清理队伍的时候因为没到农忙,所以在学校多待了些日子,批斗会上佩全的顶头一刀砍死了回学校的念头,去给集体放鸭子;寡妇姜好花用投怀送抱的方式抢去一百四十六个鸭蛋,沉重的负罪感让顾先生狠命地背诵马恩列斯毛,说话全是革命领袖的文辞。集中的笔墨把顾先生写活了,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会干什么,能干什么,要干什么,干些什么的大问题就条分缕析地摆在那里,就像玻璃罩子里的恐龙骨架,虽然不懂,却能够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老鱼叉是精悍农民的代表,在村里任何事情都打头,儿子是合作医疗的医生,分到了地主家的老宅。就是这样一个人,魂丢了,在院子里到处挖,并且看到了被杀头的这个宅子的主人王二虎,要他还脑袋和房子。他想还,却不知道该怎么还,于是拼了命卖力气,但是王二虎总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冒出来,逼得老鱼叉上吊,即使这样也死不了。终于1976年9月10日,老鱼叉跟儿子兴隆一起清理了大瓦房的瓦花,在瓦缝里点了三根香,朝着正北方磕了三个带有金属般声响的头,脑袋朝下,一头栽了下去。老鱼叉为什么会不踏实呢?人多力量大为什么也会孤单?没有答案,答案自在人心。
三丫身份不好,可是喜欢端方,死心塌地地喜欢,主动献出了自己的身子,但没有拗得过母亲孔素珍。孔素珍请出菩萨也没能够让三丫放弃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念头,于是把她锁起来,把她很快地嫁人。三丫喝农药表示抗议,母亲妥协了,端方露面了,全村人认可了。三丫胜利了,三丫却死了,死在了曾经给端方带来幸福感的兴隆从军队学来的技术制作的汽水上。年轻人,有勇气,有魄力,敢爱敢恨敢付出,但是得到了什么呢?用物质来衡量,什么都没有。用精神来衡量,一切都空虚。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顾先生、老鱼叉、三丫都不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但他们都是时代的主人公,同样的吴蔓玲、混世魔王、老骆驼、兴隆、孔素珍、沈翠珍、红粉、王存粮等也都是时代的主人公。作家用文学笔法写出了历史笔法,读者在看故事的同时,看出了时代变迁。
《平原》是一部好书!
① 毕飞宇:《平原》,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一一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