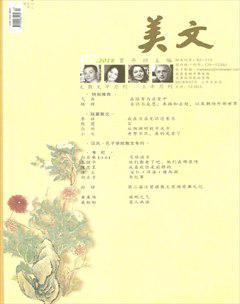心中的乡土(上)
巴里·洛佩兹 张建国
一
海冰消融季节,宾格克岛狭窄海滩上潮汐的日涨落周期很难辨认。在北冰洋的这一区域,波弗特海的海水拍打着阿拉斯加北部海岸,潮汐上涨很少,只能用指尖测量。无风的日子里,海边水面映出的云彩一如原物,没有变形。如果你有足够耐心,在水边站六个小时,水面才会上升到你靴子的跟部。这片土地还有另一个特性。北极东部,在昂加瓦湾和加拿大群岛的海湾,潮汐涨幅很大,可上涨40英尺。
宾格克岛位于北纬70°35′、西经149°35′,距阿拉斯加北部海岸几英里,在科尔维尔河三角洲东约30英里。该岛是琼斯群岛的最西部分,受到迁徙野鸭的青睐。琼斯群岛像一个长条形屏障,保护着名为辛普森浅海峡的沿海浅水区。
这部分北极海岸很少有西方人造访,直到最近,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1968年2月,在宾格克岛以东40英里的普拉德霍贝发现了油田;晴朗日子里,东边的地平线上,油田冒出的乌云般黑烟依稀可见。该岛西南几英里,在大陆上的奥里克托克角,有远程预警系统的站点。宾格克岛上有现代探索者的废弃物:工业勘察和军事行动留下的遍地碎屑,近期因纽特人和科学考察营地遗留的垃圾——黄色聚乙烯绳子、空木箱、白色汽油桶和外装马达零部件。
宾格克岛长约四英里半,有几处宽度达半英里,它最明显的人类迹象是,岛的西端屹立着一个小屋和两个淡黄色隔板建筑物,岛的东端屹立着一系列沿海勘察标识物。两个夏天的部分时间,我和几位海洋生物学家,住在该岛西部海滩边的其中一个单间小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但遇上“坏天气”,比如,八月常见的暴风雪或波涛汹涌的海面,让我们无法在小船上有效作业,我就会在岛上的苔原平原漫步。
在这片土地上缓缓行走。体验着它带来的直观感觉,期待着它可能隐藏的东西,这是我的老习惯了。眼睛突然被草丛里闪亮的东西吸引——那是昆虫的外壳。鼻子凑近小花,闻北极特有的清香。双手翻起一块奇形怪状的骨头,推断着是什么动物。直到脑海中出现它的样子,和它原来在岛上活动的情景。发现不规则的石头,就会起遐思,遇到脚印和破碎的蜘蛛网,就企图想清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儿。
那两个夏天,我还发现,野鸭蜕下的毛被冲上长长的海岸线。成堆地堆在海滩上。在泻湖区一边的浅水中,我发现了北美驯鹿完好的蹄印,清晰得就好像驯鹿刚刚在黏土上跑过。它们肯定是春末踩着最后的冰层,从这里穿过。苔原上动物痕迹非常明显的地方,我都蹲下来仔细研究:加拿大黑雁在淡水池塘边吃过草;环斑海豹的头骨被海冰或食腐动物向陆地上移动了几百码,草丛被一只休息的狐狸压平了。
在海滩阶地底层临海的一面,我看到苔原下闪闪发光的冰层边缘。悬在其上的是土壤表层和像眉毛一样浓密的植物。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尝试,但最终也没能成功靠近进食的雁群。因为雷鸟近乎完美的伪装,它们在地面上神出鬼没,时隐时现。我把下列东西带回小屋,放在床边的架子上,保存一段,沉思一番——它们是这片土地的遗迹:别卢哈鲸鱼脊椎骨的碎片,疑似史前海洋等足类动物的甲壳,数捧羽毛。在我温柔的审视下,这些有形的东西还是洋溢着某种原始的神秘。
从有时的照片上看,宾格克岛似乎荒凉凄惨,毫无生气,令人失望。冬天里,它消失在茫茫白色之中,向海一边融入波弗特海白色的海冰中。向陆一边融入沿海平原白茫茫的苔原,看不清任何界限。六月,该岛才显露出灿烂面孔,鲜花、昆虫和鸟类随处可见,但短短几个月后暴雪初临,眼前又是白茫茫一片。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矗立的全冠树令人鼓舞,云雀的飞翔和叫声令人欣喜,风吹拂高高草丛的景象更令人舒心,这样看来,宾格克岛相当贫瘠。初到岛上时,我也把荒凉看成是它的一个特征——我读过或听过此类描述。然而,在开始熟悉这个岛的短短几周里,我发现它并不荒凉。我们把这类景观想象成原始、荒芜、和异教之地,这明显是偏见。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我们不假思索地存储毒物或实验武器;我们会把它看成像沙漠一样的地方,我们曾向那样的地方流放异教徒,释放背负我们僭越罪名的替罪羊。
我们很难理解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景观。就像我们听不懂野生动物的交流。我们对故乡的亲近和自信等复杂情感,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
西方思想传统认为,所有文化的人不得不去探寻,人类因为经济驱动去寻求新土地。迷失在这一有效却缺乏人情味的观念之中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比较简单地去渴望。渴求不太复杂的生活,渴求新鲜的亲密接触和不断更新。这些渴求也驱动我们进入新土地。渴求使想象对所发现的东西产生曲解。对财富、复兴和胜利的渴求,与科学测量和描述,或经济扩张的迫切需要一样——或者比这些因素更能——决定对新发现土地的地理判断。
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芝加哥会议上宣读一篇论文,改变了美国史学的进程——转变了历史学家的观念。使他们重新认识如何把过去的基本材料按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编史方式。特纳的观点被称为“边疆假说”,当今,它已经成为我们看待一个国家的过去的重要方式,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但在当时,它因太独特了,没有得到认可。
1893年之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是由脱离欧洲影响的渴望塑造的,或者说,是由导致内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塑造的。特纳提出了第三种观点:美国是由它事实上和观念上的西进边疆塑造的。特纳认为,以进取心、首创精神和艰苦努力为显著特征的美国民族特性,可以从其公民在边疆的种种经历中看出一些端倪。历史学家改进并推断了近一个世纪,最后普遍接受了特納的假说。
特纳的观点至少表明了两点:第一,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叙述方向可以修正:第二,历史展演的场所——地理景观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原因是,一方面,它的确对人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投射,是人类感知的产物。北美历史上,19世纪的西进运动最能说明这一现象。针对低草草原还是高草草原适合耕种,政客、出资人、报纸编辑和商人进行了激烈争辩。在大多数争论中,赶往新兴地区安家的人和爱唱反调的人的政治伪言,以及农业理论家的抽象概念,压倒了当地实际的降水记录证据和当地居民的陈词。
也许这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北美地区最令人厌烦而且最具讽刺性的政治问题之一,是华盛顿和渥太华颁布法律法规时,似乎对这些法律法规要推行的地区的实际条件完全无知。然而。我们无论是谁,即使不厌其烦地在一片土地上漫步,也不能完美地了解这片土地。我们的认知会受先入之见和欲望的影响。自然景观是空间和时间未加雕饰的寓所,不可能完全看透:但这并不一定使我们在寻求了解它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境地。各种自然景观在形式和色彩上,在固有的生命多样性方面,在土壤的触觉品质、暴雨拍地的声音、花蕾的气味等方面,本来就是神秘的,相信这一点——相信各种自然景观是神秘的种种组合,就比较容易探讨它们。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承认它们的神秘本质。就像承认生活中的其他神秘现象那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神秘不同于不解之谜。
此刻,我记起两件事。在阿纳克图乌克帕斯,我问一个男士:你造访一个新地方通常做些什么啊?他回答说:“我倾听。”没有别的。他的意思是,倾听这片土地在诉说着什么:在这片土地上四处走走,长时间开启各种感官,集中注意力,欣赏它的方方面面,自己不说一句话。他相信,以这样一种尊重态度进入,这片土地就会敞开心扉。另一件相似的事儿,是一批美国画家的经历。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其十九世纪欧洲同行的价值认同,这批画家开始把这片土地想象成本身就具有非凡力量:令人着迷又让人恐惧,永远引人瞩目又丰富得不可捉摸,充满未知又野性十足。正如“上帝的面孔”。他们如是说。
二
当我迈出宾格克岛的小屋,映入眼帘的是向南部和東部蔓延的普普通通的苔原平原。几只绿灰色海鸥从地面飞起又降落。我感到湿冷空气犹如从冰箱里涌出,直扑我的面颊。离小屋的门有几码,一只死了的普通雌绒鸭,僵硬地、孤零零地躺在苔原上。再往西几码,一张髯海豹皮被老练地拉伸在短木桩间进行干燥。几码之外,一只北方瓣蹼鹬在淡水池塘水面猛烈地转来转去,捕食浮游生物。
西南风已经吹了两天,所以今天我们没出海。天空阴沉,暴风雪即将来临。我往南穿过苔原走向浅海峡,想着在那儿会不会看见野鸭。我心里有个大概的计划:走到那儿,然后向东沿着海岸走到排水较好的苔原地,那样更容易走,返回时先横穿小岛,然后沿着靠波弗特海一边的海岸回到住所。
这里地形平坦,即使天幕低沉,这片广袤的区域还是使我陷入沉思。然而,广袤是一种假象。北极探险家的日记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许多信息都隐藏在那儿,迫切期待被发现。原因是,在这片平淡无奇的景观中,突出的地方太显而易见了。这样的地方人的眼睛马上就会注意到。还有就是,这样的景观让人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就像在沙漠中穿行一样,碰见陌生人的期望不高。这里人迹罕至,而且。即使偶尔碰到一个人。他们的意图是探求隐秘怪异的信息。这些信息犹如偏远地区流淌的潜流一样诡异,因而,你想了解他们的期望也不高。有一次,我在育空河上游宿营,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独木舟上。看到他举起望远镜向游隼筑巢的悬崖瞭望,我就猜出了他是谁,他是研究游隼种群数量的生物顾问:这是我一周前在费尔班克斯的小餐厅的谈话中听说的。他很可能也知道我在这里的差事。那一刻,这一地区的某些陌生感不复存在。
如果你不像看待投资那样去看待花费时间,不像发放珍贵商品那样烦躁不安地去支出时间,而是把时间看作像平坦的大地那样浑然一体,没有任何区分,你就可能忘掉距离感——轻松自如地走到很远的地方,而不会被这片土地的辽阔吓倒。如果我们着装得当,带了一点食物,而且有办法获取更多食物、建造住所,我们就能从容地运用感官去体验、欣赏这片原野。我记得,这看似无吸引力的苔原平原,却是当地动物的食物和便捷工具宝库。
我沿着结霜区的边缘朝西南方向走,意识到有鸟在飞。远远的黑点从天空穿过,那是潜鸟的飞翔轨迹。稀树草鸦轻快掠过地面。鸟儿飞来飞去——到海上觅食或是去浅海峡休息——似乎遵循一个固定日程表。科学家们说,鸟儿们来来往往觅食和休息的程式,每二十四小时循环一次。但对这个程式的描述,像解析任何有节奏的运动一样,变得比个人体验更参差不齐,更错综复杂。
从微湿地面走到全湿地面,从全湿地面到干燥地面,我的脚步声不断变化。这儿是生物生存的微生境。我翻开脑海里北极植物的索引页,试图想起哪些植物是这些边界区所特有:哪些植物乍一看就能让人区分半湿苔原和多水苔原,多水苔原和干燥苔原?我记不得了。无论如何。这样的共性概括在我脚下的具体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个是更精确的本地知识,更谨慎地确定的边界,显得很丰富;这些微生境,如同大景观一样,难以察觉地相互融合。另一个是记忆中的景观,它可以使具体的一片土地看起来不那么陌生。在一个区域生长的动物的习性,可引发对另一区域中其亲属动物习性的猜测。但是,没有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完全一样。共性概括属抽象概念。我们的地形图上的种种线条不仅显示我们体察的空间的比例,也显示出我们对自然的差异性的认可。
一位苔原生物学家曾向我描述,她耐心地在约18英寸高、1英尺左右宽的苔原草丛中拆分一簇植物。她将活的植物组织和死的植物组织分开,并记下许多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她查看浆果的壳和里头的昆虫,甚至细究小得看不见或者一碰就会碎的细微东西。整个过程花了几个小时,期间,她的注意力凝固了,时间感消失了。她说,她记得曾一度抬头看,看到苔原上广袤的草丛一直延伸到地平线,那样的景象让她好大一会儿不能收回自己的目光。
在我正穿越的苔原上。生物看上去很丰富,但我知道,因为我感官不敏锐,缺乏分辨力,对此地又不大熟悉,所以许多东西都未被注意到。如果我通晓土著人的语言,就会有很大帮助。当地语言能够明辨当地的现象,而且可以揭去当地景观的面纱,彰显其真面目。
我知道自己漏掉了多少——因纽特忘记跟我一起行进的因纽特人的面孔。不会忘记他们的眼睛在走过的原野中不断闪亮。甚至在家里,男人们喜欢坐在窗边说话。他们总是瞭望远处的土地。或是抬头看天,来预测天气。走近浅海峡时,我看见一群雷鸟在吃东西,想知道它们在吃什么。忽然,我又想到一件事儿,并禁不住苦笑: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坏血病是北极沿海地区的荒凉引起的。
浅海峡里看不到野鸭的踪影。我用望远镜隐隐看到远处水面避风的岸边,鸭群排成黑压压的一行。我躲进苔原背风的凹褶处,理顺衣服,开始举起望远镜观察远处的海岸。十到十五分钟后,我发现了两只北美驯鹿。斯蒂芬森把望远镜首次拿给一个因纽特人看时,被问到他能否用望远镜“看到明天”。斯蒂芬森感到乐不可支,他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个问题。这个因纽特(爱斯基摩)人问的意思很可能是:这些玩意真的那么有威力。让你看到下一天才能到来的某种东西,比如迁徙中的驯鹿?或者说让你看到这片土地上你下一天才能到达的一处合适的宿营地?一些因纽特猎人有着天生的惊人视力;他们能够指出三四英里外的斜坡上吃草的驯鹿。仔细审视土地是好猎人的标志,但是,当因纽特人用望远镜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多数最有探究心的外来人,已经厌倦了用望远镜观察当地动物的活动踪迹,此后很久,一位因纽特猎人仍在用望远镜搜索这片土地上的各个边缘和缝隙。他用望远镜360度全方位地观察完看似寂静的一片苔原,可能会花上一个小时,每换一个角度只检视很小的一块区域。
你可以学着这么做;这样观察的话,你总会看到一只地松鼠,一只来回跑的狼獾,或是一只筑巢的鸟儿——它们会使你意识到你在哪儿,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当你养成习惯,找到类似的方式来克服焦躁情绪。你就会觉得自己在这片土地上不那么显而易见。
我沿着海滩走了好久,才走到苔原的干燥地带,然后轉向进入岛屿腹地。半路上,我发现一只雁的头骨,看似随机出现在这里,就如同小屋旁草地上死去的绒鸭。思维更为缜密的调查者,可以凭这些零碎信息,以某种方式找出这些鸟死在特定地方的原因,可我不是这样的调查者。在西南方向,我可以看到暴风雪的预兆——我想在下雪前赶到本岛靠海的一面,以防此后遇上更糟局面。沿海滩走是我预定的回住所的路线。我把纸一样薄的头骨放回地面。向东方望去,看到远处屹立着一根破旧的尖头浮木,那是1910年欧内斯特·莱芬韦尔在这一带海岸测绘地图时所竖的标识。该标识物稍微倾斜,其架势有点像任由风吹的歪斜废弃建筑。这是渴望控制广袤地域的见证。这是确定边界和界限的标识物,而这些边界和界限使旷野得到合适的划分和标记,以确定归属。
西方历史上宾格克岛发生过几件事。一位年轻英国海军军官约翰·富兰克林,曾在1826年率领一个陆路勘察队,从马更些河口登陆,一路向西,想在250英里外的巴罗角集结,但只走到接近宾格岛的地方——因为天气恶劣和队员身体劳损,他们“走到了无法再坚持的极限点”,在那年秋天返回了。1850年8月,罗伯特·麦克卢尔派一批考察队员上岸,向一小批因纽特人求援。因纽特人把“调查者”舰看成是“一个游动岛”,上岸人员中一位33岁的摩拉维亚传教士写道:“虽然从爱斯基摩人所在地划船到‘调查者舰需半个小时,但他们从远处望到舰体每动一下,都非常震惊,好像有电流穿身。”
19世纪后期,美国捕鲸者来到这座岛,从岛上的池塘提取淡水。1913年9月,斯蒂芬森在这附近放弃了不幸的“卡勒克”船。(这艘由双桅捕鲸船改装成的科学考察船被冻在冰里,后来向西漂了很远,结果被冰挤碎沉没,一半考察队员丧生。)像莱芬韦尔这样的商人和探险家,这些年也出现在这一地区。1952年,一位名叫威廉·欧文的考古学家最先发掘了岛上的史前遗址。几年后,远程预警系统在欧里特克角建了站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军建了两个棚屋和一个10x18英尺的小屋,让巴罗海军北极研究实验室的野外科考团队使用,之后还用于联邦外大陆架环境评估项目和其他项目。因纽特人沿海岸旅行时,偶尔也住在这些屋子里。我们住的小屋门口的苔原上所钉的髯海豹皮,就源自这些海岸。
岛上原住民的历史更久远,也更模糊。因为该岛的地理位置,它可能已经为猎人们服务了几个世纪。虽然这种服务很可能无法持续下去。如今,从苔原上露出的浮木杆和弓头鲸肋骨,可以推测出十几处400多年前的居所遗址的大概位置,这些遗址是该岛很久以前有土著人居住的仅存证据。这段北美海岸线显然从未有较多人口居住。然而,宾格克岛上的这些房屋遗迹,1981年被认定为阿拉斯加北部海岸最大的史前遗址。
机敏的考古学家会预测到这里有露营残留。宾格克岛得名于一个因纽特方言中的一个词,意思为“圆顶状冰上地面的隆起”。它具体指的是该岛向海一边的长长沙丘,这一沙丘可抵御风暴潮的侵害。这一屏障在海岸边很罕见,因此会被发现和利用。猎人在宾格克岛扎营,也可以早一些在科尔维尔河口附近捕到髯海豹和环斑海豹,因为这儿的淡水冰在海冰破裂前就开始碎裂。在辛普森浅海峡,他们会发现迁徙的雁和鸭。沿着海滩,还有大量的浮木(从马更些河冲下来),一些树干有30到40英尺长。岛上有大淡水池塘:该岛附近有大量嘉鱼和成群别卢哈鲸鱼,9月,弓头鲸由此向西到白令海峡。浅海峡朝内陆的一侧,猎人有望发现驯鹿。
宾格克岛上房屋遗址的发掘表明,1550年到1700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捕杀上述所有动物,而且还捕杀海象和北极熊。出土的物件中,比较能让人感兴趣的有:一个由北极熊牙制成的鱼饵,一张儿童用微型狩猎弓。一片驯鹿角铠甲。
站在这些屋子的遗迹旁,你会感到非常惊讶——在北极地面上,这么多人类历史竞不为人所究。相比之下,包括我们白人居住区的其他地区的历史,更容易被彰显。这儿有个捕鸟叉的叉齿,那儿有个海象牙吊坠:但这些物件蕴含着什么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