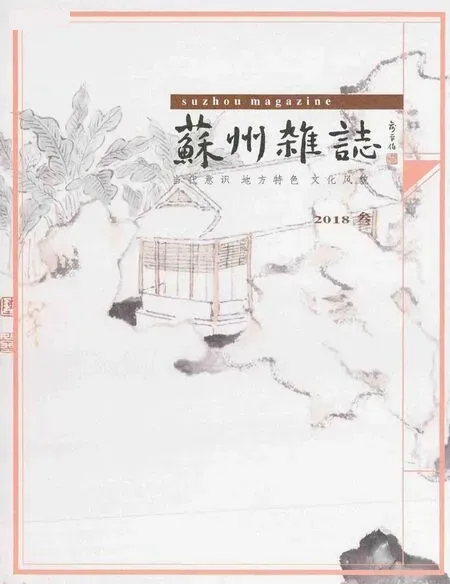黄异庵:三年三诗滨海情
顾艳龙

去年8月,《苏州杂志》主编陶文瑜在苏州大讲坛“漫谈苏州文化”时,谈到苏州典型文人黄异庵的故事。黄异庵(1913--1996年),出生太仓,原名黄易安,名沅,字冠群,又字怡庵,别号了翁、百词印斋。为著名评弹艺术家,诗书印俱绝,尤以评弹《西厢》享誉艺林,被红学家周汝昌引为知己,周恩来总理誉为“评弹才子”,识者称之“六艺大家”。黄异庵生平可用“一生三海”概括,即红在上海,难在青海,苦在滨海。红在上海是指其10岁即能鬻字沪上大世界等。劳改青海顾名思义不用说了。
对“苦在滨海”一节,因斯地是笔者故乡,便向陶主编饶舌追问,但语焉不详。近期因缘际会,得以拜访黄异庵哲嗣和女儿黄肖丹(下放时用名黄东来),获悉在1969年冬,黄异庵被以右派身份与黄肖丹一起下放,在盐城滨海县八滩公社岔河大队三小队度过三年多艰苦的岁月。
当时居委会通知黄异庵父女下放到农村去时,黄肖丹一筹莫展,因只会刺绣,21岁的她体重只有40公斤,黄异庵年近花甲,手不能拎,肩不能担,农家活基本都不会干,父女俩将何以为生?面对哭哭啼啼身体羸弱的女儿,黄异庵耐心劝导,在青海劳改我都过来了,到滨海我们还有自由,总会有办法。盐城几个县来接下放户的工作人员都嫌弃这对父女不是劳动力没有同意,最终滨海来人为完成数字才勉强接收。
离开苏州的那天,是黄肖丹二哥送行的。在船上父子谈了一会儿话,船上一片犹如生离死别的哭声,太惨了。此情此景何堪?二哥主动说每个月寄五元钱给你们吧,黄异庵欣然同意。其实二哥在苏州工作当时大概也只有二十几元工资。在农村的三年多里,这笔款成了黄异庵父女唯一的收入,也是救命钱。
到了分给下放户(知青点)住的土块垒成的房子,放下行李,父女俩定下惶惶之心,开始了与城市迥然不同的乡村生活。不久,大队召开过一次“见面会“,主要是让社员们认识本大队的”地富反坏右”,提高革命警惕性吧,黄异庵也被叫去参加,但并没有侮辱行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搞过批斗、学习班之类政治斗争。
在村里第一年,因来时发了几十元安家费,加上从家里带过来的粮食,还有队里照顾黄异庵拾麦穗等轻巧农活,每天记6个工分,虽然也拾不了多少,用秤称可能3个工分也不值。作为知青的黄东来,干农活也照顾每天记8个工分。这样勉强捱过一年,这年最高兴的事在春天,同样下放在苏南农场的哥哥、弟弟来农村,探望了父女俩。
第二年,照顾取消。黄东来麦子也割不动,父女俩挣不了多少工分。没有工分,意味着没有口粮,生存就成了最大问题。为了糊口,值点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思来想去,面对乡下缺医少药,农民头疼脑热大都硬挺着的境况,黄异庵捧起医书,拿起银针,学起了针灸。因他古文底子好,学习医书也不费力。牛刀小试,附近农民、知青中有肚痛、咳嗽等小毛病的经他针灸,大多手到病除。但毕竟没有行医资格,黄异庵定下规矩,对求治病人不包治愈,同时也不收病人治疗费。尽管如此,乡人重情,求治的病人没有人空着手来,鸡蛋、山芋、南瓜等是少不了的,为父女俩过穷日子保了底。
黄东来正是豆蔻年华,乡邻便劝黄异庵招个上门女婿,解决劳动力问题。农村也的确苦,没有劳力生存太难。生产队的山芋分在地里,无法运回家,不及时运,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了。让黄异庵在田里看着,也不是个事。他叹息,如果老天让我活下去,就没有人去拿。其时40多岁的邻居方阿姨,是个热心人,她花钱买香烟给人家,帮助将一大堆山芋运回来,几年都如此。黄东来还记得方的丈夫在公社工作。
黄异庵为女儿的将来操心,既然农活干不来,就学个手艺吧。正好,附近正好有患小儿麻痹症的人开着裁缝铺,会刺绣的黄东来打下手倒也不甚吃力。没有学费给师傅,担心不肯真教手艺的黄异庵便与师傅“谈判”,义务为残疾师傅针灸不收治疗费,师傅也不收学费。师傅满心欢喜地同意了。后因生产队要求黄东来一定要参加劳动,裁缝只是偷偷学了一个多月。为师傅治疗却一直在持续,直到其蜷缩的膝弯部能放下一个拳头。“黄神医”的名气不胫而走,有天早晨,黄东来打开门吓了一跳,门外居然排成一队有二十多个病人求治。
用二哥每月寄来的五元救命钱,黄东来学习农家人,买来小鸡喂养。人养鸡,鸡养人。小鸡成母鸡,隔几日便能聚拢十多只鸡蛋,每斤蛋0.69元。卖蛋时黄异庵最高兴,换来的钱除了可买灯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还能买几支香烟抽。整包不能买,女儿会吵架的。
生活虽苦,黄异庵文人的本色不变。他为附近的教师、退伍军人等刻印。书法也练,没有纸张,就让黄东来到生产队或大队部去求讨报纸。一张报纸写满拿到外面去晒,晒干取回再写,最后一张报纸变成二两重。诗词更是常吟,夏季半夜热得睡不着,便披衣到外面做诗。黄东来有个小本子记满父亲做的诗,可惜后来遗失了。但父亲在岔河度过三年,每年写了一首,共三首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七绝诗,她却记得很清楚。
其一
杨柳青青夹小溪,桃花层层落香泥。
此生恍若江南梦,临水人家鸭满堤。
其二
开到夭桃又一春,枝枝明艳见精神。
白头人立桃花下,妒煞春风笑煞人。
其三
亭亭玉立出檐高,三度观花客兴豪。
愿祝来年花看客,一帆风顺破江涛。
此三首诗作,被黄异庵的老友、常熟书画家秦绳祖写成书法条屏,赠送给黄东来。
1973年,黄东来在苏州绣品厂的好姐妹邀她回苏,该厂由于产品出口等原因,需代工厂加工产品。黄东来通过考核被委派到扬中等地代工厂做培训教师,月薪40多元。经过努力,黄东来将孤身在岔河的父亲接了出来。她告知二哥,不用每月再寄五元钱了。从此,结束了“苦在滨海”3年多的乡土生活。
黄肖丹回忆,虽然父亲也写过“谁令幽境绝人烟,新屋初成五月天。曲水流墙观不足,霉花开到枕头边”,“身居孤庐眼望天,除荤戒酒断香烟;一生三海均休笑,犹有姣儿傍无眠”等苦情诗,但对滨海的老乡们还是有感情的,他晚年病魔缠身,仍然希望回下放过的八滩岔河去看看,可惜没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