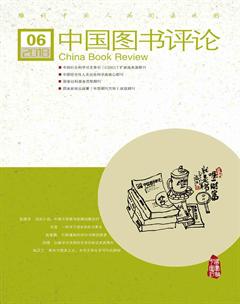艺术自律抑或艺术责任?
杨磊
杨建刚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一书,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经历了数年的精心打磨后终于面世。该书除导言、附录外共9章,大概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甄别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自的价值与追求,第二部分厘清双方从对抗到对话的逻辑,第三部分阐释二者关系如何孕育后来者,第四部分是第九章,也可以视为本书的结论,即解释一种“对话”思维的重要性。
20世纪美学、文学理论有四大支柱,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均列其中。其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这两种理论自身的魅力,更在于二者间谜一样错综复杂的关系。要从整体上把握二者关系的逻辑,以及后来者对前人的演绎或反叛,固然有不小的价值,更有极高的难度,却也是必须去做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两种理论自身的价值,还在于这两种理论以及它们的纠缠,既改变了20世纪的美学研究,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文学艺术,乃至理解世界的方式。尽管已经有先行者,但总的来看仍然是遍布荆棘。更严峻的是,因受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批评的影响,我国学术界甚至不能客观评价形式主义。杨建刚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在承认形式主义囿于自律而忽略艺术责任之時,仍然强调形式主义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贡献与地位。可以说,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这一立场出发,杨建刚认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美学”和“无产阶级美学”的对抗,双方的矛盾首先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然后才是学理上的。所谓政治原因,正是政治权力嗅出了形式主义不安分的味道。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无暇他顾之际,形式主义尚有一丝空间自由生长。一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得到确立,这最后一丝空间也就荡然无存了。看得出来,对形式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杨建刚是持同情态度的:并非形式主义没有纠偏的能力,而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然而正如杨建刚不无遗憾地指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因对形式主义的排斥而失去了自我调整的能力与机会。文学艺术不得不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苏联马克思主义也走上了庸俗化之路。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浮现了出来,艺术自律和艺术责任能否共存?书中没有专门的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以不同的形式贯穿了整本书,比如,艺术形式是否可以完全规避意识形态?对此,杨建刚坚定地认为艺术必然要反映意识形态,但艺术应该有自己的规律。巴赫金,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完成了对形式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因而,他的书中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自律论。一种是俄国形式主义式的自律论,另一种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前者具有本体论意义,但也因为摒弃历史和社会而饱受指责;后者却几乎相反。尽管它十分深刻地受到前者的影响,但它之所以坚持艺术是自律的,却不是要摆脱社会历史,而是要更好地参与社会的进程。先锋派艺术是最好的写照。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也日趋严重。先锋派正是在此时扮演了悬壶济世的良医。因而,杨建刚指出,艺术自律性使艺术和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这样的距离却使艺术和社会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同一:艺术能够有效地批判、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的异化。
我十分赞同他对艺术自律论的区分。从18世纪艺术自律论萌芽以来,不同的流派都打着艺术自律的大纛。具体的理论却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社会,甚至建构乃至取代人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实在。
然而,如果用这样的逻辑反观发生在苏联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或许会得到不同的启发。苏联官方之所以猛烈抨击形式主义,是仅仅把形式主义当成一种不合作的艺术话语,还是从中看到了危险的政治信息?我曾和杨建刚做过一些简单的讨论。我的观点略不同于他。我认为,形式主义同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当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之时,他已经在心里对着那面旗帜默默念叨,“彼可取而代之”。他把艺术自身当成了即将插到城堡上的旗帜。如果把城堡上空的旗帜视为外在的干涉,那就意味着形式主义者试图摈弃这样的干涉。这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就是回到作品自身。这一层含义被视为是形式主义者对康德美学误读式的继承,他们把康德美学理解为纯粹的形式美学是片面的,无视了康德哲学的体系性,也就人为忽略了康德伦理学的丰富内涵。然而,如果把摈弃外在干涉视为形式主义者对自由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又借助艺术作品得到表现,那就意味着形式主义者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康德伦理学对自由意志的肯定。从一开始,形式主义者就已经在有意识地建构社会实在。资产阶级美学和无产阶级美学的碰撞,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自由观的碰撞,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的碰撞。
因为政治理念的冲突,其中一方被另一方动用政治权力强行终止了学术创造。对于学术史以及人类思想、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无疑不是好的选择。柏拉图在《高尔吉亚》、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都指明,强力固然能开创秩序,但却是没有德行的。杨建刚认为,“对话”才是合理的选择。在他这里,“对话”具有多重含义。巴赫金创造性地融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被称为“对话”。此后的学术史中类似的工作还不少,法兰克福学派,罗兰·巴尔特,伯明翰学派,等等,杨建刚均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间对话的产物。杨建刚在该书第九章第三节中总结道:“20世纪西方文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对话与通融中向前推进的,对话思维对于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人类学术、思想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在几乎敌对的思想间的对话。
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对话显得更为重要。巴赫金之后,对话的伦理意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杨建刚认为,不同立场的学术思想可能会关注相同的问题,进而提出相似的见解,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和形式主义。这是一种潜对话。但更重要的是要促成一种直接的、有效的对话。真正的对话只能发生在平等、自由的主体之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也是一种脆弱的状态。君不见,在人类历史上,即便在启蒙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强力者对这种状态的不信任、鄙夷乃至破坏,仍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建刚的这本书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关系史的梳理与讨论,更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