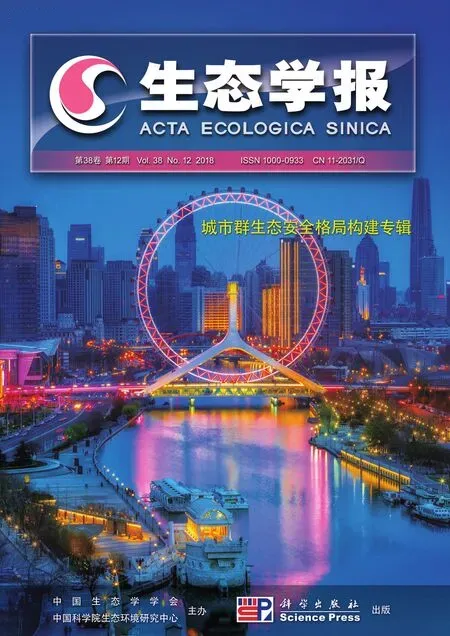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
胡炳旭,汪东川,2,王志恒,*,汪翡翠,刘金雅,孙志超,陈俊合
1 天津城建大学,地质与测绘学院,天津 300384 2 天津城建大学,天津市土木建筑结构防护与加固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84
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的载体,随着京津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用地流失、水生态失衡[1- 2],大型生态用地破碎化、岛屿化现象日益严重,重要生态用地如绿地、水域、湿地等出现不同程度的破碎[3- 5],导致生态用地的数量、质量和连通性等不断降低,打破京津冀原有的正常生态系统的调节机制,迫使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生态风险加剧,严重威胁生态安全[6- 7]。因而,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及降低生态风险迫在眉睫。
目前,构建生态网络主要有两种方法:(1)通过观测动物、植物种子扩散范围等路径,结合模型构建网络[8-12]。(2)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利用最小成本路径模型来构建生态网络[13-17]。第一种方法虽可对迁移路径进行更直观的模拟,但需要详细的观测数据,且耗时长。而最小成本路径模型考虑到生态源地间连接过程中耗费成本值,得到源地间最小成本廊道,从而更好地反映出源地在耗费景观成本环境下的最优路径。近年来,景观规划和生态网络构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俞孔坚[18]基于景观连接度原理对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进行构建和预测;孔繁花等[19]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方法,模拟了济南市的潜在生态廊道;张远景[20]采用CA-Markov 模型对哈尔滨主城区生态网络格局进行模拟优化。然而上述研究多围绕建城区及周边区县小尺度区域,研究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而基于大尺度区域范围对城市群生态网络研究则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21- 22]。
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京津冀生态红线区域、自然保护区范围区域,综合叠加提取出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核心生态源地,运用GIS技术,基于最小成本路径提取研究区潜在廊道,通过重力模型及重要生态源地连通廊道,综合筛选得到研究区重要生态廊道。并对研究区内景观成本,廊道组成,及其重要生态源地等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针对重要生态节点提出区域优化,旨在为增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重要源地的连通性,强化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策略,以及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图1 研究区行政区划图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he study area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11个地级市(图1)。土地面积21.8万km2,约占全国面积的2.3%。京津冀地区主体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明显,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全区地势呈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降低,西北部紧邻内蒙古,草原较多,生态环境良好;西部北部内含太行山、燕山山脉,林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东部地区紧邻渤海,南部为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土地利用类型多为耕地。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生态源地破碎化、岛屿化严重,京津冀地区环境生态问题十分严峻,部分河湖干枯断流、水土流失、河水富营养化、土地污染、地面沉降、草场退化、沙尘暴和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做好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是改善区域资源分配不均、提升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研究区域2015年 Landsat8 OLI 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将京津冀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湿地、耕地、人工表面及其他类型用地,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遥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获得矢量数据,并进行栅格转换,最终得到30 m×30 m土地利用栅格数据。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 (Geospatial Data cloud, http://www.gscloud.cn/) 下载全球GDEMDEM 3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通过裁剪获取京津冀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 数据,其栅格大小为30 m×30 m(图1)。筛选2015京津冀1∶100万基础规划数据中河流、国道、湿地、湖泊等矢量范围,对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规划》[23]数据及京津冀《主体功能区规划》[24-26]数据中生态红线区域,环保部《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27]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面积参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28]中物种保护区范围,国家林业局《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29]中重要湿地分布区域等数据进行矢量化,得到矢量数据。
2.2 生态源地提取方法
景观生态学中,生态源地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或生态服务功能,是景观重要组成部分[14]。生态源地面积的大小对区域物种多样性、物质信息传递、交流以及综合生态服务功能有着重要意义[30]。本文基于研究区实际情况,对《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中国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等规划指南中重要生态区域的矢量范围,与土地利用数据中面积大于10 km2的林地、草地、湿地生态区域矢量范围进行矢量叠加分析,提取重叠度较高、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好的区域作为生态源地。
2.3 基于最小成本路径模型的生态网络构建
构建生态网络可以解决生态源地破碎化问题,增强生态源地间的连接度[31]。最小成本路径方法是指物种从源到目的地运动过程中所耗费的累计成本值。该模型算法具有数据结构简洁、要素拓展性强、运算快速及应用广泛等特点。通过计算源地间的最小累计成本来确定源地间连接路径,能较好的反应出景观中物质、能量的运动方向趋势。生态源地通过不同景观类型耗费成本的大小不同,首先对研究区景观赋予不同的成本值,运用“综合加权指数和法”创建研究区综合成本栅格数据,通过最小成本路径模型计算[32- 34](式1),得到生态源地间的最小成本路径。采用最小成本路径生成生态廊道有以下两个原则,第一,生态源地间生成廊道不会穿过其他生态源地;第二,所有生成廊道没有交叉。最小成本路径可以较好的反映出生态源地间的物质交流,通过构建景观综合成本值面计算源地间最小成本路径。
(1)
式中,MCR为最小累计成本值,fmin为源地间最小累计成本值,Dij表示物种从源j到景观单元i的空间距离,Ri表示景观单元i的成本值。(Dij×Ri)的值可以被作为衡量特定物种从j到空间某点的路径的相对容易达到性。
2.4 重要生态廊道筛选及生态节点识别
生态源地间相互作用强度可以反映出潜在生态廊道对生态源地连接的重要性。基于重力模型[19](式2)定量地对生态源地间相互作用强度进行评价,进而判断研究区相对重要的生态廊道,保留大型生态源地间相互作用较强的生态廊道,结合京津冀城市群重要生态源地的空间分布,以生态红线区、重点保护区和城市群周边重要生态源地的有效连通为原则,筛选得到京津冀城市群重要生态廊道,并结合现有国道,河流进行叠加分析,对区域生态网络提出优化建议。
(2)
式中,Gij是源地i与源地j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Ni与Nj分别为源地i与源地j的权重系数;Dij为源地i与源地j之间潜在廊道的标准化成本值大小;Pi与Pj为源地i与j的整体成本值;Si与Si为源地i与j的面积;Lij为源地i与源地j之间潜在廊道的累积成本值;Lmax为研究区内所有廊道的最大成本值。
生态节点是源地最小成本路径和最大耗费路径的交点[35]。在景观空间链接中,相邻源地间进行物质交流存在关键生态节点,生态节点通常在过去受到认为干扰或即将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后生态恶化的区域。在大尺度的廊道研究中,生态薄弱并且生态作用关键的区域被当作生态节点[36]。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重要生态廊道上的小型生态源地及生态廊道与现有道路、河流交叉重叠较高区域作为生态节点。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源地提取结果
对京津冀规划纲要中生态红线区、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及大型生态用地及土地利用数据中林草湿地的矢量范围,进行区域矢量化叠加,提取得到研究区重要生态源地217块,并对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源地景观组成进行统计分析(图2,表1)。

表1 景观类型分类统计表

图2 生态源地分布图与土地利用现状图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ecological source and present map of land use
由表1、图2可知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源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约21.76%,林地占比最高,占生态源地总比例的82.78%,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山区地带,面积较大,综合生态服务功能较好,林地区域小型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保定西侧、秦皇岛、承德行政区域内;湿地占比约为11.05%,主要分布在东部渤海湾及白洋淀衡水湖等大型水域以及各区域重要水库,生态等级高,综合生态服务功能较好,需要重点进行保护;草地占生态用地6.17%,草原生态结构较为脆弱,区域生态破碎度较高,小型生态源地较多,尽量维持或适当增大生态源地面积,加大研究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避免生态源地破碎化加剧,提升区域综合生态服务功能。
由图2土地利用图可见,研究区南部平原区域林地较少,耕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用地类型以湿地为主,城镇化严重,城市面积明显高于其他区域,生态综合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较弱;山区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生态综合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较好;草原土地利用以林地、草地和耕地为主,生态综合生态服务功能良好;应适当更改平原区域土地利用类型,落实退耕还林等政策,并加强平原区域大型生态源地的建设和保护。
3.2 生态网络构建分析
景观成本值的确定是构建生态网络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对景观成本值没有统一的方法,源地间物质交流、传递通过不同景观类型所耗费的成本不同。本文参考徐文彬等[37]、刘杰等[38]、袁钟等[39]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景观和高程进行成本赋值,结合景观生态重要性对景观成本赋值,林地生态功能最强成本值设置为10,人工表明对生态影响最大,成本值设置为800,其他景观成本范围在10—800之间,结合高程变化对源地连通的影响对高程进行成本赋值,获得景观成本和高程成本值分配表(表2)。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栅格数据和高程栅格数据进行重分类赋值,通过“综合加权指数和法”,运用栅格计算器构建综合成本值面,得到研究区综合成本值(图3),并对各城市景观平均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图4),计算源地到研究区各点的累计成本值(图5)。通过公式1进行计算217块生态源地间的最小成本路径,得到生态源地间潜在生态廊道579条(图6)。
对区域景观成本值及最小成本路径获取的生态廊道进行统计分析。由图3可见,华北平原景观类型主要为耕地,同时城镇化严重,平原区域景观成本值明显高于草原、林地,特别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城区及周边范围成本值最高。由图4可见,天津、廊坊景观平均成本值较高,秦皇岛、承德景观平均成本值较低,其余城市平均成本值差异不大。结合图5可见,平原东南区域生态源地向研究区各点累计成本值最高,北京、天津、唐山地区累计成本值其次,林地草地累计成本值相对较小。平原区域生态源地面积较小,分布稀疏,表明源地在平原区域进行物质交流、传递消耗成本值较高,廊道连通性较低,生态稳定性差。由廊道分布及数量图(图6和图7)可见,北京和张家口廊道数量最多,廊道数量超过200条,衡水、石家庄、秦皇岛的廊道数量最少,分别为26条、42条和51条,其他城市廊道数量约100条。通过对廊道长度统计分析(图8),张家口,北京、承德廊道总长度较大,长度大于1500 km,秦皇岛、衡水廊道总长度较小,廊坊、石家庄、沧州、唐山、邢台、邯郸、天津、保定廊道总长度趋于1100 km左右。北京行政区面积相对较小,廊道数量仅次于张家口,区域廊道密度最大,北京城镇化高,应结合实际情况加强廊道优化。衡水区域内的生态源地严重缺失,廊道数量最少,仅为26条,廊道总长度也仅513 km,应加强区域生态源地保护和建设,提升区域综合生态服务功能。

表2 不同景观类型的成本值

图3 研究区综合成本值Fig.3 Comprehensive cost of the study area

图4 各地区平均成本值Fig.4 Average cost of each study area
3.3 区域生态网络框架分析及生态节点优化
对选取的生态源地进行编号,基于重力模型构建217个生态源地间的相互作用矩阵(表3),量化评价生态源地间相互作用强度。对于廊道重要性的判别,很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本文根据许峰等和尹海伟等[15,40]的研究成果,将相互作用强度值100作为重要廊道提取的阈值,同时结合京津冀城市群重要态源地的空间分布,以林地、水涵养区、草地、湿地和湖泊间大型生态源地可连通为原则,筛选具有重要连通性的廊道作为重要生态廊道,其他剩余廊道作为一般廊道。结合京津冀现有国道、河流与所选廊道进行叠加分析,选取京津冀城市群重要生态廊道上的小型生态源地及潜在廊道与现有廊道交叉处作为生态节点,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态网络分布图(图9)。

图5 源地到研究区各点累计成本值Fig.5 Cumulative cost from source to each spot in the study area

图6 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图Fig.6 Map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corridors in the study area

图7 各地区廊道数量Fig.7 Numbers of the corridors in each study area

图8 各地区廊道总长度Fig.8 Total length of the corridors in each study area
对廊道分类提取统计分析,由图10可见,承德、保定、张家口、保定重要生态廊道总长度较大,表明研究区内生态连通性较好。由图11可见,衡水、石家庄、承德的重要廊道数量与生态廊道数量相差不大,表明区域内廊道重要性较高。由图9可见,研究区生态廊道与现有廊道重叠度较高,但张家口草原区域现有国道和河流较少,同时区域内源地破碎化严重,潜在生态廊道较多,整体生态功能较为脆弱;承德、秦皇岛、唐山靠燕山山脉,区域内廊道重叠度最高,生态源地分布较为均匀,整体生态功能好于其他区域。平原区域北京、天津、唐山、廊坊区域城镇发展较快,现有国道、河流密集与生态廊道交叉明显。平原南部生态廊道与现有国道、河流走向重叠不高,廊道间相互交叉情况较多,同时南部区域白洋淀、衡水湖和天津滨海湿地间连通效果不够理想。保定、石家庄、邢台城区间连通仅存在一条国道,其余廊道均为横向连通,应重点加强国道周边生态源地建设及保护,提升廊道连通性。综合来看,研究区现有国道河流能够确保大部分的生态景观连通性,但在张家口草原内部及平原区域存在廊道不够完善情况,应针对实际情况加强现有廊道的保护及建设新的廊道,进而提升生态综合服务功能。

表3 基于重力模型的源地间相互作用强度矩阵
生态节点可加强廊道交汇处的生态功能[41]。由图9可见,草原区域生态破碎度较高,草原生态结构较为脆弱,由小型生态源地组成的生态廊道较多,要增强小型生态源地类型节点的保护,确保大型生态源地的连通性,进而提高生态网络功能。山区增加承德、唐山、秦皇岛行政区周边廊道交叉点为生态节点。北京、天津、廊坊内部城镇化迅速,应加强廊道交叉密集区的生态节点优化,研究区东南部生态源地较少,大型生态源地间连通廊道距离较长,廊道稳定性较差。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行政区内廊道上的小型生态源地和生态节点较少,应该加强廊道间的生态源地建设,对小型生态源地加大保护力度,并增加重要廊道的生态节点建设。此外,应提高生态源地建设保护意识和增强保护措施,确保区域生态网络稳定性,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功能。
4 结论

图9 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态网络分布图 Fig.9 Ecological network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本文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模型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网络,不但对研究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生态系统功能的提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还为其他区域城市群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新思路。研究成果如下:
(1)基于主体功能规划、湿地及自然保护区等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叠加分析,获得京津冀生态源地,生态源地总面积为47031.98 km2,源地类型以林地为主,湿地、草地占比例较小,面积分别占生态源地总比例的82.78%,11.05%和 6.17%,林地主要分布在山脉地区,草地主要分布在张家口西北侧,湿地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
(2)通过综合指数加权法构建景观成本值面,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模型提取廊道579条,并对研究区景观成本及廊道分布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平原区域景观成本值高于草原和林地,特别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城区及周边范围景观成本值最高;天津市、廊坊市景观平均成本值较高,为200左右,承德市景观平均成本值最低,为70左右。另外,北京和张家口区域内廊道数量最多,超过200条,同时区域内廊道总长度最大,达1500 km以上。北京、张家口区域网络结构复杂,表明其综合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较好。
(3)根据源地间相互作用强度,通过重力模型评价廊道的重要程度,同时确保大型、重要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筛选出重要生态廊道。张家口区域重要廊道数量最多,达70条以上。承德区域重要廊道总长度最长,表明区域综合生态服务功能较好。衡水重要廊道数量最少,廊道总长度也相对较小,大型生态源地数量不多,区域综合生态服务功能较差,廊道较为脆弱。生态节点上,研究区东南部的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区域内廊道上的小型生态源地和生态节点较少。

图10 各地区重要廊道数量 Fig.10 Numbers of the important corridors in each study area

图11 各地区重要廊道总长度 Fig.11 Total length of the important corridors in each study area
综合京津冀地区现有源地、廊道的空间分布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源地分布上,平原区域生态源地面积小、分布不均。研究区东南部重要大型生态源地较少,源地间廊道长度较大,应加强长距离廊道上生态源地的建设保护,提升区域景观连通性,特别是在京津冀快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应在北京东南部廊坊及天津西部适当建立大型生态源地;其次,雄安新区的扩建将对白洋淀湿地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加大,需重点加强白洋淀区域生态保护建设;再次,衡水湖是平原中心最大的生态源地,对周围生态综合服务功能最高,要重点加强白洋淀与衡水湖间生态廊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