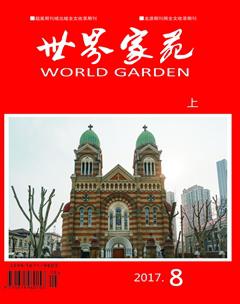记老舍对狄更斯写作风格的批判继承
胡雲鹤
摘 要:英国大家狄更斯与中国二十世纪文人老舍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此文着眼于阅读两位文豪的《我这一辈子》和《艰难时世》两部作品,在人道主义精神、讽刺幽默的手法、“笑与泪”的流变以及悲剧性的差异上感受其中批判继承的关系的奥妙。
关键词:狄更斯;老舍;《我这一辈子》;《艰难时世》
同作为文人,狄更斯同老舍都将目光投射于底层人物,用幽默讽刺的语言表达内心对于政治现实的重视与抨击,作为笔尖上的“斗士”向社会死水投下重弹。著名文学批评家约翰·罗斯金曾评价:“狄更斯在自己所有著作中的主旨和意图都是完全正确的,所有关注社会问题的人都应该对他的每一本书,尤其是《艰难时世》加以仔细的研读。”而《我这一辈子》是一纸站在巡警的角度向旧社会发起的控诉书。老舍在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下,继承发展总结出自己的写作风格。
一、人道主义的变异发展
不难发现两位文人都在揭露现实黑暗中流泻出人道主义情怀。相比于狄更斯将人道主义作为和缓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冲突的工具,老舍则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对旧社会的完全否定中去。
狄更斯秉持着他的“人类之爱”的核心观点,端起强调人类的公共属性的大枪,主张“改良主义”。他明显表达出用道德感化的力量以达到对社会黑暗颠覆的目的的幻想,通过用“圣人”的爱,关怀感化“恶人”。在《艰难时世》中,西丝便是“圣人”的化身。在父亲离去后,她被迫住入资产阶级的家庭——庞德贝家中,好比光明坠落黑暗。在教条化的逆境中,西丝受尽天性的折磨与被泯灭。但她坚守本心,甚至在格雷戈林家中以和谐关系的纽带存在,以圣人的姿态照亮黑暗。她帮助他人找回人性的温暖。正如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曾说过:“狄更斯的小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与爱。”“圣人”形象的存在感化“悔过者”,从而达到人性的还原。狄更斯用他的“感化精神”树立起主观化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以及改良主义,将讽刺溶解为同情。
老舍继承了狄更斯对底层人物重点关注以及集中体现的风格,肯定了人作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与权力,肯定了底层人物对于幸福拥有的权力。但是,老舍偏向直面剖析社会现实,将矛头直指旧社会中官僚机构的腐败,警察制度的黑暗内幕,人们的麻木,“人吃人”与人麻木于“人吃人”现状的悲怆,撑托悲怆的是底层民众人格破裂和精神碾压的惨烈。在他逞强的笔尖下,我们在痛楚中摸索着老舍对贫困受苦人发自本真的人道主义关怀。
归根结底,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流露出了浓烈的资产阶级的味道,狄更斯虽然同情受剥削的下层民众,但更反对“以暴制暴”的暴力与流血。纯粹地重视生命在社会尖锐矛盾中不堪一击,“感化”只能流向“无痛呻吟”。不同于狄更斯的博爱,老舍咬着牙,流着市民阶层的血和泪走进文学。切实地生活状况给他打了一剂强痛针,虽然老舍也表现出了对革命的迟疑,但其在狄更斯反对的基础上已经跨出了一大步,他继承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与对底层人物的关怀,在这基础上树立起直面黑暗时代的旗帜,更有力抨击社会,肯定出人的价值与尊严,批判人的国民性。
二、从讽刺走向“笑与泪”
狄更斯的讽刺技巧实在是值得称赞的。在《艰难时世》中,反讽便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格雷戈林拥护功利主义,他是一位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以滑稽的“不折不扣”跳出舞台,在近乎“失真”的诙谐幽默的背后是对格雷戈林的教条化和死板的突出讽刺。作为一名教师,他泯灭了孩子们的天性,抑制甚至消除孩子们的人欲和天性。甚至之于他的孩子,也生活在他的荼毒之下——压制孩子们的想象力、消除好奇心、阻止娱乐。人性的打压到了低谷必然引起反抗,无论是正面还是相反向,格雷戈林只能获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狄更斯对善的信仰体现在了格雷戈林的善化与悔过中,这种转折也是功利主义的反抗。然而,狄更斯依旧秉持着“违背人性的哲学必然失败”的口号吹起所谓“胜利”的号角。
老舍的讽刺风格并没有止步于讽刺幽默的写作风格,而是融入“笑与泪”的艺术发展,在讽刺的基础上贯通幽默,用苦笑表达悲痛。老舍的“笑”被拉扯浸染着现实生活的气息,他所表达的笑不再是仅有的娱乐意味,而是走向深层的严肃、无奈与悲痛,在笑中思考、流泪。韵味深远,倒是可以说吸收了“堂吉诃德式”的“笑语中带有悲壮”的特性了。正如林语堂所言:“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老舍用其诙谐但实则沉重的笔调,向不公平的社会控诉,用血和泪向麻木的人们呼喊。文本夹杂着脏话俗语才能表现的气愤,其中的亲切以及幽默感是令人感受深刻的。但愈是幽默,愈是用胸腔中的怒火叠加的愤恨。站在文本的鏡子面前,相比于人性的善,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被压迫的无力感,我们几乎除了文本最后的“希望”看不到任何出路。幽默在沉重中尤其凸显悲剧的味道。
三、人物悲剧性的差异
不同于“圆形”(“但并不是扎扎实实的,与其说是固体,倒不如说他们是泡沫。”)的格雷戈林,“扁形”的庞德贝应着诺曼·道格拉斯的“小说家的说法——看不到普通人们思想的复杂性”贯穿了资本家的虚伪面庞,可以为了金钱与权力失了人性中最本真的亲情的人,除了欲望还看得见什么呢?作品被拉近真实,也同时拉近了悲剧。但狄老笔下的人物往往是直面苦难的。就好比西丝迎来了好结局,格雷戈林幡然醒悟,露易丝重燃人性温暖等等。
老舍的论调则更倾向于描写底层人物的默默无闻与逆来顺受。“我”是具有知识性的,“我”认识到了社会问题的残忍沉重与制度对个体、人的平等的消磨,但是沉重的现实强行扭转着觉醒者的头颅。世人带着西洋镜看着“我”超前的行为与落后的社会环境形成的冲突,在麻木中将“我”看作敌人与可笑之辈。同时,贫穷使“我”无奈,也是贫穷使“我”认清世道,利欲向来与悲剧效果结伴而行。并且,人物的悲剧性在于,认识到受迫害的人无法选择改变,并依旧忍受迫害。绝望在循环中走向枉然。老舍在喜剧的大门前叩响了时代的悲音。
无论是在人道主义精神、讽刺幽默的手法与“笑与泪”的流变上,还是在作品悲剧性上,我们抚摸着狄更斯与老舍的时代伤痕,感受指尖摩挲的沉重。“如果人们认认真真的久久注视一件有趣的事,那故事就会越来越发愁。”作家用灵巧的手快速地编制着喜剧的外衣,幽默在理性与感性的交织的棒针尖跳动着,它牵引着我们缩小距离,剥开时间与历史沉淀的外壳,在迎面扑来的沉重气息中自我分解,泪流满面。站在一扇名为时间的门外,正如“我”死时所期盼的“希望”。“善行是不会像轻烟那样飞散的,它比最光辉的美还更要万古长存,主的信徒说:‘一切都将过去,只有爱永存。”那饱经沧桑留下的,是亘古不变的经典。
参考文献
[1] [英]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陈才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2] 老舍:《老舍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
[3] 朱维之:《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5] 唐建清:《欧美文学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7] 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8] 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