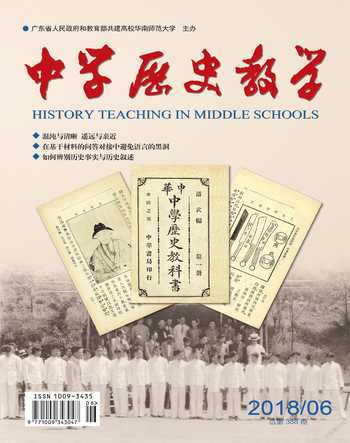陪审制度起源考
冒兵 许天
陪审制度是一种由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或非职业审判员为陪审官或陪审员参加审判刑事、民事案件的审判制度。[1]这种机制使得社会公众能够监督司法权的行使,确保司法公正。
高中历史教材《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介绍了雅典城邦的“陪审法庭”,《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又认为“古罗马的陪审制度对近代西方国家有重要影响。”由此引发的问题有些扑朔迷离:古罗马的陪审制度是不是与古希腊有明显不同?近代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是不是更类似于古罗马而非古希腊?然而,探寻陪审制度的源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延展已经远超认识的存续。但是,人们只有通过搜集、整理、辨析和研究现存史料,去伪存真、舍芜取精,才可能形成正确、客观的历史认知。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史料实证核心素养正是历史研究与学习的基础。
一、氏族社会的人民大会——陪审制度的渊源
在原始社会时期高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存在着一个酋长会议、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来代表部族或人民的“三权并立政府”。[2]三权政府是氏族社会民主制的最高形式,通常以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和王政时代的意大利部落为代表。
在人民大会召开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凡是想说话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大会听取了讨论以后,即作出决议。[3]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4]
《荷马史诗》中有这样的记载:“人群集聚在市场,观望两位男子吵架……两人于是求助于仲裁,听凭他的判罚。公众意见不一,双方都有人说话帮忙……中间放着两塔兰同黄金,准备支付给评议最公的判家。”[5]在这里可以大致看到当时氏族社会人民大会的审判程序:氏族酋长主持审判;人们在集会上自由发表意见;当事人双方在人民大会上控辩;精通法律的智者们提出多种判决意见;参加人民大会的自由民采纳其中最好的一个由此结案。[6]
在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原始民主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尽管那时的民主与阶级社会的民主截然不同,只是一种非政治、非法律意义的民主。但这种人民大会审判法庭的集体裁决方法,蕴含着陪审制度的思想文化渊源。
二、雅典城邦的陪审法庭——陪审机构的产生
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早期,氏族贵族掌控政权,社会矛盾尖锐。
(一)“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
公元前594年,执政官梭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创公民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关于“公民陪审法庭”的解释纷繁芜杂,但史学家们现在基本认同顾准的看法:“Heliaea”意为集会,陪审法庭的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7]也就是说,全体公民集体履行司法职能时即为陪审法庭,而非公民大会。因此,理论上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作为陪审员参加陪审法庭并参与审理案件,但实际上陪审员主要由年收入二百麦斗以下的第四等级公民担任。
梭伦改革时的陪审法庭,不仅是国事罪、渎职罪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级,而且也是其他法院判决案件的上诉审级。[8]这时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最高法院,其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民陪审法庭对案件的受理采用集会开庭的方式,经过原告和被告的辩论,审判结果由陪审员投票表决,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内投放石子。这大概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陪审制度。[9]
由于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梭伦改革中的陪审法庭没有与公民大会彻底脱离而成为独立的司法机关,这反映出早期国家政权职能划分不明晰。但是,陪审法庭的设立扩大了公民大会的权限,是政治民主化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言:“规定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确实是引入了民主精神。”[10]
(二)独立的司法机构
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作为平民领袖进行改革,在司法方面扩大陪审法庭的权力,陪审员改为抽签决定。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新设立的陪审法庭(dikasteria)共有10个,每个法庭由年初分配的500名陪审员组成,专司审理同一类型的案件。[11]随后,伯利克里改革又扩大了陪审员数量。这时的陪审法庭已经脱离公民大会成为了独立的司法机构。
此时,雅典城邦的任何公民都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不法申诉”,即使是五百人议事会或者公民大会的决议,如有违反现行宪法或不合立法程序者,普通公民亦可申诉,陪审法庭有审理之权。[12]
从公元前399年由501人陪审法庭制造的“苏格拉底冤案”可以看到当时陪审法庭的审判程序: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举证,陪审团进行第一轮投票,表决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多数,即获得清白之名。但案件并未就此完结,还要看原告获得票数的多寡:如果他获得的票数不到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即被判为恶意诬告而遭受到处罚;如若出现有罪和无罪的票数相等的情况,则被告无罪释放)。如果裁定有罪,陪审团在量刑上要再投一次票,但不能决定刑罚,而应在起诉方和辩护方所建议的刑罚之间作一选择。[13]
雅典城邦后期,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伯利克里改革给予陪审员工作津贴,使其不至于因生活贫困而无法享受民主权利。“穷人也能有暇从政,公民全都享有政治权利,群众在数量上就占了优势。……‘平民群众遂掌握了这种政体的最高治权。”[14]
雅典民主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令人赞叹,特别是陪审法庭由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组成,成为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典范和民主巅峰的标志。但是,陪审法庭毕竟发生在人類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特别是富于政治热情和正义感的陪审员们完全不懂法律,却拥有独立决定被告命运的权力,这就可能导致“多数人专制”,苏格拉底一案也成为法制史上形式正义抑制实质正义的的典型悲剧。在一个没有主审官,也没有上诉,在法律和事实两个方面都由人数众多的普通人组成陪审团来作出判断的纯民主审判中,这是必然的结果。[15]
三、罗马共和国的刑事法庭——陪审成为司法诉讼普通程序
公元前509年,王政时代终结,罗马确立了共和政体,这与雅典城邦民主政体基本是同时期的。
(一)民众会议诉讼
与雅典城邦一样,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民众会议(人民大会)也具有司法审判权,历史上称为民众会议诉讼。当然,古罗马民众会议的形式更为复杂。
古罗马的民众会议诉讼可能并不是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执法官审判并判决,然后被告人向民众会议申诉。至少,在现存史料中从未找到相关实证。根据格罗索的研究,民众会议诉讼的具体程序是:执法官在民众会议上提起诉讼,勒令被告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民众会议出庭;在民众们参加的三次非正式执行会议上,执法官提出控告并提交证据;被告人发表演说进行辩护。执法官如果不打算中止诉讼,就在第四次会议中正式提出控告,要求判处某人极刑或罚金刑,开始真正的民众会议审判;民众会议或者按照执法官的建议科处刑罚,或者宣布无罪开释。[16]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法律精神在司法过程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是并没有超越希腊法治的水平,民众会议诉讼也是一样。这些非专业性的法庭掌握着法律和事实的裁判权,既缺乏专业性的法律指导,也没有上诉程序的约束。裁判庭的决定糅合着法律和事实、正义和仁慈、逻辑和大众情绪,但却是终审。[17]
(二)索贿罪刑事诉讼
民众会议虽然对死刑等刑罚具有最高管辖权,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先认定犯罪后实行制裁的刑事案件,这是由一种新的普通刑事诉讼模式——索贿罪刑事诉讼来解决的。
公元前149年,罗马元老院通过《坎布尔尼法案》创设刑事法庭,成立独立陪审团负责调查和审判行省官员的贪污勒索案,这就出现了索贿罪刑事诉讼程序。公元前123年的《索贿罪法》对陪审员名单以及陪审团组成进行了调整:授权一位裁判官专门负责对索贿罪的审判,并成立一个陪审团。为此,裁判官准备一份450名骑士的名单,诉讼控告人从这份名单中挑选出100人并通知被控告人,后者再从这100人中选出50人组成陪审团。[18]陪审团在庭审时进行辩论并调取证据;陪审员表决时用“A”(absolvo)表示开释,用“C”(condemno)表示判罚;诉讼结束时,裁判官(不参加表决)收集陪审团成员的表决意见,按多数票决定。[19]针对陪审团的决定不能提起民众会议诉讼。
司法程序离不开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在许多情况下,前者要远比后者艰难,因为事实认定是重现已经消逝的真实。在索贿罪刑事诉讼中,陪审员只证实是否存在犯罪事实,以便决定是判罚还是开释,而不用操心具体的制裁。因此,“陪审员的任务是定罪,刑罚则由法律确定。”[20]由此,陪审制度开始进入刑事诉讼普通程序,具备查证事实并确定被控告者是否有罪的职能。
在综合性的东方思维看来,陪审制度作为一种司法制度起源于古希腊或古罗马,这种看法既尊重历史传统,又符合文明的传承。在古罗马的刑事诉讼中,裁判官负责审查诉讼形式的合法性,执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而陪审员则主持案件事实的审查和裁决。近代英美法体系实行陪审团认定事实、法官适用法律的司法分工,以及司法过程体现出“先审事实、后作判断”的“无罪推定”原则,无不与古罗马的刑事诉讼程序及其法治精神相类似。但近代陪审团承继雅典城邦陪审制度的,除了法庭辩护技术之外,恐怕只剩下那句熟悉的开场白“陪审团先生们”。
陪审制度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法治道路上的里程碑,软化了法官在是非判断上的僵硬性,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审度案件事实,有利于防止司法擅断、增强司法公信力。其实,正是欧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保障了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的传承、发展与完善。通过史料实证探寻陪审制度的起源,确是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从中提取有效信息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努力重现历史,并据此提高、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这才是核心素养观照下历史教学和学习的应有之义。
【注释】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6-117页。
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
荷马著,陈中梅译:《伊利亚特》,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18-519页。
J·威格摩尔著,何勤华等译:《世界法系概览》(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何勤华:《外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3年第3期。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3页。
阿里斯托芬:《马蜂》,《罗念生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第51页。
I·斯东著,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16页。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195页。
J·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第255页。
G·格羅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3-194页。
J·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第329页。
G·格罗索:《罗马法史》,第269页。
G·格罗索:《罗马法史》,第271页。
G·格罗索:《罗马法史》,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