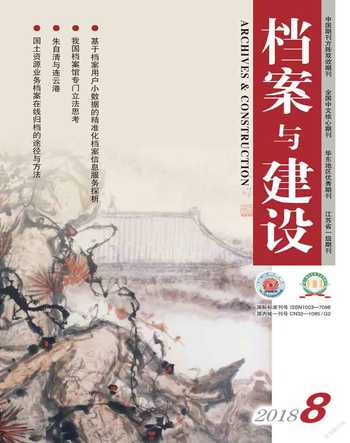近代民族工业的巨子荣宗敬、荣德生
钱江
荣宗敬,名宗锦,1873年生于江苏无锡西乡荣巷;荣德生,名宗铨,号乐农,生于1875年。两兄弟在20世纪前期,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以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为主体,包括一些相关企业的“三新”荣氏企业集团,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实业家。
(一)
荣宗敬7岁入私塾,师从殷省甫,陆续学习了《论语》《孟子》《幼学》《尚书》《礼记》《古文》等。自小聪明伶俐,活泼可爱。
荣德生开智较晚,8岁那年,其父荣熙泰开始教识字。1883年,9岁的荣德生进私塾读书,先后学了《千家诗》《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等。随着年龄增长,荣德生进步很快,以至塾师外出办事,就委托他代教学生。他对手工活尤感兴趣,书桌里收集了不少刀钻工具以备随时使用。
1886年,经父亲朋友的介绍,荣宗敬结束了读书生涯,赴上海南市铁锚厂学徒。不久,得伤寒病,母亲赶到上海,雇船把他接回家,延医调治,后病虽愈,头发却全脱落。第二年,15岁的荣宗敬再次赴沪,在卫姓所开永安街源豫钱庄做学徒,三年后满师,即转入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任收解。该号专理无锡、江阴、宜兴等地汇兑。在汇划号任职期间,荣宗敬不仅了解并熟悉了金融业务,同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资金的周转,棉麦的产销流向等情况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1889年秋,15岁的荣德生第一次离开家乡赴上海永安街通顺钱庄学徒。在四年的学徒生涯中,他通晓了珠算、记账、结账等金融业务。日后,荣德生回忆这段时间,深情地说:“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1893年,荣德生满师后,即随其父去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办理进出口税务。这一经历使他进一步熟悉税收、贸易、进出口等经济方面的知识,为他后来投身实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森泰蓉汇划号因做小麦蚀本盘歇,荣宗敬因而失业回到了无锡。1896年正月,荣宗敬随父亲去上海寻觅工作,遇见以前的熟人,他们都说与其为人打工,不如自设钱庄。荣宗敬父亲动了心,就从自己毕生的积蓄中拿出1500元,另向社会招股1500元,合成3000元,在上海鸿升码头开设“广生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任正帐。这是他们兄弟立业的基础。为开拓业务,不久,广生钱庄在无锡开设分庄,由荣德生任经理。
广生钱庄开设之初,虽无亏蚀,但业务平平,盈余不多。由于荣氏兄弟业务精通,办事踏实、恪守信誉,经营渐有起色,业务拓展到江阴、宜兴、常熟、溧阳等地,仅1898至1899年两年间就获利白银近万两。但胸怀大志的荣氏兄弟对蝇头小利并不在意。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也是西化最典型的城市之一,西人开办的近代企业到处林立,而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民族企业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荣氏兄弟耳闻目睹上海滩的这一切,寻思钱庄虽能获利,但利润微薄,不及投资实业,利润更大。他们萌发了创办实业的想法。
1899年秋,经父亲的好友朱仲甫的一再延请,荣德生再次赴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任总账。广州是近代中国瞭望世界的第一个窗口,西方近代文明首先在这里与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冲突。这样一个环境,对荣德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时,荣德生一有闲暇就往书店跑,那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个人致富的书刊如《事业杂志》《美国十大富豪传》等让他爱不释手。他买回后反复研读,以至通篇都能背诵。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时战火连天,风声鹤唳。家里不放心荣德生孤身一人漂泊在外,去信催他回家。荣德生由此踏上了返乡之路,不料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实业救国的新路。
返乡途中,在香港码头候船时,荣德生看到许多中国劳工正从远途而来的外国大型商船上把进口面粉驳上岸;船到上海,又见市面萧条,各业凋零,唯独内地小麦大批涌进上海,申城不多的几家面粉厂均获利丰厚。由此他想到自己在广东税局收税时,清政府对当时进口的204种商品中的面粉是予以免税的,原因是面粉为“洋人食品”。其实那时进口面粉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在华洋人的需要量,绝大部分在国内市场上售与国人。因此,荣德生萌发了自己创办一家面粉厂的想法。在沪见到了兄长荣宗敬,荣德生提起这个新收获、新思想。不料英雄所见略同,荣宗敬完全赞同。因此兄弟俩决定试着办一家面粉厂。
但是,荣氏兄弟不懂技术、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办厂谈何容易。为此,荣氏兄弟虚心求教,各方奔走,先后考察了我国当时仅有的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和美商经营的增裕等面粉厂,虽然各厂实行技术封锁,但他们对粉厂的大略还是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他们又去瑞生洋行探问美、英、法等国面粉机械的性能、价格及订购手续;在资金上,得到了官僚朱仲甫的支持。这样,荣氏兄弟的办厂工作就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他俩各出3000元,朱仲甫出资1.5万元,其余对外招股,凑足3.9万元,购买了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太保墩上的17亩地,建造厂房。同时向清政府办理立案,向洋行订购设备。
在建厂过程中,无锡地方乡绅以私圈公地,烟囱正对学宫,有碍风水等名义加以阻挠致讼。荣宗敬与荣德生由县到府,由府到省,往返奔走,寻门路,疏关系,历经十个月,终于排除了阻碍,取得了胜利。
1902年阴历二月初八,保兴面粉厂正式开机生产。它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面粉企业之一,采用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和60匹马力引擎,雇工30多人,一昼夜用麦2万斤,出粉300包。规模不大,设备也很简陋,但这是荣氏兄弟创办的第一家近代企业,是荣氏企业集团的发韧。该企业开办之初,营利不多。1903年,做惯大差使的官僚朱仲甫抽走了股金。而荣氏兄弟信心十足,把自己的股份增至2.4万元,成为控股的大股东,加上其他股东的增资,保兴厂股金增至5万元。为表示一个新的开端,荣氏兄弟将“保兴”改名为“茂新”,即茂新第一面粉厂。
1904年,日俄交战,俄国商人在哈尔滨开设的20多家面粉厂纷纷停业减产,但日俄双方对面粉的需求大大增加。荣氏兄弟抓住这一机会,通过设在烟台的批发处,扩大对东北的销售。为提高产量,他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怡和洋行定购18英寸钢磨6台,从而使茂新日产量提高到800包。1905年,茂新厂获利达6.6万两。受着丰厚利润的鼓舞,1905年荣宗敬与荣德生又联合了張石君、荣瑞馨、叶慎斋等7人集资27万余元,在茂新旁兴建振新纱厂。该厂1907年春投产,是为荣氏兄弟经营纺织的开端。
正当荣氏兄弟由钱庄而至面粉、纺织,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经济形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1904到1907年间,全国新增了36家面粉厂,而1906年国内小麦因天灾产量锐减,这一增一减使小麦价格猛涨。同时,洋粉进口量逐年增加,而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面粉销量骤减,这一增一减又使面粉价格猛跌。在这背景下,自1906年起茂新面粉厂连续3年发生亏损,总额达2万余元。1908年因装载天津各商号订货的海轮触礁沉没,荣氏兄弟又损失5万多元。同年,荣宗敬因裕大祥商号投机失败,宣告倒闭,受到牵连,损失白银60多万两。而振新纱厂因经营大权掌握在他人手里,自开工后也连年亏损……这一系列的困难使广生钱庄搁浅。荣氏兄弟手中除了借据外已无资金,债主上门索款无望,诉使道台来茂新厂贴封条,广生钱庄多年树立起来的信誉也荡然无存,汇兑已微,放款无力,经营陷于绝境。在此危难之际,荣氏兄弟商量弃钱庄而保实业,痛心地盘歇了父亲为他们开创的广生钱庄,并用田产作抵押借钱周转,终于使茂新起死回生,度过了难关。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荣氏兄弟的心胸也豁然开朗。1912年秋,荣德生作为无锡商会的代表,赴北京参加民国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会上,荣德生提出了发展纺织工业、设立机器制造厂、由政府出资遣派留学生等三项议案。出席这次会议的各省代表有100多人,提出议案80余项,通过27项,而荣德生提出的3项均获通过。这充分反映了荣氏兄弟顺应时势,希望发展实业、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
(二)
1912年,荣氏兄弟开始把自己创业的舞台由家乡无锡转向中国近代最大的城市上海,以展宏图。这一年,他们在上海新闸桥开设了福新第一面粉厂,由此开创了与茂新并列的福新面粉公司。
福新面粉公司,作为日后形成的荣氏企业集团——“三新”公司的一部分,是由荣宗敬、荣德生、王禹卿、王尧臣和浦文汀、浦文渭6人共同创办的。在荣氏兄弟创办茂新面粉厂时,王氏及浦氏兄弟均是无锡粮食业的好手。为开拓茂新业务,荣氏兄弟请王氏及浦氏兄弟前来相助,其中浦文汀负责茂新小麦的采购,担任办麦主任,王禹卿负责茂新面粉的销售。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茂新度过了难关,得到了发展。王氏及浦氏兄弟在展示自己营销才华的同时,经济上也得到了较大的回报。但这毕竟是寄人篱下,为人做嫁衣,因此他们私下计议,决计另创面粉厂,图谋独立经营,以期获得更大发展。可是王氏、浦氏兄弟资金有限,东拼西凑只筹到2万元。当时,王禹卿的族人王祝云(上海鸿章纱厂账房)介绍老板郑培之在上海的一块地基作厂址,但厂房建筑费就需4万元,此外还要买机器和保障流动资金,因而资本太小,开不了厂。后来这事被荣氏兄弟知道了。为了免于业务骨干人才的流失,他们当即表示愿意合伙投资,两人出资2万元,合股4万元。为解决资金不够的困难,荣氏兄弟就把厂房建筑交给了郑培之,使福新省去了一笔基建费,交换条件是福新负担年利一分的较高租金,即年租金4000元。另外,荣氏兄弟出面向茂生洋行订购机器,取得了分期付款的通融。这样便把厂开了起来,为福新第一厂,由荣宗敬担任总经理,王尧臣为经理,浦文渭为副经理,浦文汀负责办麦,荣德生因业务以无锡为主,故为公正董事。该厂开业后,由于有茂新的基础,仅几个月便赚了4万余元。在这一过程中,荣氏兄弟与王氏和浦氏兄弟的关系由过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提升到了合作合伙关系。假如说茂新公司是荣宗敬、荣德生的兄弟公司,那么以之为起点的福新公司则开始了三姓六兄弟合作的独特局面。同时,荣氏兄弟作为一代大企业家在用人、融资、经营等方面的胆略与才干得到了初步的显露。
1913年夏,荣氏兄弟集股3万元,以每年租金规银2万两的代价,租用了上海中兴面粉厂,更名为中兴恒记公司,租期为两年。在租用他人厂赚钱的同时,1913年冬,荣氏兄弟在中兴厂之东购地近17亩,建造六层厂房,向恒丰洋行定购美国胡而夫厂面粉机器全副,计800筒,即为福新二厂。该厂1914年秋正式开机,每日夜出粉约5500包。该厂股本10万元,全由福新一厂盈余中提出。因为在创办福新一厂之初,荣氏兄弟就订下一条规矩:各股东三年不得提取红利,股息也一律存厂,用于清偿建厂欠款、企业生产周转和增资建新厂。事实上,这条规矩在荣家各企业中均延用了下来。因此接下来,在1914年夏,荣氏兄弟用福新一厂、二厂的盈余,创办了福新三厂,直至1919年和1921年创办当时被称为“大型企业”的福新七厂和八厂,雪球越滚越大。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交战国国内粮食生产骤减,不但无力输出,而且还要向国外采购,以弥补其不足;同时,处在战线外的广大国际市场由于参战国的暂时退出,也需另觅货源。这极大地刺激了我国面粉工业的发展,荣氏兄弟的办厂热情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茂新一厂规模不断扩大,至1913年,该厂已拥有美机钢磨24座,日产面粉5500包。一次大战期间,该厂营业蒸蒸日上,获利甚丰,故于1918年再添美机钢磨12座,日产量达8000包左右,资本也增至60万元。1916年,荣氏兄弟租办无锡惠元面粉厂,改名茂新二厂,两年后租期届满,荣氏兄弟以经营两年的利润16万元买了下来,平赚了一家厂。1919年再建茂新三厂。1921年,茂新系统唯一不在无锡,建在济南的茂新四厂投产,所产面粉提供给火车餐室,中外乘客均乐意享用,以此而行销北京、天津。
荣宗敬与荣德生通过集资开办、收购兼并、借贷扩建、租赁合作等方式,使企业不断裂变、增生。从1912年至1921年,所经营的面粉厂达到12家,其中茂新4家,3家在无锡,1家在济南,福新8家,7家在上海,1家在武汉。12个面粉厂拥有粉磨301部,日产面粉能力7.6万包,十年间扩张了24倍,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生产能力的31.4%,因而荣氏兄弟获得了“面粉大王”的桂冠。
(三)
在经营面粉业的同时,荣氏兄弟还在纺织业大有所为。他们投资创办的第一家纺织厂是无锡振新纱厂。办厂之初,该厂经营大权不在荣氏兄弟手中,经营毫无起色。由于荣氏兄弟表现出卓越的经营才能,在1909年振新纱厂改组时,荣宗敬被聘为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他们上任后,对振新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良,新添设备,提高规模效益,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13年荣氏兄弟集资租办中兴面粉厂时,振新大股东、族人荣瑞馨欲入股未着,颇为不快,因而引发了荣氏兄弟与他的矛盾。后来,他们在关于企业战略发展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致使荣氏兄弟无法经营。1915年,荣氏兄弟将自己在振新的股份与荣瑞馨在茂新的股份互換,退出了振新纱厂。同年,荣氏兄弟在上海筹创申新纺织厂,从而使以经营面粉、纺织为主的荣氏三新企业集团初具规模。
1915年,荣氏兄弟在上海集资30万元,创办申新一厂。为了吸取振新纱厂由于股东不和、小股东不敌大股东,影响生产经营的教训,在该厂股份中,荣宗敬与荣德生兄弟占了六成,为创办该厂作了很大贡献的张叔和占了二成,其余二成为多人分掌,从而形成了荣氏兄弟控股的局面。为进一步避免日后股东间的相互掣肘,他们决定申新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不设董事会,由荣宗敬自任总经理,由他一手掌握各处办事员的选任和解位,实行集权制,凡企业的经营大权、资金调度、原料采办、产品销售以及人员雇用或调动,均由荣宗敬一人全权处理。这一制度后来推行至整个荣氏企业的茂新、福新、申新三系统之中,成为荣氏企业在短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申新一厂投产后,取得了可观的利润。1916年盈余11万多元,1917年盈余40万,1919年盈余100万,1920年盈余110萬。这既为荣氏兄弟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保证,也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扩大发展的欲望。1917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得到消息:祝兰舫等人合资的恒昌源纱厂有售让的意愿。虽然该厂机器设备较为陈旧,但他们认为该厂所处地段好,加上当时是生产的黄金时机,买来就可投产获利,比新造一厂合算,因而集资40万元买下该厂,为申新二厂。至1932年申新纺纱厂办了九家,其中无锡、武汉各一家,其余均在上海,形成了庞大的申新系统,成为荣氏企业中,继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外的又一公司。它拥有纱锭52万枚,布机5357万台,分别占到全国民族资本企业纱锭和布机总数的11.3%和13.5%,因而荣氏兄弟摘取了“棉纱大王”的桂冠。
1921年,荣氏兄弟在上海江西路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简称“三新总公司”,由荣宗敬任总经理,下设庶务、文牍、会计、麦粉、花纱、五金、电气、运输八个部,当时有固定资产1959万元,自有资本1043万元,在册职工1.3万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四)
荣氏兄弟在20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几乎白手起家,通过举债办厂添机、租办收购,不断兼并扩充,使企业资产出现了裂变式的发展。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们在继续扩张企业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企业内部管理的革新上,最典型的是在无锡的申新三厂。该厂创办于1919年,股本150万元,荣氏兄弟出资108.5万元。1922年正式开工,拥有纱锭5万枚,布机500台,电机两座计3200千瓦,年产棉纱3万余件,棉布30万匹,由荣德生出任经理。
该厂在创办之初,承袭了中国早期棉纺织企业的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企业在经理之下,分设文场总管和武场头脑。文场总管以下设领班,分管人事、考工、账册、购销、运输等业务;武场总头脑下设工头,掌管全厂生产技术和原料、产品的质量检验,并包揽机工的招雇、升除。这些人不懂技术,文化低、素质差,管理混乱,思想守旧,并且多以亲属、同乡、师徒关系结成帮派,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荣氏兄弟在研究了欧美及日本纺织厂的管理经验后,决定在申新三厂实行改革。他们把留学生汪孚札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人才延聘至厂,为了减少阻力,把申三5万纱锭中效率较高的3万英式新机交给工头管理,而把2万美制旧式纱锭交给新招进的技术人员。结果,旧机在新职员的有效管理下,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大大超过了工头管理的新机。两种管理方法的鲜明对比,更坚定了荣氏兄弟进行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他们取消文场、武场的管理体制,统一全厂的行政、生产和技术管理,以工程师、技术员管理替代原来的“工头制”管理模式,进而实行类似“泰罗制”的生产定员制、劳动定额制、论货工资制、论工赏罚制和标准工作法,重点是整顿、改善车间一级的生产管理。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工头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以闹事、殴打技术员工等方法进行抵制,在1925年4月策动了轰动一时的“申三殴人风潮”。但荣氏兄弟不为所动,坚持改革方向,只是在具体操作中通过教育、调离、劝退等温和、渐进的方式排除阻力,最终逐步达到改革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1933年他们又在申三进行了旨在提高工人福利,调和劳资矛盾的“劳工自治区”活动。他们把企业作为社会事业的一个实验区。在“自治区”内,建有职工单身宿舍和家属宿舍,按区、村、室三级进行管理,设有食堂、消费合作社、储蓄所、医院等,为职工提供生活便利;开办工人补习夜(晨)校、职工子弟学校和图书馆、电影院等,兼顾职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和文化娱乐;组织职工养兔、种菜等,通过副业生产以补贴膳食。除此之外,“自治区”内还有工人自治法庭、公墓、功德祠、尊贤堂等,俨然是一个组织健全的小社会。通过这些中西文化合璧、富有特色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化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改善了工人生活条件,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短短三年中,申新三厂纱锭的平均日出纱率增长了33.3%,每件纱的成本降低了34.6%,每万纱锭雇工由原来450人减至270人。荣氏兄弟在申三采取的这些举措名噪一时,各地各界人士包括新闻记者纷纷前往参观、学习。荣氏企业集团各厂也纷纷效仿,进行改制,普遍取得了成效。
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作为事业来做的,自称“事业迷”。荣德生曾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他们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如饮食、衣着、居住等都很节俭,甚至于显得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他们办企业是作为一项慈善事业来做的。他们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大小烟囱论”,意思是说:给钱给物救济人,不如办厂招人来做工。施舍的钱物是有限的,用完了还是穷;招进厂里,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可以养家糊口,只要企业的大烟囱冒烟,那人家里的小烟囱也定会有生气。有这样的思想指导,他们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对地方上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及城市建设也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
在创业之初,他们有感于企业职工文盲多,文化水平低,不利于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有碍企业的发展,提出“实教相辅”,即实业和教育是相互促进的观点。他们从1906年起,在家乡附近农村先后开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各4所。1919年春,他们又亲自筹划,在荣巷创办了一所别具一格的公益工商中学。该校分工、商两科,校内设有供学生实习的工场、商店和银行。学生在该校既要学习理论知识,又要进行实际操作,完全是学以致用。毕业后,这些学生相当部分进了荣氏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6年,荣氏兄弟出资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该馆占地2亩,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可藏书20万卷。荣德生花了很多精力,从各处购置、收集到各类经史子集书籍,充实其间。该馆全天对外开放,吸引了学生和地方人士前往阅读。1920年,他们还捐款1万元,资助上海南洋大学兴建图书馆,并购赠一批图书。
1912年,荣氏兄弟在家乡无锡荣巷西侧购地150亩,开始兴筑梅园。这是一处由私人出资兴筑,对外免费开放,供游客休闲、赏景的近代公园。在近20年的修建过程中,广植各种梅树3000多棵,并以各种花木、奇石点缀其间,还先后建筑了如香雪海、研泉、楠木厅、荷轩、揖蠡亭、豁然洞、念劬塔等景点,从而使该园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赏梅胜地。每年冬去春来之时吸引了无数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豪商巨富、平民百姓前往观赏。
在建筑园林的同时,他们还致力于铺路修桥。梅园兴建后,因距無锡城区有7公里,游人前往十分不便。1914年,他们会同乡绅共同出资修筑了路基宽6米、路面宽2.5米的石片路,起名开原路,沟通城区和梅园。1918年,又集资创办开原公共汽车公司,让汽车往来其间,大大方便了游客前往游览。
1929年,他们与地方人士一起创办千桥会(后改称百桥公司),专门从事桥梁建筑,其费用由荣氏兄弟独承或与地方人士分担。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先后在无锡、武进、宜兴、丹阳等地建筑了大小桥梁88座,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横跨五里湖,长达375米的宝界桥。
该桥建于1934年。这年荣德生60寿庆,至亲好友聚会为他祝寿。席间,宾客们提出为他60大寿共同捐资建一桥,以志纪念。荣德生说:诸君要造桥,正如敬酒,我作为主人理应先敬大家一杯,故先造一桥以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也多造桥,贡献于地方建设。荣德生选中了五里湖边的宝界山下,经过八个月的建造,1934年9月该桥竣工通车。它有60个桥洞,钢筋水泥结构,当时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尚在建设中,故它号称江南第一长桥。荣德生对该桥情有独钟,1940年代末,他陪时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钱穆散步于桥头时曾说:我这一辈子,唯有这横跨五里湖上的宝界桥可以留作一个纪念。我所回报故乡养育之恩的礼物,唯有此桥,时光流逝,日后无锡乡亲也会因为这座桥而记得我荣德生。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荣氏企业遇到了空前的困难。由于历年来企业的扩展依赖于负债,至1934年3月,申新纺织公司总资产为6899万元,负债则为6376万元,资负大体相当。3月间中国、上海两银行放风不再给予申新贷款,数十家小行庄闻风一起扑向申新逼债,使申新公司陷于崩溃的危地。荣氏兄弟无奈之下向国民政府乞求帮助,要求统税记帐,并由政府保息发行500万元债券。国民政府表面同情,却拿出了提供300万元营运资金,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申新公司的方案,实质是要侵吞整个申新公司。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商人串通英国汇丰银行,趁申新七厂借款无力归还之机,宣布要将申七作为借款担保金予以低价拍卖,因而引发了著名的“拍卖申七事件”。在这过程中,荣氏兄弟相互配合,奔走呼号,请求各方支持,最后终于抵制了政府和日商企图侵吞的图谋,度过了一大关。
(五)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战火烧到上海及江南地区,荣氏企业当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经协商后,荣德生西走避居武汉,荣宗敬则暂留上海租界,料理企业。不料,这成为他们兄弟的诀别。
荣宗敬在沪期间,指挥开设在租界内的申二、申九、福二、福七、福八等厂坚持生产,同时令处在战区内的申一、申八等厂,召回逃散的职工,开机复工。在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又断然拒绝了日方提出的“合作”引诱。1937年底,一心想保住企业的荣宗敬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参加了“上海市民协会”,事实上它是日军策划的以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为主体组成的亲日组织。不少爱国人士及抗日团体写信或当面劝告荣宗敬尽快脱离。这样,1938年1月4日,荣宗敬悄然离沪赴港,不料,至港后,由于心火郁积,疲惫不堪,竟致病倒,于2月10日与世长辞。荣德生闻讯,痛心万分。
失去了勇于开拓的兄长的依托,加之战火连绵、企业无法生产的现实,从此荣德生变得沉默寡言,深居简出,每天不是浏览先秦诸子格言或宋人语录,就是浏览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消闲书刊,或沉湎于收购一些在战火中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古董、字画典籍。实际上,一直到抗战胜利的八年间,荣德生在反思前瞻。当敌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企图强行收买荣氏企业,或示意可以“合作”经营时,荣德生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他斩钉截铁地正告他们“宁为玉碎,不欲瓦全”,表现了决不同日伪妥协、合作的高尚民族气节。
这一阶段,荣德生在为国家、为自己企业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兴,勾画着蓝图,提出了“天元计划”和“大农业计划”。
所谓“天元计划”就是荣德生准备在战后创立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的“天元实业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金、木、水、火、土、食品、纺织七大门类,涉及采矿、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不下数十种。食品、纺织两大门类要发展深加工,食品工业由面粉而至点心、饼干,纺织工业则包括了棉、麻、毛、丝、人造纤维的纺、织、染整以及裁制、缝纫。
所谓“大农业计划”,实际上是荣德生心目中勾画的“理想国”,是他改革社会政治经济的思想的集中表现。他设想:以户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每户授田50亩。每十户为一村,十村为一乡,十乡为一镇,十镇为一区。区是基本的行政组织,设有区长管理行政,建有街市互易有无,设有交通、电讯、学校、图书馆、医院、文化娱乐场所和工厂企业,还有农业机械供全区农民轮流租用耕种。荣德生认为:农村应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如植树,育蚕,养鸡、鸭、兔、猪,西北地区还可饲养马、牛、羊,各择所好,分头进行。小城镇可开设一些季节性工厂,吸收农民农闲时进厂做工,农忙时回乡种地,使他们“一年四季不为闲游”,从而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荣德生提出:在区以上设县、专区和省;各省要对人民的衣食住行作出周密的安排,建立起由小学、初中、高中而至大专、大学的教育体系,培养适用人才。荣德生认为这个计划可在甘肃、青海等人少地多的西部区域首先推行,使那里粮食获得丰收,这样不仅可养活贫民,而且可以原料支援人口稠密的沿海城市。沿海城市可大力发展工业,制造衣食住行所需各种机械,支援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东西之间,建筑公路、铁路以相互沟通,对沿路矿藏要集资合力开发。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工商全面发展,林牧副各业兴旺,文教科技发达,交通邮电便利,人民生活富足的新国家。这些设想虽然不够缜密,有的也不一定可行,但充分反映了荣德生这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当荣德生从收音机里获得这一消息后,年逾古稀的他竟如年轻人一样,搀扶着同龄的老伴上街观灯,融进了载歌载舞的人海。荣德生带着欢庆胜利的喜悦心情、投身到了旧事业的恢复和新事业的创建工作之中。
(六)
1945年末,荣德生回到无锡,立即收回了申三、茂二的发电间,使两厂获得动力,马上投产。随后又着手整理、修复上海的申二、申五,使两厂在1946年底开出了全部纱锭。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已彻底毁坏,但它是荣氏兄弟创业的起点和基石,荣德生对它充满了感情,他令四子荣毅仁主持重建。对申新三厂,荣德生于1947年扩大规模,新建第二工场,订购美国先进纱机,至1948年开工时,加上原有设备,该厂拥有纱锭10万,纺纱能力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成为当时江苏最大的纺织厂。
正当荣德生的战后复兴工作稍有头绪,1946年4月25日,震惊全国的“荣德生绑架案”发生了。那天上午8时多,荣德生在上海高安路寓所前遭到持枪匪徒的绑架,后在四面无窗、又无灯烛照明的黑屋里呆了30多天。起先绑匪勒索100万美金,经讨价还价,绑匪在获得50万美金后于5月28日夜放回了荣德生。后来国民政府军警破了案,但为了答谢军警,荣德生又用去了10万美金,这使荣德生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均遭到了重大打击。事实上所谓绑架是少数警匪勾结的结果。
绑架案大大影响了荣德生对“天元计划”的实施,后来仅在无锡创办了天元麻毛棉纺织厂。该厂从1945年8月起筹建,至1948年6月才全面开工,拥有1万多枚棉纺锭、2440枚麻纺绽、70台麻织机等设备,所产“双熊牌”麻胶布、平布、西装衬布和本色绒线畅销无锡、上海,远销香港、东南亚,其中用国产苎麻试纺的皮鞋缝制线和棉纺工场生产的嫘萦纱,在国内尚属首创。1947年4月,荣德生还在无锡创办了开源机器厂,制造纺织、面粉工业所需的“工作母机”。
1947年,荣德生又在无锡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该校设农、理、工三个学院,分设中文、外语、史地、经济、机电、化工、数理、农艺、农产品制造等九个系和面粉专修一个科,系科专业的设置完全立足于为荣氏企业服务的宗旨。为了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荣德生不惜重金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如文史专家钱穆、唐君毅,农学家金善宝,物理学家周同庆等到校任教。在他们的指导下,江南大学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1948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走到穷途末路,饱受国民党反动政策之苦的荣德生也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但这时他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因而对自己企业和事业的命运深深地担忧。这时,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关系,把毛泽东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重要文章、材料送到了他手里,让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没收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总目标,从而使他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1948年11月,荣德生赴上海,看到总公司不少人准备外逃港台以至美国、巴西。他坦然地说:我决不离开家乡,希望大家也不要迁居海外。当中共地下党派人捎信给荣德生,说申三厂里正在拆卸二万多纱锭准备运往台湾,他连夜赶回无锡,坚决予以制止。他激动地说:余平生未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从而阻止了抽资外逃。
1949年春,荣德生又派私人代表赴苏北向中共华东地区领导人管文蔚、陳丕显等表达解放后能保障社会安宁、企业正常生产的希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无锡地方当局在溃逃之际,胁迫荣德生与他们一起南迁,可他坚决地答道:“我什么地方也不去,生在无锡,死在无锡,除非你们再来绑架”。4月23日,解放军进驻无锡。第二天,荣德生特地坐黄包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向家乡父老和实业界同仁表明了信守的诺言,起到了很好地稳定地方的作用。
建国后,党和人民为荣德生作了妥善安排,他先后被推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委员和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1951年10月,荣德生原定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因病未能成行。1952年春,他抱病上书毛泽东,向领袖致敬,并陈述解放以后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表示要为国家建设多出力。1952年7月29日清晨,荣德生怀着对新时代的无限眷恋,病逝于无锡寓所,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