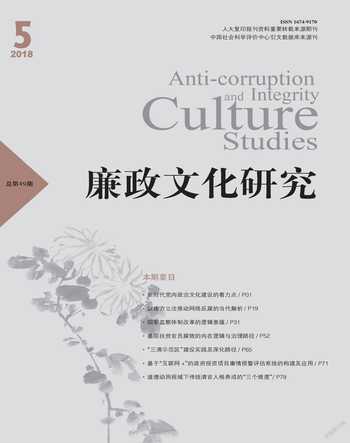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李辉山
摘 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逻辑意蕴;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5-0031-07
审时度势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把分散的反腐败工作力量整合起来,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的改革思维、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实践方法、从战略部署到法治保障法理基础、从党内监督到国家监察内容覆盖,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对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丰富和发展。
一、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
权力具有扩张性,公共权力异化必然会导致腐败。建立科学高效的权力监督体系,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方式。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能够逾越不同系统场域的壁垒,优化和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充分发挥权力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实现对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
(一)权力必须受到监督的基本法则要求强化对权力的制约
权力是一种集中起来的以强制力为后盾产生影响的控制力。权力行使者对权力客体的支配与调控具有强制性,被支配一方必须绝对服从,这就决定了权力行使者具有特殊身份,有可能出现凌驾于他人之上滥用权力的现象。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要防止权力行使者滥用权力,必须对用权者进行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法则。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就是源于对权力缺少约束,杜绝权力滥用现象,就必须对权力进行约束和规范,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制衡。“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2]。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公共权力展开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人格化的个体或集体,这就意味着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具有公共性身份和私人性身份。集双重身份的公共权力行使者在运用权力时可能会存在冲突,即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可能会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健全国家监察体系,通过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问责、依法监督,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3]。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党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整合行政监察权和检查侦查权等监督资源形成国家监督权,克服了监察体制上的缺陷。国家监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等,构成了全面监督体系,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保证国家机关秉公用权,确保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监督对象受制约、监督范围难以全覆盖、监督能力很难高效率等一系列难题,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
(二)党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监督要求廉政监督全覆盖
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具有很强的诱惑性,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监督和制约权力是一项历史性课题,也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核心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且这种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是全方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6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管”和“治”都包含监督。在当代中国,执政国家公共权力、掌握国家机器运行的工作人员中,党员占有比例較高。“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5]。党对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进行党内监督,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必须通过国家监察体系这个载体来实现全覆盖。
我国从1954年开始采用“双元双规”的治理结构模式,我国的反腐败监督体系主要由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组成,实现对权力全方位监督。党的纪检组织作为党内执纪的专门机关,是党内监督权的执掌机构,以党纪强制力为后盾,“坚持纪在法前,充分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种形态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又坚决处理‘少数,切实肩负起‘党纪严于国法的职能责任”[3]。国家监察机关以国法的强制力为后盾,是反腐败执行法律的专门机关,通过依法检查国家公职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问题、违反法律法规的惩处,实现对国家公职人员廉政监督的全覆盖。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监察体制是反腐败工作转向治本的关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健全国家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是制度反腐的深入推进,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
(三)权力属于人民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对权力的监督
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6]这意味着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国家机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受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监督表现为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直接监督主要是保障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知情权、参与权,人民群众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依法定程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政勤政进行监督。但在监督实践中,由于各监督部门职能有局限,对人民群众的举报等监督方式需要各部门传递办理,这就使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很难及时得到反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集中统一行使监督权,整合各种执法执纪资源,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
间接监督主要是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计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立法监督、工作监督、行政管理监督、司法监督和审查监督等,但是这些监督难以体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意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宏观调整国家权力的法治实践,是建立监督公权力的良性机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通过组建监察权,使监察权与行政权、检察权并列。这些权力设置坚持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授权并进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从而实现人民最大限度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保证人们授权的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为人民谋利。
二、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逻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导向是其改革的动力源。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后,现行监察体制、监督体制与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不相适应,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回应时代需要破解难题的突破口。
(一)适应新时代反腐败制度设计的现实需要
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行稳致远的重要原因,国家监察体制是反腐败必不可少的制度化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拓展了制度反腐的内涵,提出了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其中“不能腐”是属于治本的监督制约制度,有效开展反腐败,健全完善的国家监察体制是重要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反腐工作由治标转向治本阶段,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败工作的全过程,关键在于解决现行监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也包括行政监察、司法检察等国家法律制度,两种制度的分工合作是我国制度反腐的优势和特色。但是,这种合作在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影响反腐败成效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和制度创新”[7]。我国反腐败机构各自为战的反腐职能往往使反腐败陷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8]的困境,制约了整体反腐效能的发挥,无法及时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结合大部制改革思维,在制度设计层面与我国政治改革方向相契合,通过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改变现行反腐机构的隶属关系,强化人大监督权,使我国的监察体制由同体监督变为异体监督。从组织机构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职权、监察对象、组织结构、监察手段等方面,通过制度安排整合了不同的反腐职能,形成了一个综合履行监察职权的机构,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适应了新时代将反腐败向纵深推进的需要,化解了当前监察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和功能性改革的压力,是超越体制困境的现实策略。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9],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话语中,党的纪检部门、行政监察机关、检察侦查机关、预防腐败机关、审计部门等负有反腐职责,多个机构各自承担体系的监督反腐职责,体制上缺乏有效的连接纽带,容易造成各部门各自为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整合了与反腐败有关的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等相关机构职能,把行政监察拔高为国家监察,成立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提升了政治站位,增强了监督合力与实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4] 6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从战略部署到法治保障、从党内监督到国家监察,都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新时代,构建科学、严密、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必然要求实现监督全覆盖,体现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的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的国家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相应地,监察委员会行使的监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并列,改变了监察权的隶属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能够形成“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纪检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结合,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党纪监督与法律监督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监督格局”[10],使监督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地整合,充分发挥反腐败监督体系的整合功能。
(三)破解新时代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难题的关键举措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整体性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改革,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结构、权力关系和权力配置。从权力调整层面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旨在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到重构国家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格局的变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设置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是专门行使监察权、履行监督执纪职责的独立监督组织,这一改革形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新形态,体现出组织结构的完善、功能的有效发挥和资源的合理运用。
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权力的重组与完善,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破解改革难题的突破口和关键举措。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从北京、山西、浙江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组建,体现了我国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保持了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国家监察委员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科学严密设计监察制度,建立全面的监督监察体系,在整体上、制度上提升反腐成效,可以实现制度效益最大化,完善国家权力制约体制。
三、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以史为鉴,方可知得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2]当前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建立在以往改革探索的历史基础上,借鉴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有效推进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基础功”。
(一)坚持党的领导,有序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重视党内纪律监督,建立了监督体制保障纪律的执行。党内监督机构的历史演变体现出我们党对建立监督体制认识的深化,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监察体制仅限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纪律监督,主要是以党内监督的方式存在。党内先后出现的“监察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蕴含并透视着党内监督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确保政权的稳定,更加重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监察,从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到“国务院监察部”的组建;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名称修改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从党的监督检查工作撤销到重新恢复;从国家监察部设立到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从重点监督主要领导干部到党内监督的全覆盖;从党内监督制度的构建到国家监察体制的设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中,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国家行政监察部门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有序地推进了监察体制的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合时代背景和目标任务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党的统一领导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加强的时候,监察体制就能够得到顺利运行;反之,党的统一领导受到削弱的时候,监察体制改革就会面临挫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到人们对公共权力监督和反腐败工作规律的认识,包括人们思想共识、国家机构整合和相关利益协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党的统一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人们认识到反腐败的重要性,通过机构整合将分散的监督力量重新配置,积极引导相关利益者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支持并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二)坚持问题导向,科学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提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3]发现、解决时代问题是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改革的动力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监察体制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原动力是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适应性反应。建国以来,我国监察体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置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到1954年设置监察部,再到1959年监察部被撤销。改革开放以后,1986年恢复设立监察部,行政监察体制重新确立。1992年10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这种管理体制沿用至今。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原有的监察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需要。
制度治党是反腐败工作的治本之策,通过制度设计约束和监督权力是有效开展反腐败的制度保障。现行的监察体制面临着职能分散、力量分散、查办困难、追责不够等现实困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困境的现实策略。从机构上看,党的纪检机关,行政部门的监察机关、审计机关、预防腐败机关,检察部门的反贪机关、反渎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等机关,都是反腐败机构,共同构成了我国监察体制。但由于各个机关的特点不同、职权不同,在现实的反腐败实践中,由于受到不同部门领导,各级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往往陷入多头管理、互相牵制的困境,难以完成本身的监督职责和任务。例如,现行国家权力监督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权威性,但在现实监督、人大监督中还存在着监督弱化、监督不力、监督效果不明显、监督范围有限等问题。现行监察机关具有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等职责,但在实践工作中,由于行政监察范围宽泛、运行不透明等,对申诉和举报等职责履行较好,但对法律执行、政策落实、政令畅通等事项监督不力,出现了职责不清、监督缺位或越位问题。因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聚焦现实突出问题,借鉴国际社会通行做法,以大部制改革思维整合不同的反腐职能,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集中统一行使监察职权,改变“有权无能、有权无效”的现状,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全覆盖,使之真正成为一个权威有效的反腐败机构。
(三)坚持系统思维,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系统思维,简单地讲,就是要有大局观和协调意识。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改革举措具有耦合性,既互相配合又互相促进,坚持系统思维推进改革就是要促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同步推进党内监督制度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我国原有的国家监察体系是根据反腐败的职能设立的,纪委与监察机关、国家预防腐败机关、反贪污贿赂机关、检察机关等一起构成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职能重合、缺乏协调机制、合作松散未能形成合力、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国家监察力量分散、监督监察未能实现全覆盖等问题。因此,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现有监察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整合监察力量,健全组织结构,实现对党和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全覆盖,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互配合,构建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真正走上中国特色的监察道路。
四、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逻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体制改革,发展了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整合监督资源,完善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体制
充分利用现有政治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政治绩效,是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目标。对权力实施有效监督,是保障权力正确运用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构建有效的国家监察体制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根本保障。分属在政党、行政和司法中的纪委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是我国监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监督机构的共同点是都行使监督职能,不同点是监督对象、监督权限和程序方法等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需要彼此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各种监督资源,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全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制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彻底构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设廉洁政治。
(二)完善监察立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法有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4]66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既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又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是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监察法》对监察机关职责范围、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的权限和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新修订宪法和《监察法》规定设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对国家机构的重要调整,对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设置监察机关,是对公权力监督的重大改革。《监察法》的颁布,明确了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纳入监察对象的扩大,确保了监督的全覆盖,对违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视情节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惩处方式。通过制定《监察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实现立法与改革衔接,以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完善监督制度,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使改革于法有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法治防腐的具体体现,《宪法修正案》《监察法》的颁布实施,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实现无缝对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主导腐败治理。国家治理的前提是腐败治理,腐败治理既是执政党的自我革新,又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是有效保障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14]。这就决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相关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重构,是对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权力结构的调整。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本质,制度建设是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重要工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权威高效、集中统一的监察体系,实现法法衔接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健全执纪执法配套制度,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在制度安排上实现“无缝对接”,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两个体系共同发力,对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确保监督全覆盖。
总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契合了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新形势,利用法治原理解决改革的难题,采用法治手段规制监督监察权力,能够确保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优势互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法)孟德斯鸿. 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4.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6-10-28.
[3] 吴建雄,刘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价值、逻辑与路径[J].求索,2017(1):27-36.
[4]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1-12.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B/OL].(2018-03-22)[2018-05-14].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3/22/content_20524
89.htm.
[7] 若蔚,姜洁. 问题导向 立行立改[N].人民日报,2014-07-11.
[8] 庄德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行动逻辑与实践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4):79-87.
[9] 林尚立.中国反腐败体系的构建及其框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3.
[10] 吴建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构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1):48-58.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2.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
[13] 中共中央編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14]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6.
责任编校 陈 瑶
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LI Huishan1,2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Beijing,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is a vital decision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entering around president Xi Jinping, a key innovation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embodies four logical elements: Its theoretical logic arising out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consumm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of power; Its practical logic coming from the response of the real problem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 Its historical logic dating back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ith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ts value logic ly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the efficiency in management by means of consumm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nnovation and consummatio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which realizes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between legal mentality and legal means in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that is authoritative and effective, covering all aspects having been constructed, a path for supervi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ong-term stability and security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aving been cut out.
Key words: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logical implication; path for supervi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