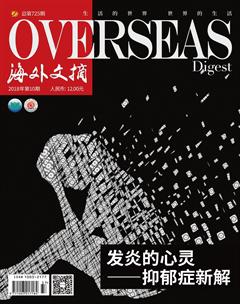被手机打搅的亲子时光
埃丽卡·克里斯塔基斯
在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家长们不必为孩子们整天盯着屏幕而忧心忡忡,他们反而更应该反思自己对屏幕的沉迷。
现今,智能手机引发的诸多恶果我们已司空见惯,如交通肇事、睡眠障碍、相互体谅之情沦丧、人际关系问题丛生、对周遭新奇的事物熟视无睹等。手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不胜枚举,以至于要举出未受其不良影响的事例反倒更加容易。或许,当今社会正在一步步逼近对电子产品口诛笔伐的巅峰。
即便如此,仍不断有研究表明,一个关键性问题仍未得到重视。该问题与儿童的发展相关,但可能并非你所想的那样。与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孩子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心不在焉的父母。
诚然,现在的父母比历史上几乎任何时期的父母都有更多的亲子时光。尽管劳动大军中女性所占的比率急剧增加,如今的母亲照料孩子的时间却远比20世纪60年代的母亲多得多。然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处日趋失和,甚至流于虚假。虽然父母们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但他们却不能做到彼此心心相印。我想说的是,对于父母们这一尴尬处境我并非毫无同情心。我的几个孩子都已成年,他们总爱开玩笑说,如果25年前我整天抱着一台智能手机不放,他们可能都活不过婴儿期。
不只成年人,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直接危害也没有得到重视:大量证据表明,盯着屏幕观看各种画面(尤其是那些快节奏的或是暴力画面)会对孩子的大脑造成损害。现在的学龄前儿童每天用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已超过了4小时。而且,1970年以来,开始“定期”观看电子屏幕的儿童的平均年龄已从4岁提前到了出生后的4个月。
儿童在手机或是平板上玩的某些新型的互动游戏可能要比看电视(或者看YouTube上的视频)对他们有利,因为这些游戏更为逼真地模拟了孩子们玩耍的天性。当然,许多建树颇多的成年人在童年时期也曾观看大量对个人认知毫无益处的“垃圾”,以此打发无趣的童年时光。我的母亲曾做过在那个时代看来很不寻常的举动,她以无趣为由不许我看《极速赛车手》和《盖里甘的岛》这样的影片。不过,我后来还是想方设法把两部片子里的每一幕都看了很多遍,至今我也没弄清我这样做是为什么。不过,沉溺于电子屏幕的儿童所付出的巨大的机会成本是不容任何人争辩的:每在电子产品上多花1分钟,便是少了1分钟去积极地探索世界和与他人交流。
然而,尽管大家都在热议儿童在电子屏幕上消耗的时间,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父母自身对于电子产品的迷恋。正如科技专家琳达·斯通20年前提出的概念——“持续性分心”,现在的父母们正饱受其困扰。斯通已有言在先,这种趋势不仅在危害我们自身,还在危害着我们的后代。这种新型的亲子互动方式会使潜藏于人类基因中的“情感提示系统”中止运行,而这一系統正是构建人类大多数学习能力的基础——反应交际。
儿童成长专家对于成人与儿童间的“二元信号系统” 这一组建人脑基本架构的系统有不同的称呼。儿科医生、哈佛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杰克·肖恩科夫将此系统称为“发球与接球”式的交际;心理学家凯茜·赫什-帕塞克与罗伯塔·米奇尼克·戈林科夫则将其表述为“对话二重奏”。无论身处何地,在与婴幼儿交流时,父母们总是会用音调更高、语法简单,情绪投入且夸张的语言模式。尽管对于一个成年的旁观者而言,这种说话方式让人腻烦,但对宝宝们来说这可是百听不厌。不仅如此,一项研究还表明,婴儿沉浸在这种互动式与情绪饱满的应激对话环境时,比没有沉浸在这一环境时,词汇量要丰富一倍。
儿童的成长跟亲子互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实验中,9个月大的婴儿在接受数小时的真人中文教学后就能够分辨出该语言中的某些音素,而另一组婴儿通过视频教学接受相同的内容后,却无法分辨。天普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赫什-帕塞克认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亲子交流的重要性,她表示:“语言是评估学校表现的唯一最佳指标,而强化语言能力的关键则在于幼儿与成人之间流畅的对话互动。”
因此,一旦成人与儿童间的情感共鸣提示系统(对早期学习能力至关重要的系统)出现中断(例如家长们收到一条信息或瞟了一眼“照片墙”),问题就出现了。所有那些曾被边看手机边推婴儿车的父母们撞倒过的行人都能证明,这一现象确实无处不在。家长育儿时频繁分心造成的后果已得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关注。该经济学家发现,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儿童受伤的案例也在持续增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根据地点与时段的不同推出了相应的智能手机服务,借此开展了一项饶有趣味的实验。在每一处,只要智能手机的使用率上升,儿童的急诊案例就会相应增多。这些发现使相当一部分媒体的注意力转到了因家长沉迷手机而给孩子带来的安全危害上,但对于此行为给孩子的认知发展造成的影响,我们却没有及早给予高度重视。“如果我们在与儿童交流时拿起手机或者是查看手机屏幕上一闪而过的信息,交流的流畅性就被破坏了,幼儿也学不到任何东西。”赫什-帕塞克如是说。
在2010年前后,波士顿的研究人员曾暗访了55位在快餐厅就餐的看护人,他们身边均有一位或多位儿童。经观察发现,这些看护人中有40人在不同程度上沉迷手机,有些几乎完全无视身边的孩子(研究人员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不是接打电话,而是在手机上打字和刷屏)。这样一来,许多孩子自然开始想方设法吸引大人的注意。当然,大人们通常对此置之不理。在后续的一项研究里,有225名母亲及她们约6岁的孩子被研究人员带到一个熟悉的环境中,每位母亲和孩子均分有食物,他们之间的交流互动被摄像机记录下来。观察过程中,有四分之一的母亲本能地用起了手机,而她们在玩手机的同时,与孩子间的语言与非语言交流明显减少。
此外,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项精心设计的实验,用以评估父母使用手机对孩子语言学习的影响。该实验在美国费城地区开展,由赫什-帕塞克、戈林科夫以及天普大学的杰萨·里德负责。实验中,38位母亲和她们2岁的孩子被带到了一间房内。按要求,母亲们需教会孩子两个新单词(blicking,意为“弹跳的”;frepping,意为“颤动”),同时每位母亲都配了一台手机,以便研究人员从另一间房与她们取得联系。实验表明,每当有电话打断母亲时,孩子便无法习得这两个词汇。没有电话打扰时,孩子则能习得词汇。不过,在此项研究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研究人员不得不将7位母亲的实验数据排除在外,因为她们根本没有接电话。虽然她们没有遵守实验规则,但是我们真应该由衷地赞叹她们!
一直以来,要让大人与孩子间的需求达到平衡并非易事。如果总以为孩子永远是父母关注的焦点,那就太天真了。父母们总免不了偶尔将视线离开孩子,享受一下自我时光,就像《柳林风声》中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乘船游逛”,或者只是想懒洋洋地歪在幼儿玩耍护栏里无所事事。从某些方面看来,21世纪的孩子们手中的电子产品实际上与保姆们的作用并无二致。每一代家长们都曾聘请保姆照顾和陪伴孩子,以免孩子们过于无聊,而现在的这些电子设备的作用也正是如此。一旦父母们的周围没有了护栏,无论是真正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的护栏,慌乱也就离他们不远了。
作家卡罗琳·弗拉泽最近出版了一部关于《草原上的小木屋》的作者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的传记——《草原之火: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的美国梦》。书中描写了19世纪边远地区的父母们照料孩子的极为随意的方式。为给孩子保暖,他们会把孩子置于烤炉的炉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只好撇下孩子任其自生自灭,因为各种职责铺天盖地飞来,母亲们拙于招架。书中,怀尔德叙述了女儿罗斯在危难关头遭遇的种种惊险的经历。有一次,她正忙着做家务活,突然抬起头,看见一对小马正从尚在蹒跚学步的女儿头上跃过。
父母们偶尔的疏忽当然不能算是灾难(甚至还可以帮助建立应激机制),但若长期心不在焉就要另当别论了。人们常常把智能手机的使用和随处可见的手机瘾联系在一起:沉浸在手机世界中的大人们若在此时被人打扰,就会变得非常暴躁;他们不仅会忽略周围的人发出的“情绪信号”,而且甚至会曲解这些信号。设想一个孩子竭力在父母面前耍赖,他实际上是想要博得父母的关注,而此时沉迷于手机中的父母可能会比与孩子进行亲子交流的父母更容易发脾气。
父母与孩子间刻意的短暂分离当然不会有任何危害,甚至可以说对双方都有益处(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会需要更多独立空间)。但这种刻意的疏远不能与父母的疏忽相提并论,后者表现于父母就在孩子身边,但交流的过程却是人在心不在,孩子还不如一封邮件重要。母亲告诉孩子去外面玩儿,父亲说他得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专心处理事情,成年人生活中的各种事务让人应接不暇,用以上回应来打发孩子确实也合情合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父母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切都由手机的嗶哔声和手机上的各种诱惑主宰。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了能够想到的最坏的育儿模式之中——常常只是身体和孩子在一起,确保不让他们自行其是,但心灵上却只是偶尔才会贴近孩子。
要纠正这一问题并非易事,尤其是考虑到教育中的巨大变革会使这一问题不断恶化。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孩子(约三分之二的4岁儿童)由各种机构托管照料。如今的儿童早教中照本宣科式的课堂模式和老师们枯燥无趣、一厢情愿的说教已靡然成风。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孩子们鲜有机会与他人自发性的交流。
由此,一条好消息则是,小孩子总会事先想到一些主意,以便从大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沉迷在手机中的目光原来是被孩子那双胖胖的表示着不满的小手拉回来的。为了夺回大人们的注意力,孩子们总会想出很多办法。若我们不能及时纠正自己,他们则会试着帮我们纠正;随着适龄儿童步入学校,我们将来会目睹越来越多的孩子任性耍赖。但孩子们最终或许会放弃。“探戈起舞需两人”,罗马尼亚孤儿院的研究向整个世界表明,若没有一个愿与之共舞的“舞伴”,孩子们的认知会受到一些限制。事实上,我们根本不了解当我们没有全身心参与亲子互动时他们会有多么沮丧和难过。
当然,成年人对于自己当前的生活安排也颇感苦闷。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围绕着一个让人烦恼的前提进行的——他们得一直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马不停蹄地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孩子,当爱人和父母以及其他任何人需要他们帮助时得随叫随到,同时还要对最新的资讯保持敏感,准备开车时走在路上还要记得在亚马逊购物网站上下单多买一些厕纸。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忙得不可开交,在数码世界中也一样连轴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容易在孩子们对着电子屏幕时感到焦虑,而对自己手中的电子产品难以割舍。我对这种态度了如指掌。我自己就是一位母亲,也是几个孩子的养母,还是一只肥胖中年腊肠犬的女主人。我虽然也已人到中年且身体发福,但我更关心家中爱犬的卡路里摄入量,严格控制它的饮食,只许它吃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却不愿让自己吃得更养生,还难以放弃每天早上的肉桂面包(罪过罪过)。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投射”现象,即,防御性移除自己的过失,然后转嫁到其他无辜者身上。在如何看待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都要尽量减少“投射”心理的作祟。
如果我们能驾驭某些心理学家所称的“科技干扰”,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只要我们少忙一些,就能为孩子多做一些。全身心投入在孩子身上的那几个小时,我们不要想其他事情,而其他时间,我们可以自由支配。家长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由,摆脱让人无法喘息的重重压力,不再为迎合所有人而大包大揽。把你的孩子抱进游戏园区的围栏,现在就去!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尽情观看足球比赛,你的孩子当然会平安无事。可一旦你和孩子在一起,就赶紧把你那讨厌的手机收起来。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