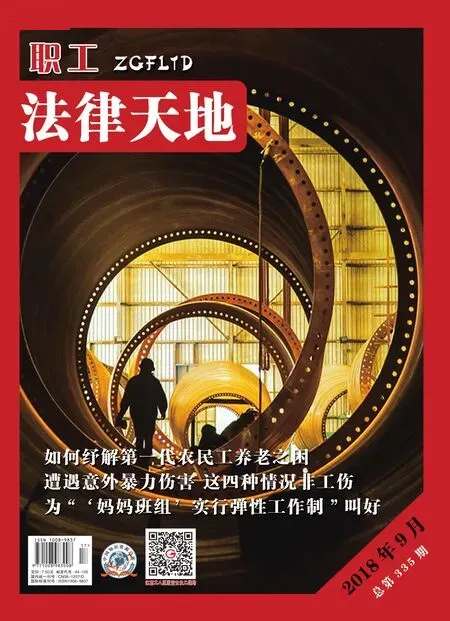如何纾解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之困
□宗 禾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落户在我国沿海地区,那里也成了最早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自那以后,或始于维持生计的初衷,或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一批批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工厂,走进城市,把青春岁月留在那里。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时,都特别强调“劳动力红利”因素。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勤劳的双手,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片蓝天。
如今,我国第一代农民工都年事渐高,不少人已年过花甲,在拼体力的劳务竞争中他们不再具优势,这个群体已到思考人生归宿的节点,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
面临“裸老”命运的第一代农民工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养老保险的遗留问题已经显现,并且将在未来数年内集中显现。
近年来,深圳市社保部门被农民工群体接二连三地告上法庭。“旁听席第一排的,你们分别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方的?”龙岗区法院小小的审判庭里坐满了人。庭审未开始,法官便逐个询问旁听者的姓名与立场。在奇怪的开场白下,所有人都伸出右手,指向了原告席。循着人们的目光,可以看到一个穿着暗褐色短袖、身板单薄的女人,偶尔回应法官的问话,声音低得听不见。这一切让她在严肃的法庭上显得毫无存在感,虽然她身后有一支强大的“后援团”。她叫苏贵琴,是最早起诉社保部门的农民工之一。她在一家工厂里打了10年工,老板没有给她交过一分钱的养老保险。社保部门说,根据现行政策,只能补缴两年之内的保险。“凭什么只能补缴两年?”苏贵琴将社保局告上了法庭。这支“后援团”来自深圳的各个工厂。与其说关注着苏案,不如说他们关注着与养老保险补缴有关的一切。是否能成功补缴,关系到他们后半辈子的衣食冷暖。而在法庭之外,还有散落在深圳乃至全国各个工厂里的老工人,他们或是诉求无门,或是认了命,无可奈何地回到农村。
他们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跟随打工大潮南下深圳。同时,他们也是逆潮而动的一批人:在同一家厂里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工作的稳定性让他们看起来与城镇职工无异。但在退休的节骨眼上,他们却因为没有缴满足够年限的养老保险,可能面临“裸老”的命运。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老龄比例连年攀升。目前,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深圳,异地来深劳务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虽然达到八成以上。然而,大多数农民工的参保年份在2008年之后。这意味着近年退休的农民工里,将有一批人因不满15年缴费年限而无法领取养老金。
一份民间调研报告显示,六成以上的农民工不了解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也不知道补缴政策。而对每天在流水线上干活的农民工来说,“没有途径去了解”成为最主要的原因。许多人到快退休时开始关注养老保险,才发现这扇门早已关上了。
几多忧愁几多无奈
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农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从那时开始,李秀梅留了个心眼,每年厂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保险没达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累计缴费满15年”,因此也没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退保。
到目前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厂”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但他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他退休时养老保险缴够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点人情关系,于是转回老家某单位“挂靠”继续缴费,如今已快满15年,马上能领到养老金了。年纪大了,每个月还能有一两千元,在老家农村,是招人羡慕的。
这个“案例”在厂里广为流传,毕竟,五十来岁的“老人”越来越多。根据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退休或正考虑退休的农民工,已超过5000万人。
李秀梅也是其中一员,前几个月,她满50岁了。

某种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尴尬。她发现,自己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深圳工作,但直到2004年起厂里才给她买了“当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养老保险,如今已缴12年零4个月;麻烦的是,她想补缴2004年之前的养老保险,或者延长缴纳期限,补齐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操办的事。
如今五六十岁的农民工群体中,养老保险缴满15年的并不多。毕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普遍观念是“干一天算一天”,根本就不会去奢望什么养老保险。
比如肖叶青,若不是10年前工厂老是“无故”给她放假导致挣不到钱,她也许至今都接触不到“养老保险”这个词。当年她和工友们集体去问老板“放假的原因”,原来是为了应付“上头检查”,没有缴纳社保的员工不能到车间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与每月放假减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缴纳一点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叶青才有了买社保的契机。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问题又来了。她从2006年缴起,尚不满8年,更不用说15年了!如今,工厂也倒闭了。对已经52岁、文化程度不高的肖叶青来说,进退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识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少之又少,所以到了退休年龄能拿到退休金的第一代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农民工,他叫郭锦钊,从1987年在某宾馆做保安和客服人员,整整干了16年。幸运的是,宾馆一直给他按时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退休时他每月能领到养老金700多元。当年曾被媒体广泛报道,郭锦钊自己都没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样拿退休金养老”!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郭锦钊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门曾在2007年首次通报,220名农民工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待遇。到2010年,这个数字是320人,人均养老金为1500元。但是,这个数字与当下数千万正要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实在太少。
不过,我国在养老保险统筹上,一直在进步。以农民工数量较多的深圳为例,1989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后来借鉴了新加坡经验,1992年在国内率先创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能与统筹账户相结合;1995年深圳颁布规定,允许外来农民工离开时可以退保……

2010年,国家出台《社会保险法》,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肖叶青一直珍藏着当年从宣传摊位上拿来的这份文件,在第十六条下,重重地画了黑线。
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该市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而东莞2007年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金达30多万元。“那时大家都在问,可不可以不买,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很多农民工这么说,许多人都是到快退休时开始关注养老保险。
而对肖叶青来说,工厂的倒闭,使她补缴养老保险的希望也落空了。已经交了7年半的养老保险依然放在社保局,尴尬的是,这笔钱不知如何处理好。由于城乡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操作问题尚未解决,无法转回老家;由于深圳市出台的相关规定,补缴社保只有两年的追溯期,所以她目前也补缴不了。她打起了官司,希望能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争取养老金。
深圳市的有关规定虽然允许企业与工人协商补缴,但两年的追溯期与“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额”大大增加了工人们与企业协议补缴的难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补缴金额为3万元,而滞纳金则高达10万元。
事实上,即使工人与企业达成补缴协议,目前来看,他们依然无法实现养老夙愿。因为农民工养老不仅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课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改革。
多管齐下破解农民工养老困局
由于收入低、故土难离等原因,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在城市颐养天年,而是会选择叶落归根,回到农村。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整体步入老年,养老问题必须摆上议程。这一特殊群体的“超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时评员凌国华在光明网撰文指出,在社会养老金存在较大缺口等整体形势至今仍不甚乐观的情况下,农民工养老可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不单单体现在农民工养老工作的面大线长,更因为城乡二元化等历史遗留和现实困境的加剧,故使得农民工养老一直停留在“养儿防老”的“自给自足”层面上。体制内外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养老体系,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自然无法获得体制内的“垂青”,而鉴于农民工只是暂时离乡的打工者,他们的最终身份仍旧是农民,这也就使得他们的养老困局仍旧桎梏在城乡二元化所带来的制度迷思当中。
改革开放40年了,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收获了辛酸、歧视以及并不丰厚的收入之后,他们的身体逐渐佝偻,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他们不再有任何竞争力,“没有活干”是他们不能改变的趋势,更大的困境则在于,已经整体步入老年的他们,能否“颐养天年”,又该如何“颐养天年”?传统社会的断裂使得“养儿防老”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日渐增长的养老需求,而体制造成的裂缝短时间内难以弥缝。如此看来,横亘在农民工面前的养老困局,显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讲,不论是“超龄”的坚守还是被迫的返乡,都无法抹去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时代变奏色彩。这些年过半百甚至已届花甲的农民工,不论是仍坚守工地出卖残存的体力,还是回乡依附离开已久的土地,显然都无法回避养老难题。而40年巨变导致的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传统观念的嬗变,都在或多或少侵蚀着乡村“养儿防老”的社会保障模式。不错,40年中农村也在发展,但却是城乡二元化体制下的不平衡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城乡间的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对于包括养老在内的农村公共保障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
不论是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来讲,还是从农村、农民、农业等“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来讲,发展都不能畸轻畸重,不能搞体制歧视,更不能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包括农民工)为发展垫底。“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农村养老问题又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讲,包括养老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也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从“三农”的层次上说,中国梦应该也包括兴农梦,应该让农村更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
包括农民工养老在内的农村养老困局亟待“破题”。农村养老应该而且可以多元化,公共部门、社会以及个人都应该是农村养老的主体。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借鉴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政府补贴一部分,个人承担一部分,同时要鼓励企业等社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农民工养老在内的农村养老问题,更应该放到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新型城镇化过程要探索农村养老的新模式,将农村养老纳入土地流转、农村社区建设等过程中,这样不仅免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更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释放制度红利。
“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他们老了,却陷入老无所养的尴尬境地,政府对他们进行政策扶持,助他们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是值得期待的。
纾解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之困,需要更多制度反哺,让背井离乡建设城市的劳动者在退休时享有基本的保障。第一代农民工的境遇,实际上是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的现实投射。因此从根本上而言,解决的落点还是要放到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来,实现权利的平等,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包括第一代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才能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破解第一代农民工养老困境意义深远,不仅能切实解决这些人面临的现实困难,还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今后养老探索出一条制度性路子来。从现实看,农民工养老问题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问题,社保能否覆盖到每名农民工,到了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年龄,养老金能否支撑他们的生活开支?二是看病问题,医保能否解决农民工看不起病,重大疾病会不会导致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不论是收入问题还是看病问题,反映的都是农民工养老的制度性缺失。目前,政府层面已经形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多从宏观层面出发,对农民工自身的特点考虑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导致制定的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比如,规定参保只有累计缴费满15年才可领取退休金,但农民工从事的多数是体力活,多数是灵活就业,鲜有单位会这么长时间雇佣他们;又比如,农民工流动性大,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却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省际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从而造成“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恶性循环,等等。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曾动情地说:“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也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破解农民工“城市无法养老、农村无力养老”,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进,更需要健全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或采取“进城养老”立法模式,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适用范围;或采取“返乡养老”立法模式,把农民工纳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还可以采取专门的立法模式,针对进城农民工制定专门的养老保险法律。但不管采取哪种立法模式,都必须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权利义务,让农民工养老得到法律的保护,让违法行为得到应有的制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养老“几面都靠,每面都靠不住”的现状。(据光明网《大众日报》《上观新闻》《小康》《农家书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