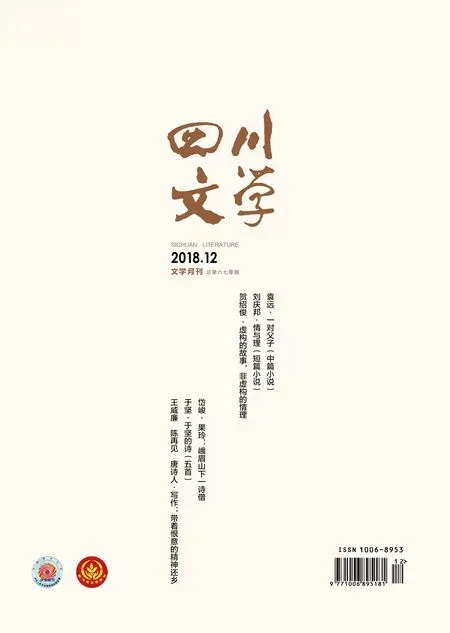逍遥游
一
付建涛找到我这里,本是意料之中。他是张晓婉的丈夫,我是张晓婉的闺蜜,张晓婉出走,他不找我找谁。但我真不知道张晓婉的下落。付建涛鼻子一哼,眉毛吊起来,吼道:不信!你们在合伙骗我!他在我的房间里风一样的穿梭、寻找,连阳台外面都仔细看了。
此时是2016年4月6日,清明节刚过,花开的香气自窗外涌进来,我和付建涛都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在如此美好的春天里,付建涛一脸阴郁,眉头紧皱,为找不到他的妻子而发愁。据付建涛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做生意赔本后张晓婉觉得没有混头才出走的。但她去了哪里,会不会自杀?付建涛问我。我嗤地一笑,你和她混了这么多年,还不了解她,谁死她也不会去死!她可能只是不想见你,躲起来了。
那你肯定知道她在哪里!他叫嚣起来,在我面前拉一张凳子坐下来,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不走了。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气呼呼地一饮而尽,手掌拍了一下桌子,你交不出张晓婉,就得留我喝酒!他逼视着我,耍赖了,我知道他刚刚在别处喝了酒。付建涛就是这么一个怂样子,醒时胆小如鼠,连个屁都不敢放,醉了才敢胡吆喝。此刻我重新打量他:一米七左右,七十公斤,头发白了三分之一。他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干一些粗活。因张晓婉的原因,他混迹于我们这帮油腔滑调的文人之中,但奇怪的是他又对我们深恶痛绝,常常暗地里声讨我们。而我们自然不肯放过他,常常当面耻笑他配不上美女作家张晓婉,而张晓婉对跟屁虫似的付建涛更是讨厌,所以故意不给他做饭洗衣,任由他叫花子一般在街上晃荡。就像今天,他上身穿一件旧败的灰蓝夹克衫,下身是一条皱皱巴巴的黑色运动裤。见我打量,他故意将磨得起毛的袖口抻开给我看,你看看,张晓婉就让我穿这样的衣裳,挣的钱她都拿走了,也不给我买件新衣裳!
我嗤的一声,没忍住笑了。说实话,我看不起这样的男人,这两年他们根本没挣到钱,倒欠了一屁股债。但我这一笑却让付建涛哭了。他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我的对面一次次喝酒抹泪,没完没了。他知道凭我们三人的关系,我是不会撵他的,他也好像赖上了我,之前我一撵他,他就说,谁让你当年将张晓婉介绍给我,我不赖你赖谁!
这话听着好无理,但我不和酒鬼计较。现在付建涛已喝掉了我面前的一瓶白酒,又用食指敲敲桌台,示意我把酒给他续上。我给他续酒的时候,无意中碰着了他面前的花生米碟,我说花生米没有了,我下去给你买。说着我起身迈步,但他却猛地抓住我的手,两眼可怜兮兮地望着我,姐,再借我一万块钱吧,我保证能够东山再起,不让你和张晓婉失望!
我恨恨地抽回手,钱当然没借他。我关了房门,走了出来,留下他在身后叫嚣了好一阵子。要搁以前,我会借给他,还会鼓励他好好干,但实践证明,他的能力真不敢恭维,那么多钱投进去,竟没有赚回一分钱,而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见了人还爱吹:我又在街南开了一个公司,连某某局副局长都入了股,你不入?到时候分红没你的份,你可别眼红!人家就问,某某局副局长年底分红分了多少?他伸出一巴掌,努着嘴说,这个数,整整这个数,五万!你入不入?人家掩嘴笑,不信,等我再打听打听。一打听不要紧,他的老底浮出水面。
走在街上,我突然就理解了张晓婉。这么多年,她和付建涛分分合合,而真离婚她又没有胆量,只有靠一次次出走做徒劳的逃离。街上的桃花开得粉红烂漫,一朵又一朵,带着芬芳,从我眼前倏忽而过,像我们那些美丽的过往。张晓婉是我们这个圈子中公认的才女,写诗写小说,出版过几本诗集和长篇小说,也算著作等身,又加上人长得漂亮,性情又浪漫,所以别人一恭维她,她就晕头转向,特别是面对那个梳着大背头、一脸讪笑地夸她的吕主编,她就会失去把控。
吕主编年过五旬,依旧身形修长,风度翩翩,脸部线条也柔和,特别是一笑,是那种很有女人气的味道,但最卓尔不群的,是他眉宇间的桀骜和淡漠。他想热闹的时候比别人更爱说笑,但他的热闹是瞬间可以被收起的,他细长的眼睛里立马就能射出拒人千里的光。一次笔会,他和我们一帮女作者炫耀他的大牌衣履,我们都嘲笑他,只有张晓婉没有。张晓婉上前摸着他的名牌西装,赞不绝口。就是那一次,吕主编夸了张晓婉的小说,并炫耀似的挽起了张晓婉的胳膊。
没过多久,张晓婉对我说,吕主编要调我去南城呢,还说要给我再出几本书!说这话时,她还在我们当地农业局上班,农业局工作清闲,所以她才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而我就在她隔壁水利局工作,工作也没什么事,就将她的书推荐给我远在北京的表哥。表哥是书商,让他来替她做书也比较放心,但表哥却打来电话,说我做还不如你做,这样我能带带你,增加一些收入。就这样我和表哥将张晓婉的第一本诗集《我与非我》推出去,给她的稿酬虽不多,但比那些自费出书的强很多。后来我们又推出她的长篇小说《局内人》,卖得很火,给她的稿酬很多,我也算没白忙活,确也有了那么一点儿收入。但让人生气的是,张晓婉总怀疑我克扣了她的版税,言语里总带出讽刺,一着急我就说了伤她心的话,如果你看着吕主编好,就让他给你出书,再不要来找我!
撇下这话,我后悔了好几天,以为她再不来找我。但某一天黄昏,她又在我单位门口截住了我,大大咧咧地说要请我吃饭。这我当然会答应。张晓婉是那种幼稚到骨子里却偏要摆深沉的女人,让人可怜、可气,又可笑,但这也正是我喜欢她不忍拒绝她的原因。再说,我们的友谊可以往上追溯到南城技校,当时我、张晓婉、付建涛都是文学爱好者,在一个叫“逍遥游”的文学社团里相识。“逍遥游”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有“鲲鹏”大志,都要做“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之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张晓婉和付建涛相爱、结婚,而我也在风浪里摔打,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这样的友谊基础,所以张晓婉永不会对我记仇,但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惊到了:今晚上吕主编做东,说要聘我去南城当编辑,你也替我掌掌眼!我当即奚落她,怎么可能?弱智,没心眼,老油条文人的话你也信!不会是耍你玩骗你上床吧?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她措辞强硬,且逻辑性很强地反驳了我: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诋毁一个喜欢我的文友?莫不是你妒忌了吧?怪不得你这么多年没有男人喜欢你,除了拒人千里之外,还把所有人当坏人!不得不承认她一刀子戳到了我的痛点,前夫是我一个单位的同事,本来眼皮子底下再怎么也不会出事,但他还是和我的另一名女同事发生了关系,这让我不得不选择离婚。我气呼呼地回身想走,但一抬眼却见到吕主编正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走来。
我的眉眼和嘴角往上不自然地一拉,僵硬地笑着和吕主编打招呼。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前,表哥曾叮嘱过我,文界水很深,你一抬腿一动嘴说不准就碰着谁,你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喽。吕主编已风度翩翩地走过来,握着我的手打着官腔说,你的这位蜜友张晓婉可是跟我经常提起你,你可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对她的帮助很大呀,我替她谢谢你!再有这次让张晓婉约你,我是想借你一臂之力,通过你表哥把我们的《南城文艺》推到京城去啊,为了文化的发展,你怎么能推辞不见我呢?
茶上来的时候,吕主编捏起一支烟,吸了一口,淡青色的烟圈自他的鼻孔缓缓喷出。张晓婉望着他出了一会儿神,突然以沏茶的名义走到他身边问:你不是说你们《南城文艺》缺编辑吗,还招人吗?吕主编当然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耸耸肩,伸出左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当然喽,缺你这样的人才啊。吕主编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有点权力但也不是多么大,对于调动人员这样的大事能不能办到,真是不好说。我记得他当时一下子转移了话题,夸奖起张晓婉的白色连衣裙,说她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像仙女下凡一样亮瞎了他的眼。而推杯换盏之间,他也再没有说起让我帮忙将《南城文艺》推到北京去,我知道在他这种人的心里,是有些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城女人的,既然看不起怎么又会将说过的话当真。接下来在我看向他想问他话时,他端起面前的青瓷茶碗,轻嘬了一口茶,但却不小心嘬到一根茶梗,他哎哟了一声愤愤地将茶梗吐到纸巾上,团了团扔在垃圾桶里,昂着头瞟一眼远处的侍者,这叫什么茶啊!但接着又朝我们回过头来说,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茶,不计较了,别耽误我们说话。
后来,我们说的什么我都忘记了,只记得那天张晓婉一个劲儿地给吕主编倒酒,自己也频频举杯,直喝得满嘴胡话,两腮泛红,脚步踉跄,不得不打起“黄瓜架”离去……
再后来,就有一帮文人说张晓婉和吕主编好上了。
二
我回来的时候,除带了付建涛吃的水煮花生米,还将回家探亲的北京表哥带了回来。表哥说,像付建涛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我跟你去,他不敢再赖着你,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当然知道付建涛不敢把我怎么样,但左右邻居都是长眼睛的,尤其像我这样的单身女人,唾沫星子还不得把我淹起来。我总觉着像付建涛和张晓婉这样的夫妻是不会选择离婚的,离婚是需要勇气的,尤其像我这样带着一个孩子的。但付建涛对张晓婉的爱,我真不敢恭维,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后来张晓婉向我哭诉,你知道吗,每次出差付建涛除了检查我的手机,还让我将内衣一件件脱掉,像狗一样嗅闻上面是否有异味……我真想死,受不了啊!我扶着她啜泣的肩膀,安慰她说,付建涛对你可能是真爱吧,像我在外游荡多久都没人管,也是一种不幸啊。
这话说了没多久,我就听人说两人在闹离婚,张晓婉执意要离,但付建涛说什么也不离。此时他还没抓到张晓婉和吕主编相好的证据,表面上也摆出一副不相信外界传言的样子,在我们面前他对张晓婉唯命是从,但张晓婉就是不给他好声气,嚷得他像孙子似的。周日吕主编来我们这里,顺便约了我、张晓婉和其他几个文友一起喝茶,但我们刚到茶室,付建涛就尾随而来。张晓婉立刻就埋怨起我来,说一定是我将消息透漏给了他,他才会找到这里!为了洗清自己,我气呼呼地让付建涛向众人展示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同时我也将自己的通话记录公布于众。文友中有人说张晓婉你这样做有点过了,她不听则已,一听又委屈地抹开了眼泪,还不是她(她指着我)给我做的好媒,让我嫁了这么一个衰货!我一听又急了,要不是当年你俩千次万次地撺掇我当你们席面上的媒人,谁会倒了八辈子血霉管这档子事,再说你们好与不好与我何干?张晓婉的脸羞得更红,病了样大口喘着气。还是吕主编有度量,他风度翩翩地从人群中走出,笑得脸摊成了面饼,隔着老远就热情地握起付建涛的手。
付建涛一把甩开他的手,说,什么脏爪子,摸我干嘛!我早就听说张晓婉喜欢你了,是男人就和我去外面单挑!吕主编轻松地拍拍双手,真跟着付建涛走了出去,这有什么了不起,单挑就单挑!
据说那天付建涛领着吕主编去了莫愁湖畔。阳光普照绿树掩映中,两人没有头破血流,倒是付建涛对吕主编讲了他和张晓婉的恋爱史,最后还恳请吕主编为他指点迷津,告诉他张晓婉为什么会移情别恋?吕主编嘿嘿两声,耸了耸肩,接着就发挥起文人的口才来,男人优秀必然招蜂引蝶,这怪不得张晓婉。再有,你呀,别只沉醉却不知“生长”,年轻人,你要懂得生长,不要拒绝生长,而且婚姻里的成长是互相和共生的!你要像我,有钱给女人精致的生活,她自然会爱我;你要像我,懂浪漫每天过得像诗,有梦就有爱情幻想,你说女人不爱我?付建涛醍醐灌顶,本来想要跳湖以表殉情,但面前突然就劈开一条通天大道,使他身不由己地踏了上去——他颤抖地握住吕主编伸过来的那双已有老年斑的手,滋味复杂地看他的大背头在阳光里闪闪发亮。
吕主编回到茶室的时候,我们已喝了两盏茶。他为自己的英明决策(刚才我们要求和他一起去外面被他一口回绝)和与众不同的口才而陶醉了好一阵子。他拍着张晓婉的肩膀,轻飘飘地说,解决了。但他说得越轻飘我们就越好奇,特别是文友中的女士们,都抬起一双秀目紧抿着嘴唇等待他的下文。很简单,他又说,桌子下面他的手却不安分,放在了张晓婉的膝盖上。张晓婉又像刚才那样喘了一口,袖着手正不知哪里放时,吕主编的手却伸过来,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小白手。
于是,一切皆大欢喜。后来听说付建涛在吕主编的指导下开了一家小书店。而他爱吹牛的毛病就是从此时培养起来的。后来他的书店关了门,又开了文具店,文具店也关了门,这才走投无路,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付建涛从桌子上抬起他的鸡窝头,见我手里拎着花生米,还将一个男人领来,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表哥深谙文化圈里的人和事,自然对付建涛看不到眼里,但碍于我的面子,他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文化事业不好做,你还是改行吧。此时,付建涛的酒已全醒,不再向我闹着要张晓婉,而是规规矩矩地坐到我和表哥的对面。
三
一周后,出走的张晓婉却奇迹般地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张晓婉这次回来却有点炫耀的意思。她约了我们一帮文友在最有名的东来顺饭馆吃饭。她点了饭馆里最有名的海鲜菜——海参宴,又点了许多特色菜,要了两瓶海之蓝白酒和十打啤酒,看她的样子,明明是憋着劲往大里花。付建涛也在,他很少说话,只是时不时伸手握握张晓婉的手,告知我们张晓婉失而复得的艰辛。有人告诉我,付建涛在电视台打了寻人启事,又联合张晓婉的亲友,才在青岛将她找到然后将她带回。张晓婉今天穿了一件嫣然牌孔雀蓝旗袍,旗袍本来就为凸显女人身材而生,又是名牌,自然精致到领口和滚边,而她身材又好,脸蛋也没得说,又施了薄粉,遮住了因出走所带来的悲伤,眉眼虽笑得失了真,但眼波流转,黑瞳仁里映满了亮星星。面对这样的张晓婉,我们个个被怄得酸水横流,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捏着旗袍的绿滚边,打量她旗袍领里的美颈,一边热情地问这问那,一边想象她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但奇怪的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吕主编,就好像他从没有出现过。
等菜端上酒也斟上,席面上出现了片刻宁静。还是张晓婉清了清嗓子,抬了一下藕似的臂膀,挥着她的小白手,笑着说,喝啊,大家怎么不喝酒?哦,对了,喝酒前忘了给你们讲故事当下酒菜了。我这次去了青岛海滩,在海滩上晒了七天大太阳。你们也知道我所在的农业局那间办公室不朝阳,背阴,平时潮得能滴出水来,我是真向往阳光了,所以就给自己放了假,去了海边……但这样却吓坏了付建涛,他满世界里找我,我也挺感动的,所以也主动让他找到我并跟他回来了。她说得滴水不漏,有人已冲她鼓起掌,接着噼里啪啦的掌声像下雨般哗哗啦啦。我们说,回来就好,回来好好过日子吧。张晓婉点点头,嗯,我打算和付建涛东山再起,一起再做生意。
她的话,又吓着了我。但我看别人都在恭维她,我也不好意思出声。张晓婉留了下来,过了很长一段消停的日子。不久之后,张晓婉和付建涛还真就在迎宾路盘下一处门店,上挂“茶语·艺香”的牌匾。直到开业,我都不知他们这门店是做什么的,上前一问,张晓婉偷偷告诉我,我们这里是举办艺术沙龙的地方!
沙龙?我更加搞不懂了,谁来入你的沙龙啊!
看我皱着眉,一副不开窍的样子,张晓婉说,我们上面有人,是吕主编帮我们联系的。
又是吕主编。我好像懂了。
“茶语·书香”很是风光了一阵。付建涛逢人就说,他和张晓婉承办过多次当地或者市里的艺术沙龙,连市长和省长都去过他们那个阳春白雪的地方,他们现在不光有了钱也有了名,整天过着养生喝茶陶冶情操的神仙生活……但说到最后,他会抬起头,继续吹牛,说如果我们入股合伙,年底分红可达到10万。在说服我们入股合伙的时候,付建涛和张晓婉会一唱一和,像在我们面前秀恩爱,但也更像我们要是不入会损失很大,以后会哭着闹着求他们。付建涛略带沙哑的嗓音,类似宣言,更像恫吓,你们会出名的,会轰动的,来和我们一起干吧!你们现在不决定,到时后悔都来不及。此时,我觉得付建涛相当陌生,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提醒我,他走的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为了见证他和张晓婉的辉煌,那次省里名作家来我们这里,吕主编在“茶语·书香”举办文学沙龙的时候,我们都到了场。张晓婉那天又穿了她从青岛回来时的那件孔雀蓝旗袍。身穿旗袍的她,自然和我们这些土包子不同,又兼能说会道,妩媚婀娜,要么扭着她的蜜桃臀,风过拂柳般走过大堂的人群,要么亭亭玉立在吕主编身边,俏笑嫣然,眼波流转,周到细致,滴水不漏。而付建涛和张晓婉不同,那天他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旧中山装,衣服前襟第二个纽扣处还有一块亮油渍没有洗掉。那天付建涛就穿着那件有油渍的藏蓝旧中山装,陀螺一样拿凳子摆桌子忙得团团转,大家正襟危坐的间隙,我曾拿眼睛四外找寻他,想让他换掉那件衣服,但奇怪的是,我却没有发现他。
此后他们又承办过几次吕主编安排的文化活动,都说付建涛和张晓婉赚大发了。发了的他们从穿衣打扮举止言行到会客见友人情往来都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两人都不和我来往了。
四
过了腊月,雪多了起来。
张晓婉在一个雪夜突然不期而至。在这之前,我已有大半年没有见过她了。她里面穿着睡衣睡裤,外罩一件大红羽绒服,面容憔悴,头发蓬乱,我开门时她扶着我的门框两眼红肿地喊我姐姐。我将满身雪花的她拉进屋,但她还没有在沙发上坐定,就问我,你知道吕主编被双规了吗?
不知道。
她的眼神是破碎的,脚步是踉跄的。全城人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她的眼睛充血般瞪着我。我说我真不知道,你知道离婚后我一个人带女儿,还有工作,没有时间打听这些事。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突然她就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脚尖,我是一个不光彩的人,吕主编在上头调查他时供出了我,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导她。她呜咽着说,我与付建涛走在一起就是错,后来将错就错,但我很想逃离,要不是可怜他和顾忌老同学你的面子,我早就不回来了。
我很想问你不回来去哪里,和谁在一起?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口。突然她目光炯炯地望着我,眼角的一滴清泪瞬间滑落,砸在我们相握的手背上。她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最好还是不要开口,当年我们的“逍遥”,并不是真正的“逍遥”,那是一个莫须有的名头,我们举着这个莫须有的名头,错过了自己的幸福,被某些看不见的东西绑架了。
窗外大雪纷飞。就要过年了,街上零星挂起了红灯笼,已有喜庆的味道了。此刻吕主编在我的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我想不起他真实的面容,就连他的笑都是假的。而后来他与张晓婉且歌且舞导演的这一出又算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活着?那个雪夜张晓婉留宿在了我家,奇怪的是,付建涛也没有来找她。和我并排躺在床上的时候,张晓婉突然拥抱了我,她说,不知怎么我的心里很空,我很怕这种感觉,总幻想自己有垂天之翼,扶摇直上是不罢不休的逍遥之梦。我简直不可救药了,但我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有人给我织梦,我就会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去。
果然,不久后“茶语·书香”关了门。张晓婉已不知去向。被债主们追赶的付建涛常常深夜来敲我的门,我将御寒的衣服和一些吃食偷偷从门缝里递给他,他朝我咧嘴一笑,说,不知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还不如去死!我劝他,好死不如赖活着,说不定张晓婉还会回来找你。他摇摇头说,这次我不打算让她找到我,当然她也不会回来,我的心,已经——碎了!
他说“碎了”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烁出晶莹的泪光。
之后不久,我听说付建涛逃到了北京。在北京成了一个有个性的游吟诗人,经常以“逍遥”为笔名,写一些“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神仙道语。
一次,从北京回来的表哥无意中和我谈起诗人逍遥,说北京人也不知怎么了,都喜欢上了求仙问道的诗,逍遥写的那是什么呀,诗集竟然能够畅销。我告诉他,“逍遥”就是付建涛,付建涛经过人生大风大浪,他笔下的“逍遥”,是真正的“逍遥”!
不会吧。没想到表哥一下子皱起眉头,你说的“逍遥”,不是付建涛!付建涛被债主们追到北京一栋高楼上,跳下来摔死了!
怎么会呢,说着我将付建涛邮寄给我的《逍遥集》摆到了表哥面前。表哥拿着那本署名“逍遥”的《逍遥集》,摩挲着说,没错,就是这本书!但付建涛已经死了啊!你不信,看看报纸上的这则报道。
当他将一张一个月前的报纸推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惊呆了:付建涛的身份证号和他那张没有被摔散的脸,证明死者就是付建涛。
夜色不知什么时候漫了过来,将我和表哥一起淹没。我们突然无语,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只听到夜鸟拍打树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