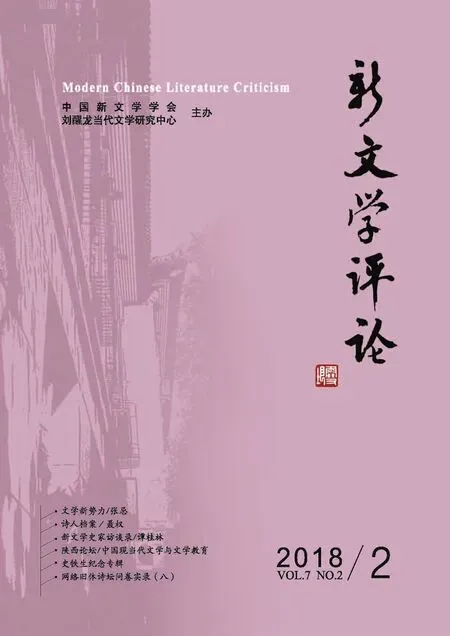等候神启的片刻
——张忌小说论
◆ 樊迎春
张忌的小说读来有难得的质朴自然感,没有丝毫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炫技,也罕见古典传统的谱系承接,有的是对人物和故事的坦率叙述,对文字和篇章的娴熟建构,当然,更多的是对当下现实的敏感把握,对人心困境的细腻触摸。我们太习惯于用西方/东方、传统/现代、历史/现实、革命/启蒙、城市/乡土等话语将要评述和研究的对象摆放至相应的位置,这本身是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建构焦虑的缓解,但也使得多种文学特质被有意无意地压抑和忽视。张忌的小说谈不上异质性体会或震惊性经验,却在平稳流畅的书写中充斥着对以上话语的有力抵抗,蕴含着对朴素文学美感的坦荡回归。而足以使张忌之为作家张忌的标签或许落实于他对某些片刻的敏锐捕捉,这种捕捉并非一时兴起,也非信手拈来,而是蕴藏于作品内部的情感本质的自然发散,是恰如其分地对困境与圈套的自我救赎。但不论是对情感的表征还是对困境的超越,张忌其实局限于虚幻的樊篱之中,游离于自我设置的成功与失败的边缘。他塑造了一个个在生活中浮沉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与人生伴随着他本人的坚定和动摇,对世俗的眷恋与抛弃便开始了张忌式的漫长拉锯,偶然的片刻便在此间被焦灼等候。张忌的写作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一群人的人生演绎,成为一群人的精神出口。
一、 “我是一只小小鸟”
如果说每一位作家的创作起点或写作宝库都是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物的话,张忌似乎是个没有起点和宝库的作家。他不仅塑造了不同年龄、性别、行业、阶层的多种人物,故事题材也广泛涉猎凶杀、刑侦、校园、乡村、城市、底层、少数族群,且全部通透自然,毫无疏离造作之感,没有起点和宝库的张忌也没有天然的局限。当然,张忌无疑也带着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写作,在“低端人口”、“三种颜色”等事件饱受挞伐的寒冬,在不论底层还是中产阶级都人心惶惶的当下,已经白纸黑字存在多时的张忌的人物和故事依然触目惊心。但这种触目惊心并非因为类似《小京》、《夫妻店》、《丈夫》等作品中的凶杀或死亡,也不是因为《宁宁》、《公羊》、《出家》中的各层劳动者的悲伤,而是因为写作中那种超越物质生活表象的文学注视。
以赛亚·伯林在论述托尔斯泰时多次强调作家具有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即“感知何物与何物相适、何物与何物无法并存的能力”,伯林认为这种“现实感”名称很多,可以是洞识、智慧、实用天才、对于过去的感受,以及对生命、对人类性格的了解等等。在伯林看来,这种感觉并非可以习得和巩固的科学知识,“而是对我们适巧置身其中的环境形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是“对宇宙取向的这种无法言喻的感悟”,“现实感”是生命正道之“知”。这里的枯燥引用并非要将这种理论生搬硬套至张忌的写作,而是希望在古今、中西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对现实进行详细描摹的作家并非具有了“现实感”,而“现实感”作为一种天赋,如何融进文学书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写作者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意义上,张忌无疑是幸运和优秀的,不只在于他感知了社会不同阶层的艰难并存,更在于他在这种并存中关注到了那些“不可言喻”之处。
一直以来,她都不讨厌这个行业。她是一个认真的人,无论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份怎样的工作。既然做了,她就会把它做好。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化好妆来到浴场的。每晚,她也是坚持到最后一个钟的那个。她从不挑客,无论对方是谁,她都能笑容满面地完整而细致地服务好。她有许多回头客,但她从来不会为自己有这么多点钟而感到懈怠。相反,她会花更多的力气,想着如何讨好客人,如何不让他们觉得厌倦。别的女孩儿,客人熟了,服务便粗糙了,言语就放肆了。但她从来不会,无论跟客人怎样熟稔,她都会把握住分寸感,无论是服务的第一分钟还是最后一分钟,从来不打折扣。这是她的原则。
亚飞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变得这么多愁善感。小美跟自己算什么关系,不过是一起打牌的搭子而已。说得难听一点,连露水夫妻都不如。在麻将这个圈子里,搭子多的是,聚聚散散都是极正常的事情。如果小美是自己的女儿,就像唐唐一样,那她有什么事,自己这么惦记,倒也说得过去。可现在小美又算什么,连搭子也算不上,自己干吗这么勾着肝儿地想?
在繁华都市中从事灰色工作的“浴场技师”却能够不顾世俗眼光,内心坚守着极为严格的职业操守,而靠和别人组成“搭子”合力在麻将桌上赚钱的中年女人却真诚地关爱一个并不相关的年轻女孩,还有爱上了自己晚辈亲戚的退休老人,因丈夫的过错而受到荒谬报复的普通女人,为了教学成绩勾心斗角的中学老师,处理鸡毛蒜皮案件的乡镇民警,怪异孤独却又带着邪恶的郁闷少年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普遍关注乡土乃至“新乡土”,关注城市乃至城市各阶层,张忌的视角显得有些独特,这些人物都不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被关注者,不携带激烈的城乡的矛盾,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失败者群体,张忌却在文学虚构的基础上将“现实感”投射进这些普通的人心。正是这些人心实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完善,也是这些人心承受了人性的幽暗与光明。张忌没有用苦难兮兮的表述为他们代言,却以“现实感”为每个人打开了一扇窗。在这里,各行各业的每个个体和其周遭都被赋予光晕,不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灵韵(Aura),却可以是杜夫海纳意义上的“氛围”(atmosphere),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实现了真实与虚伪的自洽,实现了个体意义上的审美日常。贺桂梅在引述洲之内彻对赵树理的评价时说道,“作为一个‘现代人’,必然会体验到‘现代的个人主义’主体的困境;而在文学表现上,则必然采取‘心理分析’,这构成文学是否‘现代’的一个基本标志”,张忌并非只是给他们一段普通的心理描写以证明自己写作的“现代”,而是切实在“现代的个人主义”主体的困境中发现了我们不曾认真凝视的蓝天。这片蓝天之下,他们都是张忌的一只又一只“小小鸟”。
这是拥有翅膀却无法飞翔的小小鸟,在早已“告别革命”的年代,它们依然在起飞之前就被雨水打湿了羽毛,或家世贫苦,或精神创伤,或突遇意外,或浑浑噩噩,更多的是对实然与应然差异的不满,是精神与内心的空虚与不安。当赵传深情唱到,“未来会怎么样/究竟有谁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对张忌笔下的“小小鸟”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谶言。但这样的“小小鸟”的独特恰恰在于“小”,在于对蓝天的未知和渴望,在于不知未来只关乎当下的现实,即使从事“见不得光”的职业,也要相信爱情甚至为爱而死;即使人到暮年,也要内心澎湃,为情所动;即使改变宗教信仰,化身“难民”,也要不屈不挠,坚守初衷;即使被所有人耻笑被自己都看不起,也要尝试着保留要回亲生儿子的尊严这些“小小鸟”都谈不上“高尚”,甚至多有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者,但张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赋予他们权利,让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缝隙之中光明正大地过自己的人生,在或恶劣或舒适的物质环境中坦然解剖自己的精神世界。
张忌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对爱与美的渴求,对善与良知的需要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而是普遍存在于人性所及之处,不论这人性是阳光还是黑暗。阻碍这种渴求与需要被获取的,正是他们所欠缺的可以起飞的风,正是可以让他们不再“小小”的人生片刻。这,正是张忌的落脚点与书写吁求。
二、 “恋恋风尘”
对“小小鸟”们物质与精神现状的书写和解剖显然只是我们读到的表面,张忌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他们的困境并找寻出路或至少尝试找寻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或许可以从其最新的、饱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出家》中发现他铺排多时的救赎之路。《出家》中贯穿始终的是宗教元素,其实未及《出家》,在稍早一些的短篇小说《素人》、《光明》、《小姐楼》等作品中,张忌已经表现出了对宗教的浓厚兴趣,及至《出家》,张忌已经将宗教或者说出家做和尚建构为一种“方法”,随着“方法”含义的渐变,张忌的寻找脉络也逐渐清晰。
主人公方泉和妻子秀珍和他们朴实的名字一样,是城市中最普通的打工者,但和其他漂在城市的人不一样,他们不仅将孩子带在身边,还罕见地生了二胎、三胎。对生儿子的执着使得他们的生活愈发困窘,从现代和女权的观念来看,他们并不值得同情,但正是这种“不同情”反映了我们对自我持有的观念的既定优越感。方泉和秀珍夫妻二人自主自愿生育子女并用自己的劳动亲自抚养,这注定了他们成为张忌的“小小鸟”,挣扎、迷惘但始终保有对蓝天的渴望和飞翔的动力。在同时兼顾了送牛奶、送报纸、捡废品等多项工作后,做了一次替补空班的方泉正式成为“兼职和尚”,端起一个新的饭碗,所以在第一层含义上,这种“方法”首先是让方泉一家获得额外收入,摆脱贫困的路径。但即使是在方法建构之初,张忌书写的裂隙便已显现:
我走到寺院的围墙外,随手从边旁的桂花树上折了根细枝,当作根烟放在嘴里叼着。我站在树下,我听见檐牙上的挂钟叮叮咚咚地响,随后,我便觉着一阵风过来了,吹得身边的桂花树一阵窸窸窣窣地抖动。我依在桂花树上,叼着树枝,眯着眼睛看山下像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房子以及远处蓝色的海,觉得满心的自在。
我想,如果还有机会,我还会出来当空班的。
此时的方泉显然对自己的“自在”和“还会出来当空班”没有清晰的认知,他只是把它当作对日常辛劳的一种逃离。但此时不妨再次使用比较的视野,朗西埃在《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爱玛·包法利》中写到了福楼拜书写的“感官体验”,夏尔在农庄里第一次见到艾玛时,“风从门底下吹进来,吹起石板上的微尘;他看着尘土沿地面散开”;艾玛爱上罗多夫的时候,看到他瞳孔周围发射出细微的金色光线,闻到香草和柠檬的香气,还看到马车后面掀起的尘土。而她爱上莱昂的时候,“细长的水草成片地倒伏在流水里,随水浮动,好像没人梳理的绿头发,摊开在一片清澈之中”,在福楼拜笔下,每一次“感官体验”的变化正是情感的变迁,但在张忌这里是否也如此呢?如果“通感”是世界性的,那么至少在方泉这里,这种变化是悄然而无意识的,这也使得他之后的情感变迁总是复杂而不彻底,与艾玛的热忱激烈形成对照的,正是方泉的暧昧摇摆。
在他意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偷懒,生活却越窘迫而绝望的时候,宗教便开始浮上心头。但显然,此刻的宗教和他之间,对彼此都关着门。方泉坐在庵堂门口痛哭失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始捡可以卖的塑料瓶子,身处大规模的法事活动中也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这些,这是方泉对宗教最初的也最本能的抵抗。但在阿宏叔告诉他他适合吃这碗饭之后,在夜晚听了众僧的念诵后,方泉的内心和外在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妻子生产的前夜,他靠念经缓解了身体的不适,并顿悟般看到了广阔宁静的水面,继而许愿生儿子后必将下半生皈依佛祖。这似乎是佛法渡人、灵光乍现的现实案例,但小说又不断向读者呈现其中掺杂的诸多杂质。方泉把对佛祖许的愿当作悬在头顶的利刃,在慧明给他介绍庵里的情况时,他想的是,“既然做了当家,怎么能不计划着将寺庙建大呢?没有大寺庙,哪来的香火?想着这些,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来做这个寺庙的当家,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这里建设成一个比阿宏叔那里还大的大寺庙”。面对象征宗教的寺庙,方泉俨然表现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意人头脑”,他之后所做的一切也是以现代企业管理的方式在运营寺庙,也收到了市场给的应有的回报。张忌书写中刻意设置的世俗与宗教两个世界的分裂与纠缠也越发清晰,他借长了师父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这就是一个行业,赚钱的行业。难道你真相信你坐在寺里,念念经,烧烧香,睡上一觉,菩萨就会发善心,把钱撞到你的口袋里啊?
这一行没那么干净,你真的要做这一行,就要做到六个字,要不怕丑,不怕狗。
张忌在写方泉的故事,显然也在写今天的中国故事,这是小说中慧明说的“末法时代”,但张忌显然没有止步于反讽或揭示,而是更进一步地追问,对于像方泉这样的有“佛缘”的人来说,或者对更多没有佛缘的芸芸众生来说,到底何为宗教,又如何对他们实现有效的救赎?
有一天,躺在草垛子上,我突然就想起了慧明师父。那一刻,我仿佛理解了她。我想,她刚来这里的时候,肯定也跟我一样,心里充满了干劲,要把这个寺庙修葺一新。但后来,她便发现这样做根本毫无意义。这里本就是个死地,无论是我,还是慧明,我们都是过客,都是道具,只有这些生长在这里的老太太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这是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变的现实。
文字至此,张忌其实可以结束整部作品,他建构的“方法”也实现了第二层内涵:民间佛教与寺庙终究是要返归于民,真正的出路不是出家侍佛而是回归世俗,这是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与最可实现的救赎之路。正如徐兆寿在最新长篇小说《鸠摩罗什》中以文学虚构的方法书写了一代高僧鸠摩罗什的一生,但洋洋五百多页的篇幅中,时刻透露着儒释道互相学习、和平共处的现代愿望,儒家通晓人伦生活,佛家教人看待生死,道家主张天人自然,但不管何门何派,终究是为解众生之苦,终究是为了民众更好地去生活。方泉以最普通的男人身份为众生做了有力的尝试,也揭晓了这一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但在这一道理已然明朗之后,张忌却没有停笔,不惜笔墨又一次描绘了方泉返回家庭终究又正式出家的经历。秀珍质疑方泉的真实动机并非只有“还愿”这么简单,方泉自己也心虚无言。因为在他的想象中,“护法”周郁坐于杜鹃花开的山顶,他即将建设成的寺庙前面三排,后面三排,无比绚烂,这是一幅可以满足世俗男人所有事业心与梦想的美好蓝图,这种满足无关事业的性质,无关事业的地点,甚至无关事业的在俗还是出家。当方泉在夜深人静中与当时坐在庵堂门槛上哭泣的自己面对面时,似乎又来到了朗西埃说的“感官体验”的变化,但此时此刻,方泉恐怕也无力区分自己对温暖的家庭与绚烂的寺庙之间的情感倾向,当然,也没有了区分的必要,他已然做出的选择便是新的共生与纠缠的开始。
至此,张忌建构的“方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三层内涵:世俗生活永垂不朽,宗教是出口,亦是新的入口,所有的艰难困苦无非来自七情六欲,终究落于恋恋风尘。
三、 “一生所爱”
如果说《出家》于漫长的故事架构中终于蹚出一条纠缠共生路,那么在以一群“小小鸟”的人生故事铺排的整个文学世界中,张忌无疑一直于其中斡旋游离,《出家》的道路显然不是所有“小小鸟”的道路,但寻找者却只有张忌一人。
在稍早些的短篇小说中,张忌习惯于加入一些令人震惊的元素,如城市血案或村庄凶杀,如青少年死亡或海外偷渡,但这些小说的出彩之处显然在于对人物情感细节的把握,对生命与生活无常无奈的悲悯。张忌是个深知或者逐渐摸索到自己长处的作家,在之后的诸多创作中,他写出的人物和情感,他展现的生命和生活都愈发动人心弦。基层的教师、民警,特殊行业的性工作者、小偷,退休后的老人,看似不具名的“小小鸟”给了张忌广阔的书写空间,使得他的小说情感充沛而内敛,故事单纯却深刻。而在另一部长篇《公羊》中,张忌却一反创作常态,把自己擅长的单线故事复杂化,不仅用近乎失实的巧合和设计推进情节,塑造了截然不同的多个领域人物,在结尾中又回归了最初的对死亡案件的偏爱。这里当然无意人为地梳理张忌创作的线性分期,却可以在《公羊》的“集大成”中窥见张忌写作的意识、姿态,乃至局限。
《公羊》以一个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心理医生的家庭为中心,通过一个夜晚的入室行窃案件铺展开城市底层工作者的生活图景和另一段匪夷所思的夫妻关系和爱情故事。作为一部有一定体量的长篇小说,《公羊》牵涉了多种社会和伦理问题,包括出轨、卖淫、偷窃、强奸、代孕、无性婚姻等等,张忌似乎有意将当下社会面对的诸多困境通过小说展现和叩问。整部作品情节紧凑,步步为营,张忌的语言和技巧纯熟自然,但对现实的书写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现实的问题。面对今天的法律和伦理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张忌如何给出文学的解答其实至关重要。以小说的方式给故事一个结尾其实是容易的,艰难的是我们如何抵达这个结尾。
在近乎离奇的小说虚构情节中,出轨者被情人抛弃,“代孕者”被强行流产,卖淫者良心发现不知所踪,无性夫妻悄然离婚,而偷窃者和被损害者同归于尽小说以异常激烈的情节给了每个人物以结局,揭示出生活的无常流变,生命的可能与限制。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整部小说的主要角色,在无形中历经甚至主动推动了这一切发生发展的心理医生该如何自处?当他对妻子和情人的幻想相继破灭,他信仰的家庭、生活、职业伦理全部崩塌之后,他将如何自我拯救?短暂地沉迷酒色之后,张忌使用的方式是让他背起与自己全然无关的殉情者的骨灰远赴死者家乡,在这个全书最纯洁无瑕者的家乡,在阳光沙滩下,在青山绿水间,在乡野温暖中,心理医生似乎完成了莫须有的赎罪。
小说结尾,心理医生开车等红灯时,在旁边停着的卡车中看到了一只被雨淋湿的公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辆车,会有这样一只羊?这羊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此时,这头公羊忽然扭过头来,看着郁可风。它显得那样的疲惫,一撮白色的羊毛耷拉在它的眼睛上,它的眼神却透过羊毛,直视着郁可风。这眼神迷茫而深邃。郁可风着迷地看着它,这眼神是如此的熟悉,就如同他们曾这样对视过一般。
张忌将全书以这个最后出现的“公羊”命名似乎大有深意。“羊”作为古老的意象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因为相传在酒神狄俄尼索斯身边有一位半人半羊的随从,因此在祭祀酒神时,人们就会身披羊皮,戴着羊角和羊胡须,扮成酒神的随从载歌载舞。后来,这种祭祀活动逐步转变为“悲剧”演出,于是,“山羊之歌”也成为“悲剧”一词最初的含义。在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中,心理医生本人并非无辜,他自己也深知此理,但结局带来的创痛与悲戚依然真实可感。对面卡车里的公羊,似乎就是自己的化身,被雨打湿,疲惫、迷茫,不知来自何处,不知去往哪里。具体的事件总是不值一提,公羊带来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与悲剧“氛围”(atmosphere)才最直击人心。就在这一瞬间,沧桑渡尽的心理医生终于在认清自我后实现了彻底的疗愈。

这时,太阳忽然出来了。金黄的阳光像瀑布一样向整个树林倾泻下来。他站在她的身后,看见她的身上竟然生出了一层淡淡的湿润的金色光晕。

我没有再沿着石阶往上走,我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看着看着,我的脑中不由重叠出了另一番景象,我仿佛看见坐在高台上的那个人,不再是阿宏叔,而是变成了我自己。那些僧众和信徒,站在高台前,温和而赤诚,而我就那样面容安详地坐在高台上,身上笼着一层淡却辉煌的光芒。

我终于流泪了,这还是我到北京后第一次流泪呢!为了不让大伯和姐夫看到我流眼泪,我将头仰了起来。我一仰头,就看见了天边金黄色的那个太阳,此刻的太阳,就像一张金色的大饼,发着温暖的光芒。

张忌不只捕捉了关键片刻,同时对这些关键片刻里的“光亮”有着别样的执迷,这光亮有时候是阳光,有时候是月光,还有可能是喷溅的鲜血,是滚烫的开水,是诵经的声音,是银杏树的召唤他人为地让这种光亮带有了宗教式的神启味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他不厌其烦地蹲守于“小小鸟”们的人生,期待着神启片刻的光临,继而准确地捕捉,优雅地处理,小说的推进与升华也随即完成。多种类型、多种人物的故事中,不变的是张忌始终挚爱和依赖这样一种方式,他之为作家的可贵与局限也暴露无遗。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张忌对某些片刻的敏感依托于内部的情感本质和外在的对救赎道路的追寻。对于“小小鸟”们的生活与情感,张忌以天赋的“现实感”给予他们“氛围”的营造,以深沉内敛的方式解剖他们的精神内在;在对困境与救赎出路的追寻中,张忌寄希望于民间化、内心化的宗教,成功与失败边缘的犹疑终究落于对风尘的眷恋与期待。故事总要结尾,生活却没有尽头。在漫长的表达与寻找中,张忌总在等候神启的片刻,等候捕捉这个时刻带来的转折或裂变。敢问路在何方?真的在脚下吗?脚下的路必定指向“小小鸟”的蓝天,指向俗世的救赎吗?在一切都没有答案以及一切答案都是试错的文学与现实的双重幻境中,被等候的片刻既是神启,其容纳的善恶美丑指向的,至少,总是新的路径。由此,张忌的塑造与解剖、眷恋与游离、可贵与局限,便都有了切实的价值,神启的片刻也获得了需要和值得被等候的意义。
注释
:①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1、85页。
②张忌:《宁宁》,《素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③张忌:《搭子》,《海云》,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④贺桂梅:《赵树理的现代性问题》,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89页。
⑤张忌:《出家》,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47页。
⑥雅克·朗西埃:《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艾玛·包法利》,原载《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2008年冬季刊。
⑦张忌:《出家》,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5页。
⑧张忌:《出家》,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16页。
⑨徐兆寿:《鸠摩罗什》,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⑩张忌:《公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