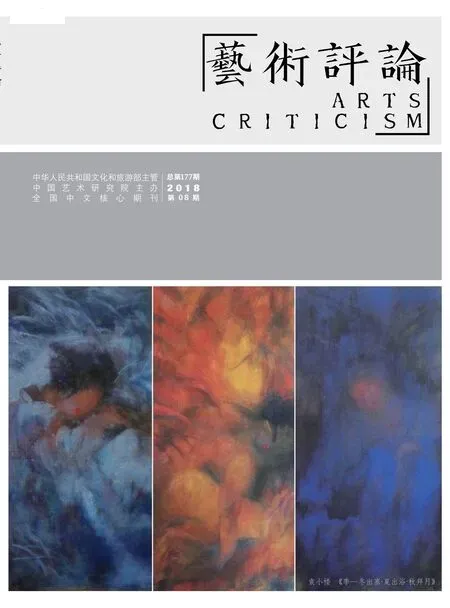“圣”与“俗”的博弈
——再论山西宋金元时期神庙戏台的形制演变
李仁伟
我国现存的金元戏台大概12座,全在山西境内,并且大部分集中在晋东南。现有的研究表明,戏台的发展与元杂剧在山西的兴盛密切相关,尤其是戏台形制的演变,一般认为主要与元杂剧的繁荣密切相关,元杂剧艺术原本脱胎于宋金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等说唱技艺,但它最终却得以从歌舞百戏中独立出来,至元代时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表演场地从露台向戏台的转变,并且由四面观转向三面观,最后定型于一面观,这个演变过程的原因一是元杂剧的成型,二是由于戏台由敬神逐渐发展为娱神与娱人并重。本文在大的历史脉络上同意这样的判断,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戏台所处的神庙,山西在由宋入元之后,其功能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在异族统治者的眼里都发生了变化,而戏台形制的演变的原因如果纯从形式分析入手的话,很容易产生类似于“形式自律”的错觉,而功能主义的解释也会让我们看不到山西在蒙元治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与人的观念对戏台形制变化同样是有影响的。
考虑到金元戏台遗存的稀有性,通过按年代排列起来的形制演变的序列来观察戏台的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有必要的,对由形式分析得出来的戏台形制变化的大趋势的判断,应当也是可以接受的。本文试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做一些细致的观察与历史研究,试图由此能发现戏台演变背后的另外一些原因。
从金代后期开始直至元朝,形制上更为固定统一的戏台与正殿之间的距离则明显拉大,为台下容纳更多观众提供了条件。原先只能在四面或侧面“陪同”神灵进行观看的普通百姓,如今被纳入了与神灵同向的视野之中,甚至能够在神灵前方进行观看。我们在元后之世可以看到更清楚的是,这种以“酬神”为口号的献戏逐步向“娱人”目的转变,发展到明末时期甚至出现了为观众中的妇女儿童提供了特别的坐席的“看楼”,使得观演空间进一步纵向延展,更多人得以参与到这项集体活动中来。元代由此戏台实现了从大三面向小三面、最终过渡到一面观戏的镜框式舞台的转变。王曲村东岳戏台仍然保持着三面观戏的格局,但到了东羊村戏台则已经发展为一面观,使得舞台的音响和观看环境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这样一种演进过程,有一种实用主义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演出艺术或戏剧作为神灵的供品这一本质又不能轻易改变。就是说,演出在一个长时期中还必须面对神灵。为了照顾神灵、观众的双重需要……神灵与观众一前一后,都能够从正面观赏演出,各得其所。
本文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需要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戏台作为神庙的一部分,神庙又作为地方信仰的礼拜场所,并不纯粹是一种当地村民自发的行为,从许多神庙的碑文就可以看出神庙的修建都是由地方政府与乡贤组织的,我们不难看出它与许多世侯在其领地实行地方自治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这其中其实是有政治需要的,因为神祇崇拜与祭祀本身就与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东岳崇拜为例,东岳大帝泰山神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庙祀制度,是官方祀典的重要神灵。在忽必烈夺取政权后,也并未废黜此例,东岳崇拜在有元一代得到了延续。但是,根据历代方志碑文的记载,元代时期官方并不直接致祭东岳行祠,而是由民间组织代行。而在此过程中,最能表现庶民参与热情的便是演戏献神这一环节。在山西现存的十余座金元戏台中,有三座都位于东岳庙内,前述的两座位于临汾市内的元代戏台。由此可见,元廷并不关心这类承汉而来的国家祭典,所以并不直接参与,因为蒙元统治阶层的礼乐制度是以蒙古本俗为主,后来渐杂金夏,再参以宋制,而形成的一种胡汉杂糅的体制,所以事实上元廷甚至无意去了解这类承宋而来的地方神。即便是经元廷敕封的地方神祭祀,从相关的碑文来看,蒙元统治者之所以敕封这类地方神,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类民间信仰与崇拜有劝农之用而已。而山西有元一代的地方信仰从宋以来的贤人崇拜向保农防旱的水神崇拜的转变,恰恰与元廷重农之风是相互呼应的,我们在元代山西神庙的碑文中也能看到对祈雨兴农的强调已经超过了对前进、对圣贤的信仰。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神崇拜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就在于,此时山西地区的国家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地方权柄主要由汉族世侯所把持,宗族观念与宗族势力此时也开始萌芽,国家信仰事实上已经让位于地方信仰,祭祀中传统礼制的重要性才因而会逐渐被实用主义的考量所取代,而此时的戏台由中庭向正对正殿的山门转移,并由三面观逐渐转变为一面观,由“酬神”转向“娱人”,可以说是对传统祭祀礼制的突破,而地方祭祀取代国家祭祀,这正如孔子批评季氏僭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样,其实都是由于汉人世侯领地自治度高、地方势力变强后取代国家权力的结果,这一点也许我们从现存元代戏台大部分都采用藻井与斗拱的事实中能看得清楚。
众所周知,藻井在古代建筑中是等级较高的规制,一般并不用于宫廷楼阁和大型庙宇之外的建筑。元代以前的宋金戏台也很少见到斗八藻井的梁架,而是用两层枋木组成方框、多为平置的梁荷载结构。这是因为封建礼法在对建筑等级作出的相应限制中曾有规定,外表繁复隆重的藻井建筑只能用于体现皇权与神权的威严——“王宫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稽古定制·唐制》)。而入元以来,如前撰述,这些以“礼乐”为名的戏台逐渐突破了传统礼法的束缚,在梁架上与斗拱相结合,形成了构思奇巧而又隆重规整的藻井。车文明教授曾在《金元戏台研究回顾》中描述,这些元代神庙戏台的梁架大多“为四角施抹角梁承大角梁,梁上设斗拱,与补间铺作后尾共同承起直角梁(井口枋),组成第二层框架。井口枋上再施斗拱(四铺作或五铺作)一圈托起第三层框架,架上再施斗拱承由戗或挑杆,层层收缩至顶,中设雷公柱,组成雄壮瑰丽的大藻井”。元代戏台上普遍施用的藻井结构,正如一般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有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并使整体构造更具有立体性与整体性,层层叠进的造型不仅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而且其呈半圆的形状加强了对声音的聚拢效果,在加强音响的同时还改善了演员的表演体验,因为穹顶圆心对声音的散射为其在耳际高度起到了一定的排除干扰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某种实用主义对礼制的“僭越”。需要稍做辨析的是,神庙按理亦属礼制建筑与高级建筑,但对于这种地方神崇拜的“淫祀”而言,“僭越”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甚至可以在戏台藻井与斗拱由元入明,直至清代,反而是在雕饰上变得更为华丽精美这一点,看到这两种建筑部件在礼制上的重要性。因为明清时期藻井与斗拱精雕细琢的技艺其实是宫廷意识到戏曲艺术及其在宗教祭祀中的地位而借势戏台魅力,礼教势力卷土重来的结果。明清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它对普罗大众所具有的深刻影响,是以将这种世俗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新的手段纳入到了“神道设教”的体系中,而戏台外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据晋城市周村大庙明隆庆四年重修庙碑记载,“至演乐之楼,尤念侑神之重,补茸添绘,则使金碧与舞衣相争辉”。所以与雕画精美而以修饰性过分艳丽、充满宫廷色彩的明清戏台装饰相比,以雄浑古朴而著称的元代戏台,其风格仍然不难辨认。
行文至此,本文想指出的是,金元戏台由于其本身就涉及祭祀背后隐含政治正统性的观念,它们由“圣”到“俗”的风格变化,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形式自律”或者实用主义考量的结果,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少数民族政权之下的汉文化重镇山西,尤其是晋东南,国家权力的真空与汉人地方宗族势力的兴起,会对涉及礼制的公共空间与建筑产生戏台作为神庙的一部分,因而神庙戏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娱乐空间或者普通的“公共场所”,而是一个集宗教、政治、文化于一体的“神圣空间”——既用于敬神,也是地方宗族团结乡里的一个场域,其背后的政治与文化以及地方信仰观念的相互作用,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风格演变的动力,而戏台形制的这种“圣俗之变”因而也便成为了国家与地方势力博弈的一个表征。
注释:
[1]延保全.宋金元时期北方农村神庙剧场的演进[J].文艺研究.2011(5):89-100.
[2]麻国钧.中国古典戏剧流变与形态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68-270.
[3]这一点涉及金元戏台与山西世侯领地的地方社会的关系,笔者拟另文详述,这里不具体展开。
[4]赵世瑜.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J].社会科学.2011(2):162-171.
[5]王霞蔚.金元以降山西中东部地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D].天津:南开大学.2010.
[6]车文明.金元戏台研究回顾[J].戏曲研究.2002(2):113-123.
[7]王季卿.中国传统戏场声学问题初探[J].声学技术.2002(C1):74-80.
[8]段建宏.戏台与社会——明清山西戏台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3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