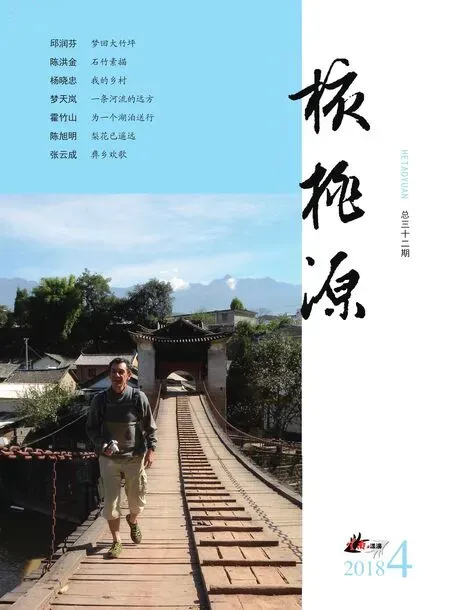梦回大竹坪
邱润芬
一
当大竹坪的石头房子映入眼帘的时候,我想起我曾来过这里,在恍若隔世的梦里来过。梦境中我闯进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庄园,庄园的外墙全是用浑圆、光滑的石头垒砌的。深红色柱子,黑灰色瓦砾,雕花的阁楼,好多间这样的石头房子构成三四个建筑群落,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府邸,又或是某个奴隶主的庄园,处处透着古朴而又华丽的气息。主体建筑群外,零星散落着几座小房子,大概是雇佣工人暂居的地方。庄园的后山,山势较陡。我刚想进入庄园仔细参观,就被一群恶狗的狂吠惊出了梦境。
再看眼前的地势和人工垒砌的石头长城,与梦境如此神似。梦境中那座古老的石头庄园似乎就在你眼前演化成了一块块散落的石头。那间小小的石头房子,就停靠在庄园外的空地上。庄园主体建筑的旧址上,生长着几棵老冬瓜树,躬身向着大地,似在垂询岁月深处的变迁。说不定,我还是那石头庄园内的小主,几经转世轮回到了故居,才会感觉到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那些山坡、石头墙、黄板房,都在我断断续续的梦痕里。围墙是石头砌的,住房是石头砌的,菜地是石头砌的,搁置蜂桶的平台也是用石头砌的。那么多的石头在金黄的大地上延伸,依山而垒,随地而筑,在日晒雨淋中成了碳黑色,以纯自然的元素构成了一座石头城。置身其中,我恍若走进了亘古的岁月,看造艺非凡的老者正在挥笔绘制辽阔的写意山水画。青山绿意绵延,大地宁静深远。那一块块散落的石头仿佛是无意间滴落的墨滴,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石头长墙,是作者浓墨勾勒的一笔。那一道金黄色的竹篱笆,是出入石头城的玄关。游人穿过篱笆走进城堡,就好像穿越到了前世,抑或是突围了国之疆域,到了遥远的古英国。
偌大的庄园中,常住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阿伯。老阿伯用了六年多的时间,两千多个日夜,就用那一块块石头,将高低起伏的百余亩山地,围成了一座石头城堡。一个人,徒手垒建一座城,如此浩大的工程,得需要多么坚韧的毅力!城堡中到处有阿伯为保护小树苗而编制的竹笼。竹笼编制在树苗周围的木桩上,可以随着长高的树苗不断升高。笼子没有顶,笼中的树苗不会受到外界的侵袭,既能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很好地接收阳光雨露的洗礼。有的竹笼已经发黑,有的还是鲜亮的金黄色,有的黄中带黑,像一团团摄录定格的龙卷风。七八只大红公鸡和八九只大母鸡围着石屋前的竹笼,平和地商讨着家事。远处,慢吞吞地走来两头小黑猪。一切进入城堡中的物事都是那么的相衬与自然,毫无违和之感。
石屋四周的墙面上,有几个长方形的小孔,是阿伯在砌墙时设计的给老母鸡产蛋的窝,一只黑母鸡正一动不动地趴在窝里孵蛋,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石屋周围散发出阵阵炊烟。老阿伯端来了刚取出的蜂蜜,在金黄的蜂房中红得发亮。阿伯说,这是花蜜,是蜂儿采撷周围这些野坝蒿、映山红花的花蜜酿制的。的确,还未吃到蜂蜜,就先闻到了一阵扑面而来的花香。我夹了一块蜂房,入口,咀嚼,香甜的蜜汁中还有柔滑的花粉。为谁辛苦为谁甜,小小的蜜蜂,不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还是能工巧匠,是伟大的创造者。
下午,一群野猪拱开篱笆门,慢悠悠地摇到了石屋前,大大小小十余只。它们是阿伯的黑母猪与山里的老野猪的后代。有黑的,红的,嘴长牙尖,红色的背毛间还有几条黄色的条纹。它们自己上山找食,在枯冷的冬季里消瘦得骨突毛长,一副野性的模样。见到人却不躲不闪,不慌不乱,也没有要讨要食物的意思,就那么淡定的看你两眼,兀自趴在石屋前休憩了。一只老母猪带着七八只刚出生的小猪仔,在渗水的草地上拱食。老母猪拱得很快,很专注,丝毫不受我的近距离拍摄所干扰,也未因为护仔而向我示威。那些小野猪比寻常刚出生的家猪仔还要小,在奶水的滋养中闪亮着油润光滑的小身板。它们时而蹿到母猪身边咂几口奶水,时而三两成群地扎进草丛中卧眠,还时不时地嘟嘟小嘴,可爱极了。
圆木制的蜂桶到处都是,有的放在石台上,有的搁在石墙上,还有的架在水冬瓜树上。蜜蜂进进出出,似乎无暇顾及突然莅临的人们。我拣了个蜂桶,大胆地靠在了暖和的蜂巢外边,听里面的嗡嗡细语,吮吸着花蜜的香味儿。一向顾家的蜜蜂竟然也未出巢向我发动攻击。平缓的草甸上,放养着一群小黄牛,有的在埋头吃草,有的在蜷腿休憩,偶尔甩一甩那条大长的尾巴。
阿伯用了那么多的石头垒建石头城,地上仍散落着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石块。这么多的石头宝贝从哪而来呢?是地壳运动,陆地板块挤压,将这原本的大海或是湖泊变成了高山?还是河道原本是从这地经过的,在万千年的迁移中改了道?
大竹坪,这是我在梦里到过的地方。我又回到了深深的梦境里。
二
当看到一棵野生茶花盛开的时候,我飞奔至花树下,全景、微距,顺光、逆光,变换着角度和模式拍了一张又一张。我要把它们装进我的梦囊,在某个云淡风轻的夜晚再打开,用它抚慰疲惫的身心。当漫山都盛开着山茶花的时候,我开始后悔,后悔不该带相机上山,以至于让自己无暇细细端详每一朵花瓣的纹路,每一棵老树的姿态,而成了一个匆匆赶路的过客,我远远落在巡山队伍的后边,东抓一张,西拍一树,循着那即将消失的最后一个背影,追向下一片树林。回看镜头里的那些碎片,微距没有明显的主题特写,全景依然只是一个微镜头,没有一张能够吻合视线里的风物。风景永远是画外最美,岂是一个镜头能够装下的呢?我只能在那些细碎的镜头里,依稀记录那些老树的姿态和野生山茶花的韵致。
像每一片西坡丛林一样,大竹坪的树依然是自然生长的。有千年古树,也有刚出土的幼苗。茶花树、大栗树、香樟树,还有很多熟悉的树种,我甚至可以看一眼便知它枝叶的味道,却不知道它们的树名。它们每一棵都以自己喜欢的姿态生长着。那些挺拔刚劲的大树,单看它那直冲云霄的枝叶和长满青苔的糙皮,就可以感受到它在岁月轮回里的千年值守。无论是需要几个人才能合围的粗壮枝干,还是每一根虬枝的儒雅,都让你忍不住心生赞叹。走进那些空心的树干,偎依在挺拔坚韧的大树的怀抱中,脚底会生发一股暖流,被坚韧的力量包裹着,你完全可以放心地睡上一觉。一些藤本植物攀附在大树上,缠绕成了一把天然的藤椅,还狡黠地伪装成了树的枝干。云里雾里,很难辨别本真所在。还有一些树根紧紧地包裹着石头,好像捂着的是一颗跳动的心脏,石头与树早已融为一体。
树下,峭楞楞的石头随处都是,它们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风骨,随便一块石头上都能容得下五六个、七八个,甚至一二十个人站立,像古树一般巍然挺立。父亲从小生活在大竹坪,他说这是他们小时候放羊的地方,那时候的丛林比现在还要茂密,经常还有黑熊出没。如今,年近七旬的他爬到了石头上,变换各种造型让我给他拍照,花白的胡须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多少童年的美好记忆在他的笑容里回放。与古树,与山石相比,他其实是年轻的。坐在古道边,树荫下,那一块块铺满青苔的石头上,听鸟鸣,嗅花香,任由微风拂过脸颊。此番,岁月静好。
横卧在石头与树干间的,是那些露宿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残枝朽木。发灰、斑驳、腐朽,却依旧以一棵树的姿态支撑着来往的松鼠、山羊或行人。它们不知在地上历经了多少日晒雨淋,抠开腐朽的表皮,露出的依旧是上好的木质。要是拿到善于雕刻的剑川木匠手中,不知该有多少件价值连城的木雕作品。当然,这些腐木应当只属于这里,腐化也好,烧柴也罢,这是它的宿命,也是它终其一生也无法释怀的情结。
最惹眼的就是那树荫下,石头边的茶花树。它在油绿的叶堆里开得那么耀眼,那么欢畅。想仰望么?可以。躺在那块铺满青苔、铺满落叶的石头上,又或是那根浑圆热乎的木杆上都行。想近观么?也行。粉白、粉红、玫红,站着、坐着、躺着,都可以细细端详每一棵山茶的风姿,每一朵茶花的异样。
不同于人工培育的茶花,只能以各种奇异的花朵吸引眼球。大竹坪的野生山茶花,总可以满足你很多关于茶花的向往。园林的设计大都模仿自然,但终究不是自然的,园林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而大自然的创造是无穷的,它不会创造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地方,这就总能给人新鲜感,总是充满吸引力,总能满足人的好奇心。这些茶花在布满苍苔的石缝中更加鲜艳,在幽深的丛林中更加绚丽。说是来看茶花,其实看到的又岂止是茶花呢?
清风徐徐而来,空气中溢满八爪金龙那如桂、如兰的清香。大自然把娇艳的花朵给了山茶,把浓郁的香气给了八爪金龙。它们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同一时间开花。八爪金龙那龙爪般细碎而紧凑的白色花蕊,藏在了墨绿色的枝叶间,不仔细搜寻辨别,你还会错以为那一缕浓淡相宜的香味儿是来自于山茶花呢。
还有些香味儿来自于野桂花,与古茶花树大小相当,却不与八爪金龙争功。它的花期在后,与映山红开放的时间大致相同,却也不与映山红争艳,兀自藏在静谧的山林里释放着花香,又在雨后,洒落一地细碎的金黄。树干上的“青蛙皮”“树花菜”,还有即将生长出的蘑菇,采回家都是山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
来吧!亲爱的。让我们一同在这大山深处,老树周围,在香远益清的微风里,享一场视觉盛宴!
三
转回石头城,大家都已汗流浃背。阿伯家的忠哥说再带我们去看看大竹坪里面的水,老人家们留在原地休息,我们就跟着忠哥去了。穿过石头城堡向里山走,经过一片平缓的草地。一棵映山红正值盛花期,大红的花朵在金黄的草地上分外惹眼。林边,几棵山茶花与映山红相互映衬着。一棵映山红的花是玫红色的,兴许是哪位上古画神途经时,在映山红那红艳的颜料中添了点蓝,晕了点白,让它开出了别样的韵致,又或许是为了区分什么而作的特别的标记。忠哥指着那棵花树说,待会儿我们可以从这里爬上来,但下边的峭壁太陡,上来容易下去难,只能先绕行。
之前未曾听闻大竹坪的水有什么奇特的,至于西坡的溪流,无疑都是清澈见底的,所以就算只是看看寻常的溪流,也能让人心情舒畅,何乐而不为呢?果真,就在眉眼触及溪水的那一刻,那股似水的柔情便也流进了心底,瞬间激发出了轻快的元素,让我那原本套着雪地靴,裹着毛呢大衣的笨拙的躯壳也开始变得轻快起来,灵活地腾跃在溪流间,就连呼吸都饱含惬意。
我们沿着大竹坪林边的溪涧向上穿行。猝不及防间便遇到了瀑布。它从斜卧着的石头上滚过,又随机地打了几个弯拐,恰如睡美人背后飘逸的长发, 自然,柔顺,润滑,然后悄无声息地藏进平躺的河流里。像顽皮的孩子熟睡后变得乖巧起来,看不到半点逐波破浪的痕迹。一滴水,能穿石,一段流水,摩挲石块,形成绮丽的风景。柔的何止是水,韧的又岂止是石呢?
惊叹过后,才想起带了相机,却不知如何把水拍成纱状。路遇独行的驴友,向她请教,却因相机型号不同而无果。好在如今信息网络全覆盖,大山深处也有手机信号。我立马向世伟老师打电话请教,在他的指引下放慢了快门速度。那些瀑布的水花便在镜头里变成了一道白纱。你还可以轻轻地走到瀑布的任何一个地方,任由那一道柔美的白纱从你身后滑落,从你指尖穿过。
在苍山西坡,有许多这样尚未开发的景点。这些形态万千的瀑布,在当地只有一个朴素而统一的名字“飙水岩”。因为初见,我想给它安个名字,却一时墨空,不敢贸然定下。如果没有更多的追寻,在这样寂静的空山里,我会把脚步停在这绵软的柔情里,枕着被阳光温热的石头,吸着从瀑水中飞出的凉丝,在此起彼落的飞鸟声中,做一个微醺的梦。
然而,贪婪的心还是在大姐的呼唤声中起离。她们说上边还有更美的风景。于是,我们继续沿溪行。晴朗的冬日,杂草倒伏,蛇类冬眠,在山涧中畅行,也不用担心爆发山洪,内心有了份安全感,便可分散更多的注意力收揽山间的景色。比如那些垂挂的藤条,路边的野花,水中的落叶,以及朗照的晴空。当然,时刻吸引着目光的,还是那条静静流淌的河流,那些布满苍苔的石头以及沧桑的古树。
抬头,转身,左前方又一道瀑布撞进了胸怀。像是雨后的流云,又像是一片硕大的芭蕉叶,它从凸凹不平又满是青苔的岩石槽中簌簌落下。洞天水银地,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明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却虚掩门扉不示人。金庸笔下的小龙女或许就住在这水帘后,齐天大圣的花果山水帘洞就是这个样的吧?此刻,着一身古装,是不是也可以与令狐师兄在白纱般的瀑流中上下游走,尽情舞剑呢?右前方,一条小溪流蜿蜒而至,见到这么美的瀑布,一不小心从石缝中跌落,溅起一阵水花,迫不及待地汇进了瀑流中。
眼前的景象恍若梦境,我生怕梦醒了,就忘了。于是放大了瞳孔,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把倾泻的瀑流、翠绿的青苔、五彩斑斓的石头以及溪边的丛林一同刻在了脑海,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右转,向上十来米,又一道瀑布跌入眼中。它从高处的岩石冲出,束状落下,溅出了一个聚宝盆,又从聚宝盆边缓缓流淌。再流下,并入了下一道瀑流。要是穿一双防滑鞋,或者在聚宝盆中铺上一块防滑地毯,那么这一束清冽的泉水,也会为你洗尽铅尘。坐在这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听着流水跌落幽潭,再叮叮咚咚绕过脚边,带着你忧伤的往事远去,或者揉碎在另一个深潭中。抬头,看枫叶如花,如梦初醒,推开另一扇心门。时光如水,每个人都会在波折坎坷中成长,又将在岁月中老去。
同是出自大自然的手笔,此地与金盏河的三叠水神似,三山之间,两溪汇聚之地。如举行某种皈依的仪式一般,先呈现两道瀑布展示各自的神韵再融为一体,庄重得体,天然无琢。若要归隐,择这一静地“夜阑卧听”,定会勾起许多家国情怀。
折返,我们凭借树根的牵引,从一面只容半只脚掌站立的峭壁上,手脚并用地爬回了大竹坪边的花树下,像是经历了一场梦游。如此奇异的风景,竟不为外人所知,得以窥见的我们,当真是幸运的。据说上游还有瀑布群,下游也还有,这一次我没能一一亲临观赏。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还会再来,延续这一场未了的梦境。
四
再回大竹坪,已是阳春三月。地上开始长出了新鲜的草芽。干老暗红的蕨科丛中冒出了成片的新鲜蕨苔,向一只只攥紧的小拳头。它们有的会被人采撷,过水,成为瓜菜,龙爪菜;有的会伸开,长大,成为牲畜的暖窝;有的可能一抬头就进了小猪嘴,只好来年再会。山间的茶花与周围的映山红一同谢幕,洒落了一地花瓣,老树顶上,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嫩叶。
我不再一一向每一片丛林,每一棵老树,每一个石头,每一片花蕊注目行礼。我只是微笑着,轻声应和着。是的,我回来了。同行的大多是摄友,一路行走一路拍摄。专注于拍摄的游人,也是艺术建构的一部分,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我参演了向导的角色,把大家带向丛林深处。为便于区分,我姑且把那三道瀑布依次唤作 “滑石瀑”“一帘幽梦”和“碧幽潭”。后人若是认同,兴许会在某块碑帖上注明:“二零一八,戊戌年间,草民××到此一游,见景生情,心生感慨,固将此地唤作‘碧幽潭’”之类的。不过,这次石头城的老阿伯特别申明,最上面这两道瀑布最早是他发现的,上边还有个水潭,名字他都想好了,叫“仙女洗澡潭”“姊妹瀑布”,大的是姐姐,小的是妹妹。形象贴切,还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意味,遂依他老人家。至于第一道瀑布嘛,在老人家心里,还算不上景点,暂且还叫“滑石瀑”吧。
汇集了两条溪流,对比三道瀑布,滑石瀑的水是最大的。它上下两端各有一个存水的潭口,像一对眼眸。那一段激流,是眉眼间流转的电波。俯瞰,即可与底端的潭水对眼,感受那回眸一笑中的情意。潭水皆浅,石沙显得真切。由于拍照过于专注,纷纷有人落水,幸而只是湿鞋。因为是踩点,行程较紧,我们来不及等待恰当的光影,也未细细择选最佳拍摄角度便转移阵地了。回看照片,最美的风景依然不在我的镜头中。相比之下,那些抓拍摄影师的拍摄动作镜头更有意味。
陪同的向导芳姐和阿艳穿着民族服装,被我们强拉着担任兼职模特。她们虽然是当地人,但是未到过姊妹瀑布。为躲避不明刺茬对我长裙的纠缠,找寻上一次来过的记忆碎片中的小路,我未再收录水花的倩影,而是转任向导一职。在每一次队员询问:“快到了吗?还远不远?”的时候,肯定地说:“快了!快了!就在前面,不远。”然后带着大家走过那一段段长满青苔的河道,一步步走近仙女洗澡潭、姊妹瀑布。其实上次踩着大侄子的脚印跑得太快,我没仔细看清路线,更没注意走了多长时间。有时候我还会在心里嘀咕会不会走错了路,或者像《桃花源记》那般找不到入口。但作为向导,不能把心中的疑虑带给大家,只能不断探路,预测距离。美丽的风景终归是在现实中存在的,终于到了姊妹瀑布跟前,大家一阵欢呼雀跃,然后便是一阵狂拍。
这次的阳光尚未移到瀑布之上,少了些阴阳水的拍摄困扰。只是我虽然带了相机脚架却未使用。我依旧放慢了快门,随意收取了几个镜头。镜头里,深绿的岩石槽下,瀑布的流纱遮隐着打坐的高僧,高僧头上约三米,横游过一条橘黄色的金鱼,鱼尾显露,鱼头刚入暗影。这应当是姊妹瀑布中的“姐姐”吧。来到瀑布前,清凉的气流穿过发丝。衣袂飘飘,附和着瀑布飘落的节奏。左面的峭壁,深一窝,浅一埂,给人想要一攀而上的冲动。那上面一定有异样的风景和视角,但面对陡峭的石壁和两手空空的攀岩装备,为了安全,忍住好奇心也是必须的。
碧幽潭,是我们上次到的第三道瀑布。之所以称作“碧幽潭”,是因为瀑布两面的山势较高,树木茂密,如饺子一般将瀑布包在了树林之中,很少有阳光照射。瀑布溅出的石潭碧绿清澈,故以此作名区分。不过,依照老阿伯的说法,应当是姊妹瀑布中的“妹妹”,被我当做了聚宝盆。不过,真有仙女的话,大概也在这聚宝盆中冲过凉吧。瀑布左上方,一棵五角枫发出了新叶。瀑布,枫叶,加上秋水伊人,又将演绎怎样唯美的画面呢?
上次忠哥带我们到这就折返了。周围似乎也没了路。侄女阿艳说,海哥说过从这有条路可上到傈僳岩,傈僳岩附近的映山红开得正好。看到瀑布左面的石岩不算太陡,还有树木相连,我试着空身爬了上去。每上一步都想好了能不能返回,回来时又该怎样走。我可不想让一群人看着我上下为难而束手无策。到了与瀑布顶端同样高的地方,隐约见一条小路穿进了丛林,那大约就是海哥说的出路了。沿着树根还可以下到瀑布的顶上,那地儿还算平坦。
我小心地爬到瀑布顶上,再仔细看了看上方的山势。旱季的泥土虽然有些松软,但不会湿滑,还有能够支撑行人通过的树木。来的都是山里人,都穿着运动鞋,背包也不算庞大,应该能够上去。衡量确定之后才呼叫下面的同伴们说找到了路,并且迅速返身背上了行囊,指明了行走路线,与大家一道开始小心谨慎地向上攀爬。一边攀爬一边互相嘱咐踩哪,拉哪,哪个地方会挂住背包,哪个石头是松动的。大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脚边,不敢往下望。
五
借着断后的便利,我又一次来到了的瀑布的顶端。上方流水从石岩的缝隙中流出,在一个平缓的小水潭打了个转,才转进光滑的石槽落进下面的碧幽潭中。苍苔布满瀑布边的岩石,在阳光中苍翠柔软。瀑布顶端的岩石成横断层状,像是两堆紧挨着的横向累放的木条化石,中间还有个小窝可容一人。流水左面有一段岩石呈炭灰色的蜂窝状,不知又是何种成分。能够与险要的瀑布这么亲近,甚至可以触摸到瀑布之顶,这真是一种征服世界的体验。不过,也只有在枯水季节才敢这么肆无忌惮,要不,柔滑的青苔虽美,却也是温柔的陷阱,可远观而不可踩踏也。
还没看够呢,大家却不见了踪迹,我只好也钻回了林子。向上十米,面前有一小段长满苔藓的岩石。右下方,流水经过石壁刷出了一条深浅不一、坎坷波折的水道,眼前除了几根藤蔓别无遮拦。站在高悬的岩石上,看脚下深涧里的涓涓细流,惊喜过后又有些脚底酸软。在丛林里落单也不是什么好事,我小心地收好了相机,循着急切地呼声,开始沿着落叶中的足迹追赶同伴。
灌木丛里,堆积的落叶腐化,新的叶片又不断添覆,风干,踩着松软,脆响。茂密的树林掩盖了山坡的险峻。同时,也成了强有力的登山助手。要么抓着树根向上攀登,要么搂着树干左右跨越,只要有树木接应的地方,就一定能够过去像是在梦里飞行。当然,现实可不是梦境,你得先分辨是不是枯枝,够不够牢固,以及你身处的地势、环境,预测将会面临的危险因素。在丛林里行走,你可以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偶尔有雨滴穿过密实的丛林,落在手背上。我们一直向上行走,就像在迷途中摸索,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将要通向何方,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火树繁花,只是坚信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总会走到山的那一边。
西坡是有熊出没的,黑狗熊,抓羊、伤牛,狭路相逢也伤人。遇到老野猪也算够呛,特别是护仔的时候。蛇类出现的频率高,也骇人,只是你不动它,它也很少发动攻击。至于说山鸡、野兔、岩羊和麂子之类的,一般情况下倒没什么威胁。咱们这群文弱书生,赤手空拳的,行走在密林深处,是必须提高警惕的。
终于,出现了几团牛粪。牛都能到的地方定是人迹所致。果然,芳姐说这地儿她捡蘑菇时曾经来过,知道该怎么走了。为赶时间,我们抄了条去傈僳岩的近道。傈僳岩,是一座天然的石头“房子”,或者说是不规则的岩洞。可供七八个人避雨。刀耕火种的时代,曾有人在里面居住打猎。现在说不定已经成为了蛇居。不过,雨越下越大,能不能到达还是未知数呢。出门之前忘了关注天气预报,没带雨具,好在丛林幽深,树叶茂密,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
到了人烟所及的地方,心中的戒备也解除了不少,突然觉得,行走于此,是多么愉悦,我似乎又进入了一场梦境。那些树木都是独特的,每一截树枝,每一束“胡须”,甚至是一片落叶,都值得细细端详。小七抱了块树皮,说要带回家珍藏。抱着抱着,却不知在哪次拍摄时遗落了。远方,一棵棵大红花树如火炬手般在草甸中奔走传递,点红了整座山头,适用于全景或航拍。过段时间白色杜鹃开放的时候,又会是满山泛白,白中还会带粉。眼前,林暗花明,古木撑天,虬枝交错,当用3D相机送你身临其境。那一棵棵跻身在老树身前的红杜鹃、白杜鹃、粉杜鹃傲放枝头,随着微风轻轻摇曳,这般姿态若录制为视频,后期还可以再加上幻化为人形的特效。
每一个走进丛林的人也都是灵动的风景。你对大自然的触摸,对生命体的呵护,和一块石头相依,与一朵花的对视,都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我其实并没有打开镜头,只是任凭肉眼的检索与想象交织为最喜欢的画卷。要是没有足够的摄录装备,何不如用脚步丈量,用感官记录,把最美的风景收藏于最纯粹的记忆中。心若在风景就在,时光悬浮其上,成为记忆。
我轻轻地走过了那条铺满落叶的小径,走进了另一个清凉的梦境,在梦里穿过丛林,掠过树梢,凝视花蕊,抚摸大地,在淡然的岁月里,静静地守护着这一方净土。
六
“到了!快看!花林到了。”艳儿的呼声拉回了我的神智。几棵花树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丛林边。“到了!到了!”大家一边传达着这消息,一边冲出丛林。林边,两棵大红花树相拥相抱,像两位头顶花冠,搭肩拉背的千手观音。“花王,这就是花王。”老杨同志说。阿艳笑了,她说:“花王还在上面呢。”
出了丛林,视线变得开阔了起来。映山红花树一棵接着一棵,一片连着一片。其间穿插着几棵水冬瓜树,刚发出翠绿的新叶。我们开始追拍花树,流连不前。雨却更大了,迅速地打湿了帽檐。未加防雨措施的镜头也开始变得模糊。到场的风景却未能入镜,我们悻悻地躲到了花树下避雨。
看着大家一脸的遗憾,天空暂时扎起了雨袋,现出了一丝阳光。“走!看花王去!”我们趁机冲上山坡。一棵映山红如小山一般出现在了眼前。花王,这就是这儿的“花王”。它高过了三层楼房,枝繁叶茂,占地比一块篮球场还大,扎在斜坡之上,满树红花分外惹眼。从四周都能观赏花王,除上端两棵水冬瓜树外镜头内别无遮拦。我们打开镜头,正准备狂拍,豆大的雨滴却又落了下来。雨水浸湿镜头的顾虑哪及花王的魅力,我们冒雨拍摄着烟雨中的西坡。最终还是被赶回到花王下避雨。
花王把我们拥入怀中,我们把花王揽进心海,七个人,只占用了树下的一角。再来二三十个人也没问题。其他地方的有些花树虽然也大,但地势险要,不容亲近,也不可能让你这么清晰地看到花树的每一个枝干,每一簇花蕊。有花王庇护,雨水很少落在身上,地面都是干的。我们就站在花树下,看着偌大的花帐和透过花窗的远景。雨雾迷蒙,山林浓绿,那淡黄的草坡中的点点黑土,还有远处的花树都是虚化的背景,焦点在眼前的树干,花朵,还有落红之上。
视线移开花王,每一棵花树都有各自的风骨,幼小的,硕大的,健壮的,瘦削的,繁茂的,沧桑的,他们各得其所,又相得益彰,相互陪伴,繁衍生息。与富恒石竹或者安南的杜鹃相比,这儿的花树更高,更大,更为密集。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棵完全相同的树木。都是映山红,都长在从苍山西坡,都在春天里绽放,却不在同一时间开放。而是以海拔区分,大概以一百米为一个区分段,从低到高逐一而开。苍山西坡,同样的海拔在同一时间横扫千里,都是相似的色彩。
花王对面,有个叫“金月亮”的地方,传说在很久以前,石壁上镶嵌着一个金月亮,照着上邑村某户人家的水井。有个外国人到井边打水时看见了金月亮,上山取走了金月亮。如今还能看到曾经镶过月亮的地方。据父亲说,金月亮那还有个天然的石盆,盆里有两条活灵活现的石鱼,石盆的上方垂悬着一道石岩,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他曾经想把手伸进石盆里摸摸石鱼。却总感觉上边的石岩就要落下而不敢伸手。年迈的老人家总是念叨着,啥时候要再去看看那两条石鱼,我们也好奇地附和着要同去看看。只是,并未听他人提及有这样的地方。就算还在,周围的地形定是险要的,也是罕有人迹的。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也不适合再去冒险了。
芳姐说中梁子的木莲花可漂亮了。不过隔年才开一次花,去年的花开得特别繁茂,今年可就没有福分观赏了。早听说过苍山西坡有野生木莲花,却从未亲眼见过。石头城的阿伯倒是种有两棵,今年也未开花。来年花开时,兴许可以如愿。
雨停了,身后的傈僳岩虽然近在咫尺,但天色已晚,我们还是放弃了探寻。沿着半山腰返回,沿途的映山红一片片,一丛丛,依旧不断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如此博大的西坡,又怎是我们能够寻遍的呢?途中的美景无数,我们却不再一一摄录。世间的风物,又怎能一一记住呢?
转了个圈回到大竹坪后方的山梁上,看着这一棵棵低头俯视着石头庄园的映山红,似是某种守卫又或者是用生命体做的镶饰。林间的茶花虽已落幕,许多生命还在孕育着,令人期许。若在梦中,我一定会在最大的那棵花树上起飞,然后飞过花海,飞过溪涧,飞过草甸,再转身飞回石头城。兴许哪一天,我还会再回来,回来看看山花,看看流水,看看不老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