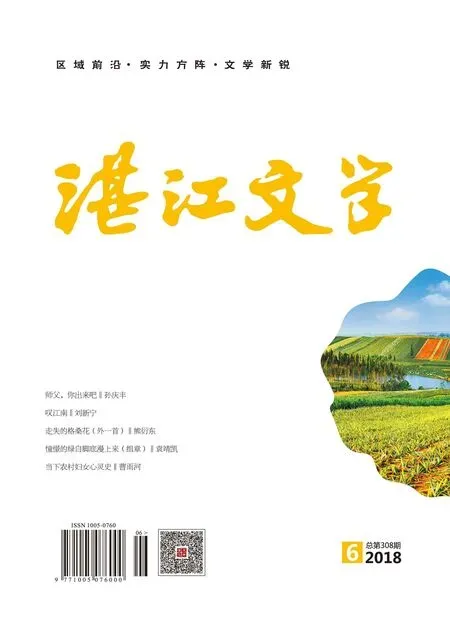当下农村妇女心灵史
——读付秀莹的《陌上》
◎ 曹雨河
一直生活在乡村的我,读《陌上》既陌生又熟悉。陌生于文本里久违的生活图、风景画和月辉般缓缓流动的语言,蕴藉而饱含诗意;熟悉于乡村的那些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邻里关系。人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加入世贸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紧锣密鼓的进程,资本的力量、西方享乐思潮借助新媒体的东风,汹涌澎湃冲荡着农村固有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现代性”观念,潜滋暗长成为涌动的暗流,改变着人们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这就催逼着脑子灵活的人“急转弯”,很快脱贫致富了,老脑筋的人依靠诚实的劳动被甩在富裕的圈子之外。这就形成了农村阶层分化:老板与雇工。在这些显象下面,人们的心灵有怎样的颤动?尤其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心理有怎样的嬗变与坚守?
无奈的身体自援
权力与资本交姘滋生无比强大的力量,“权即贵富必尊”,“笑贫不笑别的”,“有奶就是娘”等观念打开市场;财富处于低凹之地乡村农户,遭受着有形的挤压和无形的鄙视,他们无以自援,尤其是家中的女人,眼看着男人死脑筋指望不上,不得不“开动脑筋”利用身体资源,摆脱低凹处境。芳村的女人中香罗首当其冲,这自然有其家传因素,更有生存环境之迫。香罗是小蜜果(风骚出名的女人)的女儿,可她也不是生来就风骚的,“很小的时候,香罗走在街上,就有不三不四的男人们,拿不三不四的眼光打量她。香罗先是怕,后来呢,略解了人事,是气,再后来,待到长成了大姑娘,便只剩下恨了。恨谁?自然是恨她娘小蜜果。”这儿的独白可以看到她虽出身污泥,有着清白良女的心地,本能地对风骚的远离与怨恨;“姑娘时代的香罗,怎么说,好像一颗干净净水滴滴的小白菜。”她偏偏找了个老实疙瘩丈夫根生,“根生的性子,实在是太软了一些。胆子又小,脑子呢,又钝。”“这些年,村子里一天一个样,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根生呢,却依旧是老样子。眼看着他不温不火的自在劲儿,香罗恨的直咬牙。”男人依靠不上,只有她披甲上阵了,重复了母亲的命运。她与村上最大的老板通了私情,又在城里开了几家洗头店,有了小轿车,门楼也高高竖起来。可她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作为女人不能生养是她天然的缺陷;她虽然致富了,也招惹了村人另一种鄙视的目光,这目光甚至来自最好的姐妹;独处审视内心,良知啮咬着她,她有愧善良憨厚又百依百顺悉心呵护她的丈夫。这就是香罗,由时代大潮挟裹着,纠结着、痛苦着、享乐着、行走着,她的哭笑无常,正是她繁复内心世界的外显。
芳村的女子思想转变能与香罗比肩的要数望日莲了。望日莲的生存处境更不堪,她家无论经济还是精神都处在芳村的最凹地,老实巴交的父母,村上没有谁拿正眼看过;低矮的房屋一下雨就被四周高楼的流水漫灌了。可她从小就要强,刻苦念书,希望通过读书走出芳村走进城市,过上让村人另眼相看的日子,事与愿违,她终究落到与父母同样的境地,成为村办厂子的一名雇工。凭她的家庭背景、雇工的身份,她的家境永无走出凹地之日,出人头地与她永远无缘。村人还真小看了这个未出阁的丫头,她竟然能让票子像雨水似的哗哗往家流;能让村主任给差两岁的父母办了老年补贴,在凹地突兀竖起楼房;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村上头号公子学军(村里头号厂主大全的独生子)竟死去活来地要娶她为妻。她的功夫使在情场上摸爬滚打、历经征战的大全束手无策,眼看着大半生拼打的财富要落到一个丫头片子手里,大全一筹莫展不得已求助香罗,两个老家贼老谋深算才拿下了望日莲这个小家雀,可见她的功夫一斑。此外,她还浑身武装铜盔铁甲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污言秽语和异样目光的暗箭,兵来将挡水来土埋;回到家还承受死脑筋父亲的呵斥。一个柔弱的女子变得如此刚硬,这些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位乡村女孩怎样的心灵蜕变与疼痛呢?作品没有明示(这成就了作品蕴藉的品质、给读者留下开阔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从村
“第一夫人”的梦中感知,由裂变疼痛演化的怨恨(用剪刀除去村主任的生殖器)隐匿于静水流深中。由此可见资本给农村带来的生存挤压,也投射出“现代思潮”的强劲,原有的道德伦理漫漶。
若说香罗、望日莲识时务,意识与时俱进,得意脱贫致富,那么春米就显得被动半推半就了。春米虽只念过小学,可她对文化人心向往之,为此她嫁了既矮又瘦的小学代课老师,因合校并点,丈夫被辞退外出打工,心里五味杂陈。她在家里边带孩子边帮公婆打理在村上开的小饭馆。小饭馆不是随便开的,由村上一把手背后撑腰才能开起来。公婆是一对爱财不知廉耻的人,有意无意地让春米取悦一把手,一把手自然有恃无恐,春米成为他怀中人。其实春米是不情愿的,她心里怜惜老公,再就是她不是图财不顾尊严的人,事后她想起老公的种种温情,厌恶地将一把手碰过的东西清洗一遍,心中的坎儿还过不去,去找好姐妹小鸾排解。她的就范多因公婆作为对一把手报答而默许;再就是春米夫妻长期分离,身体饥渴。当然春米算不得自我意志坚强的人,可一把手毫无征兆、随意将其“弄进小车里”拉走,也昭示了权力的霸道与劫掠性。
低入尘埃的保全
上面说了“底层”女人因经济挤压和开放思潮的影响内心的动荡与嬗变,而那些老板娘、“第一夫人”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芳村“第一夫人”村主任建信的媳妇,荣耀光鲜自然不是一般芳村女子可比。她儿子才几岁,不仅在村里造了出眼的楼房,还在县城、甚至省城都置了房产,这还不算,就是她娘家侄子结婚,大半个村的人都主动凑来帮忙,体面与尊贵就是如此显赫。这些都是显形的,而她的内心有着外人不知晓的伤与痛、怨与恨。建信常在外边沾花惹草,感情跑马,她不仅经受着身体的冷落,还饱受心灵的煎熬,她容忍建信就是容忍建信手里的权力,利用他手里的权力捞体面,捞实惠,帮衬娘家,她内心的怨恨由她的梦中可见一斑,尽管是望日莲教她用剪子除掉建信的生殖器,也正是她潜在心理的反映。
大全在芳村开的厂子最大,资金最雄厚,雄厚到操纵芳村的政权。按说大全媳妇也够风光的,而她实质是生育机器、家庭保姆,甚至比保姆还低贱的伺候着大全,每天想着做大全可口的饭菜,给大全洗脚、揉背;大全之所以没有开了她,是因为他生了儿子完成了传宗接代,大全偶尔喂她一顿也是舍施性的。她在家里没有任何话语权,为了帮娘家救急向大全要钱,她甚至扑到地上,搂着大全的腿苦苦哀求,她哪里还敢过问大全玩女人的事?只是想着不把香的臭的带家来,在外面爱怎样就怎样好了。她也是有肉有心的女人,她时刻期盼着大全回心转意,回到她身边,作为女人她没有任何优势把大全的心拉回来,只得诉求“识破”,求神拜仙寻得心理慰藉。
素台是芳村厂子的老板娘,厂子是她与老公一起打拼出来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厂子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可她依然阻挡不住丈夫与莺莺燕燕们的瓜葛,只不过隐蔽一些罢了。这还是在维稳的前提下,惹翻了,丈夫就不甩乎她了,家庭的小船说翻就翻。她略微限制丈夫的私生活,即使在夜晚,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公整装甩门而去。她为了保住已有的位置,她专职保养美容,购置化妆品,贴面膜、跑美容店;为了拴住男人,甚而偷学了性技巧,连在情场上历经百战的老公都感到吃惊,真是低到尘埃了。
小瑞是芳村女子中的一个异数,她既不属于上层也不属于低层,她是跑皮革生意勇子的媳妇。勇子曾经一度是芳村的一个能人,才娶了她这个人尖子。小瑞本来是一个服服帖帖的好媳妇,小瑞头一回跟着丈夫跑东北,她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鸭子,缩头缩脑的,总躲在丈夫身后。没承想,就是这样一位曾经羞怯的乡村女子,到后来居然一个人到东北跑起了生意,跑生意倒也罢了,关键是,她竟然丢下了勇子,舍弃了芳村这个属于她的家,干脆连过春节都不回来了。小瑞的举动和心灵的蜕变起因何在呢?她弃家不归固然与勇子这几年生意的不景气,外面的精彩生活诱惑有关,更深层原因还是现代思潮对原本伦理的瓦解。我们就小瑞行踪的隐匿消失与精神蜕变,可以感受到时代与社会一种重大转型正在发生。
凄惶的守望
世势之潮催逼世道不古,人心蜕变成为大势所趋,坚守者如逆水行舟,悲壮且凄惶,非有坚如磐石的“心心念念”不可为。翠台和香罗原本是要好的姐妹,还是近门第的妯娌。论哪样翠台都比香罗出色,可日子过得被香罗甩出十万八千里,娶儿媳妇吧,人家都建新楼、买新车,而自家没能力建楼,买车还是借妹妹素台的钱,可人家香罗呢?轿车开着,高高的台阶上杵着小楼,穿金戴银的,跟村上体面人物打得火热。是的,香罗这一切获得的方式翠台打心底瞧不上,瞧不上又怎样呢?儿子结婚了,为了儿子能留在家近前打工、与儿媳相守,还不是包了香罗爱吃的饺子,踮着脚尖巴巴地给人家香罗送去,求人家跟大全说情。翠台心里瞧不起香罗,生活里她又得巴结香罗,实在不甘心,实在委屈,这又能怎样能?也只能在老实巴交的丈夫面前发作,大哭一场。和翠台住对门的是喜针。喜针小毛病不少,嘴碎爱说儿子、媳妇的不是,还斤斤计较(卖瓜),她甚至“亲下不亲上”,讨好儿媳妇给亲家买那么多好吃的,却不舍得给老母亲买,被娘家嫂子骂不孝。她也试图和村上的上层女人拉近乎,总是热脸遭遇冷屁股。她有攀附富人的机会却不利用,厂主团聚(年轻时跟她谈过对象,因家人不同意没能如愿)就多次想靠近她,一次“团聚见她汗淋淋的,有一绺头发贴在额前,虽说是一身干活的衣裳,却仍是结结实实的,饱满劲道,要哪儿有哪儿,心里不由一动,伸手就想帮她把那一绺头发弄一弄,不想被喜针劈手一挡,就把他手打掉了。”“团聚见她这个样儿,身子立马酥了半边儿,也不顾左右有人没人,伸手就要拽她。喜针急得没法儿,也不敢叫,一口咬在他的手腕上,团聚哎呀一声,抬头看时,喜针早骑车走远了。”喜针情愿流汗出力,过自己辛苦穷困的日子,也不放弃做人的尊严、放弃常伦来获取物质上的富足,情愿让别人低看自己,也不自我下贱。
小鸾比翠台喜针要小一辈,按说脑子该活一些,可她也是个死脑筋。丈夫在厂子里打工,一月也就挣那么几个钱,她倒是心灵手巧,在村里开片裁缝铺。可村上都是熟人啊,挣钱的活要做,不挣钱的活也要做,甚至官差也要搭,要给她看不上的女人娘家侄做满月虎头棉鞋,要给素台娘家母做大襟袄,甚至做送老衣,这些都是费工不挣钱的活,她顾不上念小学的儿子学习,昼夜不息地忙活,眼都瞅坏了,苦争苦争的,依然过着苦巴巴的日子。她联络邻里感情,买了礼物去看望邻家病人,却遭遇硬塞给她长绿毛的点心;放下手头的活计,赶着给村主任建信的内侄子帮喜,建新媳妇“老远看见小鸾过来,手里拿着一把菜刀,笑得明晃晃的,赶着叫她婶子。建信媳妇拿下巴颏儿指了指院子里,笑道,人多着哩。也不差你一个半个的。看把你忙的。小鸾脸上就讪讪的。说我哪能不来呀,谁家老娶媳妇?建信媳妇只是笑。小鸾拎着菜刀,急火火就去了。”建信媳妇那“人多着哩”“也不差你一个半个的”话语中,隐含着热辣辣的傲慢与冷冰冰轻慢。其中的潜台词很显然是:“反正我们家办事帮忙的人多着呢,你爱来不来吧。”面对着建信媳妇这一番夹枪带棒充满挑战意味的冷言冷语,“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小鸾,自然毫无还手之力。作家仅只是通过一句“小鸾脸上就讪讪的”,便活画出了小鸾那样一种万般无奈的尴尬神态。眼看着小鸾的讪讪神态,建信媳妇的“只是笑”,所透露出的,也就是一种胜利者的得意情状。所谓的世道人心与人情冷暖,所谓芳村人的精神奥秘,在这看似三言两语的简短对话中,其实有着格外蜿蜒曲折的流露与表现。这就不难理解小鸾曾经的想法了,若自己的男人有本事过上体面的日子,就是他在外面招猫惹狗也愿意!经济的窘迫精神的挤压,她渴望过上体面的日子,可她到底没有放松自己,依然坚守底线。中树本来是个二流子,不知怎么回事,这二年走南闯北竟发达起来了,他来小鸾这儿做衣服,量身时,小鸾被他趁机强行上了身,还送给小鸾金首饰,身心自然愉悦,可她是有自我约束的女人,自那次遭突然袭击后,严加防范,再没给过中树可乘之机,然中树多次企图终未得逞。小鸾心里苦、委屈、百般滋味,压抑不住在丈夫面前耍性子,打儿子,甚而推倒裁缝案子、掀锅,发泄内心的憋屈。这些正昭示了小鸾这样忍辱负重的乡村女性坚守乡村传统伦理的艰难,承受着政治、经济的双重挤压,苦涩地喘息。
经济野蛮生长,乡村政权芜杂蛮横,现代性浪潮的强劲冲击,一些乡村女性开始酝酿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心理变化,她们对于情感、婚姻以及性的理解,很显然已经构成了对于传统伦理的强大叛逆;而另外的一些女性,却依然辗转腾挪坚守传统伦理规范,忍辱负重如修行。这些悄无声息运作,汇集成一条暗潮涌动的心灵之河,静水流深,正如《十月》编辑所言:“那些乡村的女性站在命运的风口,任时代风潮裹挟而去。她们内心的辗转、跌宕和进退失据,都得到细腻的描绘和呈现,而笔底则始终鼓荡着生命隐秘的呼啸风声。”《陌上》触摸乡村女性的内心皱褶与纹理、曲径通远昭微显幽,呈现出乡村女性的心理嬗变与坚守的内在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