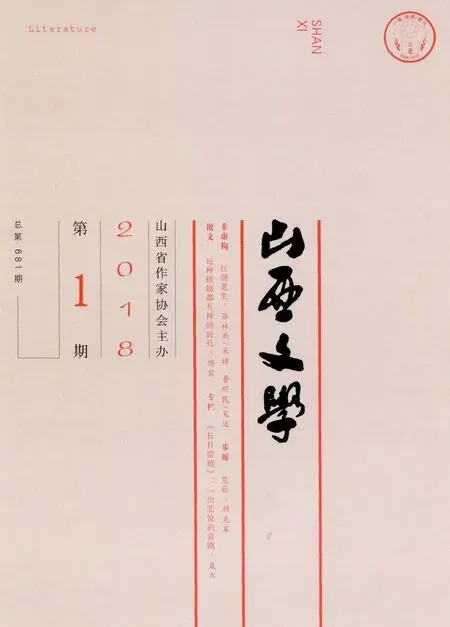红颜老生(上)
—— 晋剧表演艺术家谢涛口述
张林雨 / 采访 鲁顺民 / 笔述
头一回面对观众哭了
我1967年6月4日出生在太原,我们兄妹共3人,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父亲当时担任太原戏曲学校的副校长,他的资格很老,是当年晋绥边区七月剧社的老演员。母亲则是太原市实验晋剧团青衣兼老旦演员。
一方面来自家庭的熏陶,父母的遗传,另一方面是环境的影响,每天耳边是晋胡、二弦、打击乐,每天都看叔叔阿姨们在排练场排练和舞台上表演,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戏曲的种子应该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所以自己后来从事戏曲艺术,已经不能用酷爱来表达,那真是沉淀在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
当时的太原市实验晋剧院有“六大员”,过去的说法叫“角儿”。这些人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这个影响远不止“六大员”。
所谓“六大员”,共六位,有郭彩萍老师,她是晋剧小生名家;有武忠老师,是晋剧老生名家;李月仙老师,晋剧须生名家,后来我磕头拜其为师;后边还有阎慧珍老师、高翠英老师。他们都是咱们晋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最后还有另一位白桂英老师。
实际上,优秀的演员还不止这六位,包括薛维义老师、唱花脸的戴占寿老师、薛玲花老师,还有我妈妈张翠英,他们是一代人。他们这一代人,是解放之后晋剧培养的第一代接班人。这一代人中间,也包括田桂兰老师,还有调到省晋剧院的张友莲老师。
我六岁上学之前,就是看他们排练和演出,那种影响和熏陶就很厉害了。院里孩子们在一起玩,也是照猫画虎在那里演戏。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就是按照父母演什么角色来分配各自的角色。
我当时很不乐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唱青衣兼老旦,她演的最多的就是老太太,我一个小姑娘,不想演老太太。想演啥?演舞台中间那个小姑娘,比方《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后来还有《朝阳沟》里的银环,还有《苗岭风雷》《平原作战》《杜鹃山》里面的旦角,站在舞台中央很漂亮啊。可妈妈不演这些角色,她演张大娘、杜妈妈、沙奶奶,就这些角色。
当时,院里的叔叔阿姨他们演的角色我照猫画虎都会的,但他们总让我演老太太。演就演吧,演老太太,我也并没有觉得影响到我对戏曲这种艺术出自骨子里那一份喜欢。
这些记忆应该是三岁之后的事情了。三岁之前有记忆吗?很小很小,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够像叔叔阿姨和妈妈那样站在舞台中间表演,让那么多观众给我鼓掌,给我叫好!
盛夏时节的傍晚,屋里热,人们就在大院里乘凉,点起艾草熏蚊子,一堆一堆的,叔叔阿姨们坐在院里聊天,聊家常,聊排练。我们一群孩子就在他们中间来回穿梭。记得我穿着爸爸的一个大衬衣,穿起来像裙子一样。后来我问妈妈,我那时几岁?妈妈说,那时候也就三岁出头。
我们一群孩子们在大人中间疯玩疯跑,跑着跑着,就有叔叔阿姨一伸手逮住我,叫我小名:红红,来一段!这时候我特别高兴的,好像也特别爱表现,大人拉住我的手,站在中间来一段,像模像样。唱什么?当然是自己喜欢的那些旦角,《红灯记》啦,《杜鹃山》啦。现在想想都特别甜蜜美好。
真正显现出对戏曲的爱好与痴迷,应该是上学之后。
1974年9月,我上小学。上的是新建路小学,现在叫一校二校。当时就是一个新建路小学。新建路小学是一所戴帽小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小学和初中都有,是所谓的“七年制小学”。
其实,在上学之前,已经跟新建路小学有接触。上学之前,院里有一个哥哥,大我五岁,叫陈亚平,我记得应该是五岁左右,他应该是在五年级的样子。那一年“六一”儿童节,他跟我讲:红红,我们学校过“六一”儿童节要演节目,你能不能给唱个山西梆子?
我说:能。
他说:你敢吗?
我说:敢。
有什么不敢的?两三岁就在院里唱,现在五岁了嘛!
他讲:那你跟妈妈说,明天早晨化个淡妆,我带你去学校。
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胆子也挺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和面对这么多观众。后来想想,师生合起来有一两千人。舞台由土堆起来,外头再砌一些砖,很不整齐,而且也陈旧,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搭起来的,有三个台阶,当时我五岁,很小的个子,还是老师把我抱上台上去的。
在上台之前,学校的音乐老师拉手风琴,问我说:孩子,你唱什么?
我说:晋剧!
后来我知道音乐老师是裴老师。裴老师说:晋剧我不会伴奏,你就独唱吧。
这样我就被抱上台了,那个话筒装在一根杆子上,老师把它压到最低,就那还在我的头顶上。那天操场里面坐满了老师和学生,一大片,老师把我放下之后让我站在中间唱。当时高老师问我说你唱几段,我说两段,一段是《红灯记》里铁梅唱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段是《平原作战》中小英唱的《枪林弹雨》。就准备了这两段。
他们给我报幕,我一上台大家就开始鼓掌。现在可以理解,“六一”儿童节,把一个学龄前儿童请到台上给大家唱,大家不很开心吗?我一张嘴唱的晋剧,是山西梆子,平时大家听得不多,小姑娘一唱,又觉得很好玩,唱完又鼓掌。我呢,就是这种人来疯,他们一鼓掌,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觉得我唱得好,这个劲儿就上来了,自己给自己报幕说我再来一段《平原作战》小英的唱段。大家又热烈鼓掌。唱完之后,大家更开心了,掌声比上一段掌声更加热烈。这时候脑子就有点晕,有些膨胀,竟然还不想下台。
老师一看我准备的两段唱完之后没有下去,就说:你再来一段。我点点头,他问我:你唱什么?我说:《朝阳沟》。
我就唱《亲家母,你坐下》,演俩老太太。五岁年纪,乳牙刚退,新牙还没长齐,前面两个大板牙长长短短不齐,我一说《朝阳沟》,先摆出那个老太太的动作,小板嘴一撇,那个效果可想而知了,大家哄然大笑。他们这一笑不要紧,我把第一句词给忘掉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下好,大家又开始鼓掌,现在想,大家的掌声是善意的,鼓励的。一个小姑娘摆出那样一个姿势,大家觉得更有意思或者更可爱,可我站在那里很尴尬,一听到掌声响起来,不乐意了,冲着那个话筒哇一声就哭了。记得是裴老师,在台下一看这个情况,赶紧上台把我夹在他胳膊肘底下抱了下去。
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一段,在新建路小学出名了。入学前去报名,两个班主任抢着要我,说我们要这个孩子我们要这个孩子,就那个在“六一”儿童节在台上唱了两段不肯下来,最后在台上哭了的那个孩子。
所以,上小学之后,老师对我特别好。我自己呢,学习也特别好,开始当班长,后来是中队长,后面又是大队委员,在大队委里还担任宣传委员。担任宣传委员,自己是文艺骨干,这没有问题,但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尤其是语文作文,还有朗诵。11岁那一年,代表山西省出席全国普通话比赛。全省7名代表,有教师,有中学生,还有小学生,我是其中之一。
小学五年,过得特别快乐,除了学习用功成绩特别好,也没有离开过文艺。可能也是人来疯,过年过节学校搞什么活动,积极参加积极表现,不单单唱晋剧,还跳《草原英雄小姐妹》之类的舞蹈,还有朗诵。上学的时候文艺活动也特别多特别丰富,文化馆、少年宫都有。这样,我其实已经不单单是新建路小学的文艺骨干,而是太原市青少年中的文艺骨干和文艺苗子。
小学五年,我觉得跟文艺的接触更近了,在舞台上更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我要上戏校
小学毕业,面临着升学。
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上戏校。
在11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戏校招生,那会儿叫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爸爸担任主管业务和招生的副校长。为什么要上艺术学校呢?因为打心里喜欢当演员,当戏曲演员,喜欢唱戏,这个没有办法。或者说,这就是我的理想。
当年写作文,曾经写自己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那都是违心的,特别违心。其实理想是做演员,唱戏。因为除了在学校读书之外,课余时间的生活环境还是剧团,经常看叔叔阿姨们演出,尤其是节假日,放寒暑假,他们在长风剧场、和平剧院、山大剧院演戏,我都是要跟着去看的。那个时候就特别憧憬,心说啊呀,自己将来的职业就是演员嘛。这样,对他们的工作状态都十分熟,每天演什么什么戏,每天提前多长时间化妆,都很清楚。他们还经常下乡演出,扛着行李卷,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很喜欢。
但上艺校并不顺利。
首先是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她希望我能顺利上初中、高中,考大学。张老师是太原市和山西省的优秀班主任。上初中、上高中,顺利考个好大学,是任何一个老师对好学生的期许。所以上艺校,张老师很不理解,也很不高兴。现在张老师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见了我都不说她改变了当初的主意。
有一次,师生见了面,张老师只是说:孩子,你现在唱戏唱得不错,挺有出息啊。
她老公马上阻止她:你别再说了,人家谢涛唱戏现在都得大奖了。意思是你应该夸人家呀!但张老师还是很固执,她讲:她就是搞了别的也一样有出息。
很固执的一个老太太。
老师不同意,妈妈也反对。反对得特别厉害。她知道我要报戏校,直截了当阻止:你不能学戏,你不能唱戏。
这个时候,我哥哥已经考入太原市碗碗腔剧团,妈妈实际是不乐意的,她一直阻止我,说:你得学习,你得学文化,将来考大学。
妈妈常年下乡演出,一走就是两三个月,家里管不上。她就跟我爸爸讲:你不许谢涛去上戏校,不许谢涛考戏校,不许让她唱戏。
我们这个家庭,是慈父严母。母亲对我们三个孩子特别严格,虽然没有打过我骂过我,但对我们特别严格,不许这不许那,她个性也很要强。相反爸爸对我们相对温和,所以她下乡之前再三叮嘱爸爸来阻止我。
妈妈反对,要比老师不乐意来得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报名要户口,妈妈反对,她不给你户口怎么办?但是,我还是偷偷取了户口本报了名——户口在哪个抽屉里我知道。不过,爸爸其实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他作为主考官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家的姑娘报了名?虽然他不参加初试这些过程,但他是知道我要做什么的,说明他赞成我的选择,至少不反对。
这就考试了,当然同时也参加了中学的考试,现在叫“小升初”。结果,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的通知发下来,同时也接到了12中的录取通知。12中是太原市的重点中学。这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那时候新建路小学已经取消了“戴帽”,变成完全小学。小学毕业,要么上12中,然后上高中,考大学,要么就去读戏校,做我喜欢做愿意做的事情。其实也没有怎么多想,把12中那个录取通知给撕了。现在想想,那时候12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主见?直接就撕了。回家之后,把文化艺术学校的通知书放在自己的小抽屉里,夹在一个日记本里藏起来。我们三个孩子每人有一个小抽屉。给家里人撒谎说自己没考上重点中学。
这中间,妈妈回来过一趟,我就跟她聊,探她口风,说:妈,我要是考不上重点中学,你让我上戏校。
妈妈回答很决绝:不可以,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她一口回绝,但我觉得自己一定能上成戏校,一点也不气馁,有一种认准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的感觉。这可能就是我性格里的执拗,一根筋那种劲头。我也不吭气了。
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中间妈妈曾问我说谁谁谁家的孩子考上12中了,谢涛,你这通知书就没拿到?我就摇头。
可是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记得是8月底9月初,各学校的新生都开学报到了,那一天家里就我和妈妈,妈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大盆里架了搓板,在那里忙碌。这时候,我的小学老师找来了,她一进门就说:这孩子怎么回事不去报到呀?妈妈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沫,说孩子没有考上呀!
她们在那里聊,我一听不好,不敢在院里待了,刺溜一下子跑回自己小屋子里躲起来。听得老师在外头跟妈妈说话,老师说谢涛考上12中了,人家都报到了,这孩子到底上还是不上?
我记得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一边应着老师说:上上,一定上,我让她去报到。一边用那样一种眼神找我,狠狠的那种眼神。我吓得哪里敢出去?
老师简单说了几句就走了,这时候妈妈甩干净手上的肥皂沫,擦净手,左顾右盼找东西,结果找到一条马鞭。是练功用的那种马鞭。这时候哥哥已经开始练功,妈妈也有这些练功的东西,实际就是一根藤杆,上面的穗子都掉了,就剩下一个马鞭杆。妈妈一把把我揪过来按到床上就抽,在屁股上抽了十几下。真是很疼啊。晚上我摸腿,都是一棱一棱的鞭痕,在灯光下能看见好几种颜色,青的黄的绿的紫的。现在想起来都很疼。
就那样,我没有哭。一声都没哭。妈妈打我抽我,我就咬着牙不哭。
这已经是将近40年前的事情,至今还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妈妈打完我,扔掉鞭子,抱着我哭。
我安慰她:妈妈你别难过,我肯定给你争气!
妈妈说:你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唱戏有多苦。它还不是你身体的皮肉之苦,远不止胳膊腿骨折那些闪失,主要是得靠多少人帮衬你才能成啊。
唱戏苦我理解,但是妈妈说的帮衬我当时真的不理解。妈妈是个要强的人,那会儿没有出大名,观众也知道,也熟悉,也喜欢,但不是大角儿,我想妈妈可能有一种不得志,心里头不服。出大名也好,做大角儿也好,可能就是命运或者人生。
现在想想,妈妈的话有许多道理,这一路走过来,多少人去推着你,帮着你,托着你做成一件又一件的事,你最后才能成为一个大家喜欢的好演员好艺术家。帮衬,是妈妈对唱戏这一行的理解。
但当时我是不理解的,12岁的孩子就是那么简单的喜欢,就是喜欢唱戏。所以我对妈妈说,我一定给你争气。
挨了妈妈的打,实际上等于妈妈接纳了我的选择,我可以顺利地上戏校了。
上戏校那一年是12岁,我们那一届是78届,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耽误了一年。
入学是1979年的事情。
戏校春秋
戏校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起来的,校舍在一座庙里,那条件跟今天的戏校不能比。那座庙很有名,后来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叫窦大夫祠,离城二十多公里,老师从城里来上课,学校安排有一辆大轿子车,每天早上来,晚上回,一白天都在学校上课,学生则两周回一次家。我们的学制是五年,我在这里待了整整三年,第四年就实习去了。现在想,所有的唱做念舞基本功就是在戏校里打下的,我特别感谢戏校的三年。
刚入戏校,我的基础要好得多,并不是生茬子从来没有接触过戏曲,从小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不说,而且在上学之前就练过腰腿,从小叔叔阿姨经常把我两个脚一提溜,两个手就拖到地下,拿大顶倒立。这个从五六岁就开始了,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不是每天练功,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底子,相对其他孩子是有些基础的。
那座著名的窦大夫祠是恢复戏校后的一个教学点,那个时候庙很破,很空,我们的教室和练功房就在庙里。那个地是砖漫的,老旧的砖大而长,但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我们练功跑圆场就在这个老砖地上,尤其是走跪步。现在练功房都铺着地毯了,但那个练功场真还有它的效果,后来我跟同事们开玩笑,我说如果说我的跪步走得好,那都是在坑洼不平的砖地上练出来的。
环境虽然跟今天不能比,但戏校里集中了一批传统戏曲表演很过硬的老师。这一批老师和我妈妈是一茬人,是晋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传承人。比方田翠兰老师、吕铁成老师、王玉珍老师、秦英环老师等等,这些老师跟武忠老师、郭彩萍老师,都是一茬人,后来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离开了舞台,搞戏曲教育。他们肚子里有很多功夫玩意儿,所以我们这批学生很幸运,从他们身上学习和继承了比较扎实的戏曲功夫。
进入戏校,一开始给我分配的是青衣行当,第一出戏学的是《女起解》,也就是《苏三起解》。这出戏是我们当时的沈毅校长帮我排的,他是搞京剧的导演,整出戏是京剧打的基础。同时辅导我的还有花艳君老师,她也是我妈妈的师父,晋剧华派的代表人物,她给我传授指导《女起解》。学的第一出戏,我们叫做开蒙戏,我的开蒙戏就是《女起解》。开蒙戏很关键,基础打得也很扎实。
《女起解》之后,我和一部分同学,大概有七八个人,都是所谓的“尖子”,被派到临汾戏校学蒲剧。又学了几出戏,《杀狗》《挂画》 《双锁山》。跟张巧凤老师学的 《杀狗》。《杀狗》它不完全是一个青衣戏,它糅合了泼辣旦、彩旦、花旦的一些东西,包括道白,都不一样。所以这出戏无疑给我打开一条戏路。
学的第三出戏是《永寿庵》,这是晋剧正工青衣的一个戏,40多分钟,一出场就唱,一直唱到结束。里面所有晋剧青衣的板式基本上都包含了,非常之丰富。
可能老师考虑到我的行当是青衣,就着意选了这么三出戏。但第四出戏《挡马》则是我自己选的。《挡马》跟青衣没有什么关系,主角杨八姐是旦角里的刀马旦,还要结合一些小生的东西,这个在晋剧里叫做“夹生旦”,或者反串。可能我这个性格起作用,好像天生就喜欢这个角色,就选了《挡马》。
选这出戏也有意思。上学的时候,我还是很淘气的,一副不务正业的样子。每天路过另外一个教室,看见吕铁成老师给其他同学排这出戏,就特别喜欢。那时候我正学《永寿庵》,已经学会了,心里有些烦,就想再学一个戏。
我去找教青衣的秦英环老师,跟她讲我想再学一个戏。秦老师问我说想学什么?我说我要学《挡马》。秦老师当然很吃惊了,她说:那不是你的行当。但我坚持说我想学,秦老师很好的,她想了想说:那我给你建议建议。
我们当时学什么戏,是由教导处统一按行当来安排的,所以她说给我建议建议。当时的教导主任是鲍云鹏老师,那是京剧的大武生,人很和霭。他知道我想学《挡马》,就找到我们宿舍里,问我说:你干吗不想学这个青衣戏?我也敢说,我说青衣戏就是咿咿呀呀坐在那里唱,从上台就坐在那里一直唱,我想动。
他说:你想动,要学什么?
我说:要学《挡马》。
他说:你能好好学?
我说:我能好好学。
很顺利,他就把我推荐给吕铁成老师。去了之后,人家那里已经有两个杨八姐,两个焦光普,我是个单的。吕老师就让那两个焦光普给我配。我学得很快的,学到什么程度呢?学得比他们原来教的学生都快,吕老师总让我来当示范,教完我以后就招呼大家:来,你们跟谢涛走,谢涛走前面,你们在后边。我学得很带劲的。
这就是在戏校里学的四出戏。四出戏,四个样子,风格完全不一样,虽然当时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但戏路拓得很宽,不单单是一个行当一个角色,尝试了四种。所以在校戏三年,过得特别充实。学校里有那么多好的老师,他们都有如此高超的技术,有如此扎实的传统唱念做舞功夫,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这是我们最初汲取到的养份。
改行当
在艺校上了三年,第四年就下团实习,那一年我15岁了,被派到太原市实验晋剧团,也就是现在的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
当时太原市实验晋剧团的实力很强,开始讲的“六大员”像郭彩萍老师、武忠老师、李月仙老师等等,这些名家正在舞台上。他们都在40岁左右,郭彩萍老师好像还不到40岁,这是一个演员艺术家最好的年纪,是艺术的黄金期,他们带着团演出好多好多剧目。我们这些学生娃一来,就是给跑龙套,演丫鬟、扮才女,还有男兵女兵一类。下团实习,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和我小时候看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感觉不一样。小时候懵懵懂懂,岁数不大,只是喜欢模仿,戏校学了三年,有了一些唱念做舞的小基础小功夫,一下子来到真正的剧团真正的舞台上,眼界自然不一样,打得很开。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们就像海绵吸水那样,各种艺术营养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慢慢吸收,慢慢吸纳。
进团之后,我分配的是旦角。那一年15岁,开始变声,本来我的声音在女孩子中就比较粗,变声之后声音变得更宽更厚了,身材呢,也随着发育越来越结实。这时候我心里就琢磨,我唱旦角优势并不大。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太明显,而且我唱得也蛮好。在戏校的时候,学校要和周边单位联欢,或者有什么实践的机会,我的《杀狗》《挡马》两出戏都是要出去的,算是戏校我们这茬学生的代表剧目吧。能出去演一两出戏,大家都很羡慕。包括下团实习,老师们也要在我们这茬学生中选那么一两出,像《打店》《挡马》,包括我的《杀狗》,让大家有锻炼的机会。在一个台口演出。我们台口很长,比方到内蒙,一演就是五六天七八天,一天要演两场,一场本戏就是3个小时,3个小时之前还要加半个小到40分钟小折子戏,这些小折子戏就是锻炼我们的。能演上这么一两出小折子戏,应该是蛮得意的。
但这个时候,我开始变声,声音粗了,唱旦的时候还要捏着,身材越来越结实,也不苗条,长得也不算漂亮。自己就在底下琢磨,对着镜子照,冷静下来想,你到底适合什么行当?
可能没几个15岁的孩子会这样想,这个与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因为环境熏陶,就是在艺术圈子里长大,会比普通孩子想得长一些,远一些。来到实验团,打开眼界,发现,噢,有这么多老生。小时候看叔叔阿姨们演出,包括爸爸妈妈他们,更多的是现代戏,只知道是男唱男女唱女,后来上戏校,恢复了传统戏,现在看就不一样了。熟悉的阿姨像郭彩萍啊阎慧珍啊,都叫阿姨,还有李月仙老师,小时候叫她爱子姨姨,她们在舞台上都是演男角的,如此潇洒,如此豪迈,如此有气势。舞台上女人是可以这么去演的,我要唱这个!我要演这个!
实验团分为两个演出队,实际就是两个团。郭彩萍老师带一个团,李月仙老师带一个团,我跟的是李月仙老师这个团。
决定要唱男角色,每天就看李月仙老师,像着魔一样,她演戏,我在幕条旁边看。她演完之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在舞台上模仿。她演《点帅》的杨六郎,我就演杨六郎,就让其他同学演什么穆桂英啊杨宗保啊。天天就这样子。
这个事情持续时间不长,让我妈妈发现了。我妈妈那会儿也跟着李月仙老师这个团。
她说我:你瞎琢磨什么,你每天在台上那是演什么!你是唱旦的,每天琢磨须生干吗呀?杨六郎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不独是妈妈吃惊,团里的叔叔阿姨们也早看在眼里,他们跟妈妈讲:你也管管你闺女,那在台上是干吗呢?那是她要唱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唱旦,下乡演那么一出《杀狗》,效果还好。这就等于是起了风波了。
我跟妈妈讲:我要唱须生。
妈妈马上说:胡闹,你知不知道,隔行如隔山?我们一茬一茬同事就是唱女的再改男的,最后改得不男不女,再也改不回来了,唱男的像女的,演女的又像男的,没有彻底改好。你不要改。
妈妈苦口婆心,她讲:我都起过这个意,我都改过。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丁果仙大师在他们这一茬演员里觉得我妈妈的嗓子特别好,而且给扮过戏。戴上髯口,她长的也是这种长脸,扮起来特别好看。但后来花老师,也就是我妈妈的师父舍不得让她改,而且她自己也舍不得改,也就唱了几出。当时花派戏也是小有名气,舍不得改就改回来了。因此妈妈讲:你千万不要改,到时候改得会不男不女。
妈妈不同意,我还是那股拗劲儿,不管她,照样每天还是老师演戏我去看,演完之后在底下瞎琢磨瞎折腾。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告状,就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妈妈拗不过我,就正儿八经跟我谈:这样吧谢涛,我领你去见李老师你爱子姨姨,她如果说你唱须生合适,她教你,我就把你交给她,我不反对。如果说李老师也说你不适合,那你就死了那条心。
我点头。
那时候也是在下乡演出,妈妈拉着我去见李老师,是在一个大教室里边, 李老师在那里织毛衣。妈妈拉我进去之后跟她说:你看孩子就跟着了魔一样,就要学须生,我的话她也不听,那你说吧,她适合不适合唱须生?
到今天也没有问过李老师,也没有问过妈妈,她们是不是提前商量过,通过气?李老师抬起头看一看就笑了。她是个特别文静的那种性格,她笑完之后,细声细语说:不要改须生,你唱青衣挺合适,唱须生不一定合适。可惜啊,不要改!
她就说了这么几句,妈妈看看,说:走吧。
我听了之后也没有多沮丧,有多失落,心里头只是想,不管你们谁说,反正我认定我要改。就这样出来了。出来之后妈妈说:怎么样?听清楚老师跟你说的了吧?我点头,她说:以后咱们还是唱旦角。我摇头。妈妈就急了,开始数落我。她在那里数落我,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当回事。
这之后,原来是怎么样还继续是怎么样,还看老师表演,还是瞎琢磨。时间大概是李老师谈话过后没超过三个月,大概就一两个月,有一天李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她住的那个大教室,说:我看你每天看我演戏,你学会了没有?
我说:学会了。
她说:你学会了什么?
我说:《三关点帅》杨六郎的唱。
李老师说:那就给我来两句。
我一下就冒汗了,紧张得不得了,没有任何准备啊。实际是真的学会了,真学会那么几句了,但一紧张就有点蒙,我想唱“眼前落下金彩凤”,就是杨六郎见了穆桂英唱的第一句。我边唱边想,眼前落下……想不起落下什么漂亮的鸟。但老师让你唱你又不能停下来,就张嘴唱,“眼前嗯嗯嗯嗯唉落下金丝鸟”。李老师噗嗤就笑,说:还金丝猴呢,你把词儿给我改了——好啦,不要唱了,你跟我学,我教你!
从这时开始,就跟老师改学须生。那时候还不到16岁的样子。从开始琢磨自己要唱须生,到最后被老师接纳,这个过程折腾了有半年多时间,这样,真正跟老师学,也就16岁了。
老师教我的第一出戏是《杀驿》,《杀驿》这出戏特别要演员的功夫。什么功夫呢?做工技巧,帽翅也好,髯口也好,捎子也好,靴子也好,就是这些功夫。我觉得老师给我选的这出戏特别好,这些功夫你能拿下,以后唱老生唱须生跟这些有关系的戏就能拿下了。这出戏的难度非常非常大,它就是唱少一点,这个戏主要是技巧。老师教我这出戏,就是打下扎实做工的基础。学这出戏我学得也挺难,因为我不是扎的须生的基础,现在要演一个须生戏,即便你扎的就是须生的基础,学《杀驿》也挺难,何况我的基础是旦角,一下子跳过来,特别难。
比方台步,旦角是夹着地,收着地走,而生行呢,它是放着地走。就是说走台步时,胯得打开。唱呢,我那个阶段就是以旦角的唱法去唱须生的腔,很难听。
团里拉晋胡的张步昌老师,是我妈的同学。我妈还想给我吃偏饭,拉着我去找张老师,给我吊嗓子。我不是不唱旦了唱老生了嘛,去唱。张老师本来是端端正正坐着,给我拉着拉着身子就扭过来,脑袋扭得很痛苦,他是听不下去了。他说不是这么个唱法!他告诉我妈:让孩子改回去吧,唱这个不灵。
他当时没有讲出来,从我本身来讲,唱的方法和位置都不对,他觉得挺可惜,因为张老师看过我的旦角。所以他说:还让唱旦吧,不要唱生了,这个太费劲,而且改不好,将来也是不伦不类,男不男女不女。
老一代教师教你发声,他们有他们一套方法,如果他一下子点不透你,就要走很多弯路。后来我知道,我的老师就是在她声音坏掉之后,她找到一个我们称之为“背躬音”(“脑后音”),不一样的发声位置唱出来的。这个音他们叫“救命音”,它是一个假音,真假声结合,假声大于真声。我现在学了一些发声方法,知道这个位置,当时真不知道老师是这么唱的,她找的音我找不到,只能用我自己的本嗓去唱,用青衣嗓去唱须生。
那个时候特别头疼,只能在练功房里跑圆场。我们那会儿招了一批插班生,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茬学生的基本功都好,但没嗓子——实际不是没嗓子,都是演唱方法不对,不会唱,大家就怵这个唱,都不唱,都是练功,搞表演这些戏。招来的十来个插班学生,个个唱功都非常棒,他们站在琴师跟前,一个人一唱就是四十来分钟一个小时。我们一上午练功,三到四个小时,人家就在琴师跟前唱三四个小时,就那么几个人。我们这一帮人在底下练功跑圆场,踢腿下腰,靶子功、身段功都练。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底下跑圆场,穿个靴子跑,练嗓子的就在台上练。我想,我多会儿能站在那个胡琴跟前放开嗓子唱那么完整的一段须生腔就好了。
当时,我只有16岁。以后要走很漫长的路。但是,我凭着自己的坚持,凭着自己的一种喜欢,自己给自己拿主意,自己给自己一个选择。16岁已经经过了两个关节点,一个是撕了12中的通知书上戏校,一个就是放弃旦角唱须生。
这两个关节点在16岁之前完成了。
(未完待续)
——读李如茹《理想、视野、规范: 戏曲教育的实验——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中华戏校)(1930—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