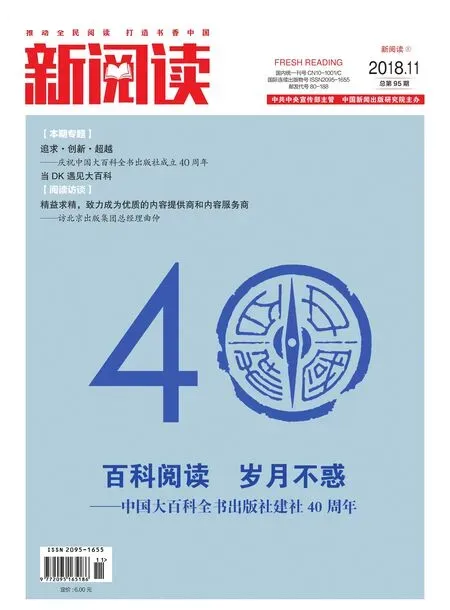我的书剑恩仇录
文/贾想
世人称嗜书如命的人为“书虫”。在我们胶东乡下,书虫倒很少,“懒虫”却很多。20世纪90年代末,我还是一个穿着开裆裤的不知廉耻之人,从日常行为上看,很有成为一只“懒虫”的危险。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装着几本教科书的书包扔得远远的,甚至希望它识相一点,自己长腿,从我的世界里消失。扔掉书包后,我必要去储物间里找到自己的“木剑”。那本来是一根长条木板,父亲砌墙用的。一个月黑风高夜,我潜入储物间,擅作主张,先削出了“剑尖”,再拿铁丝缠上一块短木做“剑柄”,制成了我的“佩剑”。
我的“佩剑时代”,在吃着玩伴母亲送来的鸡蛋的甜蜜时光里,悄悄陨落。这时候,一直被木剑敌视的书籍,立即趁虚而入。我想那是2005年左右,我的小学生涯都要结束了。大概是语文老师从图书室可怜巴巴的藏书中借回了几本给我们看,我分到了一本叫《海怪》的悬疑小说。讲的是“二战”结束,希特勒并未自杀,而是逃到了海底一艘潜水艇当中,鞠躬尽瘁,谋划复仇大业。现在看来,倒有点新历史主义的意味。当时看得又害怕又沉醉,夜里挑灯奋读,堪比当年醉里挑灯看剑。我的身体还依稀记得读完最后一页时的体验:浑身一颤,而后世界寂静,长长的一口凉气从七窍飘出。
文字、故事、纸质书,在几个夜晚之内,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我。后来小学毕业,语文老师“送”了一整套《青少年百科全书》给我。那套《百科全书》实在把我迷得丢了魂。宇宙天文、地球地理、人类历史、生命过程、美术史、音乐史、文学史……虽然都是入门知识,但对于一个满脑子只想仗剑走天涯的孩子而言,每一点知识都是一枚炸开无明的核弹。世界迅速在我眼前膨胀开来,原本“铁屋”的天窗一时间纷纷打开,光芒落了下来,落在了一个从大梦中清醒过来的小堂·吉诃德身上。

“书”与“剑”的对决,以“剑”的落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真的从“懒虫疑似人群”当中,登堂入室,成了一只“书虫”。那时我的身边,倒是有一只真正的“书虫”,况且叫他小潘同学。小潘同学的姥姥家是我家邻居,所以我们一到节日和假期,就常常见面。他三七分头,肤如凝脂,尤其一副六百度上下的厚眼镜,得意洋洋地架在鹰钩鼻上,极为惹眼。眼泡总是肿的,甚至肿得吓人,但按他的想法,那应该是身体里的智慧盛不了,所以鼓了出来,大家不必惊慌。他用知识征服我的那个课间,发生在初一。当时他捧着一本四五百页的经典文学作品简写本,奉若珍宝,谁也不给看。但他爱讲,那个课间,他一只脚踩着我的凳子,一只手高擎着那本书,以列宁在广场征服整个俄罗斯的姿态,向我们一众看客讲了一个“巨人”的故事。“那个巨人一泡尿,你猜怎么着,把一座城给淹了!”讲到这儿他哈哈大笑,许久都没停下来,像一台“哈哈”复读机。我们也笑翻了,教室的屋顶像瓦特的茶壶盖子一样乱颤。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讲的是名著《巨人传》。就这样,拉伯雷、塞万提斯、雨果这些古代的缪斯,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指挥着他的嘴巴,迷住了我和我的同学。
其实当时更多的同学,是被“地摊文学”偷走了魂儿。事情还是要从一个冗长的夏日午后讲起。我们三十几个男生挤在一间“大通铺”的宿舍里,蚊虫雷鸣,热浪灼人。左右睡不着的时候,忽见身旁的小李同学正趴在黏糊糊的床铺上,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大书,欣欣然如处冰室。那是一部近千万字的地摊网络小说,讲一个瘪三如何成为天地间六层世界的主宰,讲得他五蕴皆空、六神无主。在那种“巨著”面前,我的“书虫”细胞吓得迅速坏死。后来慢慢发现,身边的男生都开始捧起了这种“巨著”。一时间,一群自称“剑圣”“妖王”“傲天”“洪荒老祖”的书迷,把大通铺的宿舍变成了一座群魔乱舞的镇妖塔。而一本盗版《哈利·波特》也同时在校园里神秘出现,迅雷般形成了新的阅读旋涡。预约的人排着卡夫卡式的长队,怎么也看不到头。这群“傲天”们不只是“书虫”,而且知行合一,开始自己模仿着写起了玄幻小说。通俗文学与网络文学,就这样泄洪一样涌入了我们的年纪。
《巨人传》中,拉伯雷让自己笔下的巨人在神秘的岛屿上寻找宝物,找到最后,发现宝物只是一个字:“喝!”这近似文学作品在当时对我们的命令:“看!”总之,肿眼泡的小潘同学,神游太虚的小李同学,还有身边那一众一百单八线玄幻小说家们,成功勾起了我心灵深处那庞大固埃似的“渴”。接下来几年,读书对我成了和解渴一样日常又必需的事务,这得益于当时整个乡村校园读书的氛围。无论是文学经典《巨人传》、通俗文学《哈利·波特》还是网络小说《悟空传》,其内核都是人的欢笑与悲哀、光芒与阴影,尽管处理的手法有高下之分,但在打动人心的程度上,他们是平等的。它们共同激活了我们这群被尘土遮蔽的乡野孩童的心灵。
后来,书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洛阳纸贵的紧俏东西了。一是因为哥哥大学毕业之后,把一大堆书寄回了家,装进了一口放嫁妆的木箱子里。书籍与嫁妆,真是一个完美的隐喻。同样隐秘、珍稀,不可轻易触摸,但触摸的日子,一定是欢喜的日子。我记得箱子里躲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笛卡尔这些古典哲学家们,梭罗、蒙田、夏多布里昂这样的散文大家,还有《古文观止》《圣经》这样的东西方人枕边书,更不必说当代的小说、诗歌和思想随笔。总之琳琅满目,成了我的小型图书馆。二是,我哥还对我采取了考试奖励书籍的机制,随着我考了第一、再考第一、又考第一、总考第一,我的书库慢慢“肥胖”了起来。与此同时,那些装进我脑子的五花八门的词语、意象、思想碎片,也窸窸窣窣地开始躁动。它们你推我搡,争着和青春期的忧郁、冲动、敏感、野心相结合,一不小心就从我的笔尖溜出来,变成一行行羞涩的文字。于是,一种天然无公害的“自动化”写作,降临到我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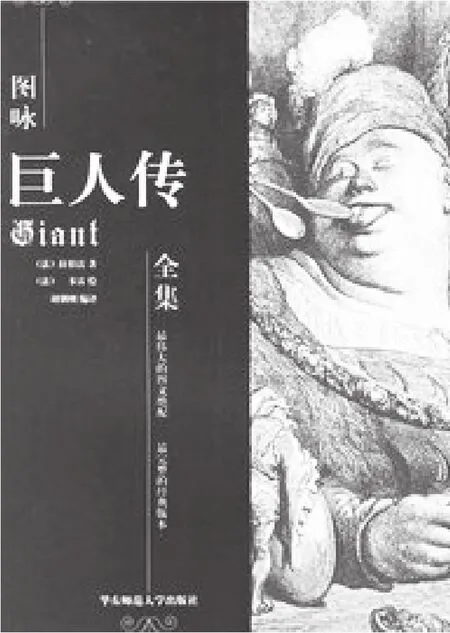
一开始写出来的,是一种徒有诗表的分行韵文。由古典韵律诗、流行歌词和浪漫主义抒情肥大症勾兑出来的黑暗料理。所谓拔起萝卜带上泥,你可以从我的字里行间揪出来这些诗人:朦胧诗的顾城、舒婷,台湾地区的郑愁予、余光中,浪漫主义的惠特曼、拜伦、普希金,外加几滴泰戈尔与纪伯伦调味。最终,我写了一两本所谓的“诗集”,一直羞于示人。在后来,读了高中,对于小说和思想性著作的趣味又猛然上升。《红楼梦》《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百年孤独》《变形记》《雪国》这样的外国现代小说,《平凡的世界》《活着》这样的当代作品,还有罗素、尼采等人的哲学著作,都不懂装懂地读了一通。这样读的后果是,我又心血来潮,开始去祸害小说、随笔这样的文体了。
“读”与“写”,似乎总是黏在一起,像事物与事物的影子。我的写作,一开始不过是阅读的投影。可叹我生性愚钝,那时读了好书,也没有写出多少好文。我还记得自己写过这样的“诗句”:鸟儿啁啾又啁啾,唱着异国的歌谣。天哪,我那时候连县城都没去过。而且,鸟儿为什么要“啁啾”两次呢,难道是因为结巴?但无论如何,随着笔下的文字积累得多了,“写”反而又开始呼唤“读”,阅读又变成了写作的影子。这种奇妙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概每个写作的人都体会过。
总之,跟当初被武侠电视剧迷住,执意要仗剑天涯成就一代武林宗师的偏执类似,我又被阅读与写作偷偷给下了迷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不顾家人和老师的苦口婆心,执意要读“只能培养语文老师”的中文系了。在那之后,就开始了“哪里不会补哪里”的更加丰沛的阅读。波德莱尔、里尔克之后的现代诗,19世纪与古典时代的小说,现代主义魔术师们的大作……终于,木剑毁弃,书页雷鸣。在大学导师和文学同道的指点与切磋中,一个胃口不大的“书虫”,慢吞吞地破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