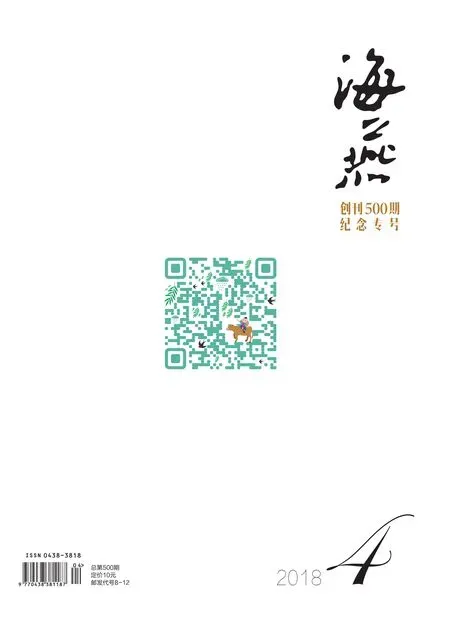又说“新辽西派”散文
□宁珍志
十多年前,辞去《鸭绿江》副主编之后调往创研部,担当关注年度辽宁散文创作工作,即写一篇两三千字有关本省作者散文发表情况的评述文字,备忘、积累、存档,同时在《辽宁日报》文艺评论专版发表,算作对辽宁文学整体发展态势的一种体裁的零星观照。此当口,齐明达、崔士学、魏泽先、李广智等新人的散文作品便一股脑地涌进眼帘,我有了集中阅读的机会。面对鲜亮而独特的文字,“新”——我几乎脱口而出,带有颠覆性的乡土题材处理方式,确实另立起来了一面辽宁青年散文创作的旗帜。加之作者们所处地理位置,“新辽西派”散文便在我的语句中首次出现。至于“派”,仅为一个集体称呼。
“新辽西派”散文命名只是代码,并不囊括同属辽西地区的锦州、阜新,这两地小说成绩斐然,有质量的散文过去和现在不多(张宏杰的叙述我称其为缀满生命细节的历史人物传记,与我们言及的艺术散文篇格多有不同)。而齐明达、李广智的境地又是从朝阳的建昌划归至葫芦岛,所以“新辽西派”散文创作区域指向主要面对朝阳。1970年代中后期牛成厚一篇《塞外银花》(有称其为报告文学或文艺通讯),差点红遍了大东北,尽管不乏人定胜天等意识形态的时代痕迹,可文本洋溢出的叙述才华和描写功力还是令读者感受到了散文作品贴近生活贴近本土的冲击力。之后有影响力骤大的便是谢子安了,他的散文集《雨走青纱》的确是辽西散文创作发展的集大成者、承上启下者。
谢子安的散文能够从贫瘠的辽西土地发掘诗意,从古典韵致与现代格调的交融中彰显生命情怀,细腻婉约的内心表达让单纯的托物言志寄情山水成为过去式,越过贾平凹式的语序和节奏突然而至,风格凸现,的确愉悦读者耳目。谢子安是首位获得辽宁文学奖散文奖的辽西作者,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在《美文》《散文》等散文名刊接二连三发表,即得益于作家的去公共话语化、去主题明朗化、去概念说教化,粗砺、熟稔的辽西散文语言忽然之间有了唯美、陌生的品质,并感染和带动了些许作者。诚然,谢子安等的散文书写未免会有一些杨朔、秦牧、刘白羽等名家多少年来成就的影响(课本、选本的量大),理想主义元素过剩,主旨、议论性的言说还会在经常出现的方位出现,“大”的表现欲望仍有余地。“新辽西派”们则不同,就是写“小”。齐明达《院子里的事情》中不少篇章能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转载,被看重的就是散文题材的“小”。魏泽先的《五月节打驴》能被《散文》重点推出,被感动的也只有在自家土地上才能生长出来的人畜灵性。崔士学说:“要是我能把村子里的事都弄明白了,那么世界上所有的道理我也就都清楚了。”
“新辽西派”散文创作一改常态,放弃或者正在放弃散文表现“艳”“奢”的一些修辞语象,比如:伪精神高蹈笼罩下的文本虚空有加,文化表演幕后的本色性地气性原生性信息很少,公共特质的叙述程序使得艺术涵盖成为稀客,偏离朴素偏离真诚的文字令乡土糅进了过多的水泥气息印刷气息“贵族”气息,照余秋雨先生的“葫芦”却画不出自己的“瓢”……“新辽西派”的散文作者群当然不同,他们的散文和父辈们的劳作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直接面对贫穷面对落后,面对愚昧面对偏狭,面对自然的风水,面对迷信的风俗,甚至直接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命运中诸多的逆来顺受。在“新辽西派”作品的字里行间,生命笑容与生命理想宛如漫漫长夜的一芽灯火,微弱而执着,向小、向下、向真、向善成为他们散文抒写的心灵格尺。读他们作品,像是体验乡下三间平房坦陈的一铺热炕,灶膛前准备续上的一把柴火,房顶上忽浓忽淡的几柱炊烟,贴面贴脊贴心。
“新辽西派”散文不是研究课题,不是专业方向,暂时还没有为此撰写硕士、博士论文的必要性(以后难说),商榷与争论显得小题大做。有一点需要明确,“新辽西派”绝不会因为必须有“旧辽西派”它才能够出现,“新”与“旧”应该是发展传承的关系。如同日本川端康成小说的“新感觉派”、意大利电影的“新现实主义”、法国西蒙等人的“新小说派”,以及我国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等等。并非是先有“旧感觉派”“旧现实主义”“旧小说派”“旧历史主义”才会用“新”来冠名各种文学流派、思潮的。文学跟随时代前行,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改变、深化或者颠覆,很正常;应运而生的阶段性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以“新”来涵盖言说,很正常。我们可以简化“新辽西派”在散文创作的一些新的艺术追求与探索,单凭他们作为新的一代文学创作个体,名曰“新辽西派”并不为过。
言顺非一定要求名正。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个体精神劳动内心生活的典型化过程,丰富而又庞杂。浏览古今中外文学史,各种流派、主义、思潮、现象名下的作家们难以胜数,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徒有其名,有的张冠李戴,有的以偏概全。然而,多数作家们不以为意,你说你的,我写我的,作品的评述与解析各有各的角度,作家的主观意图与客观回响也每每相违。当下几乎没有谁还在意作家们的流派、主义归属问题,好的作品在那儿,竞相赏读,天下流传,足够威武,其他已无足轻重。现在只要提到川端康成、西蒙的名字,直接对号入座的即是他们作品,什么“新感觉”“新小说”早被搁置脑后。“新辽西派”的散文创作有理由被界定为时间性地域性的艺术文本,至于时间性能否久远漫长,那是这一批“新人”的硕大提升空间,虽然我们寄予厚望,但是必须付出努力。若成绩显著,“新辽西派”的“帽子”也会悄然脱去,读者自然会把青睐的重心直接置于作品本身,作品的魅力毕竟大于无任何签字画押的口授流派“头衔”。
辽西地区十年九旱,风调雨顺的季候很少,大地的丰收来之不易。此生态倒与“新辽西派”作家的精神劳动几乎吻合,他们很小心地写着,生怕题材重复,思想与情感过程相同。他们像田野里的一秆秆庄稼,如同等待雨水滋润一般渴盼心灵与山梁、房舍、路径、茅草的融合,从而发出“四季”声音。感谢《海燕》编辑部,本期为“新辽西派”散文辟出的宝贵版面。这个小辑只是一个窗口,选发崔士学、魏泽先、李广智、郭宏文、杨庆华等五人的新作,篇幅都不长。在此,不对每篇作品再作评述,相信读者的获得比我的赘言更深刻,更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