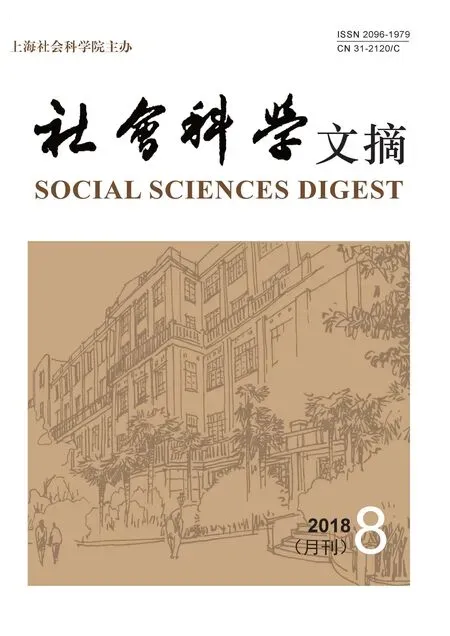历史现象学的现状与目标
近年来,“历史现象学”(Phänomenologieder Geschichte, phenomenology of history)这个术语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学界日益关注到现象学运动与历史问题之间广泛深切的关联;对具体领域的现象学研究,也日益彰显了历史视角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系统展开历史现象学研究都具备重要意义。但至目前为止,我们对历史现象学的涵义、研究意义以及主要研究任务,都还欠缺足够整体的阐明。
“历史现象学”的涵义
“历史现象学”一词,既能被理解为“关于历史”的“现象学”,也能被理解为“关于历史现象”的“学”。这种“句读”的用法不同其实基于对“现象”的不同理解,即“现象学”之“现象”与通常所言“现象”不同。不仅是“现象”一词,对“现象学”和“历史”的不同理解,也会引发不同的“历史现象学”含义。对现象学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至狭者仅指胡塞尔现象学,至广者则延及黑格尔、尼采、狄尔泰、萨特、德里达、雅斯贝斯等。因而“历史现象学”可能仅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部分内容,也可能宽泛指向广义现象学。而“历史”一词,则既可以指历史本身,也可以指历史学,前者与存在有关,后者则主要指向历史知识文本。因而历史现象学既可指向历史存在论,也可指向历史知识论。而所谓存在论并非指实在论意义上的存在论,而是现象学视域下特有的存在论问题,它集中表现为“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historicity)问题。
就胡塞尔本人而言,他似乎并未使用过“历史现象学”术语,运用较多的是德里达。也就是说,在现象学运动几乎到达了末尾阶段,“历史现象学”一词才出现。然而德里达之后,“历史现象学”也并未通行,而只是在论及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克莱茵(Jacob Klein)、萨特(Jean-Paul Sartre)等人时零星出现。但自2000前后,“历史现象学”一词的出现频率逐渐增加。其中大卫·卡尔(David Carr)摆脱了学术史用法,用“历史现象学”命名其从现象学出发研究历史知识理论的工作。而在2006年出版的AnalectaHusserliana第90卷,以“历史现象学”为标题的第一部分内容亦甚广,不仅包括学术史,也涉及更宽广意义上的历史理论。这或许已经意味着“历史现象学”已经开始被理解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方向。
在国内,此词最早见于1996年雷戈的《历史现象学论纲》,指的是“关于历史现象”的“学”这最宽泛的含义。大致在2000年左右哲学界开始使用“历史现象学”,最初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张一兵《回到马克思》(1999)为代表。丁耘则将胡塞尔定位于“生活世界现象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将世界“把握为历史现象”。显然,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历史现象学”的用法,是与“现象”的不同理解有关。此后,随着中国现象学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现象”的使用意义开始低于“现象学”。由于狄尔泰、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利科、梅洛-庞蒂等广义现象学家都与历史问题紧密相关,也就在实质上推进了历史现象学的学术史研究。但由于此前胡塞尔被广泛认为是“最不具有历史性”的哲学家,直到孔明安先生在2007年发表的《意义的历史及其回溯》中开始明确提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同年,倪梁康先生在《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2007年)一文也开始讨论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台湾的罗丽君则在2006年就开始以“历史现象学”为题开展胡塞尔研究,只是未发表出来。)至此,整个现象学运动便都与历史现象学发生了关联,“历史现象学”术语开始通行起来。明确使用这一术语国内学者此后还有杨大春、朱刚、方向红、李云飞、潘建屯、黄旺、任军、单斌、王庆丰等人。
要之,“历史现象学”首先不是现象学哲学家的原创术语,而是研究型术语;其次,如若整个现象学运动都与“历史现象学”有关,那么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之间便不止是包含关系,而应当具备更深的内在关联;其三,历史维度对于现象学的重要意义,是在反思自身时才逐步彰显,直到最后才回溯到胡塞尔现象学,其深层原因值得深究。
目前为止,对历史现象学本身展开研究的,主要有倪梁康、孔明安、朱刚、颜岩、潘建屯、罗丽君等学者。颜岩区分古典现象学(黑格尔与马克思)与现当代现象学(胡塞尔现象学创立以来),相当于按“现象”的不同用法划分二者,并认为它们彼此异质。孔明安则是按现象学的狭义与广义之别区分了狭义的历史现象学与广义的历史现象学。倪梁康主要在狭义历史现象学的意义上使用“历史现象学”。但倪先生通过将历史现象学定位于对历史的内在本质或内历史的研究这一点,隐含了将历史现象学扩大为历史哲学的含义。罗丽君则认为“历史现象学”从字面意义看是指向完整的历史哲学,但目前还仅局限于历史性问题。因此,倪梁康与罗丽君实际上有将历史现象学扩大至历史哲学的意图。潘建屯在论文《历史现象学内涵探析》继承了这个意图,认为历史现象学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应当同时考虑从历史哲学和现象学两种视角来界定历史现象学,但他同时又否认了确立历史现象学统一内涵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目前关于历史现象学的理解和用法,基本上是分裂的。但按照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本旨,我们对历史现象学涵义的把握即使不能是“一劳永逸”的,但却完全可以获得统一的本质把握。这种统一性的关键在于,“历史现象学”中的“历史”应被作为视角而非对象,“历史现象学”应当是“历史地现象学地看”,而非“现象学地看历史”。前者意味着“历史”与“现象学”之间必定存在着本质的观念关联,从这种本质关联出发,诸种现象学之间也获得了一种统一性;而后者则在作为对象的“历史”的差异性之中扼制了研究历史现象学的意义。
历史性与现象学的本质关联
把“历史现象学”的“历史”作为“视角”的关键在于,正是由于“现象学的看”,才涌现了“历史性”问题,现象学造就了全新的历史性,现象学的“看”由此成为“历史性的看”,它指的不是那种演化地研究的历史方法,而是将历史性的生存或自我视为世界展开的根本,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之域由此重新构造起自身而成为“对象”。
如果我们把现象学视为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超越的话,它便是以消解理性与历史的冲突问题为中心,这也正是“历史性”问题的意义所在。对于现象学而言,超越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意义便在于,近代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试图超越历史的理性主义,但恰恰是在近代理性主义中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反而导致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前提被消解。
近代理性主义试图超越的历史,必须在近代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念基础上理解。只是在西方近代,一个预先的自在的自然世界观念才被建立起来。近代理性主义根本上是普遍数学的胜利,随着事物的属性和质料都全面地被数学化,世界被整体地转换为一个被认识的形式的世界与一个永远不可抵达的自在之物的对置,在数学的无限的观念中成为一个永远预先在此的绝对容器。历史性问题从此便进入了哲学反思的中心区域。因为真理试图超越的“变”从依附于“物”的“变”,变成了依附于世界本身的本质之变。所谓历史性,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本质,即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处于历史生成之中这种历史性,对应于胡塞尔所批判的“事实的历史性”。绝对的历史生成意味着绝对的变化,因此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对绝对的无穷而不可逆的变化的肯定。
这种肯定世界自身之绝对变化的历史性观念,意味着由于世界自身绝对变化,任何生于世界中的物也是绝对变化着的。历史实际上取代了“质”,成为多样性的源头,永恒的理性与瞬时的流变/感知的对立,就转化为普遍的理性与多样的历史的对立,真理的最大目标就从追寻永恒本质转变成了超越历史。因此,哲学追问关注历史本身是近代的事情。传统哲学追问的是流变,这导致时间问题构成追问的内核,时间问题因而是哲学中的关键问题,而历史问题往往是在讨论时间时被笼统地包含在内。这也是在现象学中长久以来不直接提出“历史现象学”的一个原因。而自现象学诞生之后,历史一词便显得越来越重要的。当我们把万物都视为是“生成的”,从而绝对地具备历史性之后,人本身连同人的理性也成为在世界中的历史性生成物,而这意味着主客二元论这一近代理性主义基本图式的普遍主体这一极为之崩解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还有什么真理是超越于历史的?倘若连数学真理都是生成的,那么近代理性主义自身岂不也成为相对于某一时代有效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了?
现象学正是诞生于这种试图超越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中,而历史现象学,从后期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到海德格尔一直到梅洛-庞蒂,都是为了进一步超越近代理性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期胡塞尔激烈地反对历史主义,至少是那种他视为自然主义变种的历史主义。
关键在于,当现象学把“万变之源”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的现象学,便开启了第二种历史性。在现象学视野中,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被倒转了,人不仅不再是神的被造物,或只是被动生成于世界中的高级物种,而是一个自主的创造者,甚至世界也是因人而获得存在意义。就生活世界而言,生存着的人的历史性是彻底的绝对者,以至理性再也无法凌驾它、超越它、拒斥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质直观最终催生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胡塞尔前期坚持的彻底的纯粹的理性也被绝对的历史性吞噬。
胡塞尔在后期已经注意到了新的历史性,这才引发了他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胡塞尔后期的历史现象学思想,仍然坚持了先验(超越论)的原则,他进一步提出的是“先验自我的历史性”,从而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历史性。胡塞尔将这种历史称为“内在历史”,或“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历史。这实际上意味着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是在坚持着理性主义路线上对前期的推陈出新,它不再是“超越历史”的理性主义,而是类似黑格尔的“包容历史”的理性主义,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理性主义才能真正是彻底的和严格的。而从这样的新的理性主义出发,我们也才可能走向社会历史存在领域的重新回归,并重新奠定全部人类知识与人文社会历史理论的合法性。
历史现象学的任务
当前的历史现象学研究,更多偏重广义现象学,而较为忽视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直到近年,胡塞尔后期的历史现象学才越发引起学界瞩目,并主要针对历史性、发生问题、时间意识、习性自我、生活世界、几何学起源、交互主体性、被动综合构造等问题展开。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文本展开学术史研究,就历史现象学自身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
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视角和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学术意义认识不足这一点上。从历史现象学视角切入反思现象学运动,实际上要求基于后期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思想寻求对胡塞尔前期思想的修正。学界目前对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评估,总的来说意见不一。有将胡塞尔的前后期主张视为并列和互补的;有认为后期胡塞尔已经暗暗放弃了前期的本质哲学的;也有将胡塞尔历史现象学视为通往海德格尔式后现代思想的过渡性产品的。这些观点都没有把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最高地位。但近年已经有学者赞同兰德格雷贝,认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转向是其超越论现象学的必然结果,要求从历史现象学出发,修正对胡塞尔现象学主旨的理解。这实际上意味着胡塞尔的后期历史现象学才会是最终的超越论哲学方案,而他前期诸多论述的一再推迟面世,也与历史现象学问题对他前期思想构成的逻辑困难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从历史现象学视角切入反思现象学运动,也意味着有机会对现象学运动形成全局性的研究与统一理解。从现象学试图突破与历史相对立的近代理性,转变到包容历史的新理性主义这一点入手,不仅可以将黑格尔、尼采、狄尔泰这些以往被视为“前现象学”的哲学家纳入现象学传统中,而且可以重新建立黑格尔与胡塞尔之间被忽视甚至是被否定的本质关联。
其次,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被忽视与误读,也导致现代哲学至今弥漫着浓烈的相对主义思想。正是现象学运动推进了历史性的绝对化,从而使历史相对主义成为瓦解现代性的思想内核,并进一步波及了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然而也正是胡塞尔最为激烈地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并且也只是在胡塞尔这里才发展出了对历史相对主义思想根源最为深邃的反思。或许也可以说,只有转向后期胡塞尔的先验(超越论)历史现象学才可能获得“克服‘历史相对主义’”的洞见。
最后,既然历史性对于历史现象学仅仅意味着“历史视角”而非对象,那便意味着从历史视角出发,可以重新对广阔的诸对象领域展开反思。
一方面,从历史现象学出发反思历史学合法性等历史知识理论问题,将有可能引出全新的理论建构。大卫·卡尔(David Carr)已经率先进行了这种尝试,他试图以现象学式的经验概念为内核阐发了一种与现行“形而上学”式或“知识论”式历史哲学都不同的现象学历史知识理论。但总地来说,有关历史学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现象学至今在国内外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从历史现象学出发,我们将有可能展开一种彻底的观念史研究,以生活世界理论为核心,重新建立我们对世界及其历史,以及诸种文化客体与意义对象的理解。将“历史视角”引入现象学研究必定意味着实际存在的出场,意味着现象学研究实践性的彰显。这只能是以一种观念史的方式出场,也只能是以这种方式,历史理性才可能在突破现代性的前提下重新被建构起来。
就此而言,一种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内核的观念史的展开,便不仅意味着历史理性的重新回归,而且也意味着存在之域在先验(超越论)中的回归,这不仅将使胡塞尔现象学有可能跨越两种“现象”概念的鸿沟与黑格尔对接,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理性层面,而且也将可能重新建立对诸具体社会文化对象领域(比如伦理学、法律、艺术学等)的理论可能性的论证,包括基于超越论的生活世界理论,去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观念(尤其是儒学),及其观念发展历程。
总而言之,历史现象学如能回归胡塞尔历史现象学这一现象学内核,并由此出发重新理解胡塞尔现象学及其现象学方法,便有可能真正消解理性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建立一种新的理性主义和新的历史理性。也只有基于这种新的历史理性,才可能真正突破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困境,使诸社会文化领域的理论重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