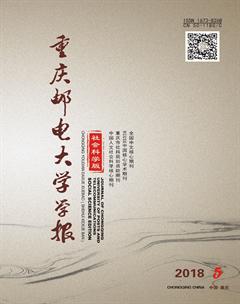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文化范式与历史逻辑
代金平 沈清容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种革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全新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既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有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致力于全人类参与的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导向,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引领。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底蕴;文化范式;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5-0001-0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从世界角度出发的治国理政、外交战略新思想,它为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类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社会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为人类未来走向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1]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价值、文化与历史三个维度。从价值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集中,赋予了国际关系发展新的内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选择与诉求;从文化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价值观并融合了现代化社会发展理念;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的思辨中萌芽,并在现实境遇中发展和凝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单一国家利益,着眼于人类全体意义上的利益共享、责任同担和命运相连,致力于构建符合人类公共价值与长远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全新探索。
(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蕴含着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主题。马克思以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异化问题作为切入口,按照从宗教批判到国家、法和政治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理路,对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人的交往活动形成的经济社会关系进行考察,提出了共同体思想。按此逻辑进路,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发展问题:第一是从人作为个体的维度来理解。人除了有作为生物体存在的物质需要之外,还有“作为人”的“类”特性,“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2]。人的真正需要是社会生产的需要,需要与社会生产互相推动,从而不断促进共同体和人的双重发展。第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来理解。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本能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一种社会历史活动,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使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获得全面的社会关系[3]。马克思认为,社会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4]。“把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使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他人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一体性关系,正是这种一体性关系,蕴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鲜明的价值追求。”[5]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现实生产活动,探究了人的异化问题产生的深层次缘由,从劳动实践活动的分工、交往中去看待人类生命、意识、历史和现实社会。除此之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异化”进行了批判,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需要即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性在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盲目崇拜下日渐扭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对人的“物性”统治进行了批判,提出要让人回归到本真的状态,在各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中把人给解放出来。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理性分析和深刻批判而提出的“共同体”思想,自然而然地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民族范围,而是跨越了民族和国家,有了世界性意义。
从人的需要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互利”“共赢”“安全”为出发点,构建命运共同體的本质和内涵属性。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全球命运休戚与共的发展大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彰显了其推动人类解放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广阔胸怀。“共赢”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属性。以共建、共享、共赢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对人的需要及人的本质的关怀。伴随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文化软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圈”不断壮大,中国在倡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同时,也为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诉求,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吸收借鉴我国古代“天下”观的基础上、基于当代国际关系格局提出的一种绿色、和平的国际发展战略。纵览泱泱华夏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以“天下”观打造的“命运共同体”一路伴随着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行走。自古以来我们就有“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先人的共同体思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放眼“天下”、放眼全人类的终极关怀,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天下”观的一脉相承,超越了“帝国”与“国族”建构,倡导在尊重各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共同诉求基础之上,以共享共建为核心理念开展国际交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非是对国家主体的否定或是超越,而是基于现实逻辑,以共同利益为价值导向,建设利益共同体。其目的在于寻求更高程度的合作与共赢,强调共赢共惠,争取国家间利益的正和博弈,达到族群间信仰的相互理解,实现利益上的互赢共利。在资本全球扩张和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世界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利益追求将不能独善其身,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时代发展理念要求在进行本国利益的发展之时必须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发展,各国发展既是利益的关联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当下是具有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等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价值理念,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6]倡导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友好往来,促进国际关系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发展。
从区域上看,无论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现代社会以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家发展予以衡量,但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利益共合体,消除全球贫困与两极分化,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是首要内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各地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与日俱增。推进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塑造新型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关系,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的应有之义。
(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选择
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成为全球化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人类的价值理念与追求随之呈现多元性和差异性特征。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人类没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所谓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就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与价值认同,这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尽管人类价值理念与追求有着多元性和差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平与发展一直以来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与价值认同。和平与发展符合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源动力即是对利益的追求,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是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只有共同发展才能高效发挥资源效用,实现互利共赢。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人类的利益和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尊重世界各国多样性、差异性,坚持多样性的统一,倡导包容平等、合作共赢的发展,主张不同文明主体或国家的平等性以及互学互鉴,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最终构建起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的这些既有理想高度又有现实基础的发展理念,既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又将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构成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思想表达。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范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范式不只是对历史的传承,还是对现实的深刻关照,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創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而行,为人类未来发展指引了方向。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
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拓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依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8]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可以看到,无论哪一种文明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依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而且延绵五千多年经久不衰,彰显出强大的人文凝聚力和历史穿透力。在长期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今天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拓展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今天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拓展依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在长期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体系,当下正通过在全社会广泛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得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也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追求人人为公、各得其所、永久和平的理想社会,以其极大的包容性和超越性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同。秦汉之际的《礼记》一书中记载了古人理想的“大同”社会,并认为只有经由衣食不愁的“小康”,才能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精神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资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涵与外延上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其思想精髓在当今世界的生动展现。
(二)社会发展的文化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最新成果,能够有效融会世界不同文明。马克思在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时,曾将“自由人的联合体”看成是“真正的共同体”,并描绘了一个人人自主平等、相互尊重,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图景。这种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和发展理念与中国传统“和”文化不谋而合,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文化共识。以和为贵、有容乃大是中华“和”文化的精髓与追求,“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核心,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中华“和”文化的延伸与发扬。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始终应该坚持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以此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各国因为文化差异性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范式,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亨廷顿指出:“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9]西方文明在解决冲突时更多采用“化异为己”的方式,将异质文明变为“与己同质”的文明,甚至直接使用霸权主义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为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确立了和谐相处的原则,即“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相处遵循“和而不同的精神”[6]。中华“和”文化最直接和最真实的表达就是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世界阐释中华“和”文化的价值内涵,将中华“和”文化理念加以创新并融入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向世界阐明了中国外交坚持中华传统“和”文化理念,推动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为解决当代文明冲突提供了中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在共同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通过海陆联动,在文化上“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10]。“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包容互鉴、兼济天下的东方智慧,拓宽了古丝绸之路的广度与深度,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距今已有五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共识。
(三)引领人类文化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科技与人文的背离与融合,不同民族生存的多样性,无不引发人们对人类文化共识与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内容的高度凝练,也与人类未来发展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为倡议者的中国,肩负着文化共识塑造者的角色,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范式的角度对未来文化发展做出构想,寻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内涵。
文化引领社会发展。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研判世界文化发展方向。从18世纪的西欧开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物质满足感,却无可避免地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精神危机。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11]。全球精神危机放在当下,我们可以理解为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或者文化心理危机。20世纪后期,西方文化出现三大转向(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12]),到21世纪初期,西方文化逐渐转向为对东方文化的研究,而东方文化则逐渐转向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东西方的文化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焦点在于东方的传统文化。发扬和传承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既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传统“和”文化交流观的继承与发扬,也前瞻性地研判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其次,人类对幸福和“共赢”命运的追求需要文化共识来引领。个人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人类共同命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背景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联,而在资本扩张的当下,“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命运的危機和人的幸福危机”[13]。由此,我们需要顺应生命进化和文化演进的规律,在新的文化转向中共同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范式,达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化共识,从而实现“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将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目的”[14]。最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倡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引领人类文化发展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把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主动地推向世界,让不同文化在交流中互学互鉴,这将奠定21世纪世界文化的基本走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阶级、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题和时代命题,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发展观,是对中外历史与现代外交方略的高度总结、概括与指引,描绘了集经济、安全、社会、文明与生态五位一体的统筹发展布局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以及对当前全球化发展下人类命运的现实关照,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的价值理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思辨
纵观华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不难发现“共同体”思想一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延续并传承着。古人的“共同体”不只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以血缘联结、以家为单位的小的命运共同体,还讲求国家大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农家的“并耕而食”、道家的“小国寡民”、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都与我国“大同”思想有着不可磨灭的渊源。“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充分体现了古人超越国家与种族的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与其整体意识和全球思维密不可分,既彰显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东方传统思想的滋养。
西方最早从世界角度关注个体和人类命运的是古希腊城邦制度解体后的斯多葛主义者,他们提出了世界主义观念。他们将世界城邦理解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个由法律规范的有秩序的人类组织的地方,它们的世界城邦理念就是设想一个包容一切的人类共同体。史学家普罗塔克对该设想评价道:“所有世界上的居民不应根据他们不同城市或共同体各自所区别的正义法则生活,我们应该把所有人看成属于一个共同体或城邦。”[15]西塞罗则更多地关注维持世界城邦的正义法则,给世界城邦画上了乌托邦的色彩。在西塞罗看来,人们之所以成为共同体,是因为分享了正义的法则,世界城邦的真实在于人们分享正义法则后有了共同的权威和制度。基督教则是将世界城邦发展成了上帝之城。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国家与民族之间的阻碍被打破,联系与交流日渐频繁,世界城邦再被解读。康德提出人类“永久和平”,并将之分为了基于霍布斯式的各国力量均势与世界主义法律体系规范下的两种和平形式。罗尔斯在其《万民法》中表述了人类永久和平的构想,阐述了从“公平正义”出发构建世界正义的法则,将正义由国内扩展到国际。随着国家、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博格提出了“全球正义”,旨在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全球新秩序,完成社会正义秩序的理想,在思想脉络上一直在为人类发展谋求“共同体”。到了20世纪,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组建了联合国,从实际行动上推进了“共同体”理论付诸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在价值共识上提倡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既是亚非欧商贸流通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桥梁纽带,是亚非欧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人民融通东西、汲取不同文明精华的桥梁,是中国人民渴望从亚洲走向世界梦想的生动尝试,同时也为21世纪东西方各国的交往、沟通、交流提供了先例。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谋取更大的福祉。无论是东方传统文化对“共同体”思想的积淀与传承,还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大同”的发展与探寻,或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积淀与传承,都是构成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思辨的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关照
自互联网兴起和发展以来,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并全方位地渗透到了不同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导致全球层面的利益、权力和文化的分化与整合,使得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16]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人类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构建已然具备现实需求基础上的必然性。
地球只有一个,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维护。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发展日趋明显。同时,信息化时代也带来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问题,人们对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洪流的涤荡感受越来越清晰,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资源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以及强传染性病毒正困扰着人类,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同舟共济,需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从全世界的视野审视全球化发展难题,需要以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世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当今世界市场、资源、信息、人才的全球共享成为一种趋势,构成高度全球化的具体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发展的休戚与共需要全人类抛开种族、国家、民族之间的偏见,在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共建共享。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其行为的动因和动力。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优战略,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人类的命运与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创新合作方式,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以发展共同利益为切入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
(三)构建新时代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价值引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构建新时代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引领。一个国家民族能够不断前行的关键在其核心思想、精神灵魂与文化价值。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要想走向世界并引领世界,就需要具备能够引领世界的价值。我国汉唐宋时期有着极强的世界领航力,究其原因在于,汉唐宋时期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交往的大动脉,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主要交通干线,是带领我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通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沉淀了深厚的中华文化,以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政治主张、经济发展与文化内涵。正是因为我国古代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输出,对东亚甚至西方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甚至产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促成启蒙运动的发生,并由此带动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与发展。西方世界的近代兴起,同样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输出实现了对世界的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与逐步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必须具备中国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智慧的凝练,包含着构建新时代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价值引领。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同的国家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在世界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利益在人的利益当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实现过程。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引导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走向方案,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日渐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性与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道路自信与责任担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顺其自然地过渡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遵循,以及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以公正、平等、和平、合作、共赢、共享、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看待经济全球化并引导其走向,以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为基础构建新时代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带动周边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迈向新的征程,人类正在由“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世界,共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共同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动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站在经济、政治的世界舞台中心,国际影响力、感召力日漸加强,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政策,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结合。在国际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价值判断而需要作出选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待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中国方案”,是随着中国外交实践而不断丰富内涵和外延的“中国策略”,以中国力量、中国思想、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构建新时代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前进方向,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迈出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1]卢文芬.“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3]张永纲.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维度[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7(3):49-53.
[4]王喜.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进路[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20.
[5]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4.
[6]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8]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持[EB/OL].(2014-02-25)[2018-01-10].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55-56.
[10]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03-29(4).
[11]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44.
[12]叶舒宪.现代性的危机与文化寻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143.
[13]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7.
[14]高清海,胡海波,贺来.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83.
[15]HEATER D.Origins of Cosmopolitanism Ideas[M]//DELANTY G,INGLIS D.Cosmopolitanism.London:Routledge,2011:43.
[16]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中国青年报,2013-03-24(2).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
The Value Implication, Cultural Paradigm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AI Jinping, SHEN Qingrong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one of the basic strategies for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is an innov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societal developmen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advoc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i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Chinas wisdom and Chinas progra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but also helps build a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elps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ommon destiny community is committed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win-win participation of all human beings.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an inclusive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manner is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human destiny and is also the realistic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in-depth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common destiny community carries the historical speculation of human destiny, embodies the longing and pursuit of human life for a better life, and becomes the value guide fo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value implication; cultural paradigm; logic of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