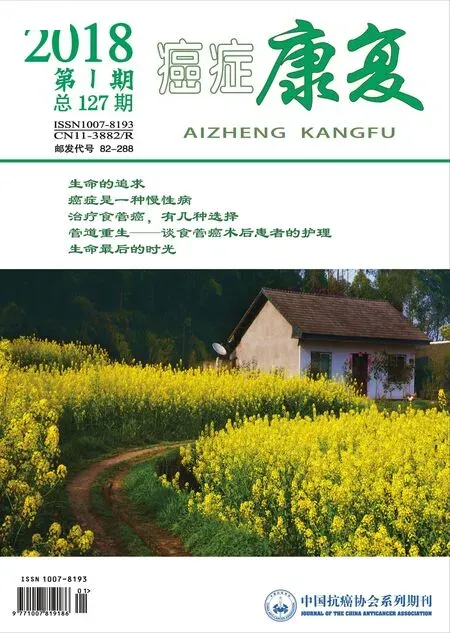“吗啡纠纷案”的样本意义:让“优逝”可行
□ 刘端祺 张建伟
2016年,陆军总医院肿瘤科因“吗啡使用纠纷”被患方告上法院,此案自发生以来一直受到业界的强烈关注。前不久,该案件出现了转机,最终以医方胜诉获得解决。那么,该案件为何最终柳暗花明?触碰了医务界的哪些痛点?判决对于医务界乃至整个社会有哪些现实意义?希望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专家刘端祺教授等人所做的详尽分析能带给读者更多深入理性的思考。
——《健康报》编者
新闻事件回放
2015年5月,章女士因胃癌切除术后胸闷、喘憋入住陆军总医院肿瘤科,影像检查显示肿瘤复发、胸腔积液、腹腔种植转移、淋巴结转移,伴间质性肺炎。在进行抗炎、平喘、胸穿抽液、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患者病情仍逐渐加重。在患者家属准备“自动出院”的当天上午,患者突然出现心前区不适,心电图显示急性心梗,伴快速房颤(心率200次/分钟),呼吸困难呈端坐状并进行性加重。
按多学科会诊意见治疗后,患者心跳转为窦性,但呼吸仍十分困难,痛苦不堪。针对上述病情,医生与患者亲属进行了交流。在患者家属表示认同后,给予静脉壶入吗啡10 mg,患者呼吸状况明显好转,可平卧入睡。次日凌晨,患者再次出现呼吸困难,予皮下注射吗啡10 mg,呼吸状况再次好转。下午患者呼吸困难逐渐加重,皮下注射吗啡10 mg无效,患者终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在场亲属平静料理后事。
时隔半年,章女士的儿子以医院“过量使用吗啡,导致患者死亡,使其过早地承受了丧母之痛”为由到法院起诉,向医院索赔10万余元。诉讼过程中,某司法鉴定所认为“医方使用吗啡不够慎重,对病人死亡负有较轻微责任”,随后司法鉴定医方“应用吗啡不够慎重”,存在过错。
2017年5月17日,法院公布一审判决:某司法鉴定所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不予采信,驳回原告要求陆军总医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书明确指出,“吗啡的使用与患者的死亡无关”。
案件体现了司法系统对我国安宁疗护事业的支持,有利于“优逝”理念的推广
这一判决罕见地推翻了医疗鉴定的结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追究晚期癌症患者死因责任的“普通案件”,但对医务界而言,其判决结果直接影响到我国安宁疗护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并不“普通”。
我国长期重视优生优育,但对“优逝”鲜有提及。然而,每一个理想的生命过程都应该是“优生、优育、优逝”的过程。安宁疗护是“为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患者在临终前提供减轻痛苦的医疗护理服务”,目的是使病笃难愈无可救治的患者在现代医学理念的指导下得到尽可能周到的综合医疗护理,死亡时“身无痛苦,人有尊严;心无牵挂,灵有归宿”,即所谓“优逝”。
2016年4月,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以安宁疗护为题,对不可治愈患者临终前的医疗护理服务展开讨论,强调“安宁疗护关乎患者的生命质量,关乎医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极好地诠释了“优逝”的社会意义。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对死亡的期许就是希望在生命的尽头有一个“好死”,将“不得好死”视为恶毒的诅咒,而安宁疗护恰恰反映了老百姓的这一诉求。
与大家熟知的姑息缓和治疗或舒缓治疗的概念相比,安宁疗护涵盖的范围要窄一些,只限于生命最后阶段(一般为3~6个月)临终前的医疗护理服务,目的是帮助病笃患者实现对优逝的期许。显然,安宁疗护既不同于以战胜疾病为目的的治愈性治疗,也不是让患者停止治疗,无可奈何地消极等待死亡,更不允许对患者主动实施所谓的“安乐死”。
这一判决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体现了国家在司法层面对我国姑息缓和治疗及安宁疗护事业的支持,对优逝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判决洗脱了吗啡的污名,也使从事安宁疗护的医护人员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
2017年以来,安宁疗护已频频见诸官方文件和各大媒体,使得安宁疗护工作的开展有了国家部委规章的支持,一线医护人员也因此有了开展安宁疗护的行为和技术规范。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发生在陆军总医院肿瘤科的“吗啡纠纷案”开始出现转机,以医方胜诉而告终。一审判决出来后,悬在业内同行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也使从事安宁疗护的医护人员乃至整个医学界都从中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
在这起医疗纠纷中,原告认为医方对呼吸困难的患者“超说明书”使用了可能引起呼吸抑制的药物——吗啡,使其“过早地经历了丧母之痛”,属于“严重违规”。司法鉴定的结论也认为,医方“使用吗啡不够慎重”,要“对患者的死亡负轻微责任”。
此案发生于2015 年,当时,对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允许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2017年2月9日发布并开始实行)还没有出台,因此不能作为证据对医方作出有效支持。原告得知司法鉴定结果后,将索赔金额从10 万元提高到24万元。按以往医疗案件审判的惯例,如果判决主要依照司法鉴定,医方将“负轻微责任”,需要作出一定的赔偿。可以想见,一旦出现这个结局,我国刚刚兴起的安宁疗护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损失绝非金钱所能衡量。
幸运的是,处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们非常敬业,对控辩双方以及医疗司法鉴定的意见反复斟酌,慎之又慎。法官们认真学习并接受了姑息缓和治疗和安宁疗护的理念,专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进一步征询意见,力求“深刻把握、主动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促进政法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判决书中针对“吗啡致死”的指控,以现代医学对吗啡广泛使用的实践成果为依据,对医方使用吗啡的理由和用药过程进行了专业且严谨的分析,指出:“病人具有使用吗啡的指征”,“不存在使用吗啡的禁忌”,“用法、用量亦无不妥”,强调吗啡的使用与患者的死亡无关。
这一判决不仅洗脱了吗啡的污名、还医生以清白,也有利于原告打开心结消除疑虑,给逝者以理性的交代。
安宁疗护在伦理、法理等方面还有诸多“坎儿”,需要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细致的医患沟通
吗啡案的判决也使医务界坚定了对我国司法工作的信心。至少让大家看到一种希望,以前那种医院“一上法庭就赔钱,一死人就输理”的不正常局面有望得到扭转了。
事后,也有医疗界的同行认为,本案虽然突显了司法的力量,但“此案难以复制”,“是在北京司法环境中的偶然”。还有的网友写道“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可打不起这种官司。我绝不敢给快死的患者用吗啡,我祈祷那些在痛苦中逝去的患者理解医生的苦衷”。是的,在我国还不能就姑息缓和治疗及安宁疗护工作迅速立法的当今,本案对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形成有利于安宁疗护工作的良好的司法环境,只是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样本。安宁疗护要想获得法律的“保驾护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任何新生事物的推广都需要一个过程。安宁疗护涉及生命和多重复杂症状评估后的医学干预,在伦理、医理、药理、法理诸多方面都会触碰许多以往很少遇到的“坎儿”,需要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细致的医患沟通,以及弥补诸多法律上的困惑和空白,才能获得司法长期稳定的支持。要坚持“优逝”理念,摒弃对临终患者劳民伤财“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以及对晚期肿瘤患者“生命不息,抗癌不止”乃至“死马当活马医”的过度治疗。对笃信“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普罗大众,应该着力宣传这一移风易俗的理念,建立新的“优逝”观,为安宁疗护的立法工作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的“肯定生命的价值,将死亡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刻意加速也不延缓死亡的到来”。
在安宁疗护的临床实践中,医生所面对的是一个个长期身患痼疾、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的特殊个体。此时,拯救或延长生命已经不是一个可取的医疗原则,及时转换到“最大限度地减轻痛苦,最大化地维护人格尊严”才是明智的选择。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国医师史怀哲所说:“使患者在死前享有片刻的安宁将是医生神圣而崭新的使命。”这是医生的天职,也是医生应该具有的人文情怀。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对出现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的终末期肿瘤患者,合理使用吗啡等阿片类药物以及其他措施帮助患者解除痛苦往往十分有效。在本案中,患者有使用吗啡的明确指征,是使用吗啡治疗的实际受益者。否则,患者将会在经历万般痛苦挣扎后加速死亡。
至于患方所起诉的对于吗啡的“超说明书用药”情况,事实是,几乎所有权威性的国际医学组织都倡导和认同对晚期癌症患者应用吗啡,以发挥其镇痛、镇静与改善呼吸困难的作用。合理适当地应用吗啡既不会导致呼吸抑制,也不会缩短患者的生存期,更不会加速患者的死亡。对以吗啡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安全性的过分担心是不必要的,将吗啡妖魔化更不应该。
中国药学会于2015年4月公布了《中国药学会超说明书用药专家共识》,提出“超说明书用药必须有充分的文献报道、循证医学研究结果等证据支持”,并将具体证据分为5个不同的推荐强度。这个专家共识实际上为我国医生“超说明书用药”开了绿灯。从根本上讲,医生“超说明书用药”还是为了患者的最大利益——使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最适宜的治疗,而这也是对药物说明书一出台就存在滞后性的一种弥补。重症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可使用吗啡,这已有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证据。我国目前需要的是尽快修改说明书,而不是让正确的有利于患者的临床实践倒退,让患者受罪。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医生超说明书用药,是对医生权力的阉割,弱化了医生对患者负责的职业精神。
(来源:健康报)
——吗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