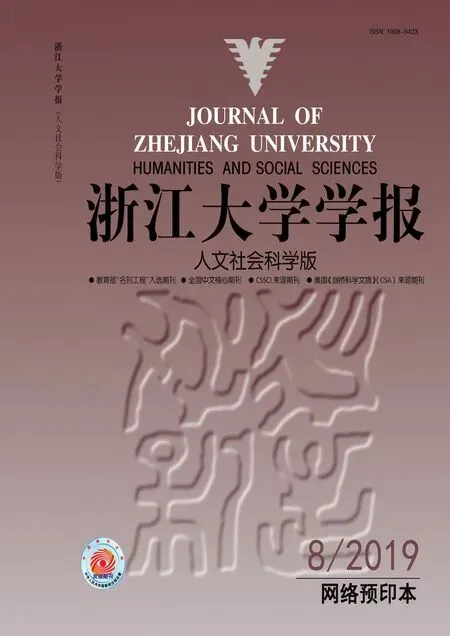词话文献整理汇编刍议
杨传庆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词话是记录词本事、评论词作、表达词学主张的专门著述,是词学批评理论的典型载体。词学史上第一部纯粹的词话丛书是况周颐辑、王文濡校阅的《词话丛钞》[1],共收词话10种,开创了汇编词话文献的新模式。之后,汇辑词话卓有成就的是唐圭璋先生,其1934年辑印的《词话丛编》收录词话60种,后经增补,共收词话达85种[2]。《词话丛编》是目前权威的词话丛书,它所体现出的词话形态观念及词话整理方法对其后的词话文献汇编影响深刻。
21世纪以来,词话文献整理蓬勃发展,不仅稀见词话渐次披露,还出现了数种大型词话文献汇编,如张璋等编《历代词话》《历代词话续编》[3]、朱崇才编《词话丛编续编》[4](下文称朱《续编》)、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5](下文称葛《补编》)、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6](下文称屈《二编》)。张璋等所编《历代词话》及《历代词话续编》共收词话与论词文章246种,朱《续编》收录词话32种,葛《补编》收录69种,屈《二编》收录48种,后三位学者均以《词话丛编》为参照,补辑汇编《词话丛编》之外的词话。除大规模汇编外,如《词学》等刊物也不断刊布新整理的词话,数量颇为可观。毫无疑问,丰硕的词话整理成果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我们首先要向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学者们致以敬意!同时,词话文献整理汇编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启发我们更进一步思考。
一、词话的边界
目前对词话的分类及整理方法大体遵循《词话丛编》,《词话丛编》所收词话约可分三类:一是原为单本专书的词话,二是由诗话、文集、笔记中辑出的词话,三是汇集词选批语而成的词话。不过,唐圭璋先生对新辑类词话有着严格的体例规定,其《词话丛编例言》云:“前人所作诗词话,诗词杂陈,非专论词者,不以入录。”“专家词集,卷首有附时贤词话者,如《珂雪词话》,亦有词后附名流评语者,如孙默《十六家词》,气类标榜,率多逾量,兹并不录。”[2]6-7他对散见于诗话、笔记中的词话以及词集评语慎加收录。反观上列诸家汇编词话,除了单本词话外,新辑入者来自笔记、诗话、论词诗词、词集评语、词籍提要等,辑自著作、论文、序跋等也不鲜见。与《词话丛编》的谨慎择录不同,“多多益善”似成为自觉的追求。诚然,每一种新辑词话自有其价值,整理者难以割舍,但是随着词学资料搜集愈加庞杂,重新汇编则有必要加以分别,而不是都挤进“词话”之中,似“全”而“杂”。
唐圭璋先生初刊《词话丛编》有甲、乙之编的设想,当有区别不同性质文献的考虑(1)《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34年)《词坛消息》之“《词话丛编》之校印”条。。今天随着词学资料的极大丰富,更应条析而列,力求清晰。如此则不至淆乱,又可保持各类词学文献的特性。如论词绝句是以韵文论词的特殊形式,具有独特的文体特点。从现有文献来看,况周颐是第一个搜集整理论词绝句的词家,其弟子赵尊岳也曾辑《论词绝句》一卷,欲入《词话丛编》乙编。其后饶宗颐、吴熊和、孙克强、王伟勇等学者都很重视论词绝句的整理研究,并且汇编论词绝句出版,如王伟勇编《清代论词绝句初编》(里仁书局2010年版),孙克强、裴喆编《论词绝句二千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可见论词绝句已然蔚为大观,若益以其他论词诗词、词集题词及填词图题词等,此类以诗词形式论词的文献不在少数,正当独立编纂。另如唐圭璋先生不录的“专家词集”所附“时贤词话”及“名流评语”,今天汇编词话多有辑录,尽管“率多逾量”,但作为词作评骘资料,辑编自然是可以的。此类“词话”往往是多人或一人评语的汇集,词话的命名往往是“词集名+词话”,如评龚鼎孳《香严斋词》者就称《香严斋词话》,评汪懋麟《锦瑟词》者称《锦瑟词话》,评曹贞吉《珂雪词》者称《珂雪词话》等等。此类“词话”与一般意义上的词话体制不同,其实质就是词集评语,而清代词集评点甚为常见,如邹祇谟、王士禛等评词之语不下千条,若能全面汇辑评点之语,或谓之“××评词”,或称“××集评语”,附以词作,清晰呈现,自较混于词话之中为胜。
那丰富的词学文献如何汇编分类?或仍可参考唐圭璋先生甲、乙之编的设想,或设正编、副编、外编之目,而大量新辑词学资料之汇编仍然使用“词话丛编”这一名称是否还合适也值得思考。毕竟唐圭璋先生是在其所见所辑的文献基础上命名为“丛编”的,而如今是某类词学文献大量出现,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窃以为,若进行词话整理,仍当尽量遵守《词话丛编》之“词话”边界;若汇编新辑词学文献,最好分门别类,体现各类文献自身的特点。
二、底本与体例
词话文献整理底本选择甚为关键,整理者应明确所据底本为何,或在总目中提供底本信息,或在正文中列示,或在叙录中交代。特别是晚清民国的词话文献,有的由出版社印行,有的来自报刊,注明出版时间及出刊年份卷号当是最基本的工作。然张璋等编《历代词话》、葛《补编》、屈《二编》于此均不无可议之处。如屈《二编》录王蕴章《然脂余韵》,计97则。其“总目”标明底本为“《小说月报》本”[6]3,正文则云“《小说月报》第五卷第八号”[6]2139,但检视《小说月报》第五卷第八号仅有12则。那是否全来自《小说月报》呢?也不可能。考察屈《二编》所录内容,很多不见于《小说月报》所载。《然脂余韵》在《小说月报》刊载是自第五卷第一号(1914年)始,至第五卷第十二号(1915年)终,后又在《妇女杂志》第一卷第五号(1915年)《杂俎》栏目续载,至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终。由于《然脂余韵》很受欢迎,商务印书馆将其汇集,在1918年出版了排印本。因此,屈《二编》所录《然脂余韵》底本应注为“《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本”,或直接使用191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更为妥当。葛《补编》未见底本书目,仅见“引用书目”,但此目缺少详细的底本信息,也没有注明晚清以来词话、论著的出版单位及时间,故而颇不规范,且时有不完善之处。如“引用书目”中的“郑文焯手批《白石道人歌曲》,宋姜夔撰,民国陈柱《白石道人词笺评》本”(2)“引用书目”作“笺评”误,应为“笺平”。见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页。。如此著录之不妥显而易见,“宋姜夔”无法撰清“郑文焯手批《白石道人歌曲》”。更有问题的是底本选择,葛《补编》所用郑批《白石道人歌曲》出自陈柱《白石道人词笺平》(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而《白石道人词笺平》中只是摘录了部分题跋。郑批《白石道人歌曲》目前所知计有四种,陈柱所见乃是郑文焯以清宣统二年(1910)沈曾植影印本为底本批校者,此批校本在郑殁后被康有为所得,陈柱从康有为子处假得过录,后入藏嘉业堂,今藏上海图书馆。故葛《补编》最好以上图藏郑文焯批校原本为底本,而非转自陈柱所录。
由于出自不同学者之手,即便是同一词学家的同一著作,也往往产生所辑词话在名称、卷数、内容多寡上的诸多不同。这主要是由辑录者在体例制定及执行上的差异造成的。例如诸家对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的辑录,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作《曼殊室词论》一卷,朱《续编》作《曼殊室词话》三卷,屈《二编》作《曼殊室词论》一卷。《曼殊室随笔》共分五部分,即词论、曲论、宗论、史论、杂论,其中“词论”部分共47节[7]。《历代词话续编》所辑《曼殊室词论》分为八节,但仅有一、四、六、七、八节辑自“词论”[3]586-596,远未将“词论”充分辑录,却将“曲论”中之“务头”辑入。另外,尚有数则辑自“杂论”,其中谈东坡“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与新会方言“失教”二则与词学毫无关系。这着实令人费解。而屈《二编》与《历代词话续编》所录完全相同,顺序也一致,当是编者直接取材于《历代词话续编》,并未翻阅《曼殊室随笔》加以辑录。朱《续编》将“词论”分为两卷,又从其他四论中辑出涉词文字作为第三卷,总计辑录202则,名之“词话”。其所辑所编与前二者相比全面可靠,但也偶有逸出体例者,如据“曲论”所辑“必传之作”[4]3017-3018、“格调之演变”[4]3018-3019二则与“凡例”所定之“收录标准”不尽符合。
三、新辑词话的辑录对象与命名
从诗话、笔记、杂著中辑录论词之语作为《词话丛编》的补充,夏敬观在1942年《汇辑宋人词话》时即已明确提及,他说《词话丛编》“凡前人诗词话、诗词杂陈者,不录”,“兹编从宋人笔记诗话,汇录成书,意在补《词话丛编》之不足”[8]。与夏敬观从有宋一代笔记、诗话中汇辑相比,今天的汇辑显得零星,随遇随辑,对新辑词话辑录对象的选择缺乏通盘考虑。某些词学名家留下了大量词学文献,但并无词话类专书传世,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整理者往往辑录其词学资料编成新的词话。比如《词话丛编》之《张惠言论词》《彊村老人评词》,屈《二编》之《曝书亭词话》,葛《补编》之《大鹤山人词话续编》均是如此。既然这种操作方式得到认可,那在汇辑一代词话时应有统一安排,如陈维崧、尤侗、厉鹗、戈载、王鹏运、张尔田等自是不可或缺的辑录对象。
新辑词话从诗词话、笔记中辑出者,其命名常是“书名+词话”;从某词学家的众多文献中辑录者,或以人命名,或以号、斋等命名。因编者不同,相同的词话文献命名不同,如《铜鼓书堂词话》在张璋等编《历代词话》中称《榕巢词话》(3)《榕巢词话》实际是查礼的另一部独立词话,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同样是取材于《百名家词钞》,朱《续编》和屈《二编》分别题作《名家词钞评》三卷和《百名家词钞词话》一卷(屈《二编》仅录聂先评语)。另外,辑者据其他文献所引用“某某词话”,就认定有这一词话,并以之命名,也易生干扰。如葛《补编》从《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八辑得“无著庵词话”两则,便列目“《无著庵词话》,朱祖谋撰”[5]6。此或为朱祖谋所言、况周颐记录的两段论词之语,专立“无著庵词话”之目让人误以为朱祖谋撰有此书。至少编者应有明确说明,告知其来源与命名之由。
窃以为对词话的命名应尽量保持原文献名称。如屈《二编》所录杨寿楠《云薖词话》,实际上就是《云在山房类稿》中的《微波榭词选书后》,编者易原名而冠以新名,并且关于“云薖”之命名毫无交代。杨寿楠在无锡的园子叫“云薖园”,时人偶称其为“杨云薖”,想来编者便据此命名了,窃觉颇为草率。此外,新辑词话当按照以人题或以书题的命名原则。以人为题,其人如有多种词学著述,则当分书罗列,分别称之,不宜统称某某词话。如朱《续编》录顾随论词之语为《驼庵词话》九卷,内收《东坡词说》《稼轩词说》《论王静安》及《驼庵诗话》论词条目、《顾随诗词讲记》涉词条目、《顾随全集》涉词之语等,以顾随之号“驼庵”命名;而屈《二编》录顾随论词之语为《苦水说词》,内收《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倦驼庵词话》,以顾随另一号“苦水”命名。《倦驼庵词话》也由《驼庵诗话》中论词条目纂辑而成,但与朱《续编》数量不同,仅录《驼庵诗话》《分论》之部的少量内容。按常理,由“驼庵诗话”辑出,应命名为“驼庵词话”,但屈《二编》称“倦驼庵词话”,又以顾随书斋“倦驼庵”命名,再转一层。实则将顾随论词之著分别列出而不统一名称或更为清晰明白。
四、甄别与求精
词话文献林林总总,整理汇编时不可为求“全”而照单全收,丢掉了甄别意识。对于已刊载的词话无须重加辑录。如沈雄的《柳塘词话》,张璋《历代词话》、屈《二编》、葛《补编》均据《词话丛钞》将该词话独立,实则此所谓《柳塘词话》全部出自沈雄编撰《古今词话》,唐圭璋先生当年对此已有明确认识,故弃《柳塘词话》不用。并且《词话丛钞》本《柳塘词话》并未将《古今词话》中沈雄论词之语辑录完整,《古今词话》中沈雄之语标明“沈雄曰”“柳塘词话曰”“沈偶僧曰”,其中署“《柳塘词话》曰”计98则,署“沈雄曰”或“沈偶僧曰”以及未署名但系沈雄语者总计148则,共246则,而《词话丛钞》本《柳塘词话》仅录191则,失收50余则。三家汇编沿用是本而未详察,致《柳塘词话》仍非全貌,故单独刊出意义不大。对于摘抄拼凑的词话,更须仔细甄别。如石林凤编《蔗农词话》两卷,计119则,主要记述词之本事,其主体内容多抄录自前人所著诗话、词话及笔记,诸如《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耆旧续闻》等等,几无个人见解。另如南社刘哲庐之《红藕花馆词话》,或是全部抄袭,或袭用而略加发挥,或拼凑嫁接前人之语,基本上是一部抄袭拼接且不注明来路的词话,其抄袭对象主要为《词源》《词苑萃编》《词学集成》《古今词话》《历代词话》等。此二例启示我们整理、研究晚清民国的词话要考虑其辗转因袭之处,对原创性较差的词学文献要有充分认识。
今日汇编词话文献要较以往更为便捷,学者们对于求“全”都有共识,也颇为努力。但同时还得考虑求“精”,在“全”编难以短时实现的情况下,不妨考虑“精”编,将理论价值低的加以筛除。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词话文献甚为纷繁,但质量却参差不齐,称得上“词学家之词话”者数量并不多。所以晚清以来的词学文献整理必须从冗杂的文献中披沙拣金,发现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如此方能对这一时期的词学进行精准建构。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