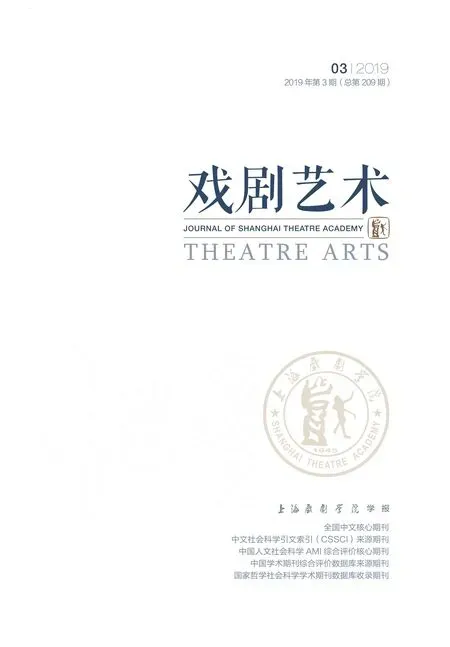“查明哲之谜”解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戏剧界,查明哲越来越像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他是第一个被冠以“新世纪杰出导演”称号的艺术家。关于他的导演艺术,北京和上海先后于2005年、2009年、2014年举行过三次专题研讨会,此外还有几十次关于他执导剧目的研讨,以及大量的相关评论。但令人奇怪的是,似乎探讨越多,反而越使得舆论中心的查明哲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基于此,笔者谈谈自己对查明哲导演艺术的认识,尝试进一步破解“查明哲之谜”。
一、叙述技巧:一剧一格,演出“悬念”
在我看来,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机遇是可以从艺术以外的因素说起的,应该从舞台艺术创造去解读查明哲之谜。
1988年,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在当年第1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叫做《扎哈罗夫之谜》。论文探讨了苏联导演扎哈罗夫舞台艺术一直保持魅力、总是受到观众追捧的原因,除了剧本选择的厚重、演员团队的给力、各个艺术生产环节的协调这些客观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扎哈罗夫剧目演出中戏剧叙述技巧所显现的个人魅力了。查明哲阐述这个问题的起因,来自他在1988年担任扎哈罗夫的副导演时的亲眼所见和细心感受。1988年,扎哈罗夫应邀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苏联名剧《红茵蓝马》,查明哲作为副导演小试锋芒,剧中浪漫主义的抒情基调和人性层面的精湛揭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苏联戏剧的光环和扎哈罗夫的耀眼,分散了中国戏剧观众对查明哲艺术的注意力,聚焦点没有放在他身上。但是我相信,《红茵蓝马》的诗性创作方法和抒情浪漫基调对查明哲的影响不小。几年后,他到莫斯科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学习,在追随扎哈罗夫的时候,延续并加强了这种影响。
在观察扎哈罗夫排演《红茵蓝马》的过程中,查明哲发现,导演艺术的关键就是把控戏剧节奏、营造戏剧氛围、设计矛盾冲突、呈现生动的细节,凡此种种,形成“演出悬念”,即如魔术般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总有要看剧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的急切愿望,但又让观众永远猜不到下面的剧情会怎样发展、下面的场面怎样出现、下面的行动有什么结果,高潮迭起,细节生动,场面感人,一直持续到矛盾解决、行动结束。查明哲一方面眼见扎哈罗夫在舞台上指挥若定,高招迭出;另一方面观察到,生活中扎哈罗夫话语不多,总是若有所思,即便在台前台后或者在剧场里转悠时遇到人也只是抿嘴微笑。他的一抹唇髭,让其抿着的嘴唇似笑非笑、含蓄有加,更加增添了他的艺术创造状态的神秘感。用查明哲的话说,扎哈罗夫整个人、整个艺术气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工作起来像一团燃烧的火,生活中像一个猜不透的谜。这“谜”和“火”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扎哈罗夫传授的舞台叙述秘诀是:保持观众的欣赏兴趣甚至吊足胃口,但是永远不要让他们猜到下面你给他们看什么,出现什么场面。[注]此处为间接引述,是笔者与查明哲就他的论文内容进行的有关扎哈罗夫的交谈。详见吴戈:《扎哈罗夫之谜》,《戏剧》,1988年第1期。听起来,这就让观众在欣赏时进入了一个“猜谜”一般的过程。这是一个魅力十足、趣味横生、丢不开放不下的“谜”。
不知道查明哲后来猜谜猜得如何。
1992年,查明哲背起行囊,远赴莫斯科,身份从扎哈罗夫的副导演,变成了扎哈罗夫的博士生。四年的朝夕相处,从远观到近察,从短暂的共事到长时间从游学习,扎哈罗夫之谜在查明哲心里揣测得如何,不得而知。查明哲学成归国后,除了论及他离开俄罗斯之前与导师的那段“剧院教堂”的对话外,似乎没有更多地说起导师扎哈罗夫。有趣的是,查明哲追随扎哈罗夫,为解“扎哈罗夫之谜”而去,结果,回国后,在众多的查明哲舞台艺术研究者、观察者、评论者眼里,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谜”。
查明哲的剧目以铁血、硬骨、雄奇的特点登上中国当代戏剧舞台后,立刻成为抢眼的风景。在众人的眼睛里,各种观察角度看到的查明哲显现了各种各样的风采,他似乎有各式各样的追求,因为他自己的艺术创作一直在发展变化,而且丰富多样。一种风格、一种观念、一种手法或一种角度似乎很难概括他。于是,研究越多,角度越多,评价越杂,他就越显得像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多棱镜。常常是每个人都只看到他的一个面或者几个面,可谓“一时一地,一剧一格”。众说纷纭中,他的艺术创造能力和艺术追求指向,越来越像个谜。
我以为,查明哲从导师扎哈罗夫那里学到的舞台叙事本领,就是一剧一格的叙事原则,就是制造“演出悬念”的本领。除形式美感、叙述节奏、舞台意象等,“演出悬念”实际上是导演艺术家面对观众引而不发、秘而不宣却又十分直观的艺术功力展现。剧目演出赏心悦目的内在力量正由此传递。
从《死无葬身之地》开始,我们看到查明哲的舞台叙述技巧对观众心理的掌控:一开始是欢快的歌曲、轻松的节奏、抒情的氛围。突然,枪声响起,把戏剧欣赏中毫无预警提示的观众吓了一大跳:二战当中抵抗法西斯的游击队员中了埋伏被捕。接下来,游击队员被关进牢房。法西斯分子对被捕的游击队员粗暴地推推搡搡,设计的造型装置当中,铁门刺耳的碰撞声、镣铐的噪音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观众的耳膜和神经。呵斥声、铁门碰撞声静下来以后,是被捕的游击队员们死一般的短暂沉默。这种心理压力的传递和不祥气氛的营造,让观众透不过气来。《纪念碑》的一开始是一个惶惶不安的少年战俘等待自己厄运时的自我辩解,然后是绝处逢生的获释——他这个在战争中干了杀人强奸之恶行的罪犯与被害者的母亲共同生活。一对仇人在战争废墟与人性荒原上跋涉,步步惊心的演出悬念,点点滴滴铺垫下去,直到23个被奸杀的女孩子的尸首被找到,这时,一顶由23袭破碎的连衣裙构成的“人性招魂幡”——战争纪念碑冉冉升起,再推出人性辨析、宽宥与和解的沉重问题。舞台叙述张弛有度、细致缜密,又常常有出人意料的场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抒情和温情中批判战争的残酷、歌颂爱国情怀,间性的色调与交替的节奏让观众如醉如痴。《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开门见山。那座矸子山有着苦难中生存的男人女人们的“底层基座”,它带着物质条件与精神世界的对比和体量,一开始就堵在观众眼前,横亘在人们的命运中。之后在矸子山上的攀爬、翻滚,以及大调度、区隔处理,让观众感到了演出叙述中戏剧时空处理的精巧自如。观众完全想不到那“山”的形象的变化运用和舞台意象被处理得如此出神入化。就拿查明哲刚刚执导的《生命行歌》来说,泰戈尔与白居易的诗的意象交替出现,护士日记被串连,一台临终老人们的元旦晚会从动员、准备到演出被贯穿起来,尤其是表现为死亡与生机变奏的太平间的死亡之车一次又一次地过场、打断剧情的处理,让一个听起来觉得可能不会好看的题材,演出得精彩之极……
例子很多,恕不繁举。但是这些已经足够说明查明哲导演艺术中的“演出悬念”所带来的魅力了,这是他从老师扎哈罗夫那里获得真传又发扬光大的结果。
二、深层底蕴:伟大的人道现实主义
查明哲是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整个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导演艺术家。中国那次思想解放运动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肯定,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深入人心和深厚运用。
查明哲念本科、硕士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正是对戏剧中出现的“庸俗社会学”和“工具论”展开批判的思想高地,是强调“人学”核心与艺术本体的大本营。在谭霈生先生、徐晓钟先生的理论倡导和实践引领中,查明哲奠定了最重要的“人学核心论”与“艺术本体论”的学术基础。关注人、表现人、塑造人成为查明哲思考社会、观察生活、判断价值、投注热情、表达理想的切入点,也成为多年来他坚持不懈、精耕细作的动力。他的舞台艺术创造贯穿了人道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正是查明哲导演创作具有震撼力、厚实感和深刻性的原因所在,这是“查明哲之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查明哲的舞台艺术创造涉及许多历史事件,但他总是以“人”为表现核心,总是关注历史事件、历史当口、历史细节中的“人”的思想、情感、选择、行动。历史事件只是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历史当口只是人物行动的时间场景,历史细节只是人物活动的人文布景,舞台上要聚焦的,是这时代背景、时间场景和人文布景中思考、选择、行动的人。这些观念,都深深地存在于查明哲的艺术认知储备中。它们慢慢发酵,成为他的艺术创造的基本底色。
查明哲将时代思潮成果和文化自觉意识成功地转化成了自己的艺术禀赋,一路行来,风光无限。在“穿越战争硝烟”“走向民生沃土”“重铸民族精神”“关注历史传奇”的不同创作阶段,深厚的人文关怀、犀利的人性解剖、崇高的人格塑造、沉郁的人世悲悯,成为了他的艺术创造追求中的“贯串动作”。
查明哲独立导演大作品,始于1989年4月。他为山东烟台话剧团执导一部叫做《半月岛的女人》的剧目,表现的是海边渔岛女人们的艰难生活与苦涩命运。她们在压抑中坚韧地生活着,在憋屈中无助地吞咽苦水的同时,还追寻着欢乐。查明哲把历经坎坷的海边女人色彩斑斓的情感状态与层次丰富的人性内容表现出来了。在烟台公演的时候,观众说这样表现海岛女人是头一次,令人耳目一新。该剧的“新”在于命运轨迹中显现出来的人性活态,整部戏没有因循创作旧路去展示苦难本身,而是表现苦难中的人性。
1997年的《死无葬身之地》、2000年的《纪念碑》、2002年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03年的《青春禁忌游戏》……一个风格硬朗的导演崛起在中国戏剧舞台,一个以直面人生、拷问灵魂、追问真相为己任的导演激活了中国剧场,一个针对轻歌曼舞中亵渎崇高、娱乐放纵中践踏人性、虚脱疲软中放弃理想的文化时弊进行“输血”“补钙”“增铁”、益元气、提振精神的导演站在了民族艺术和国家文化的阵地前沿。无论是民生关怀、战争情怀、文化情怀、家国情怀的表述,还是不同剧种、不同地域、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表现,查明哲总是把“人的表现”放在首位。变态的法西斯与不屈的游击队员(《死无葬身之地》),在救赎与复仇之间追问人性之可能性的母亲与罪犯(《纪念碑》),为祖国而战的士兵(《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为民族向死而生的铁血士兵与冷娃(《中华士兵》),连接在家族、宗族和国家关系上的乡绅草民(《淮河新娘》),揭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敢为人先的小岗村“18棵青松”(《万事根本》),选择承担苦难的下岗男女(《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这些都聚焦于“人的表现”。我曾经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上发表过文章《“形象种子”与演出形象:查明哲的舞台美感》,那是就艺术创造与演出形象而言的。这里,我特别想要说,在查明哲的所有导演创作中,“人”就是他艺术创作的“形象种子”,是他的写意底色,是他的抒情基调,是他的温情内容,是他的思考高度,是他的探查深度。2005年《中国戏剧》举办的“新世纪杰出导演系列研讨——查明哲”研讨会上,我曾经说:“查明哲丢不开放不下的就是‘人’,就艺术家而言,最大的无知就是对人的无知,最大的发现就是对人的发现。他曾经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面对枪炮刑具还是宴席酒具,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置身逆境,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保持人的尊严、追求人生意义,都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查明哲舞台追求的总体形象种子、艺术创造的最大母题、表现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人’。他逆社会心理的‘俗化潮流’而动,‘圣化’人性,格外有力;逆潮而行,格外艰难滞重。在我眼里,他就是在道德卫城里做着‘困兽之斗’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他常常把自己放到戏剧里去,通过戏剧人物、场面和细节构成的形象叙述,让观众猝不及防地体验那种深刻的孤独、怆然的悲壮、迸发的激情,因此他的剧目有分量,他的舞台呈现有撞击人心、针砭时弊、灼烫情感的内容,(能)感染人和吸引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忧郁的诗人,一个价值的守望者,一个人性的修复者,一个生命的讴歌者,一个理想的顶礼者,一个艺术的苦修者。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他作品深沉凝重、感人至深的精神品格。人的尊严和艺术的尊严,其实是查明哲明确表达在他所有作品中的一种执拗的选择:在文学艺术作品轻歌曼舞、声色犬马、饮食男女、饭后茶余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人们习焉不察、欣欣然的享受,成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主要消费热点的时候,查明哲的追求,就成为了我们值得珍视的一份坚守。新世界的中国戏剧需要这样的建设者。”[注]吴戈:《查明哲给中国新世纪剧坛带来了什么?》,《中国戏剧》,2005年第7期。这段话后来被专家们一再引用。
我至今都认为,“00后现实主义”对查明哲的概括,是一种语焉不详的模糊概括。要我说,不如“人道现实主义”对查明哲的概括来得明确和精准。查明哲从俄罗斯留学回国,大约1996年到我所供职的云南艺术学院讲学,讲述了他与导师扎哈罗夫临别的问答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剧场像是教堂。后来,这在中国戏剧界成为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实际上,查明哲对剧院的确是有宗教般虔诚的情结的,他甚至是把剧场作为人性修复、人性救赎的圣殿去热情投入工作的。他是圣殿里辛勤的圣徒。我曾说:“查明哲导师扎哈罗夫的‘剧场是教堂’的比喻已经广为人知,但查明哲喜欢这个比喻其实是与他对戏剧文化的功能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遏制人性恶、劝导人性善,讴歌理想,构建大写的‘人’;抚慰情感、升华人性、美化人生,是剧场作用于观众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目标。”我无法不把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宣泄”对于人的功能联系起来,也无法不把他与宗教劝善止恶的精神引导及人性建设联系起来。止恶,需要救赎;劝善,必须引导。查明哲在他的剧目中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开垦着人心、修复着人性、呼唤着良知、托举着价值、赞美着淳善、歌颂着理想。查明哲的现实主义有反思,有批判,有鞭笞,但是更多的,是挣扎向上、倔强攀爬、坚韧生长、百折不挠、向死而生!即便是悲剧,也是仰天长啸的“黄河浪千迭,滔滔英雄血”的壮美!即便在底层,也会在矸子山上做挺立的男人女人!即便在法西斯的地狱里熬煎,也让人的尊严和英雄的勇气坚持到最后!即便在战争的焦土、人性的荒原上,也在寻找人性复活的可能性!即便是在立秋时节的飕飕凉风里,也可以期盼立春的暖意。
历史的、现实的、战争的、和平的、深远的、厚实的、民生的、草根的……一切社会历史内容、芸芸众生百态在“人学”位置上显影,在“人本”的支点上发光,在“人性”的构建中接受检验,做到这些,剧目就厚实了,有力了,深刻了。把生动的形式、诗情的表达、象征的意境用来显影、发光、检验,演出就生动形象、细腻深刻、丰富多彩、赏心悦目了。
三、源头活水:高超的跨界杂取能力
在查明哲充沛的精力、富有创新意识的勇气和丰富的实践面前,研究者追踪的目光显得迟疑、判断的口气显得犹豫,相关研讨的结尾总是开放的、意犹未尽的。形象大于思想,实践先于理论,事实总是这样。
在公众视野里,查明哲的舞台艺术创造,经历了一个从现象到话题的过程。这首先成为一种现象,然后一次次地成为话题。“现象”就是,各种文化节庆、戏剧赛事遴选作品时总会选择查明哲导演的剧目;各大剧院选择主创人员时总会争先恐后地邀请查明哲去执导戏剧;“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精品工程”和其他重要的评审机构举办的表彰仪式上,几乎总是能看到查明哲的身影。于是,查明哲渐渐成为话题,成为热点话题。我们看到,中国近十多年来关于戏剧舞台的重要研讨会或者重要话题,也总是与查明哲有关。其实,关于查明哲的话题分两种,一种是由他而起、生发开去的关于中国戏剧发展全局的话题,诸如“现实主义”“增铁补钙”;一种是研讨查明哲个人风格的,诸如残酷虐心、诗意温情、哲理反思、民生人本、人文情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对查明哲研讨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就都呈现出来了。
但是,可以发现,以往集中的话题研讨或各种各样的评论,大家的关注焦点主要还集中在查明哲导演剧目的思想力度、人性深度与生活厚度上,相对而言,对他的艺术创造力的研究、演出形式美感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盘点一下查明哲导演作品所涉及的领域,除话剧之外,有京剧、歌剧、评剧、黄梅戏、越剧、川剧、秦腔、音乐剧,还有大型晚会和电视剧。从艺术领域上说,查明哲和许多杰出导演一样,都有“跨界”创造之举。一方面,这是导演艺术家才能的显现,是其自身能力的延展,他要让充沛的创造力惠及更广的领域;另一方面,这也是导演艺术家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体现的是导演艺术家的自我学习能力,尤其是体现了一个受外国文化滋养的导演艺术家在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时的自省的意识和自觉的实践。艺术自信、文化自信应该体现在创造自信当中,这一方面,供研究者、评论家探索的空间还很大。
查明哲是一名跨界艺术家,他以一个演话剧、学话剧、导话剧的艺术家走向别的剧种甚至别的艺术样式,其实从1998年就开始了。他为江苏省京剧院导演过京剧《青春涅槃》,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导演过黄梅戏《风雨丽人行》。之后,他为辽宁省歌剧院导演过歌剧《沧海》,还作为执行导演推出过28集电视连续剧《好汉的梦》。他执导过甘肃省京剧院的《西域星光》,还推出了大型文艺晚会,如2000年文化部春晚、2002年《华夏群星颂紫荆——庆祝香港回归五周年》。只是,“战争三部曲”太抢眼,一开始就让观众的注意力聚焦在外国经典和战争硝烟中的人性解剖与歌颂上。不仅仅是查明哲的跨界行为被忽略了,即便是《青春禁忌游戏》这样虐心尖锐、振聋发聩、广泛传播的剧作,也没有受到舆论界、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回顾查明哲的导演艺术生涯的时候,这种缺憾是应该补上的。
继黄梅戏《风雨丽人行》之后,2003年,查明哲再度执导黄梅戏,为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排演罗怀臻编剧的《孔雀东南飞》。“查罗版”《孔雀东南飞》的新意,主要来自思想情感、内容表达的形式感。我注意到,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突出了黄梅调低回婉转、一咏三叹的特点,以此去吻合这一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故事之凄婉的基调。所以,唱,成为故事发生的音乐场;唱,成为叙述故事的主要手段;唱,成为主人翁直抒胸臆的倾诉口;唱,成为戏剧铺设抒情氛围的诗意平台。实际上,音乐体正是中国戏曲的基本特征。但是查明哲在这个剧目的演出形式的创造当中,把音乐性用到了极致。一般地,传统戏曲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强调音乐的抒情性,各种唱段阻断或者滞缓了戏剧动作的发展。但是查明哲强化歌唱带来的效果恰恰相反,他用音乐、唱段延续动作发展的情绪,铺设矛盾冲突的情境,叙述动作发展的过程。于是,歌队群众混融的演唱叙述体出现了,并贯穿始终。群众演唱者帮腔、垫场、叙述,他们既是戏剧事件中焦、刘爱情悲剧的见证者,又是这个爱情悲剧故事的传播者,还是剧情发展的叙述者。功能多重,效能彰显,这显然是汇通中西、深谙传统的学院派导演查明哲在演出形式上别开生面的创造。群众演唱者像是西方经典演出中歌队的变形,也像是中国传统戏曲中帮腔的重现,二者融合,天衣无缝,化用得水乳交融。而且歌队帮腔走到前台,走到剧情中,这就有点别出心裁了。更独特的是,查明哲把一些内在隐情、心理动机场面化了,让观众在视觉形象中感受生命、判断人物。譬如其中有让一些观众“受不了”的场面:焦仲卿和刘兰芝两小无猜,在终成眷属的新婚之夜,情眷眷意绵绵的年少夫妻入了洞房、上得婚床,万料不到焦母爬上了床,睡在焦、刘二人中间。舞台正中那张大大的床,成为一个象征空间——正是焦母阻隔了焦、刘的爱情空间。这样,焦仲卿过家不敢入的剧情,焦、刘二人在织布机房偷偷幽会的细节,前序场面中的活泼野趣、青春浪漫与新婚之夜的有苦难言、羞愧难当的对比,就成为生命困境的一个形象说明,框定了一个家庭生活的关系格局。这可能是夸张的,但确是生动传神的。一个家庭的三人关系就定格在那个场景,让人过目难忘。查明哲导演的智慧,在于用形象说话,用场面概括,用细节强调。黄梅戏《孔雀东南飞》获得第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导演奖,入选“国家精品工程”。
2005年,查明哲在四川省川剧院执导《易胆大》,获得中国艺术节、戏剧节、文华奖等评奖机构颁发的各种奖项,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这些奖项实际上包含着对导演艺术家的充分肯定,尤其是标志着一个话剧导演已成功跨界到戏曲领域。其实,“查版”川剧《易胆大》比起“查罗版”《孔雀东南飞》面临的挑战更大、更严峻。“川剧《易胆大》是著名剧作家魏明伦1980年的创作,并由自贡市川剧团同年推上舞台,曾经轰动一时,接着又被省内十多家剧团及云、贵、川、湖南、湖北等省剧团移植演出……”[注]杜建华:《传承优秀剧目 造就川剧名家》,《中国戏剧》,2006年第 4期。在这样密集的被搬演的历史中,新的演出,一定要有新的高度。川剧研究者、评论家杜建华的评价是:“这个创作于二十多年前的剧本基本未作改动,但在舞台呈现上却给人以别开生面、焕然一新的质感,其中有些成功经验是值得认真研究并推广的。”她所说的成功经验是:“优秀话剧导演执导川剧或者戏曲,对于丰富和完善川剧舞台表演手段,《易胆大》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注]同上。《易胆大》演出后反响热烈,备受推崇,研讨会上大家众口一词地提到了查明哲导演艺术的动作整体性、场面细节感、舞台空间格局和演出形式感。浓郁的方言特色,鲜明的巴蜀风情,独特的码头、梨园、茶馆,都构成了浓郁的乡土文化。袍哥霸地、戏子在地理空间漂泊的生命状态,都构成表面和内里的尖锐冲突。这些,应该首先归功于魏明伦。不过,查明哲导演的功劳在于,他把这些元素集中了、提升了、渲染了。查明哲为这群人创造了一个麻、辣、烫的生活空间,渲染了泼辣诙谐、嬉笑怒骂、火爆激烈、酣畅淋漓的氛围,使川剧与这种生活空间相匹配。在川人、川话、川剧、川传奇生活表现和社会传奇里,梨园、码头这些草根生存状态的典型场所,就生动活跃起来了,显得格外相宜。厚重的剧本,“给力”的演员,都是这台演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但是,演出品相,却要靠导演艺术家的创造。李春熹评价说:“昆、高、胡、弹、灯多种声腔艺术,清唱、帮腔、伴唱各种演唱形式,这些川剧传统在《易》剧里都有着丰富多样的呈现。川剧表演上的特点和绝活如褶子功、扇子功、藏刀、变脸等的运用,也是《易》剧吸引观众的看点……”[注]李春熹:《风格、人物及其他》,《中国戏剧》,2006年第4 期。有一位观众在网上表达自己看了《易胆大》后的观感:“川剧传统的东西在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看上去有耳目一新之感。”[注]参看黄维钧:《草根本色,现代品格》,《中国戏剧》,2006年第4期。旧材料、旧元素,如何耳目一新,就需要新调度、新调配、新组合。运用手段浓墨重彩地把川剧的特点充分渲染,表演上丝丝入扣地表现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最重要的是,特色、绝活还是那些特色、绝活,但是当它们融入剧情的发展、进入人物的个性时,这些特色、绝活就不是传统炫技的存在物,而是剧情发展和人物刻画的有机构成部分了。这样,当然就会在传统的东西里呈现出耳目一新的效果来。所以,该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查明哲尊重川剧传统,还在于他创作《易胆大》的时候对川剧传统的创造性的取舍和整合。
《我那呼兰河》(2008年)与《孝庄长歌》(2016年),两个戏前后相隔8年,主演冯玉萍成为梅花奖得主。这两个剧目,都是查明哲愈加圆熟地驾驭戏曲特点、展现戏剧魅力的成功范例。查明哲导演对“落子”“蹦蹦戏”发展过来的长于说唱的评剧做了更加戏剧化的推进。首先,《我那呼兰河》不是单一的说唱。其次,它不是以一角儿为主而有多个矛盾冲突于时间线索中。第三,也是最抢眼的,该剧配合关东女人的传奇故事,体现出小人物大线条、小事件大背景、小乡村大色块、小恩怨大情感、小地方大气象的特点。这样一来,乡风民俗与天下风云、私仇恩怨与国家危亡纠结在一起,让各自讨生活、奔前程的小人物们又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共同的命运道路上,做亡国奴受尽欺凌压迫或者不做亡国奴进行殊死斗争,种种人物的行为像一条条溪流,汇入呼兰河,奔腾咆哮而去。《我那呼兰河》的恢宏气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改评剧给人的旧时面貌。显然,查明哲对评剧在今天的新发展是有贡献的。《孝庄长歌》表现了皇家气派,刻画了孝庄太后这一人物,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路子。查明哲为戏剧找到的“形象种子”,就是“格桑花,巍巍宫墙中顽强开放”。这“种子”不仅是一个形象,还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是动态的。这是查明哲对“种子”的培植,是对“形象”的定位。一个逐渐舒展开来的生命,一朵慢慢开放的小花,当然离不了宫中的权势争斗与心机较量。不幸的是,孝庄与多尔衮从两小无猜、萌生情愫,到成年后无奈分离,最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公私难辨、情仇拌杂的情况下,走完了“心有余情难相诉,咫尺相隔如隔山”的人生。赢了人生负了情,这人生如何评价?有人评价说:“深沉隽永的大义悲歌,端庄大气的评剧新形象,大开大阖(合)的戏剧处理,对舞台诗意化探索的多元表现,让大型历史评剧《孝庄长歌》有了不同以往的崭新气质,它将评剧表现带向了一个新高度,开创了评剧的大境界……成为评剧发展史上的辉煌新篇章。”[注]张彤:《〈孝庄长歌〉:一曲长歌,开辟评剧的大境界》,《新世纪剧坛》,2016年第5期。
秦腔《西京故事》,也是使查明哲获得极好口碑的一部跨界导演作品。查明哲建组开会时,面对剧团的演员,说了自己作为话剧导演进入秦腔艺术领域的心愿。他说,这个戏,他要“以歌舞演故事”,要把秦腔的传统积累都拿出来,也请演员们“把身上的绝活都拿出来”,“照单全收,我都要”。[注]参见马也:《查明哲导演艺术论——“00后现实主义”的崛起与“导演时代”的到来》,《文艺研究》,2014年第4 期。剧目演出时观众听到的,是多年没有听到的地道的秦腔传统唱腔:滚白、苦音慢板、苦音尖板……观众看到的“唱念做打舞”,确实源自传统又不拘泥于程式,化用得恰到好处。幕启时分,城市棚户区住户一亮相就是台步身段,电线起火时众人的出手救火、过场、人们在搭建的平台上的大翻、主人翁罗天福一家挑着担子迁徙入城等动作,一望而知来自戏曲身段的改变和化用。后来罗天福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与撕心裂肺的唱腔表演,无不伴随着训练有素、规范到位的戏曲身段表演,包括蹉步、跪步、碎步、劈叉等。尤其是房东的儿子金锁(西京人,一个都市混混)一角用了武丑的表演身段,这就把都市混混的那种猥琐的机灵、市俗的狡黠表达得生动传神。整个剧目演出中所唱的传统声腔不是为了显示地道或原汁原味,而是配合主人翁命运的走势。到了心疼、命苦、透心凉的时候,苦音就唱得“苦”到了位,唱得撕心裂肺,让观众因为一个大男人捶胸顿足的恸哭而动容、动情、动心地思考:乡村向城市动迁的工程,究竟有没有准备好?城市准备好接纳乡下人,乡下人融入新生活,其实有千难万难。人与树的形象和场面有着特殊的存在意义或者言说指涉,其实这种设计安排正起到隐喻的作用。就那棵生机蓊然的唐槐和乡下的两株六七百年的紫薇大树,就像那位总坐在树下的高人东方老伯。他是一个沉默的智者,守住的是足下的土地和大树的根。他的沉默与大树的伫立,对于跟前心思骚乱、情绪摇摆、东奔西跑的人群来说,像是一种对比、一份沉思、一个提示。隐喻、象征的运用,是意味深长的。
水深流缓,多智言寡。查明哲导演,也像那位沉默不语的东方老伯一样,坐在树下看风景,自己也成为风景。他和树之间并不交流却相依为命。究竟人与树、树与人之间是何种关系、如何交流,谁也不知道。这也像是一个谜,任人去猜想。查明哲与他的舞台艺术之间,也就像东方老伯与那棵根深叶茂、年代久远的唐槐之间那般,两位一体,异象同生,人树合一。如此,才能解读查明哲艺术创造之谜。毕竟,那棵艺术之树是查明哲种下、培植、呵护多年后成长起来的。与自然界的树木不同的是,查明哲那些千变万化的舞台艺术形象构成的“艺术之树”会说话、有表情、有温度、有动态、有变化,枝、叶、花、果都有纹理走向和色彩光泽,构成整体气象。从查明哲导演那里问不明白的事儿,可能“艺术之树”本身已经活灵活现地体现、表达出来了。问题在于,查明哲舞台艺术的那棵大树已经树冠蔽日、树枝流云,若看得不真切、不仔细、不深入、不全面,都会影响对查明哲艺术创造之谜的揣测。
那么,说到底,他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