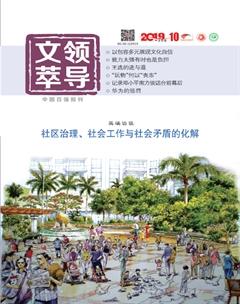社区治理、社会工作与社会矛盾的化解
徐屹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首次将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是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展。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究竟什么是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又为何特别重要?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有什么关系?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有何积极作用?为此,我们专访了原清华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两岸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社会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任主席陈社英教授。
管理与治理的区别
《领导文萃》: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并把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但究竟什么是社会治理,与以往所说的社会管理到底有什么区别,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对此,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陈社英:其实管理和治理本来并没有太大区别。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迅猛进展,治理一词在西方学界被赋予新的含义,形成了一股对传统或狭隘做法“离经叛道”的新管理理念,甚至被称之为“无政府(统管)的治理” 。这一新理念出炉便得到迅速传播,从政治学、公共事务到社会经济研究各个领域,从英语世界到欧洲其他语言国家,在各种语境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包括联合国机构官方文件都不厌其烦频繁使用。联合国还成立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了一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对治理理念的形成完善和在国际上的传播(尤其在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学者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例如治理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家James N.Rosenau,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对治理的概念作了重新界定,将其与传统的政府统治、管辖或管理区别开来。这一区别关键在于,新的理念认为权威有各种范围而非政府独享,即可以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形式,因此治理是一个可分为两部分的系统。例如,各国政府及国际体系长期主宰着公共事务,但伴随而来且越来越明显的是另一多中心系统,由多种其他集体获得许多不同范围的权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且持续不断地与以政府为中心的系统互动。就全球治理这一主题来说,Rosenau 认定有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包括:各级政府、跨国公司、国际政府组织(IGOs)、非政府组织(NGOs)、跨国非牟利组织,或非正式联结而成的协会或运动、市场,买卖双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平等交换。除此之外,还有正式组织以外的精英群体或公众人物。以上各种参与者在与日俱增地分享权威,可形成不同的治理形态。以往最为人熟知的管理模式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管辖活动;而最有新意且与自上而下模式最不同的是被称为“莫比乌斯网”式治理。这一模式以政府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群体结构相结合为基础,包含多方向垂直与水平参与过程。该模式构成一个混合式结构,其中治理的动力学机制错综复杂层次交叠,形成一个独特的网状过程,如同著名的莫比乌斯环一样,既无起点又不在任何层面或时刻形成最高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社会治理可以说是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的强大作为有目共睹,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更令人刮目相看。这一重大决定,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将历来由政府主导甚至包办的社会管理放手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有利于精简政府机构、控制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能。百花齐放,社会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而非由政府独揽或独自承担,是与过去公共管理模式的最大区别。这里要指出,“社会治理”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治理社会”,因为忽略或不理解理念、方法、策略、手段和制度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而只强调打击刑事犯罪、整顿社会治安等问题或任务,有可能偷换概念而把“治”变成过去的“管”甚至導致“过度治理”。例如,如果在领导工作中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乃至政策制定(即不仅仅是直接提供服务)不信任、不依靠而一味防范和限制,就会在实际上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背道而驰。
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领导文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标志着中国社会治理进入到新的阶段。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那么,如何理解社区这个概念,在中国,社区是怎样一种演变? 以及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一种作用?
陈社英:我在贵刊2018年对我的访谈中从总体公共政策(GPP)比较和演变的理论这一层面,讨论了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划时代意义。其实以往每个五年计划中都会提到“平衡”,但唯有这次GPP层面的战略性转变,才特别明确指出“不平衡”问题并将其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方面之一。对于发展战略的指导意义是:一是强调求“平衡”,就不能再奉行“GDP主义”,“经济国家”已在退出历史舞台;二是求“充分”,就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不能照搬“福利国家”公共政策模式,即便将来中国社会福利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超过后者。在这个历史与比较研究意义上,认为中国大陆已进入一个“后经济国家”新时期,应该是最合适的理论解释,既不会回到经济国家,也不会变成GPP意义上的福利国家。经济从特殊矫枉过正时期的“GDP中心”转变为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社会”从靠边站回到党和国家为人民谋福利、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的“宗旨”地位。这种历史的、国际的和理论的认识,有助于深刻理解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治理进入到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很大意义上是要将重点落实在社区治理上。社区治理为何特别重要?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需要首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区,以及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又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和社会工作的社区组织等方法途径及其演变分不开。
最初,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关注的是类似于初级群体的社会关系类型,中国早期社会人类学家们则通过“社区”的概念对传统地域/乡村社会进行研究。跟“社区”相对的是“社会”。与人们共同生活的初级、乡土关系类型不同,后者被认为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日渐缩小甚至消失,社区的用法已不再主要限于乡土社会了,如现在常见的“都市社区”甚至“网络社区”等;社区概念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启用,也是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社区服务的推行连在一起的,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社区在今天仍有其独特的价值。首先,“社区研究”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社区组织、社区发展等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途径之一。从这个(方法)角度来说,社区乃是社会人类学、社会工作及其他相关学科体系内容的综合而又具体的载体工具。社区在此意义上,被当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理论问题的“透镜”,亦是实现助人自助和改造社会的“施工场所”。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单位和分类依据(亦即本体论意义上的“社区”),是客观研究对象──“社会”的具体缩影。可以说社区是一个小社会,而一个大的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多种多样的社区所组成的。无论传统或是当代的社区研究,在部落村镇或小区街道层面进行得都比较多,这种研究除了注重社会关系及互动之外,还强调将有限地域作为社区的另一基本要素。不管定义有多少种,如果把社区看作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它就是由人们之间的共同(社会)关系(包括组织机构等)和社会心理互动(包括认同/团结/归属感)所构成的。倘若滕尼斯当年的奠基之作仍有教益的话,这种(传统)“社区”社会关系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相比,强调的仍是其原生、初级、亲密、非正式等特点。虽然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城市化环境中这些已经并不常见,但现代都市人的怀旧仿古心态以及各种“寻根”“护根”的努力,成为各国社会政策强调“社区”的社会心理基础(理论上也有与早期社区失落/衰落论相对立的社区继存论依据)。而“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中华传统家庭及睦邻文化,则是社区这一舶来品得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的土壤。中國人的故土乡情观念,是维系社区归属感的文化纽带。其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区单元。家庭与家居不一样,不一定受地域所限,所以,传统邻里的作用也常常被强调,即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不过,除了某种象征意义之外,关于传统地方社会的结构、功能、性质等的种种假设,已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受到极大动摇。因此,国外像“社区照顾”这样的政策主张,常常是冠冕堂皇出台,最后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另一方面,一些新的非地缘、非地方性社区类型的涌现,包括网友、群友所构成的各种社区,则为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领导文萃》:社区治理为何特别重要?具体来说,对于中国来讲,社区跟“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何关系?
陈社英:社区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源于聚居在小范围地域上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比较原始、自然、密切的社会关系互动以及社会心理上的认同、团结和归属感。这些代表着“基层”或“草根”的特点,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社会服务满足人们社会需求的质量和效能。故在社会政策发展史上,地缘社区长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常常是中心的地位。
从国际上来看,现代地方社会或地缘社区在社会政策及其实践中得到重视,最悠久、强调最多的莫过于起源于英国、流行于世界的社区照顾。起初,社区照顾是针对精神病人机构照顾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以及社会、医学进步所带来的新的治疗与照顾方式,所采取的一个去机构化的重大举措。后来也成为社会养老的一个中心议题,更把社区照顾推到了社会政策研究与辩论的中心,且长达数十年之久。最开始,西方福利国家处于上升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社区照顾与机构照顾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来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重在提供社会服务,即社会供养,只不过一个是在机构里,另一个是在社区里。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其一路顺风的社会政策不得不开始刹车、转弯甚至开起了倒车。遇到麻烦或处于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开始打起了“社区”的主意,即原本是在社区中提供的正式照顾(主要是政府责任,也包括专业服务),慢慢变味走样,从强调政府等正式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到强调由家庭、邻里、朋友等非正式网络提供的“社区”照顾。这在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争论,要求国家正视“社区”本身需求。争论导致了由政府、志愿服务组织、家庭等各方面分享责任的所谓“混合式经济”,或福利多元主义。西方进入一个后福利国家时代,而社区照顾也就在这种争论不休、时而妥协的状态中度过了几十年。
在中国,社区事业的发展演变为“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个独特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社区作为学术概念,随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专业一道退出社会生活近三十年之久,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政权建设”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0年代初恢复社会学及社区研究后,伴随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社区服务在大中城市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得益于民政部门的大力推动,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背景与西方社区照顾的起源有根本的不同,与机构照顾和去机构化并无关系,而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从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开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保障改革。但是,与西方福利改革的取向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讲求效率优先,造成大批冗余员工下岗。不仅如此,过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也被解除,其中包括重要社会福利功能如退休金、住房、医疗、教育等。谁来接手工作单位甩掉的这些社会包袱呢?社会福利社会办,这是当时明确的改革思路。但是“社会”在哪里?中国政府刚刚经历了“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无论在结构、功能还是在指导思想上,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而所谓“配套改革”,即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与西方类似的福利多元化主张。社区和社区服务在中国应运而生,被寄予很大期望,尤其是在承担社会养老方面。可以说,社区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承载体,别无选择。当时,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尚未出现。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层社区与国外的相比,也具有独特的潜能。首先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民政部门在社区管理上下了很大功夫,由区政府下设街道办事处及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等组织形式,形成了世界上少见的严密社区组织结构。经济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针指引下,原有集体经济以及新出现的各种经济实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区经济支柱和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所谓“条块”关系问题,使得各种单位的“条条”系统极大地影响到社区这个“块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