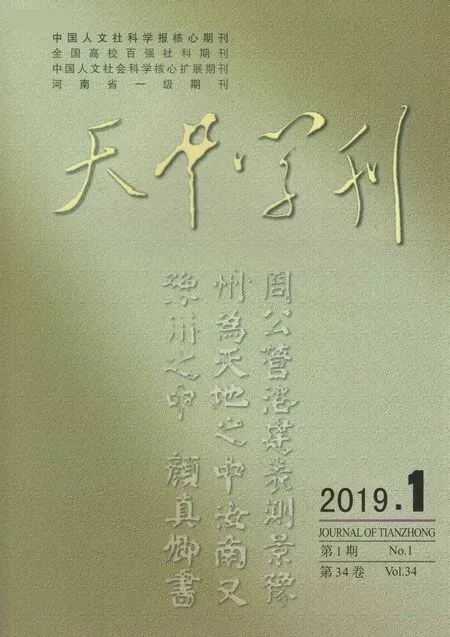西王母故事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
杜文平
西王母故事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
杜文平
(济宁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宁 272067)
自战国以降,西王母故事散见于中国古代诸子、史传、诗歌、宗教经籍、小说、戏剧、民间讲唱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中,文本分布极为零散,时代跨度大且大多文学色彩不强。因此前人对西王母的研究大多基于文献学和考古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不多。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论的应用,可以打破时代、文体和单篇文学作品的藩篱,如针对西王母故事的研究,可以在文献爬梳整理基础之上抽出王母会君、王母献授及王母开宴三大故事类型,在对其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挖掘文本流变背后的文化内涵。
中国叙事文化学;西王母故事;研究综述;前景展望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女神的代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1]7。经历了神话传说、道教仙话以及文学通俗化的改造,西王母故事所涉及的文化领域异常广泛,如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但是迄今为止,西王母研究仍然处在千头万绪、不成系统的状态下。正如叶舒宪所说:“由于各种分歧矛盾的记载,彼此牴牾的功能纷纷加诸这位西王母头上,以至于使她成了古今争议最多、身份和性质最不明确的一个神话人物。”[2]83尽管现今笼罩在西王母身上的迷雾还没有完全散去,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多学科的介入,使得关于西王母故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兹将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如下,并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角度对该研究予以展望。
一、西王母故事研究成果综述
(一)基于文献整理的西王母故事研究
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是传统意义上的西王母故事研究,自20世纪初至今一直长盛不衰。根据关注点的不同该研究又可以包括这样几类:西王母地望研究、西王母原型研究以及西王母信仰研究。
1. 西王母地望研究
20世纪初,基于对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关注,许多学者利用古文献来考证“西王母”的种族和地望。他们大多持有“中国人种西来说”,认为西王母本源于西亚地区。章炳麟在《訄书 · 序种姓》中认为“西母”即“西膜”:“至周穆王始从河宗柏夭,礼致河典,以极西土。其《传》言西膜者,西米特科,旧曰西膜,亚细亚及前后巴比伦,皆其种人。”[3]236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以西王母传说来证明“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考证玉山与昆仑的地理位置,确定了西王母国的大体范围。丁谦在《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中认为西王母国即是古代加勒底国,西王母则是其国的月神。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用数十万言证明穆天子西征见西王母皆为事实,他在自序中说道:“穆天子所见之西王母,即穆天子之女,建邦于西方者,在今波斯之第希兰附近。故穆天子也,西王母也,皆我民族上古男女有至伟大活动之能力者也。”[4]3他将《穆天子传》看作是周穆王的起居注,西王母是周穆王派去安抚边疆的。这种判断过于武断,已为后学所否定。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考证穆天子西巡路线及西王母之名,认为“西王母”本是西方地名,后由于东西民族交往而逐渐东移。此外,日本学者小川琢治有文章《昆仑与西王母》,探究了西王母在《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子》中逐渐神仙化的过程,认为《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本是西方女王,后逐渐诗化、仙化而成为女神。
五四运动以后,对西王母种族地望的研究以岑仲勉和张星烺为代表。岑仲勉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考证昆仑地名,并且对比突厥语、粟特语,认为西王母即“王权”,西王母之种族即“西膜”。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考证穆王西征,认为西王母邦在撒马尔罕附近,此外,他还驳斥了蒋智由、丁谦、顾实等人的西王母起源“西来说”,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考证,认为“其国之必在于阗西北也”。
何光岳在《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发表的《西王母的来源和迁徙》,通过参考大量古籍记载,认为西王母本为虞幕有虞氏的一个分支,夏代中叶后西迁至祁连山南山,约为春秋时期西王母又西迁新疆,汉代以后西王母故事演变为神话传说。启良在《湘潭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的《西王母神话考辨》借助古文献和人类学材料,对“昆仑”和“西王母”进行了新的考释,驳斥了昆仑位于东方和西王母是东方女神的观点,认为西王母崇拜是古代西北地区先民的生殖崇拜,昆仑山则是先民幻想的生命之山。
民俗学者刘宗迪在论文《昆仑原型考》中认为“《山海经》中之昆仑,它原本并非指西方世界的一座自然高山,而只是一座人工建筑物,这座建筑物就是古观象台,亦即明堂”[5]。刘宗迪在另外一篇论文《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中对《山海经》中的地域和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地域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西王母完全是东方本土之女神,而非迢遥而来的西方异族之神”[6]。
2. 西王母原型研究
历代典籍中对“西王母”的记载大多含混不清,而小说家之言更是难以让人信服,于是“西王母”原型便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自20世纪初开始,学者们就一直致力于对西王母原型的探究。
凌纯声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发表的《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引用各家说法和大量史料,对《山海经》和其他古文献中的昆仑丘进行了考证,又对诸多学者关于西王母的不同说法进行了梳理——或为神名,或为国名,或为王名,或为族名。此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之《西王母》篇整理了西王母传说在历代典籍中的演变过程,并通过大量文献的搜集整理来考释“西王母”之称的文化内涵,认为西表示方位,王有神义,母为貘之音假,后羿见西王母故事则是东夷部族与貘族文化融合的反映[7]145―161。饶宗颐《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从殷代祀典的“东母西母”说起,认为战国称“东皇西皇”,并且以东西分别指阳与阴,这才有了后来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张振犁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发表的《西王母神话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一文则从原始神话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变异的角度入手,认为西王母本是西方貘族供奉的图腾神话,传入中原后产生了变异,如“风后岭”“黄帝修城”在神格、职能等方面有所改变且带有原始农耕文化的色彩。
崔永红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发表的《西王母考》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西王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述,并认为《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形象可能与傩文化有关。此文为西王母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施传刚在《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发表的《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从中国的西王母信仰入手,认为与其他文化中的女神崇拜比较而言,中国女神神格的独立性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沈天水的《西王母原型探》,王卫东、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李小玲《西王母原型:善与恶的统一》,张勤的《西王母原型:生与死的统一》等文章。
3. 西王母信仰研究
西王母信仰是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汉代社会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研究西王母故事的学者所关注的视角之一。
王子今、周苏平的《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一文通过分析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来探查汉代民间的社会观念形态和社会礼俗风尚。周静的《西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一文认为西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是介于古代神话和东汉道教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神灵崇拜。作者梳理文献、考古两方面的材料,结合西汉时期社会和思想状况,探究西王母信仰在西汉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内在原因。魏崴的《四川汉代西王母崇拜现象透视》一文,通过四川出土的汉代文物来考察汉代西王母崇拜,认为汉代统治者所推崇的神仙思想与四川本土的神仙信仰相结合是四川汉代西王母崇拜的内在原因。汪小洋的《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关注点与前人有所不同,他认为:“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8]
相对于大陆学者对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关注,台湾学者对现今台湾社会的“瑶池金母”信仰予以极大注意。1997年台湾嘉义南华管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所编《西王母信仰》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郑志明《台湾瑶池金母信仰研究》一文认为台湾“瑶池金母”信仰属于中国民间信仰,既有道教神仙传说的色彩,又以罗教无生老母为信仰核心;魏光霞《台湾西王母信仰的类型研究》一文将现今西王母信仰的神格按照类型分为七类:准金母型、类玄玄上人型、师徒型、无生老母型、准地母型、地母下辖型、多母型。
(二)基于考古发现的西王母研究
得力于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得到的丰富材料,西王母研究有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以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作为基础的西王母研究,不仅弥补了传统文献研究的不足,而且赋予这个研究课题以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
国外的研究成果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奈夫1976年出版的《汉代文物》,较早从汉代文物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个问题。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以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内的图像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武梁祠石刻与汉代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巫鸿在该书的第四章《山墙:神仙世界》中,结合武梁祠西壁山墙的西王母画像以及可靠的古代典籍材料,揭示了汉代的阴阳观念、长生信仰以及西汉晚期的西王母崇拜等。美国学者简 · 詹姆斯于1995年发表论文《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侧重于西王母图像的社会背景和象征意义。
其他成果还有美国学者包华石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美国学者柯素芝的《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等等。
国内学者以文物研究为着眼点的西王母研究大多是单类文物的研究。首先是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研究。李锦山在《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发表的《西王母题材画像石及其相关问题》,将西王母题材画像石按照内容分为几大类,如西王母与侍奉仙人,西王母与灵禽瑞兽,东王公与西王母,西王母与得道仙人等,并结合古籍中的西王母神话,认为西王母题材画像石的大量出现是汉代崇道媚仙思想的产物。顾森在《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发表的《汉画中“西王母”的图像研究》,将西王母图式划分为繁式、简式和象征式,并对西王母图式中的九尾狐、伏羲女娲、龙虎座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在含义进行深刻探讨,认为西王母图像是“渴望生命的图式”。李立《汉墓神画研究——神话与神话艺术精神的考察与分析》一书第九章《汉墓神画西王母形象的“鸟化”演变与神话西王母的仙化》,通过研究汉墓神画中的西王母形象,探究其与汉代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形象的关系及其所体现的神话艺术价值和神话艺术精神。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的《画像砖(石)中的神话题材》一书则结合文献中西王母的传说,对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进行考释。其次是关于汉代铜镜及铜镜铭文研究。管维良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发表的《汉魏六朝铜镜中神兽图像及有关铭文考释》一文,结合汉镜铭文中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认为汉镜上的神兽图像及铭文与道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淞《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一书是近年来国内具有总结意义的西王母图像研究著作,其研究对象包括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铜镜、玉器、漆画等,继承了之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汉代西王母图像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建立图像与文献、图像与环境、图像与背景、图像与图像之间的整体联系来历史地阐释图像”[9]310。
尽管近年来以考古发现作为基础的西王母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数就文物谈文物,或就文物谈历史,极少涉及文学领域的西王母故事。
(三)西王母故事研究
虽然基于文献整理和考古发现的西王母研究并不完全属于文学研究,但却给西王母故事的文学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和新颖的角度。文学领域对西王母故事的研究,大多立足于西王母神话,对其进行神话流变的梳理、分期以及文化阐释。
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学术思潮涌入中国,以鲁迅、茅盾、吴晗、吕思勉为代表的学者引进西方的学术方法开始对西王母故事进行探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比了《山海经》与《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形象,认为后者“其状已颇近于人王”,为西王母神话的演变研究开了先河。1929年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第三章《演化与解释》中,以西王母神话作为“演化”的例证,认为西王母的神话演化“经过了三个时期”[10]65。1935年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第二章第四节《西王母故事的演化与东王公》中,梳理了西王母故事在古代神话与汉代神仙故事中的演变脉络[11]76。1936年陈梦家于《燕京学报》发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文,考证殷墟卜辞中的“西母”就是“西王母”的前身。这一说法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继承。
历史学家吴晗受“古史辨”史学思想影响很大,他关于西王母的文章有三篇:《西王母与西戎》《西王母的传说》《西王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今都收于《吴晗文集》。吴晗借用“层累造史说”来解读西王母神话,其观点具有启发性。他不仅通过文献的整理对西王母传说的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而且还对西王母故事在横向上所涉及的其他几个方面进行阐释,如羿与嫦娥、王母上寿、西王母与西戎等,较前人的研究更为丰满和立体。
方诗铭在《东方杂志》1946年第14期发表的《西王母传说考——汉人求仙之思想与西王母》一文,引用多部秦汉典籍和汉镜铭文来论证了汉代求仙思想与西王母故事之间的关系。同年,郑振铎出版了《民族文话》一书,其中《穆王西征记》一篇谈及西王母的形象:“大似一个女神或女巫,和河宗伯天的性质有些相同。”[12]27
1974年,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发表论文《西王母与七夕传说》,后被孙昌武译为中文,收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一书。小南一郎继承了“京都学派”重资料考据的传统,同时运用了多种新的研究方法,如民族学、宗教学、比较学派以及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西王母进行研究,将西王母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东汉以前的“原西王母”阶段,二是东汉以后与“东王公”相对的“西王母”阶段,并对故事发展中所蕴含的社会的、历史的意义进行了阐释。
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提到了西王母神话的演变,重点梳理《山海经》一书中西王母形象的演变以及西王母的仙化过程,以此证明“广义神话的合理性”,“不但原始社会以后不同的阶级社会可以产生新神话,原始社会的神话人物经历不同的阶级社会也会产生不同的演变”[13]51。
孙昌武在《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一书中对西王母如何由上古传说中的女神演化为后世的女仙进行了阐释,强调了西王母信仰与早期的道教信仰有所不同。
施爱东在《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发表的《“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减法》中,用顾颉刚的“层累造史说”来分析西王母形象的变迁,通过对不同时代西王母故事中仪仗、居所、仪容、座驾、歌声、社会关系等细枝末节的对比,来说明西王母故事变迁中“质变”与“量变”的复杂关系。
此外,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关注。施芳雅《西王母故事的衍变》一文将西王母故事分为三个衍变阶段:神话传说阶段、道教传说阶段、文学艺术和民间信仰阶段。郑志明《西王母神话的宗教衍变——神话中的通俗思想》一书对西王母神话的历史流变加以探研,将西王母神话分为三个阶段:先秦至两汉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东汉末年至宋代道教经传中的西王母,明代至今民间宗教结社信仰的西王母[14]7―35。魏光霞有《西王母与道教信仰》《西王母与神仙信仰》两篇文章,相关论述也较为透彻。
20世纪以来,西王母研究是文学、神话学、历史学、民俗学乃至宗教学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既有的研究著作卷帙浩繁。但是若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进行审视,绝大部分学者对最基本的文学文本重视不足,或者说,极少有学者将散见于史籍中的西王母故事当作文学作品来考察,使得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文学性不足,甚至多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同时,现有的西王母研究多集中于唐代以前,对唐代以后的文献重视不足。当然,这与西王母故事的实际情况有关——西王母故事在唐代基本定型,后世少有变动,且唐以后的西王母故事涉及材料和问题千头万绪,梳理不易。但是,为了文化研究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应该把唐以后的西王母故事也纳入研究范畴。
二、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下的西王母故事研究展望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宁稼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古代文学研究,并且区别于西方主题学研究和传统的叙事学研究,是一种具有极强创新性的研究方法。
首先,它以故事类型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故事主题类型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15],从而弥补了20世纪以来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的不足。其次,中国叙事文化学结合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与某一故事类型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小说、戏曲、史传、诗词歌赋、方志、通俗讲唱文学等,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系统梳理,并结合与之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包括书画作品、雕塑、陶瓷、民间工艺作品等,对故事类型的演变进行动态的分析,并深刻探讨演变背后的文化内涵。再次,除了探讨故事流变背后的文化内涵之外,中国叙事文化学同样关注文本本身,注重对文学文本艺术性的审视和探讨,使之真正符合于文学研究的要义。
现有的西王母研究普遍存在着文学性薄弱、研究对象单一、掌握材料不完整的问题,在此研究领域引入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全新的方法论,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其研究内容与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运用文献考据手段,对西王母故事相关的文献进行地毯式搜索,力图做到“竭泽而渔”。从文体来看,西王母故事涉及诸子、史传、诗歌、宗教经籍、小说、戏剧、民间讲唱文学等多种样式,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所有文体领域。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西王母故事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先秦粗陈概要的诸子之书和长于记叙的史传文学,到汉唐奇幻瑰丽的会仙之诗和道教仙话,再到宋代以后世俗性和娱乐性极强的通俗小说和戏剧作品,西王母故事借不同形式的文学书写得以与新的时代环境融合,而新兴文学样式对西王母故事的吸纳和改造又直接丰富和扩展了文学的表达领域。
其二,在对所得文献材料进行文献考证和充分阅读基础之上,理清西王母故事文本发展的基本脉络,对故事人物、情节、意象等在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进行细致对比,同时对西王母故事演变之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挖掘,关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宗教背景之下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西王母故事中的故事类型大致可以概括为王母会君故事、王母献授故事和王母开宴故事。
西王母故事中的主题类型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与其背后的历史、政治和宗教背景息息相关。战国时期,从原始神话脱胎而来的西王母一方面与神仙方士思想相结合,另一方面借诸子圣王之说而趋向于历史化。王母会君、献授以及开宴情节都已出现,表现为神话与历史相融合的文本和故事形态。两汉时期,随着神仙思想的广泛流传和儒学的宗教化,西王母故事同时为神仙之说和谶纬之书所记载,西王母的祥瑞化色彩开始定型。汉末道教产生后对西王母的吸收和改造,使其作为道教女仙而广泛见于仙话小说和道教经书,最终奠定了西王母在中国古代神祇系统中的尊贵地位。宋代以后,由于道教的式微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西王母逐步走下了神坛,成为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祥瑞俗神。
作为一个始自先秦并带有浓重神话色彩的人物形象,西王母并不具有神话人物的典型神格,甚至其使人长生的神职还是在战国时期后起的。西王母的神格是随着文学文本的演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神格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无论她是为君主王道立言、为道士仙真授经,还是为市民百姓降福,其身上的吉祥色彩和生命意识都是一脉相承的。这在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人对现世人生中的权力、享乐以及生命的孜孜以求。西王母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依托的宗教与信仰只不过是这种民族集体人格的外在表现而已。
西王母故事之所以能够自先秦产生至今连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故事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最早体现为故事文本的大纲式表述和情节、人物、意象等要素的可置换性。随着时代和文学的进步,西王母故事的文本不断丰满充实,但是故事情节和人物、意象仍旧可以随不同主题和文体而随意调整和增删。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相关文本在演变和流传过程中变得零散,但是却给西王母故事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同时还保留了其固有的文化内核。
总之,西王母故事的演变过程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宗教、政治、民俗等文化侧面演变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流传数千年生生不息的一个缩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如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讨。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 徐复.訄书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 刘宗迪.昆仑原型考:《山海经》研究之五[J].民族艺术,2003(3):28―39.
[6] 刘宗迪.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32―39.
[7] 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8] 汪小洋.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J].浙江社会科学,2009(1):86―91.
[9] 李淞.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0]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M].上海:世界书局,1929.
[11]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M].上海:光明书局,1935.
[12] 郑振铎.民族文话[M].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
[13] 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4] 郑志明.中国社会与宗教[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86.
[15] 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7―103.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eview of the Story of Chinese Western Goddess (Xiwangmu)——Based 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DU Wenping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272067, China)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the stories of Chinese Western Goddess can be found in various texts and literature types such as classical philosophy books, historical records, religious books, novels, dramas, operas, folk songs and so on. These stories or records have long-time-span and less literature features because all of them at that time were based on philology and archaeology.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can support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Western Goddess according to three types of stories including “Chinese Western Goddess Meeting Her Husband”, “Chinese Western Goddess's Offering Tributes” and “Chinese Western Goddess's Banquet”. Based o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we can fi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Story of Chinese Western Goddess; literature review; preview
2018-11-12
杜文平(1988―),女,山东泰安人,讲师,博士。
I206
A
1006–5261(2019)01–0016–07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