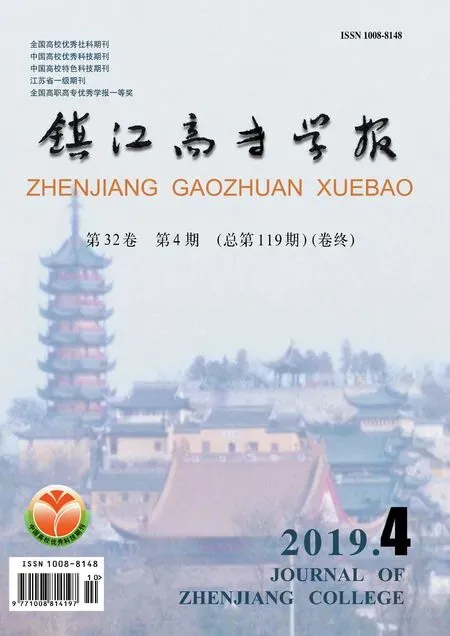平民视角下《龙子》《四世同堂》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周小英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江苏 镇江 212028)
赛珍珠和老舍都是平民作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位作家都采取平民视角进行创作,成为“战时的作家”。这个期间,他们分别发表了《龙子》和《四世同堂》。赛珍珠与老舍的这两部作品都表现出对普通大众生活的关注。孔庆东在《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中认为,老舍代表着“大众良心”,“老舍是来自于大众的作家,要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他”,“老舍把自己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1]。与老舍相仿,赛珍珠也更多关注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正如学者赵梅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她所关注的首要对象是农民,不能不说明赛珍珠切入中国人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准确的、深刻的。”[2]《龙子》和《四世同堂》这两部作品,一个着眼农民,一个着眼市民,主题相似,内容相近,都采用了平民视角。在塑造人物方面则有偏向理想化的塑造与更重现实传达的差异。笔者拟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着手,分析同样平民视角下女性形象书写的差异及其原因。
1 理想和现实中的女战士
《龙子》创作于1942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曾被有的学者评论为“洗干净了的放在友谊的橱窗里展览的”[3]中国人,意即人物形象过于理想化。《龙子》人物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儿媳妇玉儿。玉儿长得漂亮,身材高挑,但性格急躁,是“像一阵西风,到哪儿就要把哪儿搅得不安”[4]5的女人。她渴望交流,希望丈夫看重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只把她当作生孩子和做饭的工具。她渴求知识,不惜剪掉了一头乌黑的长发换钱买书。她不仅有知识有文化,还十分果敢,想说就说,想做就做。面对来村里宣传抗日的年轻人,全村只有她一个人敢大声喊出“我们能”[4]17。当村子被日本人轰炸,大家都惊慌失措时,只有她冷静思考“为什么我们没有枪炮、飞机和城堡”等问题,她认为“要是全世界都在玩这种该死的玩具,那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玩”[4]59。在丈夫决定“跑反”时,尽管已经怀有身孕,她也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并鼓励一直犹豫不决的丈夫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当她毅然带着孩子从战场赶回老家时,她再也不是从前娇俏的模样,她把头发剪短了,脸变得又黑又瘦,从外表看,她几乎蜕变成了一个男人,她“纤弱的身子硬朗了,脸上一点柔弱的影子都见不着了”[4]187。她杀起敌人来,干净利落,往往“从门阶上举起枪朝鬼子开着,干得和她丈夫一样聪明,然后照样喂孩子的奶”[4]212。由于她爱看书,有知识有文化,所以比丈夫更懂得筹谋。当听说姐夫吴廉和日本人交好后,老二又急又气,她立刻劝他,“我们应该把吴廉用作打进敌人堡垒去的敲门砖。和这号人生气,恨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只可以利用”[4]217。这个既冷静又大胆的女人,居然瞒着婆婆,乔装打扮后进城打探虚实。她买通了吴廉家的厨师,在他们大宴宾客时将毒药掺入食物,毒死了好几个敌人,同时,成功瓦解了日本人对吴廉的信任。在作者笔下,玉儿成了一位独立、果敢、机智得让人惊叹的完美女战士。
与玉儿相比,《四世同堂》中的高弟就显得平凡而懦弱。单就外表来说,高弟“嘴唇太厚,鼻子太短,只有两只眼睛还有时候显着精神”[5]43,这是一个丢在人堆里就找不见的姑娘。可是,老舍笔锋一转,说她在家里可以算是最聪明最有骨气的人。北平沦陷,大赤包仿佛看到官职、金钱、酒饭和华美的衣服向自己走来,她兴奋异常,千方百计地想着帮冠晓荷捞得一官半职。高第对此非常反感。高弟对大赤包说:“我要是你呀,妈,我就不能让女儿在这种时候去给爸爸找官儿做!丢人!”[5]43-44她甚至宣称,如果父亲去给日本人做事,她就不再吃家里的饭。但髙弟不像玉儿那么独立,除了将自己一腔少女情怀寄托在钱家二少爷身上,在自己美好想象中将他幻化成一个理想的青年外,她似乎不知道该做点什么。钱家二少爷开车摔死了一车的日本人,高第父母打算去告发,满腔的少女情怀促使高第愿意为心中的这个英雄去冒险,她打算爬墙去提醒钱先生。很明显,她这样做的目的与保家卫国没有任何关系,那一切的动机“只是出于好玩、冒险、诡秘的恋爱,搭救钱先生只是一部分”[5]70。搭救钱先生,让她觉得充实,钱大少爷去世后,她偷偷捐了钱,这也让她觉得特别有意义。与玉儿的果敢决绝不一样,她不敢逃离家里那个温柔乡,她更没有什么爱国情怀,她所作的一切不过是所有人都该拥有的那一点良知而已。她依旧穿着时髦、涂着口红、描着眉眼,依旧打麻将、逛公园。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当看到父母一味地向日本人献媚求官职,她多少是不齿的,大赤包被敌人抓了,她想得更多的是父母做多了坏事后得到的报应,最终在瑞宣的指点下,高弟决定逃出北平。她的良知让她决定和钱先生合作,她假装做敌人的特务,实际上却成为钱先生的好帮手。高弟的出走是被动的,但最终,她成了瑞全的战友。小说最后,笔墨不多的高弟再次出场,这一回,她“头发没烫,嘴唇也没抹口红。看来,她已经完全摆脱了了大赤包和招弟对她的束缚,毫不做作地显出了她的本来面目”[5]586。自此,一个女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个女战士的成长是艰辛的,不过,到底是“战争把她调教出来了”[5]587。
玉儿自小生活在中国农村,没怎么接受过教育,却富有理想,敢想敢做,她确实完美得让人惊叹。有读者质疑赛珍珠为什么会塑造这么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联想到赛珍珠创作《龙子》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我们应该就可以理解她的想法。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众多场合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抗日战争爆发,她密切关注中国的命运并在美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战精神,希望帮助战争中的中国获得更多帮助。抗日战争一爆发,她便在《亚洲》杂志上表达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物质上,或许在心理上,日本人可以打败中国。但中国人在精神上仍有希望。日本压倒性的黑色威胁将会恢复中国依旧存在的精神。中国的年轻人将会在这场战争中团结起来,夺回并拯救他们的国家”[6]。赛珍珠非常清楚,“刚刚参战的美国人民急于读到有关他们的亚洲盟友的令人鼓舞的故事”[7],所以,这个完美的女战士无疑是赛珍珠向美国人宣传中国人积极抗日的媒介之一。老舍笔下的高弟形象则完全符合老舍市民文化批判的创作主旨。与玉儿一样,她识文断字,甚至读过几年书,脑子里很有些新派思想,但她身上也有着国民性中潜藏的苟且偷安的弱点。她有良知却也不失世故,在危险面前,她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而不像玉儿那样考虑民族大义。她鄙视卖国求荣的父母和妹妹,却也没有勇气像玉儿一样寻找出路,直到家庭发生变故,她才开始变得成熟、果敢、机智,慢慢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在作者笔下,高弟一步步成长起来,她并不完美,但让读者觉得真实可爱。
2 理想和现实中的贤妻良母
在《龙子》中,母亲林嫂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特点,贤良淑德、勤劳能干,任劳任怨地相夫教子,但林嫂又是一位在战时比男性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智慧和能力的新式母亲。林嫂没有文化,她认为认字是全天下最没用的事。对她来说,最好的女人就是强壮能干、能生孩子又能伺候丈夫的女人,她甚至认为“最好的婚姻就在于男人能够打女人”[4]20。萨义德曾误解中国传统女人,认为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8]22。林嫂可不是这类形象。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新式理想的贤妻良母形象。敌人强暴了儿子和大儿媳妇,家园被日本人炸毁,自己的丈夫气得大吼大叫,林嫂反而十分冷静,并生出骨子里你不想让我活、我偏要好好活着的一股拗劲。也正是凭着这一股子拗劲,她成为家里的主心骨。她提醒丈夫没有枪要怎样对付敌人;她想出办法躲过敌人的盘查和抢夺,让一家人有吃有喝;她想到用打地洞的办法来保护二儿子一家。对成为汉奸的大女儿一家,她虽做不到像玉儿那样大义灭亲,却也表现得爱憎分明。面对残暴的敌人,她更有如男人般的勇敢,扛起锄头挖好坟,像埋猪下水一样把敌人埋进地里。林嫂,就像林郯心中爱惜的大地一样,用自己朴实的语言和行动,抚慰着丈夫受伤的心灵,让他觉得活下来有希望,同时,又细心照料着后辈们的生活,让他们在节衣缩食的战争年代得以生活无忧。这样的一位女性,在一些评论者眼中被认为塑造得过于理想化,丧失了最基本的现实性,“这可能与赛珍珠远离中国,无法真切体会中国农民生存状况与心态有关”[9]。笔者认为,赛珍珠之所以塑造出林嫂这样的中国女性形象,与她一贯的主张有关。赛珍珠一贯认为女人也应该为和平和公正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如果女人不能在家庭中把道德原则植入儿子们的心田,那么就必须帮助男人们在家庭之外抑制罪恶”[10]137。
与林嫂相比,《四世同堂》中韵梅的成长要艰难很多。韵梅是瑞宣的妻子、祁家的长孙媳妇,因为没进过学校学习,所以没有学名,是嫁到祁家才“由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一样送给了她一个名字”,然而,“这个名字并没有在祁家通行得开”[5]5,在祁家,她就是“小顺儿的妈”。这一命名的过程显然表现出她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是传统“女子许嫁,笄而字”[11]55的现代演绎,恰如拉康所言“如果说一个人显得是语言的奴仆,他更是话语的奴仆”[12]426,这个过程,也几乎是韵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主体性消失的过程。在小说开篇,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女子。她做事勤快,却又“快得并不发慌”[5]5,就算脸上的粉没擦均匀被人嘲笑时,她也随着人家笑,“她是天生的好脾气”[5]6。由于婆婆体弱多病,祁家所有的事务便基本由她来操持。她给祁家生了一儿一女,又懂得伺候老人,所以,祁家老人最喜欢这个长孙媳妇。就当读者以为韵梅就是一个以伺候长辈、照顾子女、操持家务为全部生活中心的旧式女子时,韵梅后来显露出来的生活智慧让人大吃一惊。她听说日本人要来了,不怕也不慌。韵梅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5]17-18这可真不是一位一心只会服侍老人孩子的旧式女子能说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从韵梅丈夫对她态度的变化上看出这位传统的贤妻良母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思想传统而又饱受现代教育的瑞宣对韵梅没什么感情。随着情节的发展,瑞宣对韵梅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家里没煤烧,瑞宣苦闷得只能找她谈起时,她能及时进行安慰,“虽然没有任何理想与想象,可是每一句都那么有分量,使瑞宣无从反驳”[5]166;隔壁日本孩子欺负了自家孩子,韵梅气得把那日本孩子抡了出去,瑞宣很高兴,他没想到“韵梅会那么激愤,那么勇敢。他不止满意她的举动,而且觉得应当佩服她”[5]243;瑞宣被抓,家里一片慌乱,她立刻冷静下来,知道不能靠别人,只能一点点地砸墙通消息出去,那一刻,她“自信能开一座山”[5]282;为了保出邻居方六,她替瑞宣签了字,这让瑞宣第一次觉得“她仿佛是他的一个新的收获”[5]487;养活一家人的责任让韵梅变得越来越坚强与自信,跑去当特务的招弟让她觉出了自己的“硬正”,觉得“自己应当自傲”[5]484;见到胖菊子,她再也不是一副好脾气,虽然“她向来不愿意得罪人,然而是非还是分明的”[5]528,这好心的女人最后居然把拎着礼物的胖菊子赶出家门,这让瑞宣不得不欣赏她……就这样,瑞宣从开始的无奈,到后来的感激、敬重、欣赏,到最后,战争让这对夫妻之间慢慢培养出一种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深厚感情。这种变化过程,也正是韵梅从一个只懂得以夫为尊、顺从隐忍的旧式贤妻良母成长为一个爱憎分明、坚韧勇敢的新式贤妻的过程。整个过程,没有来自家庭的压迫,也没有任何的引路人,一切皆源自她自身个性的萌发和发展。传统的贤妻良母天佑太太因身体不适日渐虚弱,退出了自己的舞台;追求摩登的菊子一味追求金钱和权力,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只有韵梅自觉自发地批判和矫正自己的行为,并最终使自身得到认可和欣赏,让瑞宣不得不承认她的价值。
笔者认为,韵梅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老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态度。在老舍看来,“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13]288。可见,在老舍的心中,中国和中国人的成长不能靠完全模仿西方的舶来品,当然,也不能光守着旧式传统,而应从中国人自己已有的传统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传统文化中求取生存之道。他的这种思想,也通过小说中的钱先生给喊了出来,“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5]324。可以说,韵梅的成长,不单单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的成长,更表现了老舍这位忧国忧民的平民作家倡导的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理想”道路——立足自身,去芜存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救亡之法。
综上可见,面对中国同样的女性群体,赛珍珠和老舍塑造的形象有明显差异。学者乐黛云认为,在形象学研究领域“人,几乎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关于‘异域’和‘他者’的研究往往决定于研究者自身及其所在过的处境和条件”[14]。沃尔夫冈·伊瑟尔也认为:“只要现实一旦转化为文本,它就必然成了一种与众多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的符号。因此,文本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它们所摹写的原型。”[15]16可见,异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会潜在地表现和传达作者的文化身份和族裔政治等问题。赛珍珠和老舍,一个是在中国度过了半生的美国作家,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面对中国这个同一对象,作家身后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和作者本人的立场势必影响他们的表达。毫无疑问,前文论述的不同女性形象也正是两位作家个人立场和背后集体想象物在其文学作品上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