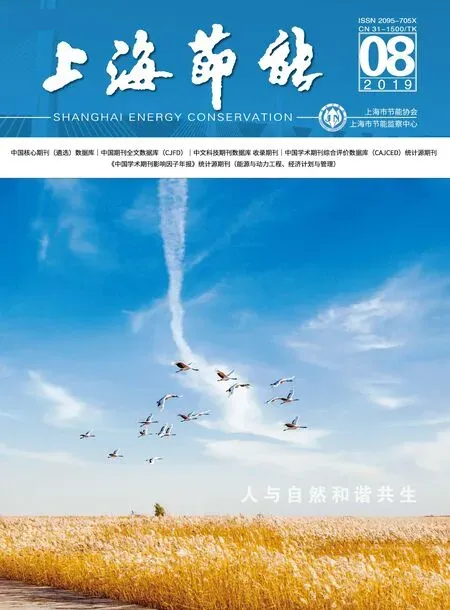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演进
刘新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0 背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阶段,我们面临不同的主要矛盾、发展任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呈现不同特征。为了适应不同的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各种生态文明理念并逐步演进,在2012年之后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1 1972至1978年中国领导人初步认识到环保重要性
这一阶段,我国领导人已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其标志是派代表团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紧接着在1973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同时,我国尚处在文革时期或尚未对文革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期,看待环境问题时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1958至1978年间,我国在资源环境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度强调人定胜天,造成了大规模的毁林开荒、毁林炼钢等严重后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人颇有远见地强调要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他们除了在具体场合、针对具体问题,就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作出具体指示,更重要的是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4]。
2 1978至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初创阶段
这一阶段,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但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加快发展和摆脱贫困的任务很重,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尚不尖锐。在这一形势下,政界和学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或理论处于初创阶段。
2.1 改革开启后与市场经济确立前的时代特征
这一阶段,党和国家高层领导重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相当于重申了1956年中共八大的相关表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肇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快发展,加快摆脱贫困,加快摆脱短缺经济。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比,必须居于第二位。而且,这一时期的改革正处于摸索、试水阶段(即“摸着石头过河”),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一些僵化的教条桎梏中解放出来,很多改革措施只是在逐步试点,没有全面推开。这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潜力没有被全面激活,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尚不尖锐。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和体制的初创阶段。如:1978版《宪法》对政府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等公害的责任作出规定;1979年,首次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开始正式设立(而不是临时的)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国家层面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设环境保护局[5]。
2.2 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朴素的生态文明理念
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要是一些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已提出了一些朴素的生态文明理念。
最典型的就是邓小平同志就我国基本国情作出“人口多、底子薄”的重要判断。中国共产党人是信奉唯物主义的,是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我们制定经济社会政策要从我国资源环境的实际出发,对这个实际判断得准确与否,决定了制定出来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否会出现偏差。1979年,邓小平对基本国情作出了“人口多、底子薄”这一精准而重要的判断。
邓小平以其务实而朴素的语言风格点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理论问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极限,考虑到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的特殊国情,这一极限就显得尤为严峻。面对这样的极限问题,邓小平又在1987年高瞻远瞩地提出“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之问[7]。
3 1992至2012年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为标志,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迈入高速增长阶段。然而,高速增长在让人民富起来、让国家摆脱短缺经济的同时,资源环境代价也越来越大,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为应对这一问题,发展方式必须进行转变。为指导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党、我国领导人逐步形成并提出科学发展观。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为给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撑,从国外引入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最新理念,加以阐释和发展,形成指导中国特色环保实践的若干理论。
3.1 市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征
我国经历了1978至1992年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到1992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随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潜力被全面激活,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经济高速增长让人民迅速富起来,国家迅速摆脱短缺经济。但随之而来的是资源环境遭到破坏的代价越来越大,经济与环境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政界和学界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初的提法是从粗放式发展转向集约式发展)。
3.2 为指导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科学发展观
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甚至只能说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为指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形成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江泽民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期间,中国引入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其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作了一部分理论准备。江泽民主政时期,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更加密切,对国际上最前沿、最先进的环保理念与做法更为积极地追踪和接轨,最为典型的是引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6年初,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7月,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又一次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位,成为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理经济与环境关系,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胡锦涛主政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理念的又一次升华。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扭转“不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的,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不能把“发展”等同于“增长”,不能把“发展是硬道理”等同于“增长是硬道理”。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错误观念,必然导致粗放式增长。
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胡锦涛第一次提出这些核心理念是在2003年7月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之一。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指导方针”、“重大战略思想”。而且,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任务,2006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这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一样,都是中国人自创的概念,围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两型社会,结出众多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成果。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粗放发展方式造成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应对这一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应运而兴,并在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被明确宣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4.1 制度乏力导致发展方式转变难,呼唤更有力的生态文明治国理念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由于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未能全面落实到制度上,虽然领导人已经有较先进的生态文明意识,但制度的乏力导致发展方式迟迟没有转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与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之间的矛盾到了一个非常尖锐、非常严重的境地。这种形势若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国家安全也要受到威胁。为了让发展方式切切实实进行转变,扭转严重的资源环境形势,使中国的生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远离险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理念和理论观点作为应对之策,逐步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全面落实到制度层面。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理念的集大成者
发端于2005年在浙江安吉提出“两山论”之时,完善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理念的集大成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内核。在实践上,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在理论上,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生态经济学界争夺话语权的一面旗帜。它包括生态生产力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民生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系统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制度论(生态文明制度保障)、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等。习近平的这些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式转型的归宿——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在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
4.2.1 生态环境民生论
习近平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体现了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或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强调了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共享性[3]。
4.2.2 生态安全论
习近平把生态安全提到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同的高度,并且以生态红线论为核心,强调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能逾越自然界的约束,要有较强的底线思维[6]。习近平把生态安全放到国家整体安全体系中去认识与定位,指出生态安全处于和其它安全的联系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1]。
4.2.3 生态环境生产力论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思想。他提出了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思想[2]。他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后劲,也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习近平形象地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比喻为金山银山和青山绿水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2.4 生态文明制度论
既然生态环境是一种生产力,那么,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受到损害、削弱甚至威胁的时候,为了保护和发展这种生产力,就需要让调节各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和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各项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
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2.5 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
习近平根据一些古文明衰落及湮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
生态环境是一种生产力,能对一定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当这种生产力得到保护和发展时,它所在的社会或文明就能取得长足进步。当这种生产力受到损害、削弱甚至消耗殆尽时,它所在的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就必然停滞、倒退甚至消亡。
4.2.6 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论
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务必强调系统性,切忌顾此失彼,否则将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决定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各自为政的碎片式管理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为此,一要加强顶层设计,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二要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8]。
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到制度层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力首先体现在它被全面落实到制度层面,切切实实地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形成硬约束,促使其摒弃错误政绩观,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2015年9月我国颁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及由该方案统领的“四梁八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逐步完备起来。其中,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环境保护督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针对党政领导干部在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履职,严明了规矩和奖惩,有力地遏制了牺牲生态环境谋求经济发展的政府行为。
5 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到今天,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的层面);二是学术界吸收国外相关社科理论并将其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学者层面)。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成体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内核,以一定逻辑脉络将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串联起来、统领起来,形成一个庞大而又在逻辑上有紧密内在关系的体系;二是用中国话语诉说,而不是单纯使用来自国外的概念和方法论,这将构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外学界争夺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