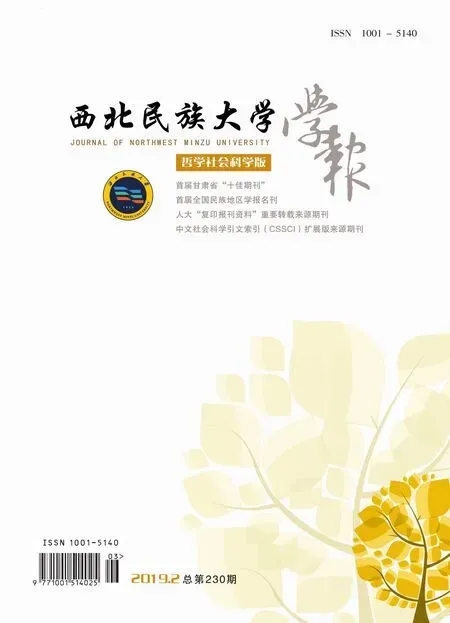清末劝学所在地方的运作及其实践特点
——以四川省南部县为例
陈慧萍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劝学所是近代地方行政教育机构的雏形,由严修首创于直隶。1906年,学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劝学所,并在《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中规定:“各厅州县,应于本城择地特设公所一处,为全境之总汇,即名曰某处劝学所。”注1906年4月,学部奏请裁撤学政改省提学使司,认为“地方官应办之学务,统系不定则推诿恒多,权限不明则侵轶可虑……尤重在教育行政与地方行政之机关各有考成”规定各厅州县均设劝学所,划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通教育。(各省劝学所统计表[C]//朱有瓛.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62.)自此,劝学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计的基层教育行政机关注劝学所自1905年在全国推广,历经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直至1922年全国学制会议决改劝学所为教育局。1923年,各省将治下州县劝学所一律改为教育局。至此,劝学所在清末民初前后延续了约18年。。各府厅州县劝学所掌管所辖区域的教育行政,总揽地方学务。随着劝学所的设立,地方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行政系统:省级的提学使司(提学使负责)——县级地方劝学所(总董负责)——学区(劝学员负责),这套系统设置到县一级止。1906年学部颁布《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1911年颁布《学部改定劝学所章程》注后文中提到《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学部改定劝学所章程》两部文件,分别简写为《章程》或《改定章程》。,以上两部法令成为劝学所建立、执行的纲领性文件。然而,无论是学部的章程或是地方政府颁布的条文都只是粗略的、方向性的,在具体操作方面并未有细致的规定,再加上各地区域差异,致使劝学所在地方的实践复杂化、多歧化。由于资料的缺失等诸多原因,现有关于劝学所的研究大多注重考查劝学所的规章,关于劝学所在地方实践的具体细节以及国家政令落实后的区域差异关注较少,至于以某地为案例来缕析劝学所的职责,更是鲜少尝试。四川省南部县保留有清代南部县衙完整的档案,其中有大量关于清末劝学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根据清末南部县的档案,再参考其他文献,具体探讨清末劝学所在南部县的运行及在地方实践中的特点。
一、劝学所在南部县的运行
南部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因居于阆中之南,故称之为“南部”,辖下分东南西北四路。当时,南都县18 521户,74 185丁口,共10乡82保[1]。1905年,清政府宣布彻底废除科举制度,令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到1909年,四川共设立劝学所145所,总董145人,劝学员1 029人[2]。南部县第一次提到劝学所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1月3日),离《章程》颁行间隔约半年,按公文传递由中央经司、道、府逐层转发的时间计算,南部县执行此项谕旨可谓迅速,但该如何改制,县正堂并不清楚,只将学务局改为劝学所,至于劝学所该如何办理,县谕中也仅是模糊地写道“照旧章办理”即可[注]“为禀明公举程光伊接充学务局首士事”条: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7-865/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到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九日(1907年4月22日)提学使司发文饬南部县要求“将学务局改为劝学所,局中款项,概行提并劝学所”[注]“为申报卑县奉到扎发各学堂考试章程事呈提学使司”条: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九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456/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三月十日(1907年4月23年)南部县在晓谕中详细描述了劝学所的任命改制情况:“本县因地制宜,酌定简明章程,改定一切支款。……查县中学款至为繁重,仍应派员经理,以专责成。所有学务局正董应改为劝学所收支员,副董改为庶务员。查去年正董邱辑瑞、谢光国老成练达;梅炳岳,王懋槐亦精干有为,应准一并留办。除示谕外,合行札委,廪生梅炳岳、文生王懋槐即便遵照充当劝学所庶务员。”[注]“为札委梅炳岳等充当劝学所庶务员等事”条: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457/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谕文中似乎对改制写得较为详细,然而,事实上对于基层县衙而言,自政府宣布改革以来,各种新规不断颁布,各种机构新设且不断调整,学务局建立不过一年有余便改名重建,基层县衙不过是摸索创制,劝学所具体该如何运行并不明晰,甚至有些县衙搞不清楚劝学所是不是在学务局之外建立的新机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保宁府提学使司在给南部县的饬文中写道:“威远县视学吴申商,以该县坐查委员,仍行查学支费,视学权限朦混,禀请核实……本司批坐查员早经裁撤,现奉部章设立劝学所,派定视学更无坐查之名,何能重复之费,该县既经误会,他县恐亦不免,仰候通饬。”[注]“为转饬办学员绅查照新照毋使查学与视学权限朦混事移儒学”条: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六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498/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威远县原学务局的坐查委员仍在查收学费,该县将学务局与劝学所并行设立。以此观之,难免其他县也有类似情况。可见学务局初改劝学所时之乱象。
1906年,学部命各省提学使分定学区,“东西各国兴学成规,莫不分析学区,俾各地方自筹经费,自行举办”[3]。按分区办学原则,划分学区之后,各地要自筹经费,兴办学堂。1907年,南部县颁布《新定南部县劝学所章程》,在章程中划定南部县为九个学区[注]后又划分为20个学区,1910年省视学到县调查改为5个学区,为东、南、西、北、中。,为正东区、正西区、正南区、正北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中区[注]劝学所所在县城及附郭为中区,谢家河、永定场、碑院寺、中兴场、清平场、楠林寺、柴家井、福德场、双河场、鲜店场、新镇壩、平头壩、王家场、富利场、石河场,为正东区。棗儿嶺、龙王堂、黄金垭、寒坡嶺、流马场、金源场、碾垭场、建舆场、万年场、义和场,为正南区。老观场、石墙垭、大桥场、柳边驿、峯司富村、驿双河场、元山场、镇江场、为正西区。皂角垭、棗碧庙、思依场、木兰庙、保城庙、神壩场、豬磳垭、店子垭、分水嶺、坵垭场,为正北区。水观音、盘龙驿、李渡场、梅家场、大佛寺、河壩场、马鞍塘、大堰壩、盘龙场、东壩场、大平桥、石龙场、为东南区。定水寺、泰华场、三官堂、郑家垭,为西南区。狮子场、万年垭、升钟寺、观音场、塞金场,为西北区。满福壩、老鸦岩、文家壩,为东北区。每区设立学堂,多寡另有表册。一般学区以劝学所为轴心向外辐射,有些州县就地理环境划分学区。。每区包括10~20个场、庙,基本按照乡为单位来划分学区。学区划定之后,各区开始分区筹款办学,南部县的具体做法是:要求每学区中所辖属的各商会、庙会等,分别具认1~2所小学。所具认小学兴办学堂使用的费用从各会抽款,至于所抽的具体比例、数字,由该区劝学员、该校学董协同保甲、会首协同商定筹款数额及比例,并签订具认状。具认状为统一格式,南部县档案中存有大量具认状,因格式相同,仅是替换地方与认具人姓名。仅举一例典型,全文录如下:“南部县南三区建兴场保正刘继尧,保下甲长何有珍,今于大老爷台前,为认缴事。今因建兴场校地,兴正庵公立初等小学堂,提清明会公款钱十二千文,以作学堂经费,其钱同劝学员李淑灃、学董刘作宝言明,即由何有珍,按十个月摊缴,每年五月缴半,十月缴清,并不拖欠,中间不虚,具认是实。”[注]“为认定公立小学堂常年经费事”条: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58/29),南充市档案馆馆藏。此份具认状,为笔者所见南部县档案记录中最早签订的具认状,签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以至少可以判定最迟于1908年9月,南部县各学区已开始认具。然而,即使各区已签认具,并答应为新学堂提供缴款,但在新学兴办的过程中,欠缴、拒缴的事件依然屡屡发生。面对欠缴与拒缴,劝学所通常的措施便是由劝学员告禀于县正堂,由县衙发文劝学所派官差锁押,强令其缴费。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十(1908年)南部县正堂令“该(县衙)役前去协同南三区建兴场地文庙公立初等小学堂劝学员李叔灃、学董敬锡光,饬令(欠款)表内抗公不缴之欠户等,速将应缴学堂经费,照数缴交该学董支用,倘再抗延,即系把持学务,该役即随签带”[注]“为差协同建兴场学董饬令表内欠公不缴户速将应缴学款交学董事”条: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40/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即使县衙用行政手段强制缴纳学款,出现大面积欠款,县衙能做的也不过是一一签唤,令其缴费。该条中同时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建兴场校地劝学员李叔灃、学董敬锡光所呈报的欠款表中,几乎各甲、各斗市都在欠费,甚至很多甲都分文未缴,可见劝学所推广学务之艰难。
当时“中国人口约计四万万,应受学之人约计一万万,此一万万人中,学龄儿童至少约计五千万,统计各行省百八三十府,所辖厅州县一千六百八十有一,每州县立小学堂三百所……教育可乃普及”[4]。要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时人计算每州县约设300多所新式学堂,在当时的财力、物力、人力情况下,州县不可能完成,此种情况下,私塾、书院改制,便成为劝学所新办学堂的最佳选择。相较书院改制的坚决,在基层,私塾改良的态度要暧昧得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提学使转发学部文件,文中写道:“去年学部大臣访问京城内外,有匪徒捏造谣言,查禁私塾……私塾是否合法只能令地方官绅按照定章广为劝导,断不容恶棍土豪藉端讹索,令地方官出示晓谕,如有冒称查学,藉端讹诈事情,一经访问或控告立即究办。”[注]“为通饬各属查禁冒充委员下乡借端讹诈各学堂捐输事饬南部县”条: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7-00811/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对于私塾是否合法,如何判定合法,学部认为由地方官、劝学所根据当地情况自行斟酌。此种对待私塾态度的暧昧不清,导致到1910年,四川除按章程规定改良9 681处私塾外,尚有66 900余处未改良,私塾仍然很多[5]。省视学巡视学务后,报告中称:“(安县)各类私塾遍及城乡,每村少则1所,多则3所,每所学生少则5人,多则50余人”[6],“该县(长寿县)初小九十八堂。学生二千九百余人,私塾仍六百余所,学生七千余人”[7]。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南部县教员在禀告学堂状况时亦写道:“职之家塾在张家祠,偏在一隅,上有悬崖,下临深涧,虽委教员汪国霖训读而学,生不过十余人,而赵士宜文武宫私塾则有三十八人之多。”[注]“为具禀遵章私立小学事”条: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531/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可以说,在乡村社会中实际上是私塾与学堂并存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私塾的功能与分布决定的。私塾多分布于清统治的基层——乡村,新式学堂虽将触角伸至乡村,但由于经费、教员的缺乏等诸多因素,根本无法实现在乡村的真正普及,私塾便是很好的补充,清政府对待私塾无法像书院一样一刀切,地方官衙对各私馆蒙师亦多是以劝谕为主,尽量引导各私塾教师补考纳入新的教育体系,而并非是严厉禁止。除政府原因外,私塾之所以大量存在也与民众的认可密切相关,与“小学学费动辄七八元不等”[8]的学费相较,塾师的束修相对便宜,且“学堂无论其为公立,为私立,入校肄业,莫不索费,购书阅报,所费滋多,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9],与此对比,乡村社会更认同私塾而非学堂。
不可否认,劝学所的建立及运作对新学堂的广泛设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南部县视学李雨苍描述南部县新式学堂发展列道:“中一区共九堂,东路六区共三十八堂,南路五区共三十二堂,西路四区共二十四堂,北路四区共十七堂。”[注]“为具禀遵札辞卸公举汪麟洲接充视学事”条:宣统元年十月二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20-00903/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到1909年,全县合计共有120余所小学堂。但必须注意的是,新式学堂建立过程中“新”与“旧”在同一时段同一场域交错杂陈,呈现极度的复杂化。
二、劝学所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的特点
(一)劝学所成员的职责界线模糊
1.劝学所总董与县视学职责的一体化。劝学总董[注]1911年劝学所设“劝学员长”一职,按《改定劝学所章程》第二条规定:“劝学所设劝学员长一人,秉承该长官办理劝学所一切事务,劝学员长得兼充县视学”。笔者认为“劝学员长”与“总董”的职能及兼充,完全重合,所谓的“劝学员长”应是“总董”更名(“劝学所章程”载于朱有瓛《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为正七品虚衔,提学使委派,总董并无特定的任职资格限制,一般由乡里有德望且热心教育的人士担任。劝学所总董的职责在《章程》中仅是笼统地表述为“综核各区事务”[3]64,解释具体事务时规定道:“考察迎神赛会演戏之存款,绅富出资建学,为禀请地方官奖励。酌量各地情形,令学生缴纳学费。”[3]63-64综合归纳总董的具体职责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调查庙会款项以作兴学之用;二是劝导绅士富户出资办学,并为其奏请奖励;三为考察各地情形,令学生缴纳学费。总结而言,从《章程》的规定来看,总董的职责仅限于考察、监督兴学的情况。如此总董的职责便与视学的职责相重合。有趣的是,《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视学察视的具体权限,然而《章程》又规定总董由县视学兼任,这就导致总董与视学名为两个官职,实际权责相似。面对这种规定,时人也在询问“总董明定有综核各区之权,而县视学转不明定权限,何也?不云县视学由总董兼充,而云总董由县视学兼充,何也?立法之初即明定兼充,则总董所务即县视学所务,而必多立名目,何也?学部岂以学董、县视学分而为二,恐生意见,或多牵掣乎?各地方财政,类皆拮据,多一人即多一开支乎?不知意见之生牵掣之类,皆由权限不明而发生。”[10]鉴于总董与视学的职责相类,所以,在地方劝学所往往将二者结合,或总董兼视学或视学兼总董。南部县总董是由县视学兼任。第一任视学为原学务局训导李雨苍改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县视学李雨苍巡视各学区,将各学区兴学情况记为日记并以劝学所的名义贴于各处,以为晓谕[注]“为嘉奖初等小学堂教员事”条: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7-00316/05),南充市档案馆馆藏。。总结县视学作为,其职责主要是对新学教员、学董进行奖惩。“兹据视学李雨苍遵章,巡视各堂,面呈日记,查得马鞍塘东林寺初等小学堂教员袁毓英,所教学生,盘问各门功课,不能回讲。学生称,系去岁讲录,居心敷衍、误人太甚。本应立予撤换,惟念该教员系属文生,宽先行记过,二次示儆。”[注]“为制定章程奖惩初等小学堂堂教员及记过教员袁毓英示做事”条: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569/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视学员李雨苍遵章,赴乡巡视,回县面呈日记,查得大堰坝任江寺小学堂,学生止(只)有五人,且多耽延学科,一切均无,师范张光烈,教育疏嫩(懒),扶同敷衍,半年之久,并无一言报告。本应立即撤换,姑,从宽记过一次,罚扣束脩钱十千,以观后效。……应将该学董卢上选、戴理琮各予记过,一次罚去薪水,以示薄惩。”[注]“为示谕劝学员学董教员及私塾师生人等遵照章程以兴学务事”条: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六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467/02),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大河坝四龙山初等小学堂表册日记,察核该堂教员陈嘉澍,尽心耐劳,学生均多进境,人心乐从,应予记功一次。学董谢鸿謨,办事亦属实心,深堪嘉许。”[注]“为嘉奖四龙山小学堂教员学董事”条: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九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541/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在南部县的实践中,总董更倾向于执行视学的职责。在其他地区的具体操作中,亦呈现不同程度的总董与县视学职责的一体化[注]1910《河南通行各属拟定劝学所总董权限专章文》中规定总董应负之责:一,各区大小分划是否完密,有无归并。二、学院是否得力,各区分配是否允协。三、各区学风校规是否完备,应行增设、应行改良几处,是否按期增改。四、随时调查全境学款,有无虚糜、有无支绌,应即时会同地方官设法清理筹措。五、各区有无阻挠滋事,各校有无冲突敷衍,会同地方官即时整饬。总结以上规定,总董的权力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为监督治下学区划分、学堂兴设情况;二、监管治下学款。三、协同地方官整饬学务纠纷。自规定而知,在河南,总董更倾向于视学的职能。且相较学部规定的总董的权限,地方规定总董的权限要大一些(“河南通行各属拟定劝学所总董权限专章文”载于朱有瓛《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所以时人评价“核总董之名,其权必统揽一切,偏重实行。核视学之名,其权不过查视学,偏重考务”[10]12。
2.劝学员与劝学学董职责界线的模糊。劝学员的职责,相较于总董,《章程》规定要细致得多,各地方劝学所章程大都依《章程》而制。劝学员的职责总结归纳为五个部分:一为劝学。劝学员的名称便来源于此。所谓“劝学”指劝各家各户将适龄儿童送至学堂;劝绅商之家捐助兴学。且学部强调,劝学员的工作重点是“劝”,只能婉言相劝,不可强迫。二为兴学。计算学龄儿童的多少以规划设立学堂的多少;规划学堂的地址、房屋的多少;协同学董核定“颁行课程、延聘教员;选用司事,稽查功课及款项;设立半日学堂”[3]63。三为筹款。劝学员报告各地情形,作为总董“考察迎神赛会演戏之存款、绅富出资建学、令学生缴纳学费”[3]64的依据。四为开风气。访有急公好义、品行端方的绅士,请其襄助学务;组织小学师范讲习所,冬夏、期讲习所,宣讲所,阅报所;宣讲停科举、兴学堂的政策。五、去阻力。阻挠学务者、造谣者禀明劝学所,由地方官办理[3]63-64。按规定,以上都为劝学员的职责。不过劝学员最核心的工作是劝募学生,此亦是劝学所评定劝学员优劣的标准。至于学董的职责,《章程》中只有寥寥数语,“劝学员于本管区内调查筹款兴学事项,商承总董拟定办法,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此项学堂经费,皆责成村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3]62-63,与劝学员商议核定“颁行课程、延聘教员,选用司事,稽查功课及款项,设立半日学堂”[3]63-64。“劝学员联合本村学董,查有学龄儿童”[3]63-64。学董的职责一言以概之,便是筹学费、办学校、察学龄。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办学校或是察学龄抑或筹学费,《章程》中规定应由劝学员与学董商议或联合办理。然而《章程》并未指出劝学员与学董的职责重点分别是什么,所以在地方实践时往往将二者放在一起。“大堰坝任江寺小学堂,学生止(只)有五人,且多耽延学科,一切均无(为)师范张光烈,教育疏嫩(懒),扶同敷衍,半年之久,并无一言报告。本应立即撤换,姑,从宽记过一次,罚扣束脩钱十千,以观后效。但教育不勤,责在师范,学生人少,责在学董,固由该处附近,私馆过多,造言阻惑,该学董不自整理劝诱,听其阻塞,即堂内之学生数人亦常不能催齐,实属大负委任,应将该学董卢上选、戴理琮各予记过,一次罚去薪水,以示薄惩。”[注]“为示谕劝学员学董教员及私塾师生人等遵照章程以兴学务事”条: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六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467/02),南充市档案馆馆藏。按照《章程》规定劝学生入学应是劝学员的主要职责,然而在这起案例中,学董因学堂学生人数稀少而遭到责罚。可见,无论是地方劝学所或是衙门都将二者混为一谈。事实上,在地方实践中出现如此情况并不难理解,劝学员负责的是一个或几个学区的学堂,管辖区域较大,无法落实到某一学堂的具体招生。而学董仅负责某一学堂的办学事项,可以说,具体的办学是由学董真正实践,则学生的招募自然而然成为其职责。
同时,劝学员的工作重心在具体实践中亦发生变化,主要倾向于对所辖学区的监察及调查。具体而言:(1)察核办学学款。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县正堂“令该区(神坝场)劝学员彻底清算”办学学款,保正在禀文中写道:“自八月二十七(劝学员)来场清算,头次劝学员算明实支钱一百一十一串,下剩钱并无支帐。”[注]“为具禀赵璧圆等缕析粘添恶撇鲸吞借公肥私事”条: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62/08),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具禀东六区劝学员周建子为查明禀覆,以重学款事情,生区内安溪寺学董谭诰被谭永源禀称吞公,生查明回覆,生已前往查核,当凭绅首、保甲算明浮款二千一百文,仍斥归公,以外实无浮款,生为此查明,是以据实回覆。”[注]“为禀覆查明谭永源具告谭诰吞公浮款事”条: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183/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2)禀报、查明学务纠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思依场学董告保正贪渎,劝学员查明事件回禀道:“北三区思依场学董文生敬艮为霸吞抗缴恳请究追以裕学费事情,思依场学堂去年经费应收之款,入不敷出……生查各处会款实系保甲蓦收,据为己有,不肯缴出,似此亏挪公项,实为学界之蠹,为此开单具禀。”[注]“为具禀思依场保甲霸吞抗缴学堂费恳请追究事”条: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62/04),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具禀西二区劝学员文生李识韩为遵示查核据实查明事情,神坝场保正谢应泽具禀学董赵壁国藉公妄派一案,生查明禀覆,生不敢怠顽,速往神坝场邀同各保甲及场头查明,本场六保十六甲,每甲派钱五串,提猪行钱十六串,提平钱四串,提充业佃钱二串抽本场仓谷二石,合钱十一串,共钱壹佰一十三串,外派杂货摊每家三百文未收,仅系实款。生查今岁上学期报销表仓谷合钱十一串,未填杂货帮项,止(只)填三千五,又填本年进款一百二十串,所筹之数与所收均与进项总数不合当,即再三劝令谢应泽等将帐算明,仍归神坝场以息此讼。伊口称不公,至意不从,复归萧家场保内,至此一堂学费虚悬无着,为此秉明恳恩详查本年报销表收支虚实,以凭讯断。”[注]“为具禀遵示查核谢应泽禀学董赵碧圆藉公妄派情形事”条: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195/1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按照学部《章程》的设计,总董负责所辖区域的全部教育事宜;视学监察兴学情况;劝学员是协调者,向上与总董商议,向下劝令村董办学;学董具体实践,是实际的执行者。然而,南部县劝学所在具体运行中,总董、视学、劝学员、学董各职员职责重合,界限模糊。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劝学所初创,无论是学部的规定还是地方法令都较为笼统而模糊,细节性的规定既缺乏也不全面,尤其是学部的《章程》规定大都是方向性的,所以地方劝学所在具体运行及实践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权责不明、越界等现象。但从深层次而言,清末时的政府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办学,学部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各府州县皆设立劝学所,欲借助地方士绅的力量筹措经费、兴办学堂,而政府在赋予士绅兴办学堂责任的同时,地方士绅必然需要相应的权力以作为支撑。而这种权限的模糊为地方士绅办理地方学务保留了较大的自主性的同时,扩展了其社会权力,进而呈现劝学所在地方实践中权力扩大化的趋势。
(二)劝学所权力在地方实践的扩大化
南部县劝学所在兴办学堂的实践中呈现明显的权力扩大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筹款权。学部《章程》规定劝学所可以鼓励绅士、富户出资办学。原文是“考察迎神赛会演戏之存款。绅富出资建学,为禀请地方官奖励。酌量各地情形,令学生缴纳学费。以上为劝学所总董之责,惟须具劝学员之报告,联合村董办理”[3]64。但事实是,南部县劝学所在具体筹款操作中,学董在集众商议的情况之下,直接将庙产、各公会等款项提为学堂的经费,甚至可以协同保甲、保正直接向民众抽厘、抽税,此种记载在南部档案中随处可见,仅枚举几例:
县正堂谕:思依场学董知悉,该场小学堂经费不足,早经面谕,协同该处保甲设法添筹。兹查该场有大文会,虽系五县公会,本厂出款之人居多,外县不及十分之一。兴学为目前最要之举,凡涉文学之款,均应提并。为此,谕仰该学董敬艮,即便传谕大文会首事任国荣、伏腾耀、宋履吉、宋永龙、蒲士齐等,遵照每年于会内提钱六十千归入学堂,不得短少,又饬该场□,蒲雨牲猪行,每年提钱四千文,一并添助学费。[注]“为谕思依场学董传谕首事任国荣等提款助学事”条: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0493/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具禀东一区石河场学董、文生何光韩等,遵照禀覆:本区高阳寺初等小学,系该区劝学员胡升庸报告公立,生等奉札后,当即会同各保会首商议,酌提筹提三次,始抽各会钱约一百一十串,(此)外有本场认拨杨建国名下二百六十串。[注]“为具禀恳请出示严饬保正何心顺等伙同催收学款事”条: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25/02),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光绪三十一年)生等该处(大堰坝)地瘠民贫,兼遭岁荒,碍难筹款,集众公议,抽神会钱及神树作公,大堰坝三保所属庙宇六处仅四座有树,兼树多寡不一,公议均抽二郎庙树十二根,约值钱十串余,观音山四十根约值钱四十串余,观子院二根约值钱四十串余,纯阳山有千余根树株。生等议抽一百二十根,约值钱百串余,共计二百余串。[注]“为具禀督率私学堂子弟入蒙养学堂事”条: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7-00308/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2.办学权。《章程》规定劝学员与学董共同商议,“查明某地不在祀典之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3]64。在提庙产之前,劝学所会派劝学员或行查员调查庙产具体情况:“庙产常业亦可酌提以资办学,该行查员所到之区务须会同保甲切实查明,何庙有若干常业,系何人经营管产?尚在庙抑已出当?如已外当,即查明业系若干?系若干价?应提若干?作何退取?一并详细核明禀覆核夺。”[注]“为委任蒲天昌为劝学员事”条: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62/1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所以,提拨哪家庙产、提拨庙产的比例,很大一部分决定于学董与劝学员,“北三区劝学员文生敬艮报告,据洛阳山……保下共十甲,向未设学。兹合众商议,酌提公款庙息,开办一堂,谨将款项列于后:一王元直桥楼滩、财神会、娘娘会提钱九千文;王廷俊,光霸头文会庙提钱九千文;王世青,青灵寺常业,清明会提钱九千文;王炳章,青灵寺常业,清明会提钱九千文;任泽清,五龙庙年例会,提钱九千文……以上各款均系会同保甲公议”[注]“为具报保甲公议筹款办学堂公举王荣昌充当学董事”条: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42/02),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河坝保正、文生学董申请设蒙学一处,在涉及学堂筹费时,学董要求抽提庙产以作学堂经费,原文是“民等两保邀集花民再三酌议外,无神会余资,有附近马村庵历年古庙宽润可设立蒙学一堂,兼此庵常业颇多,只主持二人,无人耕作,概系压佃,众公议十股抽一,稍足一堂经费”[注]“为具禀筹钱兴办蒙学并公举黄秉清等充当师范事”条: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7-00355/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在庙产兴学过程中,大量的庙宇被定为“淫祠”被迫改建为学堂[注]关于此方面的详细讨论,参见徐跃《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一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载于《中国近代史》2013年第7期,作者在此不再赘述。,而改造的过程中,劝学所的学董、劝学员等拥有了将大量的地方公产转化为学堂经费的权力。这些地方公款在办学的名义下,从其原来的管理者手中转移至劝学所来提取、管理,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并未出台相应的律法或规定来约束劝学所权力。所以大量的贪渎以及学务诉讼纠纷滋生,乃至在1905年,由于大足县文生、学董王瑞垣侵吞学款、匿帐潜逃,浙江县也因学董把持学务,侵吞肥己,当地县令提出建议,要求裁撤全县学董,可见劝学所权力之泛滥及普遍。
3.禀诉权。《章程》规定劝学员对于所辖区域内办学情况有调查、回禀之权,事实是在学堂兴办过程中,由于筹款、资源分配等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纠纷等,导致民间对学堂兴办的态度并不支持甚至是反对的,劝学所为了推行政务,在具体实践中并不仅仅局限于调查、回禀,劝学员、学董等往往会对妨碍学堂之人提出告诉,或要求县衙派出官差官役,将阻碍兴学或拒绝缴款之人锁拿:
学董何光韩等具禀杨建国违谕抗缴一案,合行签饬,为此签仰该役前去即饬杨光福应缴钱一百四十余串,赶紧照数缴交学董何光韩,倘再违抗不缴,该役立即随签带县。[注]“为即饬杨国福速将应缴当家照数缴学董事”条: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25/01),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具禀北三区洛阳山学董王荣昌为抗公阻学恳请提究,以振学校,而免废弛事情……保正杜思恭、甲长甲怀堂、杜中德,藐抗不至,塾师王昭文开馆招生毁谤公学……私塾有十三堂之多,而公学开堂数月止(只)有学生五人,似此抗公阻学,若不肯请提究,恐无以维学界而警刁顽,而学堂万难成立矣,为此开单具禀。南部县县衙传唤阻学者。[注]“为具禀保正杜思恭等抗公阻学事”条: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242/06),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具禀西一区打木垭学董、监生蒲树人为再请签唤,以资学费事情,打木垭学堂原系创办之初,需款甚巨,而筹款无多,不惟未具认状者,把持不抽。即已具认状,有亦违抗不缴,如罗汉寺、清蘸会提钱十五串;会首蒲书芳上学期尚未缴清,下学期分文未缴;打木垭猪行提抽钱八串,行户邓钟英、蒲仕元全年分文未缴,遂置公事于不问,是以學资无着,若不签唤严催,恐应缴学费者尤而效之,则经费不敷,学堂何以进步?为此再请签唤,以资学费。[注]“为具禀签唤蒲书芳等违抗不缴学款事”条:光绪三十四年,参见《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号:18-01195/15),南充市档案馆馆藏。
从以上材料可知,县衙锁拿对象包括了普通乡众、会首甚至各保保正、甲长等,几乎涵盖乡村各个阶层,而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新学,迫于压力,民众会缴清欠款或暂时不再阻学,但事实上,新学的矛盾、问题并未解决,反而是不断在激化,再加上兴学过程中劝学所权力的扩大化,学董、劝学员借助其权力屡有干涉、倚势凌人之事以及新学筹款对民间的转嫁等诸多原因,其结果是伴随着整个清末兴学的过程,民间的抗学活动、学务诉讼如影随形。就性质而言,劝学所具有双重性质,作为一个行政教育机构,劝学所无可争议地具有官方的性质,然而从劝学所内部而言,自学董到劝学员包括劝学所总董,都是在当地士绅中选任,他们在为政府推广新学的同时,在新学兴办过程中获得新的资源与权力,所以从本质上说,新学堂的兴办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总之,近代兴学的情形极为复杂,清末劝学所在各地的运行、实践更是繁杂纷乱,作为新学的主要推广机构,劝学所的建立及运用对新学堂推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劝学所逐渐拥有了大量的资金使用权以及抽税的权力,呈现了在实践中权力扩大化的倾向,而这种权力的扩张逐渐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社会权力及利益网的平衡,乡村的权力资源在兴学的过程中被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劝学所成员以及与兴学相关的士绅,成为新的利益网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