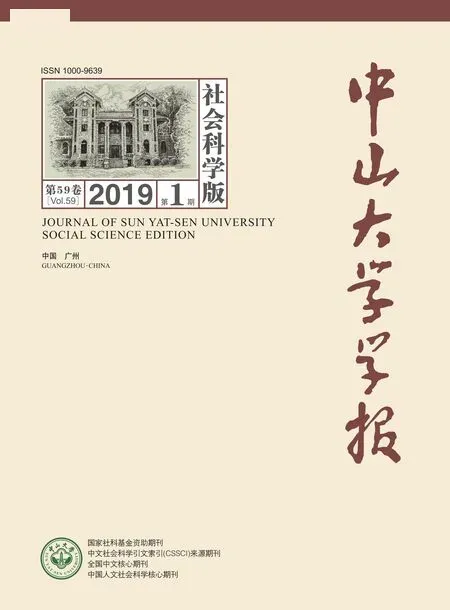东汉临湘县交阯来客案例详考*
——兼论早期南方贸易网络
张朝阳
汉武帝平灭南越之后,在今日的两广和越南北部、中部设立郡县,地理概念上统称为“粤地”①“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9页。。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又设交阯刺史部统领粤地,治所位于红河三角洲一带的交阯(交趾)郡(今河内附近)。五代时期,交阯郡及其以南地区从中原王朝独立②传统中原史籍对这一时期交阯的记载非常简略。所关注的多为叛乱、平乱等突发事件,或少数官员在当地行教化之政绩,对其“常态”记载甚少,对其普通民众则几乎完全忽视。而越南史籍也无法提供更多信息:越南历史撰述兴起甚晚,最早为13—15世纪成书的《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等,对早期的记录多为传说性质,难以作为史料来对待。。2010年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记录有交阯人在长沙郡治临湘(今长沙市)③本文所说的“临湘”皆指古代长沙郡治,即今日长沙市,并非今湖南衡阳下辖之临湘。活动的情况,提醒我们跳出当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注意汉王朝广大南部地区,包括与交阯之间的交流。
笔者曾探讨过长沙—交阯商道,但旧作主要从文化涵化的角度来解释交阯商人在长沙的行为④张朝阳:《长沙五一广场汉简所见交阯—长沙商道》,王捷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研究》第6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当时未曾留意到郴州晋简、《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等重要史料,存在很多不足。本文一方面从新的视角来解读长沙案例,一方面补充了大量史料,考证事实,同时也矫正了以前文书释读的不足之处。待更多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资料刊布后,可能还有再探讨的余地。
一、交阯来客租船运谷桂阳一案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以下简称“五一简”)有一则资料,内容如下:
江陵世,会稽纲,下邳徐、建、申,交阯孟、信、都,不处年中,各来客。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伯卖篷,孟债为桂阳送谷。船师张、建、福辟车卒,月直①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28页。本文简号根据《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公布之顺序。(简155)
该简涉及到这样一例案件:交阯人“孟”在临湘租船长途贩运谷物②本文将“为桂阳送谷”理解为商业行为,而非公粮运输等公务。详见下文分析。,欠债,从而引发一场债务纠纷。这是文献对汉代普通交阯人活动的第一手记录,非常罕见,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我们首先需要准确断句。笔者基本认同整理者的标点,但对“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有不同意见。整理者认为“福”是人名,“吏次”则是指“以吏职次”。按这种理解,这句话就是说:“福”以吏职次,于本年四月六日,兼任“庾亭”亭长。但一同出土的简146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说明“次”应该是人名:
之湘西推求伯,时伯在辅所。与纲、建俱还,伯便诣县,孟、次避侧不问。福鞭元、殴世、诡伯,无所隐切,即纲、建、申等证。案:福,吏;孟,负伯钱;次,侫辞。告③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第222,77页。
该简的直接上下文缺失,但据已有信息,它大体上是说债权人“伯”从湘西返回临湘县与债务人“孟”等对质。官方调查了有关当事人,并做出初步判断。我们首先注意到,该简提到的“伯”“纲”“建”“孟”等10名当事人,有9位都在简155出现过,这应该不会是巧合。其次,简146关涉到“孟”拖欠“伯”债务一事,这也契合简155的内容(伯卖篷,孟债为桂阳送谷)。根据这两个特征来判断,简146与前文分析的简155涉及同一案件,应该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④整理者很谨慎地指出,两简或许有关联。根据各种信息,我们大可以确信,这两简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应该存在更多的相关资料有待公开。。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次”。简146有“孟、次避侧不问”,“次,侫辞”等语,可见“次”是人名,是案件当事人之一。据此可知,整理者将简155的“吏次”解释为“以吏职次”不妥⑤“吏次”这个用法,的确存在。例如,五一简16有“普以吏次署狱掾”。但在简155的上下文中,不是很妥当。。“次”字当结合下文“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作为该句之主语。因此更恰当的断句应该是:“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换言之,这句话介绍了“福”和“次”两人的身份:“福”是正式的官府吏员,而“次”则在该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⑥笔者旧作《长沙五一广场汉简所见交阯—长沙商道》曾认为亭名“兼庾”,不妥。现予以更正。。
或者有学者要质疑:不说本来的身份A,直接说“兼任”B职,似乎很突兀⑦整理者的断句就是如此理解“兼”,认为福本身是吏而兼任庾亭长。?但“兼”在简文中并不是兼职之意,而应该释作“守兼”(即临时充任)。《汉书·王莽传》记载:“县宰缺者,数年守兼。”颜师古曰:“不拜正官,权令人守兼。”⑧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40页。也就是说,有县令的空缺时,不任命正式的县令,却权且委派人代理,一代理就是好几年。“守兼”可独立作为头衔,并不需要依托于另一个身份。五一简47有:“君教诺。兼辞曹史辉、助史襄白:民自言,辞如牒。”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第2 2 2,7 7页。此处的“辉”仅仅是一位“兼辞曹史”,并无其他头衔,证明“兼”某职可独立成为头衔。照此用例,“兼庾亭长”强调“次”的身份是临时代理,并非正式亭长。恰好与作为正式吏员的“福”构成了对照。
如此解读,不但在文意上更加清晰,也吻合简146的另一段信息——“福,吏;孟,负伯钱”。我们注意到:整理者将此处的“福吏”正断作“福,吏”。
这样我们就知道,简155中共出现了14人,具有不同的郡籍和身份,列下表(见表1)。
由这张表可知,东汉的长沙郡临湘县,四方人员辐辏。下邳(约今苏北、皖北)、江陵(约为今湖北)、会稽(约为今浙南)乃至交阯(越南北部)的人员皆来此活动。由于资料严重缺失(或尚未公布),这些人员的活动情况不知其详,但交阯人“孟”的活动,可略知一二。

表1 简155中出现的14人之郡籍和身份
孟是什么身份?①古代水路运输,遇险滩激流,一般先将货物卸下,拖船走陆地避开险滩,然后再继续下水行船。“车卒”想必和这种陆地拖行有关。东汉桂阳碑刻铭文:“及其上也,则群辈相随,檀柁提携,唱号慷慨。”就描绘了拖行船只的情况(详见后文引用)。是否是脱离户籍,流亡他乡的“流民”②王家范认为“流民就是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罗彤华也认为汉代流民的特色就是失去或脱离户籍(《汉代的流民问题》,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9页)。这些认识,得到了五一简资料的支持。?应该不是。五一简有调查流民的文书,例如:
王忠一家四口户籍在益阳,但自行迁移到了临湘。被官方查实后,又被遣返回益阳。又如:
书辄逐召,乃考问。辞:本县奇乡民,前流客,占属临湘南乡乐成里。今不还本乡,势不复还归。临湘愿以诏书随人在所占。谨听受占。④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第123页。(简11)
有来自异乡的“流客”不愿还乡,被要求在客居地占籍。可见在当时,“流民”作为一种身份会被注明,而一旦被发现,或要求占籍当地,或遣返户籍所在地,一般不允许人、籍分离。反观简155,仅说孟和其他一些人“不处年中,各来客”,既没有说“流民”,也没有被遣返或要求占籍,可见他是合法客居在临湘,不是非法脱籍。
孟在临湘的活动——租船运输谷物又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是公务运输还是商业贩卖?笔者认为是商业贩卖。原因有三:首先他没有官方头衔,不从属于任何官府机构,仅仅被称为“客”。其次,他租赁市场上出售的船只,而不是借用官船运输。最后,他运送的谷没有被称为“官”谷。这些特征与公务运送很不同。公务运送一般是官府出面组织,即便到异地去活动,也是借用异地的公船。里耶简中有一公务借船案例,可作为参考。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樛敢言:前日言竞陵汉阴狼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以求故荆积瓦。未归船。狼属司马昌官。谒告昌官,令狼归船。⑤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页。(简8—135)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官员告状说竞陵县某位司马的下属“狼”借用了迁陵县的“公船”一直不归还,因此要求该司马勒令下属归还公船。这个案例中的当事人属于官府机构,借用了“公船”去运输“故荆积瓦”。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官方也可租用民船执行公务。五一简有武陵伏波营军官雇佣船师运米一案。“前言船师皮当偿孝文钱。皮船载官米财……军粮重事,皮受僦米六百卅斛,当保米知屯营……”⑥此案甚为周折,此处省去了细节。可见,军方以六百卅斛米为佣金,雇佣船师皮运输军粮。但这里点名了货物的官方属性——“官米财”,并强调是“军粮”。而交阯客孟所运输之物仅仅被称为“谷”,应该和官府无关。
事实上,只有假设这次运输是商业贩运,我们才能解释孟何以能合法客居临湘。按汉代的户籍制度,农户不能随意迁居,但商人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居延简有一例:“酒泉郡中持牛车二两。谨案市人齐,毋官狱征事。”①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简213.1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此简缺失上下文,但推断有两种可能情况:(1)酒泉郡的“市人”名叫齐,驾驶着两辆牛车,来到张掖郡下的居延交易。官府调查了他的背景,发现没有不良记录;(2)居延“市人”齐,打算去酒泉交易,向居延申请通行证,接受背景调查。无论哪种情况为真,“市人”齐一定在从事跨郡交易。我们可以相信,交阯来客孟就是这类“市人”。
由于汉代长沙郡盛产大米,我们可以推断孟所运的谷就是大米;早在楚怀王时,就有齐国使者游说越王,称:“长沙,楚之粟也。”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品种的稻子,可为物证②司马迁:《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09页。这里的“粟”显然并非实指“粟米”,是泛指粮食。或许这句话并非历史事实,但至少说明西汉时代,长沙已经盛产大米。另,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多品种的稻子,可见长沙水稻种植之发达。见柳子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栽培植物历史考证》,《湖南农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而目的地“桂阳”应该指桂阳郡的治所,南岭北麓的郴③桂阳郡的情况较复杂,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7—128页)对此问题进行了梳理。东汉时代,桂阳郡下辖有桂阳县,因此简文所说“为桂阳送谷”,似也可以指桂阳县。但桂阳县不在航道上,因此“桂阳”特指郴的可能性最大。本文正文所用的“桂阳”皆指郴。。该郡位于长沙郡以南,南海郡以北,地跨岭北、岭南,地理位置重要。从临湘到郴,在楚怀王时代就存在一条贸易航道。例如,著名的鄂君启节(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是怀王给贵族商人鄂君颁发的凭信,用于免税与传舍招待之目的。由铭文可知,鄂君50舸(大船)的商队,被许可由湘江进入耒水,南抵南岭北麓进行交易④该文物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节用青铜,错金铭文。有车行与舟行之分,表现出的商业交通路线非常广泛和复杂。关于南岭北麓的具体地点,存在过争议:谭其骧认为是永兴县,但黄盛璋认为是郴州。黄的看法现在被多数人接受。见: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今湖南南部的水路网络清晰,临湘到郴的航运一目了然,表明汉代人早已掌握了临湘到郴的水路交通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的整理》,《古地图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王子今:《马王堆汉墓古地图交通史料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
二、运谷桂阳,何利可图?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现在我们需要提一个问题:孟从长沙运谷到桂阳,到底有何利可图?按照司马迁总结的“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⑥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950页。的原理,桂阳米价应该高出长沙米价,并且在除去运费等成本后还有可观的利润。虽然东汉简中尚未看到相关信息,但这个假设在三国简中得到了验证。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出土的三国简记载有赤乌年间(238—251)桂阳米价,“米六百八十六斛八斗六升,为钱七百九十六万”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第159页。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发掘了汉代至宋元的古井11口。在J4出土了三国时期的简牍,每简长约23—25厘米,宽约1.4—2.1厘米不等。简文包括上计、书信等内容,时代为孙吴赤乌年间。除三国简外,还出土了大量西晋简。(简40)。平均下来每斛11 590钱。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也记载有米价,嘉禾四年(235)长沙米价1斗米=160钱,推算下来一斛=1 600钱⑧有关此时期长沙米价研究,见:《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1—72页;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30页。。可知三国时代,桂阳的米价是长沙的7倍左右。东汉的价格情况估计也差不多。
有学者认为这是特殊情况,可能桂阳发生饥荒造成了米价腾涌。这样解释有些牵强,也缺乏证据。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有多种因素造成了两地米价差价巨大。首先,长沙郡农业发达,大米供应充足,所以米价较低。而桂阳郡相对而言,农业不及长沙,因此米价较高。前文已说过,早在楚国时期,长沙就是楚的粮仓,盛产大米。而桂阳郡虽然也有一定的农业基础,但由于多山的地形条件限制,生产必然不及长沙①永初七年(113)从桂阳、零陵等郡调运粮食到南阳、彭城、九江等郡救灾。见范晔:《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0页。。史载,直到茨充于建武二十五年(49)主政桂阳时,才“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②范晔:《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60,2459页。,这虽然不是说水稻种植问题,但显然间接表明当地农业经济整体较为落后。所以当地米价必然比长沙贵。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桂阳大米昂贵:当地矿产丰富,矿业经济非常发达,因此存在大量的外来非农业人口,这些人口需要依靠市场获得粮食。
《后汉书》记载:
又(桂阳郡)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桂阳太守)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③范晔:《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60,2459页。
卫飒在担任桂阳太守时,发现下辖县盛产铁矿,导致大量外郡百姓涌入开矿,私自炼铁铸器。这个规模应该相当庞大,因为当卫飒禁止私矿,建立官营的矿场后,一年就增收五百多万钱。这些外来矿工在当地没有自产粮食的来源,必然需要购买。
除了铁矿外,桂阳郡还盛产银。《汉书·地理志》载,桂阳有金官④王福昌:《西汉桂阳郡“金官”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学界对此处的金何指一直存在争议。或以为指金子,或以为当泛指金、银、铜,所谓的“三金”。但在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表明,桂阳银冶发达,从业人数众多⑤西晋简也出自苏仙桥古井中,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桂阳郡的物产、地理、人口、官吏等信息。释文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相关研究,见周能俊:《六朝桂阳郡的白银采掘与使用:以郴州晋简为中心》,《求索》2017年第4期。。先将资料罗列如下:
□一千七百卌八采银夫(2—146)
故进山乡银屯署废无人居(2—181)
由此可知,西晋时代的桂阳郡,有着规模巨大的银冶经济。仅幸存的残简就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非常了解当地银矿分布情况,并且存在大量的采银夫,至少有1 748人。由于银冶发达,当地人在交易时已经使用银两作为货币。例如,
猪一头,直银三朱(3—148)
羊一头,直银三朱(3—194)
右猪羊各一头,为吴称银,合一两二朱(3—193)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银业的兴盛,以至于在交易时普遍使用银子为交易媒介。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普遍使用银两作为货币是晚到宋元以后的事情⑧[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7—424页。白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很复杂,彭信威书中多处都有讨论。。
更重要的是,由“故进山乡银屯署废无人居”的记录可知,采银活动在当地历史悠久,以至于西晋时代,有的银矿已经被采银夫开采殆尽,导致管理机构“银屯署”被废弃,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据此可推断,很可能东汉时代,当地银冶就已经颇为发达了。这个推断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2001年,湖南常德一个墓中出土46枚东汉时代的银饼,总重达9 970克①该墓一共出土了银饼46枚,金饼8枚。桂阳设有金官,又有银矿,所以这些金、银饼可能都和桂阳有关。见王永彪:《湖南常德出土一批汉代金银饼》,《文物》2013年第6期。。这些银饼产自何地?毗邻的桂阳郡应该是合理的答案。银饼顺湘江航运,流通到了今常德地区。
事实上,在东汉时代,桂阳的银业还要比西晋简中反映的兴盛许多。这些偶然出土的记录,残缺不全,显然只是当时盛况之冰山一角。更何况,为后世称道的始兴郡银业②薛亚玲:《中国古代金矿、银矿生产分布的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在东汉本属桂阳郡,孙吴时析分出去。始兴的情况,自然无法记录在西晋桂阳文书中。
由于东汉桂阳存在发达的矿业(铁、银,或许还有金),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矿工,同时这些矿产利润丰厚,采矿者收入应该较务农丰厚。这样一方面存在大量购买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资金,当地粮价自然就被抬高了。
最后,市场时机因素,也会推高粮价。这个时机不一定需要饥荒之类的极端情况。一般而言,粮食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当陈粮被消耗殆尽,新谷尚未成熟之际,这时的粮价必然比平时高出许多。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孟在四月六日租船运谷到桂阳。这个时间节点是偶然的还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临湘(长沙)到桂阳(郴州)直线距离四百多里,水路则应该在500—600里之间。东汉时代的湘江航行速度,现无从确知。但《唐会要》载:“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③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95页。照此速度,则唐代船只负载,逆流从长沙至郴州,日行45里为标准。汉代造船和航运技术必然比唐代逊色,日行里程应该少于45里。此外,《九章算数·均输》记载:“六人共车,车载二十五斛,重车日行五十里,空车日行七十里。”④白尚恕:《九章算术注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5页。汉代陆地车运,每日50—70里,而常识告诉我们,陆路交通比水路要迅捷,这样参比可推算汉代湘江运粮,每日大约30里左右。
若这个推算可靠,则从临湘行船到桂阳大约需要二十天左右。简155末有“月直”一词,表明雇佣的船师和车卒是按月付薪,这也印证一趟行程至少需要一个月往返。孟四月六日出发,大约月底到达郴州。这个时候,当年的早稻尚未成熟,而去年的晚稻已经消耗半年多了⑤这里假定当地种植双季稻。早稻农历六月成熟,晚稻农历八月成熟。即便是单季稻,农历四月底五月初仍然是相对缺粮时节。见:陈文华:《中国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成就》,《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王福昌:《秦汉江南稻作农业的几个问题》,《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市场上的米价必然比平日昂贵。
孟显然熟悉当地市场,懂得把握商机,租船贩运谷米到郴州以博取暴利。
结论:何处是归程?
最后我们追问:桂阳是否是孟贩运的终点?就孟本人而言,或许他止步于桂阳,完成交易就返回长沙。因为该案例中仅仅说孟运谷桂阳,并且在官方调查时,孟已于当年回到临湘县。但从商业网络的角度来看,桂阳未必是交易的终点,因为它是岭北—粤地商贸的中转枢纽。
《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熹平三年,174),记载了东汉桂阳太守修建水利工程,便利粤地—岭北商贸的一段历史。
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红,一由此水……其下注也,若奔车失辔,狂牛无縻……及其上也,则群辈相随,檀柁提(携),唱号慷慨,沈深不前。其成败也,非徒丧宝玩,陨珍奇,替珠贝,流象犀也。①洪适:《隶释》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2—15页。该碑早在《水经注》即有著录,原石立于今韶关,清代尚存,现不知去向(见宋会群:《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期)。
由记载可知,桂阳郡与南海郡比邻,是粤地与岭北的商业交通要道,商旅繁忙。但由于水势险峻,行船非常危险,所以事故频发,商船损失惨重。有鉴于此,当时的太守周憬组织人力,改造水道,效果显著。
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②结合前引宝玩、珠贝等语,此处所谓“抱布贸丝”并非实指,而是引用《诗经》之典故,泛指民间贸易。
经过一番截弯取直,平高填洼的努力,粤地—岭北水路变得畅通安全了,大大促进了民间贸易。
而孟在长沙—桂阳贩运谷米的活动令人联想起《后汉书》的记载:
(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③范晔:《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64,2462页。
商人将交阯大米运送到毗邻的合浦以交换当地特产的珠宝。《后汉书》又载,除合浦外,九真郡(今越南中部)也依靠交阯提供谷物:“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④范晔:《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64,2462页。可见东汉时代,交阯商人贩卖谷米是有传统的。交阯位于红河三角洲,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由于从交阯到临湘,合浦是必经之地,孟有机会顺路购买合浦珍珠。那么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孟将本郡出产的米东向贩运到合浦,换得珍珠,再携珍珠北上临湘,交换当地的谷米,回头再运米到桂阳,赚取高额差价。若桂阳市场出现问题,还可继续西进合浦交换珍珠,再返回长沙?⑤当然,不仅仅是珠米贸易,这一路还存在很多种接力贸易的可能。《后汉书·贾琮列传》记载:“旧交阯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第1111页)可知,在东汉时代,交阯是很多奢侈品的原料(或加工成品)的产地。这些物资,除了进贡之外,也可长途贩运到中原。
必须承认,就现有的资料情况,上面的假想尚无法得到证实。但相信,随着五一广场简的不断公布,我们将发现,东汉时期南方的人口流动、物资交流之频繁远超史书记载,这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早期南方商贸网络的形成以及跨区域间的交通。